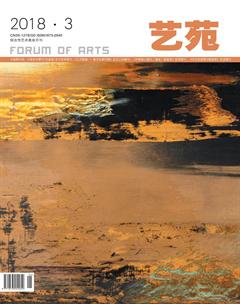语言作为表征
【摘要】 台语片作为台湾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从语言上折射出两岸三地电影往来存在的共性和交集。由大陆起源、经香港传播、受本土刺激而形成的台语片,是连接沟通两岸三地电影的一个文化现象。台语片的兴起是因为国语运动下的语言压制,而衰落同样是因为语言政策的束缚。可以说,语言作为一种表征,反映出台语片的兴衰起落。
【关键词】 语言;台语片;国语运动;间谍片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台语片,是由大陆起源、经香港传播、受本土刺激而形成,作为连接沟通两岸三地电影的一个文化现象,亦是台湾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语片的兴衰,皆与语言政策的推行有关。
一、语言的压制与宣泄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台湾电影产业中,台语片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语片,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止,以闽南语(“台语”)配音,使用台湾本土资源拍摄的,反映台湾本土文化的影片。台语片彰显出本土的特征,发出了自我的声音。实际上,台语片的产生渊源,可以追溯至海峡对岸,“先有国产(即沪产)厦语片的萌芽而后有南洋及港产厦语片的流行,進而催生台产台语片的空前繁荣”。[1]61因此,这种闽南语电影的制作与传承,成为连接沟通两岸三地电影的又一个文化现象。
台湾“光复”之后,为肃清日殖痕迹,实现国族认同,维护国民党的统治稳定,彰显执政合法性,同时为消除省籍矛盾和社会分歧,政府在台展开推行国语运动。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该委员会负责编订加注汉语拼音的汉语教材,举办汉语示范广播和各种汉语培训班,在全省各地设立汉语推行所。[2]364-365同年10月24日,在台湾“光复”一周年的前夕,国民党宣布“再中国化”和“去殖民化”政策,全面禁用日文。1946年8月,成立国语实验小学,课程加重国文科目,1947年12月,国立台湾大学设立国语专修科,次年8月,改命台湾师范学院接办;1948年,原在北平创刊的《国语小报》移至台湾出版,并改名《国语日报》。1950年,台湾省政府颁布《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学校及社教机关应加强推行国语运动。国语的推崇带来的是地方语言遭受压制,“台语”“客家话”等台湾本省人的母语被视为“方言”,这些语言在学校内被禁用,而说方言的学童们要接受处罚。诸多语言政策的在台实施,使得台语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台湾本土民众内心压抑的情绪无处释放,此时从香港而来的厦语片提供了宣泄的渠道。
按照叶龙彦的观点,最早的厦语片来自香港。厦语片是“在大陆沦陷后,从厦门、泉州移居香港的戏剧人才,利用粤语片设备拍制完成的。品质当然不好。第一部输入台湾的厦语片,是一九四九年的《雪梅思君》,是钱胡莲的古装戏”[3]107。而根据学者黄德泉考证,这个时间可以提前15年。1934年12月30日起在厦门中华大戏院上映的《陈三五娘》有声片是中国第一部厦语片。[1]厦语片虽在大陆起源,但兴盛于香港,厦语片的主要导演毕虎、王天林、陈焕文、周诗禄、马徐维邦等,大批后来成为演员的福建人如江帆、鹭红、丁兰、小娟(即凌波)等都是在1949年由上海南下赴港的。此外,还有一批客居香港的厦门南音馆阁集安堂成员,如陈鼎臣、陈金木、嵩云等。[4]99据凌波回忆:“厦语片演员个个都是大陆出来,来了之后,大家福建人聚在一起,有些人对电影有兴趣的,就找老板出钱,拍些厦语片。”[5]170厦语片所选题材多回避敏感议题,主要以具有中国古典文化色彩的古装民间故事或南音戏曲故事为主,所以能够避开意识形态的条框规范。“虽然水平不高,但因语言相通,厦语片在台湾省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聚居地的发行越来越广,题材也从厦语戏曲,到翻版粤语戏曲改编民间故事,甚至有将粤语片改配厦语发行者。”[6]90
台湾“光复”后,厦语片开始输入台湾。其实,最早输入的时间是在1948年9月,由厦门五洲影片公司制作的厦语片《破镜重圆》在台北新世界戏院上映。[7]209此后,香港制作的《雪梅思君》《相见恨晚》《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厦语片陆续来台上映。这使得以闽南语作为母语的台湾民众在听到乡音之后备感亲切,影片内容是所熟悉的戏曲故事,因而厦语片受到热烈欢迎。又因为厦语片是以歌仔戏电影的形式输入,“国民党并不反对地方戏曲来台,所以厦语片进口后颇得本省中年以上妇女的喜爱,也因此抢走不少的歌仔戏迷”[8]60。 1955年,厦语片大量登陆台湾,据“台湾电影资料馆”公布的材料,这一年台湾上映的厦语片有《牛郎织女》《儿女情深》《孟丽君》《陈世美不认前妻》《厦门杀媳案》《圣母妈祖传》等8部。不论哪家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厦语片,在台湾上映期间,所有广告宣传一律以所谓“正宗台语片”为号召。其实,剧中人所说的对白全是厦门腔而非台湾腔,时间久了,观众逐渐感觉受到欺骗,因而厦语片的票房一落千丈。加之香港地区的“厦语电影人才本来就少,一年拍几部片子还能勉强应付,要多拍几部就免不了粗制滥造,剧情模式老一套,对白陈词滥调,很快地在观众中失去信誉”。[6]90-91此后厦门人张国良由香港带到台湾的《周成过台湾》《詹典嫂告御状》等几部厦语片,几乎都是血本无归。
二、从厦语片到台语片
此时,台语片的出现成为理所当然。因为台湾民众已经对“舶来”的闽南语电影失望,迫切希望看到本土的自制电影,并借此抒发语言被压制的苦闷。所以,“台湾人对本土母语的渴望,是台语片催生动力”。[9]4在当时,国语运动推行的情况是:“台湾人口九百万,其中二百万是外省人,七百万人中约有三百万人已接受国语教育,四百万听不懂国语,就是台语片的基本观众,是台语片诞生的主因。”[10]234最早拍摄台语片的是邵罗辉,都马剧团的团长叶福盛在外演出时,“常遇到厦语古装片抢生意,而感到舞台剧的没落。同样一出戏,拍成电影,到处可以演,舞台剧却只能演给现场观众看”[11]101。由此,邀请留日的邵罗辉导演,利用自己剧团资源,拍摄本土的台语片。1955年6月13日,遂有其剧团参与制作的《六才子西厢记》上映,虽然票房不佳,出师不利,却带动台语片风潮。响应台语片制作的,首先是大陆来台的导演白克,他看过室内试映的《六才子西厢记》后,便将“台制”筹划拍摄的政宣片《黄帝子孙》,改用台语发音拍摄,并请吕诉上改写台语剧本,并以吕诉上领导的文化工作队作为演出班底。影片拍好后,在乡村免费放映,后来也配备国语拷贝。何基明也投身到台语片拍摄中,其首部影片《薛平贵与王宝钏》上映后,造成空前轰动,全省净收入新台币120万元,超过成本三倍,从此掀起台语片热潮。而1955年台湾所实施的底片器材押税进口的优待拍片办法,则让民营电影企业受惠最多,许多台语片制作公司以“香港公司名义进口底片,拍好退回香港冲印,解决成本最大的胶片问题,而且由于台语片节省底片,剩余底片转卖黑市,又有收入,直接促成台语片蓬勃兴起”[12]155。
台语片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出现拍摄热潮,其实外省人有推动之功。此时期,参与台语片制作的外省人人数比台湾本省人要多,外省人主持的台语片公司也比本省的多,因为台湾会拍电影的人很少。所以,“以拍电影为业的外省影人,自大陆来台后,正处于无片可拍的苦境,忽闻本轻利重的台语片兴起,对他们来说,正是天大好机会”;“不少听不懂台语的外省人成为台语片编导,靠副导演和演员的沟通”[11]103。此时期,白克、袁丛美、徐欣夫、张英、宗由、庄国钧、唐绍华、梁哲夫、李嘉、申江、田琛等人,都加入到台语片的拍摄热潮中。据统计,截至1959年5月中旬为止,63名台语片导演中有19名外省籍人士,占了四分之一左右;但若以所导演的影片数量来看,则占了将近三分之一。[13]13从大陆来台拍摄台语片的导演,移植、改编、仿拍不少三四十年代内地的影片,如张英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于间谍片、侦探片等电影类型,几乎都是外省人来拍。
像张英翻拍自1946年的经典间谍片《天字第一号》,在1964年上映,非常卖座,当年即赶拍续集,三年内共拍摄五集,成为当时台湾商业电影中的一个固定類型。而且加之东西方冷战与两岸对峙的特殊政治环境,催生了台语间谍片的创作热潮。于是,《第七号女间谍》(1964)、《特务女间谍王》(1965)、《天字第一号》续集三《金鸡心》(1965)、《天字第一号》续集四《假鸳鸯》(1966)、《间谍红玫瑰》(1966)、《谍报女飞龙》(1966)、《间谍红玫瑰》续集《真假红玫瑰》(1966)、《天字第一号》续集五《大胆色妲》(1966)、《国际女间谍》(1966)、《万能情报员》(1966)、《女人岛间谍战》(1966)、《谍网姐妹花》(1967)、《谍网女金刚》(1967)等间谍电影连番登场亮相,成为当时台湾电影中最为热门的一个类型。[14]122
单从片名即可直观看出,这些台语间谍片的主角大多都是女性,以歌女、情妇、女秘书、女佣等身份作为掩饰,她们大多美丽、聪明、善良而且情感细腻,都愿意为了国家抛下儿女私情,这显然与纯粹商业性的007系列的詹姆斯·邦德不同,可见1946年的《天字第一号》中以女性作为中心(欧阳莎菲主演)的人物设置在这里得到了承继和延续。身份莫测而风姿绰约的“欧阳莎菲”被不断拿来复制、模仿和展示,并将她们的身份作为影片的最大悬疑所在而加以渲染烘托,这种偏重女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情色”意味,更容易满足观众的窥视欲望和娱乐需求。由此,台语间谍片捧红了白虹、白兰、柳青、何玉华等女明星。
参与创作台语间谍片的电影公司多为民间与私营,他们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服务政治宣传,更多是纯粹商业上的逐利,也因此在具体创作上不再受制拘泥于教条化的“八股模式”。为了能够吸引观众,台语间谍片在类型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只要有卖点,其他类型元素都可以杂糅其中。因此,武侠片与其他片种的类型卖座元素常常见诸其中,如蒙面黑衣人、独行侠的形象,女间谍颇有古代女侠客的气质,使用飞镖、吹箭等武器,甚至在《特务女间谍王》等影片中,间谍人员夸张使用“隐身镜”“紫光镜”“死光炮”等。而对于当年的台语片观众而言,以《天字第一号》为代表的间谍片的魅力,还有来自台语片惯有的爱情通俗情节剧的传统:战争时代下的社会动荡,男女主角的恋爱因此而遭遇阻碍,虽然隶属同一阵营,却各自不能以真实面貌相认交流,只能以假面掩饰真心。女主角挣扎于儿女私情与国家大义之间,一方面含泪自嘲自己是没有道义不知廉耻而毫无国家民族之心的拜金女人,一方面隐忍与牺牲自我而把所爱之人送与别人,甚至还要承受不明内情的男主角的控诉指责。这种为国家利益舍弃小我情感并忍辱负重的间谍加爱情的故事情节,显然深受观众的喜爱。
也正因为当时台湾民营电影公司的资金有限与逐利目的,台语间谍片在制作成本上都比较低廉,加上当时台语电影的制作水准相对来说还处于摸索发展的阶段,因此不论编剧、摄影与场景道具,台语间谍片的质量都显得比较粗糙。譬如在《第七号女间谍》中,“主角的外型及服装均未经过考据,女人多梳60年代流行的鸡窝头,而男士多着60年代款型的西装及梳飞机头,使人不能置信其背景是抗日战争”[15]155。这类影片的制作与其说是歌颂抗战地下英雄,不如说以此为宣传噱头,重在凸显惊险、枪战、暗杀、打斗、紧张、刺激并且充满悬念、诡异、暗藏机关、高深莫测、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元素,突出表现人物的神出鬼没和机警敏捷,以及通过设置穿插其中的双角、三角甚至多角爱情或者畸恋关系,将其添油加醋以至过度化的展示。由于情节上相互模仿,人物形象几乎雷同,缺乏深度、突破与创新,具体拍摄时又多为粗制滥造,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最终造成这种类型的吸引力逐渐下降。
三、台语片的衰落
虽然台语片存在20余年,拍摄1000余部,但最终成为历史。台语片的消亡既有自身粗制滥造导致质量低劣的原因,也有电影检查部门的影响,当然,对于“台语”长久以来的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台语片存在的时期,时常出现语言的歧视政策,譬如1956年5月30日,台湾省教育厅通令“各中等学校谈话应尽量讲国语,避免用方言”。1963年,“行政院”颁布《广播及电视无线电台节目辅导原则》,规定“播音语言应以国语为主,方言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1966年7月10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各县市政府各级学校加强推行国语计划》,规定:(1)各级学校师生必须随时随地使用国语,学生违犯者依奖惩办法处理;(2)禁止电影院播放方言、外语;(3)严加劝导街头宣传勿用方言、外语;(4)各级运动会禁止使用方言报告;(5)严加劝导电影院勿以方言翻译。1970年6月10日,台湾“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通过“加强国语推行办法”,规定“各级机关、学校办公室跟各种公共场所,一律使用国语”。1972年,“教育部”函令电视台“闽南语节目每天每台不得超过一小时”。1973年1月22日,“教育部”公布“国语推行办法”十四条,强调国语教学和注音字母的使用。1975年,“行政院”公布《广播电视法》,规定:“电台对国内广播应以国语为主,逐渐减少方言。”从以上的这些政策规定,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国语政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限制方言,有的规定还明确提出禁止方言,违者给予处罚。纵观这些措施的陆续出台,可以看出国语运动的推行,其实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45年之后,主要目的是去殖民化,借此巩固自身政权统治;第二阶段在60年代,是针对大陆的“文革”而发起的“文化复兴”,从文化上大力强化大中华概念,压抑台湾地方文化。所以,这些几乎每年都出台的国语推行政策,自然对台语片发展带来不利。
根据黄仁的解释,台语片“断层的原因是業者、政府和文化界都有责任,尤其政府方面,自二二八事变后,为消除台湾情结,强力推行国语,禁用台语……在官方文书中,根本没有‘台语片这个名词存在。”金马奖自1962年举办,热闹庆典独缺台语片,因为“台语片送检时必须填报‘闽南语片……奖励电影的金马奖注明是国语片金马奖……拒绝台语片,影片中有三分之一讲台语就拒绝受理。”[9]台语片从业人员被视为“旁门左道”,遭到国语片界的排挤,全国性的影剧事业协会排斥台语片的从业人员参加,抹杀拥有众多人数的台语片从业人员的“影人”身份。[13]57政府的电影辅导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国语片,台语片被完全漠视,毫无“政策”优惠。电影主管部门在解释“国产片”时,经常以国语影片为标准,依照规定,凡生产国片者,应可分得外片配额,但台语片经常因主管单位不认定其为国产片,因此不予配额。许多台语片加配国语拷贝,以求获得配额,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放映。特别是1974年,政府将原先的《外国电影片配额辅导国片处理要点》,修改为《外国电影片配额辅导国语影片处理要点》。[16]163-164国语片成为官方文件中的唯一辅导对象,明确显示出政府的态度,台语片被正式排除在外,成为“弃婴”。加之学校又在20世纪50年代就积极推行国语教育,这使得70年代之后国语片的观众大量增加,相应抑制了台语片的市场空间。因此,从政府的姿态来看,这个由大陆起源、经香港传播、受本土刺激而形成的台语片,最终走向衰落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黄德泉.闽南语电影考源[J].当代电影,2012(9).
[2]张春英.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3]叶龙彦.台语片与厦语片大对决[J].台北文献,2000(3).
[4]吴君玉.香港厦语电影的兴衰与题材的流变[J].电影艺术,2012(4).
[5]吴君玉,蒲锋.口述历史:凌波(二访)[M]//吴君玉.香港厦语电影访踪.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2.
[6]洪卜仁.厦门电影百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7]陈世雄,曾永义.闽南戏剧[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8]叶龙彦.春花梦露——正宗台语电影兴衰录[M].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9]黄仁.悲情台语片[M].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10]黄仁.日本电影在台湾[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
[11]黄仁.台语片的过去与现在(传统与新生)[M]//黄仁.新台湾电影——台语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3.
[12]黄仁,王唯.台湾电影百年史话(上)[M].台北:中华影评人协会,2004.
[13]黄秀如.台语片的兴衰起落[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91.
[14]侯凯.从话剧《野玫瑰》到电影《天字第一号》——中国间谍电影的类型生成及余脉追寻[J].当代电影,2016(3).
[15]黄仁.电影与政治宣传:政策电影研究[M].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16]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