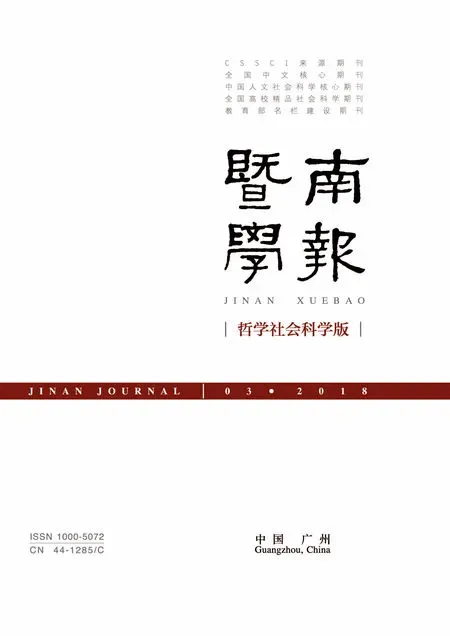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媒介传播“情绪设置”效果与机理
徐 翔
大众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和效果是得到广泛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媒体对于公共话题、热点对象、社会议题的讨论,构建和折射出公众对于议程的关注和聚焦,体现出媒介的“议程设置”。其最为核心的内涵如科亨所指出的,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则异常成功。沿着“议程设置”的理论脉络和基础,本文明确提出“情绪设置”的概念和问题:媒介传播在影响人们怎么想、怎么说方面也许并不成功,但在影响人们以怎样的情绪想、以怎样的情绪说方面,却具有足够的作用与效果。在“议程设置”理论中某种程度上缺乏对于议程中的情绪和情感谱系的足够重视,以及情绪直接作为“类议程”的本体可能性。有必要明确地和集中地聚焦于“情绪设置”,并将之作为舆情调控和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媒介“情绪设置”的理论探讨
在“议程设置”理论等经典的大众传播和媒介研究中并未明确地提出媒介“情绪设置”的效果。它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基础渊源与理论内涵可从以下方面探讨考察。
其一,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大众传播中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传播内容对于受众的影响,包括议题对象、“属性议程设置”等。它尽管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受众想什么。尽管研究者注意到了议程设置是和情感、情绪等因素相关联的,例如有研究者指出能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议程更容易成为公众议程,刘中望等对于微博的“议程设置”研究指出“感性的、情感倾向明显的微博内容更符合用户的认知模式从而更能吸引用户转发”,Schoenbach和Semetko在议程设置的研究中分析了媒介对议题的正面报道,以减少公众对议题的知觉显要性;Sheafer分析了媒介对经济议题的负面报道,以增加经济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知觉显要性。但是总体来看,议程设置理论对传播中的情绪传播和情绪扩散维度是缺乏足够的重视度的,既缺乏对于“议程设置”中情感因素的专门深入分析,更缺乏类似于“属性议程设置”之类的“情绪议程设置”理论建构。“情绪设置”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共同之处在于,从关注内容效果到关注形式效果,它们的效果都不在于影响受众具体如何想、如何说,而在于这些想和说的形式。“情绪设置”效果要求对媒介公众舆情效应中的情绪扩散效应与特征进行关注:媒介传播或许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以什么样的情绪想;而这种情绪状态,会随后对整个传播链与传播氛围产生作用,影响到舆情的环境与整体生态特质。
其二,从“沉默的螺旋”到“情绪的螺旋”。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由于从众心理、群体压力等因素,大众的意见会出现对某种主导意见的偏倚和螺旋。然而,在这种沉默的螺旋中,有没有与特定情绪的关联?沉默的螺旋仅仅是“意见”的螺旋抑或是含有情绪因子的气候的螺旋?有研究者分析了新媒体平台“沉默的螺旋”中的情绪传播,“人们通过观察主导性情绪,单向度的情绪传播越来越快,且情绪链的形成与扩展速度亦逐渐加快。”尽管这里涉及到了沉默的螺旋中的“情绪的螺旋”,但是依然把情绪简单地意见化了,寻求一种“主导性情绪”,而不是去探究在“情绪的螺旋”中不同于“沉默的螺旋”中的特殊机制,究其实质而言,情绪的螺旋的生成不是群体意见的“主导性”或“群体压力”,而是与情绪相关的情绪螺旋和情绪发展机制。或者说,某些特定的情绪元素在公众舆情气候中更易“螺旋”化,而非仅仅与意见、观点所受到的压力和驱动相关。对于这种螺旋中与情绪的关联性甚至情绪螺旋模式的探究,要求在“沉默的螺旋”的理论积淀上进而探求专门的理论路径,以考察情绪在舆情螺旋中的地位、作用和路径。
其三,“传播的偏向”与传播的“情绪偏向”。在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媒介的“时间”或“空间”偏向(bias)。然而,媒介及其传播的“情绪偏向”也是不可忽视的维度,它指的是媒介存在对于特定情绪的偏向,或者说特定媒介中特定情绪会具有更好的传播和扩散效能。从另一广义层面而言,媒介传播实际上也存在着“事实”与“情感”抑或“理性”与“娱乐”等的不同偏向。例如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媒介时代相对于印刷媒介的理性文化,具有娱乐化的主导特征。这实际上也向我们指涉了媒介形态与其内在的形式特征之间的关联。就媒介传播的情绪偏向而言,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媒介传播是否具有对于情绪化、情感化的偏向,作为一种重视情绪型的媒介而存在,而不是完全由事实或理性文化所主宰,这使得情绪化的传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第二,媒介传播中对于特定情绪的偏向,例如李勇等人对网络舆论事件案例的实证考察分析的线上和线下用户情感特征的差异。在媒介环境中,由于情绪偏向的存在,使得对于某些情绪的设置和引导、调控更具有可能性与实现度。
其四,从“群体极化”到“情绪极化”。“群体极化”现象指的是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在群体极化的研究中,主要指的是群体的决策、意见朝向极端化方向的迁移和发展。现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注意到情绪在群体极化中的倾向与程度中的作用。Sustein认为群体内的情感性联结对群体极化起推动作用,但是他的观点只是把情绪作为意见极化的一种辅助性因素。Forgas对群体的同质性效应予以关注和考察,或者说情绪体验的正、负性对群体决策的积极、消极性产生了影响。然而Forgas仍然是聚焦于决策和意见的极化,而非情绪本身的极化。情绪向度要求在“群体极化”向“情绪极化”的转换中,重视情绪本身作为一种极化的因变量,在其传播震荡过程中群体的情绪朝向更为极端的发展,并且这种情绪极化影响到或者至少和群体意见的极化之间存在着深入联系。
以上几种理论视角,尽管都涉及情绪的传播及其作用和意义,但是总体来看,并未涉及大众传播的情绪向度最为核心的层面。具体如下:一是只零散地、未系统化地涉及情绪和情绪传播的因素,但是并未突出其地位和深层的理论意义,甚至在一些理论中并未明确触及情绪传播的层面,这在“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明显的“视而不见”,尽管意见和情绪都是舆情和公众舆论的重要构成,但这些理论把聚焦侧重于前者,而有意无意地缺乏对后者的足够重视;二是对于媒介情绪设置、情绪偏向的专门注意和专门理论的阐述还不够,只是把情绪作为一种附属于内容和意见的层面,而不是具有本体性的,甚至是反过来对内容和意见具有导向性的因素;三是缺乏对于“情绪设置”的强效果论,也即媒介的“情绪设置”效果不应只是一种偶然性和零星的效果,而是符合媒介以及社会传播的规律、具有内在倾向性的现象机理;四是对于媒介“情绪设置”的后续效果的分析还不够,无论是成功的情绪设置,抑或是媒介的情绪偏向、情绪极化以及“情绪的螺旋”等,都要思考这些对于整体的传播进一步还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进一步影响和塑造情绪时代的传播格局和深层次的媒介文化特征。
媒介传播中情绪的激荡、螺旋、极化、设置,有其内在的机制和动力,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或偶然的现象,也不是附属于内容的因子,而是深入到一种本质或本体论的特征。因此,本文明确而集中地提出“情绪设置”的效果论:它指的是媒介传播在影响人们怎么想、怎么说以及想什么、说什么方面也许并不成功,但在影响人们以怎样的情绪想、以怎样的情绪说方面,却具有足够的作用与效果。
二、媒介“情绪设置”的效果机理
“情绪设置”得以形成及其作用在于:(1)媒介传播中存在着有力的情绪感染及社会扩散,它们的扩散以及设置体现着媒介用户强效果论意义上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联结机制,例如媒介讯息对于受众的情绪唤起和导向,以及传者和用户社会网络之间的情绪影响和情绪传递,这些形成群体和社会网络结构中的情绪设置;(2)媒介传播中存在着阈下“情绪启动”、“情绪一致性”和“动机性加工”等效应,用户接收到的讯息中的情绪会影响和形塑其之后的感知以及、判断、认知和态度生成等过程中的情绪色彩和情绪敏感性,生成特定情绪导向下的讯息接收、加工和再生产,形成启动意向性的情绪设置;(3)媒介传播中基于情绪的“社会比较过程”、情绪循环等机制,形成情绪传播发展过程中的情绪共变乃至“情绪的螺旋”,成为情绪设置的有力生成条件,形成传播链路中的情绪设置;(4)媒介传播中的情绪具有偏向性,特定的媒介场域与特定类型的情绪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和动力机制,这一方面使得媒介气候中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情绪特征,另一方面也使得情绪设置在倾向性路径下具有更多驱动基础与现实效应,生成符合媒介偏向性的情绪设置。
(一)媒介传播中的情绪感染与社会扩散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情绪的传染和感染现象,它们也是“情绪设置”效果的有效条件与前提。或者说,媒介讯息和媒介传播对于情绪的感染起着多方位的激发、唤起、导向等作用,媒介环境中情绪的传染和扩散性使得情绪的设置成为可能,呈现出群体性、社会性的情绪效果。在具体的媒介中,情绪的导向效应也是存在和显著的。情绪感染由于媒介的群体性和社会化使用而呈现出其情绪的引导和影响,个体媒介使用者的情绪受到群体情绪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个体的情绪并非独立于其所处的传播环境。一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或机构组织,其情感表达对于受众的情感状态及变化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例如Bae和Lee对twitter知名用户及其受众的研究中,证实了Obama、CNN Breaking News等知名用户的情感表达,能影响到对其进行转发、评论或提及这些知名用户博文的受众,和受众群体的情感变化存在相关性。
在社会网络中,情绪的传播链也易于产生感染的现象,形成用户群体和社会关系中的情感同质性与情绪体验相似性。有研究就社交网络的同质性(homophily )指出,人们倾向于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联系。Bollen等对Twitter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交网络中幸福的用户更关注幸福的用户。Fowler和Christakis分析社会网络中快乐/幸福的扩散指出,如果人们周围充满快乐的人,那么更可能变得快乐。对于大众传播而言,这种“传染模型”无疑可以切合对于某种社会网络中的“情绪设置”。社会网络的亲疏关系等因素对于情绪的激发和传递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社会网络的群体情绪模型中,用户之间的情感关系越亲近、近邻数越大,则群体情绪的最终强度也越强烈,情绪涌现所需的时间也越短。意见领袖或者说“情感领袖”对其受众的情绪影响力、媒介用户的群体情绪扩散、社会化媒介中的情感同质性等因素,都呈现出有效的“情绪设置”路径。
(二)媒介传播中的情绪启动与情绪一致性
情绪的“启动效应”指的是在情绪传染和传播中,先前呈现的材料、对象,对后续材料的感知、认知、心理加工产生更为易化或敏感的情绪色彩。这种情绪启动是深入到阈下知觉层面的 “阈下情绪启动”(subliminal affective priming)。在网络等媒介的传播中,情绪启动效应是得到证实的心理机制。秦敏辉等人对某即时通信软件中的网络表情图片的传播进行分析,被试者在正性情绪启动后倾向于将中性靶刺激判断为正性,在负性情绪启动后倾向于将中性靶刺激判断为负性。在情绪的启动效应下,媒介受众对于某种情绪的讯息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准备度,并对其情绪反应和情绪发展以及认知、接受过程产生倾向性的作用。情绪启动反映出接受者个体关联于特定情绪的心理状态,并对个人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
对于信息的接受和反馈会呈现出情绪的“一致性加工”和“情绪一致性效应”。例如在情绪一致性记忆(emotion-congruent memory)中,个体记忆与当前情绪倾向的一致性。从“易接近性”假说(accessibility hypothesis)而言,与积极/消极情感状态相联系,或者引起积极/消极情感状态的思想,能使得记忆中其他相类似积极/消极性的材料更容易接近,从而形成“情绪设置”在材料接近性上的心理机制。情绪的一致性也体现在对媒介和信息接收的效果和认知中,例如Johnson和Tversky发现,阅读具有悲伤内容的报纸的人们会高估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风险。需指出的是,这种效应并不同于“涵化”理论中偏重于宏观层面与累积效果,而是基于信息接受者个体心理特质的机制效果。在情绪一致性和“情绪框架”的理论视角中,媒介受众的情绪解读和情绪生成与其前置的媒介讯息之间体现出紧密的效价关联。在对讯息的接受、处理中,个体的信息反馈、阈下情绪、讯息认知、情绪敏感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变化,从而显现出讯息情绪色彩的作用。媒介传播的“情绪设置”过程,受到“情绪启动”、“情绪一致性”和“情绪框架”等机制的作用,表现出阈下的情绪导向和情绪影响,受者在先前所接收讯息的情绪下,导致其后续的感知和意义认知等都受到先前的前置情绪的影响,而非独立的理性情绪过程。
(三)媒介传播中的情绪共变与“情绪的螺旋”
媒介中的用户关系并不是完全虚拟和抽象的,尤其在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中更是如此,媒介传播中的用户关系、社会关系由此会对媒介情绪的社会扩散的动力和路径产生作用。在媒介讯息传播中,Hillmann等人分析论坛、微博、网络聊天等不同类型的在线交流,发现两两用户之间“情感差值”都很小,显示用户之间倾向于表达彼此相同的情感。情绪的“社会比较过程”刻画了这种群体的情绪传播机制,诚如Festinger指出,人们会把自己的情绪与他人比较,调整情绪,从而使自己的情绪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McIntyre等研究者指出,社会比较的原因是因为其不确定性,人们不确定自己对该事件的感受是否是正确的,从而不断地调整使自己的情绪与大多数人一致。媒介环境中的用户、受众受到社会比较过程和情绪社会感知情境的影响,其情绪体验不是自身的独立变量,而是受到“情绪气候”、情绪情境等因素的调整与形塑。
在“群体极化”中,群体的意见会经过公共的讨论和传播形成极端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同质共振和不断调整的过程。根据群体极化理论,也可推演到“情绪极化”的效应,某些情绪在传播过程中会趋向更加强烈或微弱的偏激化和极端化。情绪的感染在其强意义上还会形成情绪循环和社会“情绪的螺旋”。在这种情绪的扩散和传播中,不是单向过程,而是双向、互向的反馈传递,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的情绪会呈螺旋上升趋势。这对于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之外寻求“情绪的螺旋”是有独特意义的,情绪的螺旋并非依赖于从众心理和群体压力,而是情绪性的感染共振和循环反馈。当前媒介语境下,增强了群体之间的互动渠道和反馈语境的畅通性,也使得情绪的螺旋更为便利与增强。这种效果变现为,在群体性的媒介事件中,往往出现情绪较之通常情况下的增强和放大。例如周云倩、胡丽娟对于微博舆论事件的案例分析指出,网民的愤怒情绪表达存在着一定的情绪共变和同质化状态,其传播具有启动快和时间集中的特征。在群体性的媒介讯息接受中,受众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和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媒介语境中产生媒介群体情绪的循环与放大,甚至是在大规模信息爆发中的“情绪流瀑”。
(四)媒介传播中的情绪动力与情绪偏向
媒介传播的“情绪设置”遵循不同类型的情绪的发展和演化规律,某些特定类型的情绪在特定的媒介中具有更强的增长动力和偏倚性,从而使得媒介情绪的设置具有方向性的更强导向,另一方面也要求“情绪设置”遵循其媒介的“情绪偏向”。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曾就群体情绪指出:“本能性的情绪特别容易感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在媒介传播中,对于不同的媒体中的情绪偏向性,具有差异化的观察与结论。Hansen等研究了Twitter中情感对转发的影响及其复杂的关联,对于社会消息,积极情感能促进其转发;而对于新闻内容,消极情感能促进转发;Hansen等将其称为“对朋友们要说好听的话,对公众要提供坏消息”。周杨、张会平指出游离型的微博用户更多地具有愤怒、谴责等重度负面情绪。对于不同的媒介语境和使用情境,其“情绪设置”体现和遵循着不同的情绪差异,这也是不同情境所具有的情绪特征。
与媒介的“情绪偏向”相关,包含有不同情绪的媒介讯息或传播环节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和现实能效,从而使得媒介气候具有不同的情绪特征。这主要包括情绪正负性或积极/消极性、具体情绪模式、情绪分歧、情绪唤起度等方面的因素。刘丛、谢耘耕等人在微博传播的研究中将情绪分为认可、恐惧、质疑、担忧、反对、愤怒、悲哀、惊奇及无明显情绪的信息陈述,发现普通用户中愤怒和质疑情绪具有最主要的比例;微博的负面情绪越强烈,则其被评论、转发的就越多,而正面情绪的强烈程度则与微博被转发、评论数无相关性。Zhao等人在对新浪微博的研究中,将情绪分为愤怒、喜悦、低落、厌恶四种,发现愤怒情绪更容易得到传播,低落情绪则不容易得到传播。Naveed等人对微博转发量进行分析,发现带有负面情感的微博更容易被转发。Berger和Milkman对纽约时报上6 956篇文章分析指出,“高唤起”(high arousal)的情感内容更容易被分享。Pfitzner等的研究中,Twitter中“情绪分歧”(emotional divergence)高的微博被转发的机会更多。总体而言,媒介传播的情绪偏向使得“情绪设置”在倾向性的基础上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便利性,针对特定媒介在情绪的类型、极性、效价、“情绪分歧”、“情绪唤起”等方面的动力机制和偏向性,可以改变与提升“情绪设置”的实际效应。
三、结 语
情绪的有效传播对于媒介环境、社会气候产生重要影响。李普曼认为:“在具有不同反应倾向的人群中,如果你能找出一个刺激因素来唤起他们同样的感情你就可以用它来代替那个最初的刺激因素。”情绪传播中的群体设置、媒介语境中和意见领袖的情感影响力、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同质性、情绪启动与情绪一致性效应、情绪框架、情绪的“社会比较过程”和情绪共变、情绪偏向等机制,都指向着情绪设置的生成与作用路径。“情绪设置”不仅是对议程设置等效果理论的必要延伸,也是对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视域转向,从探讨受众在媒介影响下如何感知、感知什么到以什么情绪感知,以及这种情绪对于感知和后续的传播和接受而言意味着什么。
情绪设置的效果和生成对于舆情调控、情绪传播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诉求,需重视以下方面的实践关系与理论路径。
(1)内容导向与情感导向。舆论传播中的多数经典理论尤其是效果理论,例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以及认知平衡理论等,主要侧重于内容和认知的层面,其中的情绪和情感元素尽管也会被考虑和涉及,但主要仍是作为认知内容的次生因素,并未形成对于内容、认知等方面的足够区隔,也并未被这些理论作为其原生性的架构。然而在实际的考察中,可以明确情感和情绪在传播中对于传播效果、受众观念、行为、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高度价值。“情绪设置”视阈需要一种情感导向下的理论框架,把情绪传播作为基础性的元素,考察情绪传播的特质和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效果生成。
(2)舆论特征与情感治理。The
Economist
的文章“Art of the lie”对美国大选过程中竞选人川普的“断言”与他代表的“后真相政治”和“后真相社会”进行了解读,后真相舆论语境下的民众忽略事实,以立场来决定是非或者支持政见及政客。媒介传播不仅生成各种意见、观念、“事实”陈述的交互场域,也生成错综的情绪环境并对受众产生显著的影响,情感的管理和引导因此成为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社会议题。“情绪设置”要求高度重视舆论和媒介传播中的情感发展和传播的内在机理,对复杂的公共情绪环境进行有效引导。而这其中,媒介本身的情绪偏向以及媒介情绪的特质、类型、效价、扩散等因素,都是需考量的约束条件与形式机制。(3)议程设置与情绪设置。在大众传播的主导性范式视角下,受众、用户主要是认知的人、理性的人,也因此导致对于受众的引导和调控,主要仍基于认知。正是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对于议程的关注缺乏对议程中情绪和情感谱系的足够重视,甚至忽视了情绪直接作为“类议程”的本体可能性,使得有必要明确地和集中地聚焦于“情绪设置”,并将之作为舆情调控和传播效果的范式路径之一。这其中,从“议程设置”向“情绪设置”的迈进不是孤立的,它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相关联的架构,包括从“沉默的螺旋”到“情绪的螺旋”、从“群体极化”到“情绪极化”、从“认知一致性”到“情绪一致性”、从“启动效应”到“情绪启动”、从“意见领袖”到“情感领袖”等的调整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