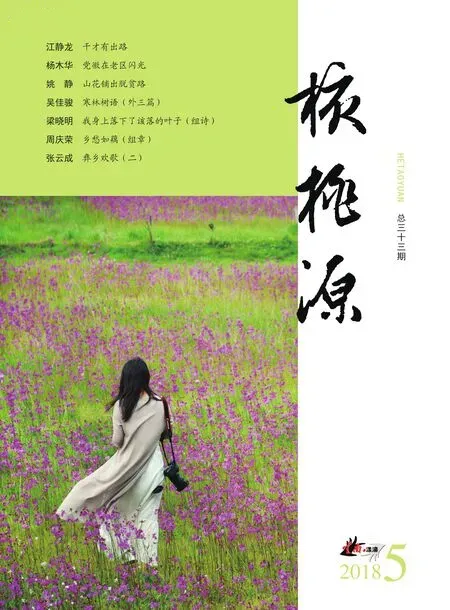沿着一条街的走向,回到宋朝(外二篇)
小 睫
一条从宋朝走来的街,载着前世的繁华,连接日月和古今。
锦衣护卫前呼后拥,那个身穿黄色锦袍的人,穿过宣德门,经过朱雀门,走过南熏门。
身后是威严肃立,身前是无上至尊。
十里长街,飞檐斗拱,黄瓦红墙,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真实又虚无的梦。
一梦千年。每一个梦里都有千秋,都淌着英雄的泪。
江山如画,仿佛昨天。我只能在时间的悬崖上一退再退,退到流年之外,于你两侧的角楼,雕梁画柱之间,赏“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风情,读“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雨”的佳句。
一条铺满遐想的路,在前朝的时光里招摇,于现代文明的窗口生辉。
脚下,被岁月磨去棱角的石头,每一块都浸润着风雨,细腻温婉,激情豪放。记载着王侯将相盛大的奢华和随风而去的荣光。
新街口至午朝门,四百多米的长度,绣出盛世,也留下了佳人的幽怨。
高大的楼阁内,装得下千娇百媚,却怎么也装不下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无奈与惆怅。
晓风残月。
寂寞了千年,爱恨了千年。
宫灯高挂,灯火绚烂,只为照亮这片土地上曾经拥有的阑珊夜色。
伫立的牌坊,石雕的大象,上骑的武士……一一躲过了烽火硝烟,人间的情仇恩怨,于御街的今世自在逍遥。
而我,恰好在风声四起的秋天穿越,走进这满城弥漫着菊香的旧时。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
宋朝的一场夜雨,淋湿了宣纸上的诗意,如蝶翩翩。
一个从前朝迷路的女子,此刻,被你四溢的墨香,鳞次节比的楼阁召唤,于半梦半醒间,沿着杨柳岸,回到宋朝。
穿行于一幅水墨的虚幻与真实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与宋朝的缘分,始于一幅水墨和它身后软红香土的古都。
走进清明上河园,你就是一阙宋词,一帧流动的风景。绚丽,旖旎。你就走进了张择端的画笔,沿着清明上河图的曲径,回到汴京。
时间如剑,碎了一帘幽梦,画卷的背影苍凉,饱满的容颜消瘦。
沉寂。一个朝代的繁荣被装帧成画像,嵌于历史长廊。
千年以后,一场浩荡的春雨莅临。呼吸,心跳,律动。生机勃勃。
多好,可以省略岁月艰辛的部分,取你怀中的一小段光阴,温暖旧事。无需打马,束腰紧扣儿,一日便可回到前朝。
虹桥,起于阳光,止于佛香。站在虹桥之上,望恋恋红尘,赏江山万里,读风情万种。
商铺林立,舟船载着宋词与粮食,一遍遍过虹桥。
鸿福寺的钟声飘荡,祈祷着苍生,穿越人间明亮的灯火。
打坐诵经的人可知,红尘已从经卷上走过经年,可曾细数过窗外飘过的晨烟暮霭?
木兰织房唧唧复唧唧的声响,摇动桥下的一池碧水,那些透明的绿,慢慢退去脸上的青涩,荡起层层柔波。
登画舫,依栏凭眺。丝竹声声,清风徐徐,一首诗的意象在莲的清香中打坐。而漕运的忙,永远地留在了东京码头的倒影里。
思绪飘渺。
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岳飞?还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李清照?
是,也不是。
河水娇嗔含怨,柳枝低眉不语。抬头望去,却见游人如织,流莺百啭,烟雨亭台。他们正在一一回到自己最初的位置,回到汴京,回到宋朝。
目光如蓝。风景如画。
恍若梦境。突然分辨不清是画在梦中飞,还是人在画中游。
汴西湖,我愿在你清澈的目光中渐渐老去
启程前,还有一些散碎的时间,足够让我扫净身上的灰尘与风雨,退去影子里的臃肿与灰暗,怀抱春天一天高过一天的暖。
这样,才好让我出现在你面前时,如梦境中所遇见的那样。
笑靥如花。洁白如雪。清净如莲。
此刻,你等在鲜花满枝的早晨,打开怀里的清澈,以六百亩的浩淼,六百亩的荡漾,迎接我。
相聚千年的距离被时光涉水而过,我在那些被你复活了的景致里找到了“琪树明霞五凤楼”,汴菊百堆,绿影千里,找到了通往汴京那条坦荡如砥的路,找到了欧阳修,秦观。
为了这场千年的约定,你让古老的土地生出嫩绿的新意,让触手可及的古韵与现代文明和解,接受所有抵达者目光的审美。
清新婉约的宋词在一湖水的宣纸上缓缓打开平仄,整座春天便跟着明媚了起来。鸟鸣合着韵律在大声朗读,朗读着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明天。
因为有你,无需烟花三月下江南,等清风送出船舫,断桥再续前缘。
我只要你湖面掀起的一缕春风,双手捧出的绿如蓝。
五公里的岸堤,绵延着你慢版的抒情,宛若西湖的倒影,隔着苏轼的那场《西湖初雨》,两两相望。
谁是谁的前生?谁又是谁的今世?
在你怀里,我是一株招摇的水草,是岸边一粒透明的石子,是倒映于粼粼波光中的一朵红云。
在西湖湾,在橄榄城,在龙亭公园,在汴西湖沙滩……
因为有你,一座承载过八朝古都古风古韵的城市,凌波起舞。迎风吐艳。花团锦簇。
来路太多沙尘弥漫。我愿栖息于你的目光中,绘画抚琴,吟诗作对,听风赏月。
与岁月一起,在一场比一场凉的秋风中,慢慢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