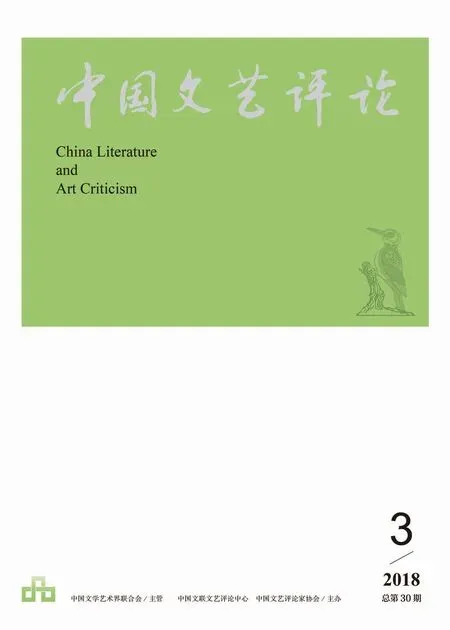本体与价值:论当代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李 伟
引 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本体”与“价值”都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哲学意义上的,第二个是一般意义上的。本文取一般意义上的,即“机器、工程等的主要部分”“用途或积极作用”。简单地说,本体,即“事物是什么”;价值,即“事物做什么用”。做什么用,还存在一个实然和应然的问题,即可以做什么用和应该做什么用,后者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本文将讨论的是“当代戏剧的本体与价值”问题,即当代戏剧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即当代戏剧的形态与功能问题。
“当代戏剧”,可以有三种理解:一、从1949年至今的新中国戏剧;二、从1979年至今的新时期戏剧;三、从2000年至今的新世纪戏剧。为了更有时代感和当下性,本文将选取第三种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客观上逐渐形成了“话剧—戏曲”的二元结构,因此,本文的讨论将聚焦在新世纪以来话剧和戏曲的形态与功能问题。
当代戏剧的确存在本体不清与价值迷失的问题。戏剧批评有责任为认清戏剧本体、找回戏剧之魂而努力。即要回答当代戏剧“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应做什么”的问题。这就要涉及两个关键词:民族性和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将回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缺失如何解决,也将回答我们如何进行理论建构与主体重塑。
一
本体与价值、形态与功能,本来是相随共生、相互联系的。有什么样的本体就会具有怎样的价值,要想实现一定的功能就要求具备一定的形态。如中国传统戏剧(戏曲)“诗、歌、舞一体”的“乐”本位特征,就是和它的娱乐与教化(“寓教于乐”)的功能紧密相连的。但进入到20世纪以后,形势的发展不断对戏剧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戏剧本体、戏剧形态的改变。
清末民初之际,为了唤醒民众、宣传革命的需要,戏曲被批判,话剧被引进。戏曲就不再是原来的戏曲了,它需要适应新的舞台、新的观众、新的思潮;话剧也不是西方戏剧的原样,它需要在全新的文化环境里站稳脚跟。“戏曲现代化,话剧民族化”是时代对戏剧提出的要求,是20世纪上半叶戏剧发展的两个主题。许多戏剧家以自己的实践回应了时代的课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汪笑侬、欧阳予倩、梅兰芳、程砚秋、田汉、周信芳等对京剧的改革,易俗社对秦腔、成兆才对评剧、樊粹庭对豫剧、袁雪芬等对越剧、延安对秧歌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陈大悲、蒲伯英、张彭春、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郭沫若、熊佛西、曹禺等则对话剧的民族化有筚路蓝缕之功。在这个过程中,戏曲在叙事结构、主题传达、舞美灯光等方面受到了很多话剧的影响,话剧也吸收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如线性叙事、诗性抒情等。这个时候,人们基本认为戏曲就是旧的、传统的、民族的,话剧就是新的、外来的、现代的,不存在戏曲要民族化、话剧要现代化的问题。
1949年以后,为了宣传新的意识形态,政府对戏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新戏曲从题材上分为“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种,编剧更多地追求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律、追求情感高潮与情节高潮的同时完成,引进导演制,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学习“体验—体现”式表导演体系,全面向话剧学习,被讥为“话剧加唱”。话剧则尝试采用锣鼓点,在形式上继续民族化。由于新时代要求歌颂工农兵的生活,不允许批判、揭露现实问题,因此体裁上逐渐淘汰了悲剧和讽刺喜剧,只剩下歌颂型喜剧和正剧。到了“文革”期间,戏曲要求只能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于是,出现了舞台布景、灯光造型、人物化妆都高度精致化、“现代化”、写实化的八台“样板戏”。而话剧更是乏善可陈,只有几个极度公式化、概念化、政治教条化的斗争话剧、阴谋话剧。这个时候,戏曲显然已经揉进了许多西方戏剧的元素,不那么民族化了;话剧显然已经僵化,停留在19世纪的经典形态上,而且观念上甚至成了专制思想的传声筒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经济建设与物质生活的改善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戏曲、话剧都先后出现危机。戏曲在“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碰壁之后,也重新回到了创编新戏的道路上,出现了《司马迁》《南唐遗事》《秋风辞》《新亭泪》《徐九经升官记》《曹操与杨修》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编戏。话剧从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揭露现实问题触了礁,不得不放弃内容上的敏感问题而转向了形式上的探索革新。由于布莱希特从梅兰芳的戏曲里获得过启发,他的打破第四堵墙,破除舞台幻觉,刻意制造间离效果,鼓吹戏剧的教育作用,都和中国传统的戏曲有相通之处,于是布莱希特一下子成为时尚,成为了新时期话剧改革的精神教父。话剧舞台呈现形式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我们并没有学习到布莱希特的精华之处: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的批判精神。这一时期,戏曲依然延续“样板戏”式的写实舞台道路,但思想内容上有对深度的追求;话剧在舞台形式上得到了解放,但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依然有束缚。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戏剧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得生存,既要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国家为了传统文化、高雅艺术不受经济浪潮的冲击,对戏曲院团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而让话剧院团进行市场化改制转型。同时,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以及各类艺术节奖等众多奖项,引导戏剧走“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道路。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同时作用下,戏剧的面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大大增多了,但也出现了一些虚假和平庸之作。戏剧繁荣了,但老百姓却不大花钱买票看戏了,“台上繁荣、台下冷清”的状况出现了。戏曲舞台充斥着豪华布景、炫目灯光、刺耳音响,然而却缺乏让人奔走相告的好故事和令人口耳相传的好唱段。评论界一时有“一流的舞美、二流的表导、三流的剧本”之讥。话剧舞台轰轰烈烈的小剧场戏剧探索,也从先锋实验精神交流型的《留守女士》、思想颠覆型的《屋里的猫头鹰》走向了商业大众的“白领戏剧”“减压戏剧”“搞笑戏剧”“粉丝戏剧”,严肃戏剧创作乏人问津。戏剧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新世纪,走到了今天。
二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哪些失去的是我们应该找回来的,哪些得到的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的?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短板如何补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与“主体重塑”应该要回答、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当代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
当代戏剧应该具备民族性。“民族性”关乎本体(是什么),要回答中国戏剧的民族传统是什么,即,中国戏剧对世界戏剧的独特贡献何在?中国传统戏剧的本体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不少人进行过理论阐释。王国维说的“以歌舞演故事”和齐如山说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突出了中国戏剧的歌舞性;吴梅说“有戏有曲”,张庚说“剧诗”,强调了中国戏剧的音乐性和文学性。余上沅说“非写实的纯粹艺术”,赵太侔说“程式化”,张厚载说“假象会意、自由时空”,阿甲说“虚拟的时空,严格的程式,写意的境界”,突出了中国戏剧表导演方面的特色。王元化说“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艺术体系”,董健说“乐(诗、歌、舞一体)本位”,叶长海说“总体性”,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如果单讲艺术形式特征的话,王元化概括最准确,若包含价值观念,则董健、叶长海最全面。
中国戏剧演出中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特点,叙事上一线到底、多线并行的特点,内容上以抒情见长、悲喜相乘的特点,舞台时空自由流转的特点,通过脚色行当体制塑造人物的特点,形态上“诗、歌、舞”一体的特点,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品格,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是对世界戏剧的独特贡献。人类历史进入到现代以后,西方很多戏剧导演纷纷从中国戏剧中获得启发、汲取营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完善了本民族的艺术体系。但他们学习的主要是中国戏剧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才子佳人与帝王将相的故事与忠孝节义的主题。
当代戏剧应该体现现代价值。“现代性”关乎价值(做什么)。现代价值是与人类进入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社会相伴生、扬弃了部分传统价值后形成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等。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吸收了这些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继承了本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结合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程而提炼出来的,在当下中国具有普遍共识,亦应该成为戏剧创作中的基本价值观。郭汉城先生在谈戏曲现代戏时也讲“现代性和民族性”:“戏曲现代戏要继承发展,必须重视现代性和民族性。既然我们搞的是现代戏,就必须紧紧把握现代性的特征。但我们搞的是戏曲现代戏,又必须紧紧把握民族性的特征。”但他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必须从生活出发,要熟悉生活,认识生活”的意思,“民族性”则是指“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表演艺术方面,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两个结合——体现与表现的结合、自由与规范的结合。中国戏曲不仅十分重视人物的内心,同时又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外在表现,有一整套唱、念、做、舞的表演程式和相应的技术规范,作为实现两个结合的具体手段。这是我国虚实相生、形神兼备、高点散视、时空流动等传统美学思想在戏曲艺术中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全面的、完整的现实主义艺术,具有更强大的人民性。”
由于西方国家比我国先行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的价值观念也比较多、比较早地体现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他们的优秀文明成果,包含体现了现代价值观念的戏剧艺术。这样就在19世纪末引进了西方戏剧,在20世纪形成了我国的话剧艺术。在话剧艺术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艺术家,如剧作家曹禺、田汉、熊佛西、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老舍、沙叶新、李龙云、姚远、赵耀民等,导演洪深、焦菊隐、黄佐临、徐晓钟、徐企平、陈明正、王晓鹰、査明哲、谷亦安、孟京辉、田沁鑫等。现代价值观念在话剧艺术上集中体现在写实主义戏剧观的贯彻上。除了在人物塑造、主题提炼、故事讲述上都严格追求逻辑真实外,在舞台美术、人物造型、表演艺术上都追求细节的真实。斯坦尼—易卜生式追求幻觉真实的戏剧观在我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直到1980年代戏剧观大讨论才使布莱希特大张旗鼓地进入中国,写意的戏剧观开始在话剧舞台占据一席之地。迄今为止,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他们的话剧,既学习他们的技艺形式,也学习他们的思想内容,但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我们学到了他们的技艺形式,还没有真正学习到他们宥于批判与怀疑精神的思想内容。
由于现代价值观念在社会上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包括话剧艺术的影响,改编戏曲和新编戏曲也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备现代价值观念的剧作家、体现现代价值观念的戏曲作品大量涌现,如欧阳予倩的《武松与潘金莲》、田汉的《谢瑶环》《白蛇传》、吴祖光的《花为媒》《三打陶三春》、成兆才的《杨三姐告状》、陆朝非的《天仙配》《女驸马》、陈仁鉴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陈静的《十五贯》、吴白匋的《杨门女将》《百岁挂帅》、王冬青的《连升三级》、郭启宏的《南唐遗事》、王仁杰的《董生与李氏》《节妇吟》、郑怀兴的《新亭泪》《傅山进京》、周长赋的《秋风辞》《景阳钟》、魏明伦的《巴山秀才》《夕照祁山》、徐棻的《死水微澜》《马前泼水》、罗怀臻的《金龙与蜉蝣》《西施归越》、曹路生的《玉卿嫂》《旧京绝唱》等,表现了中国人争取平等自由、获得独立尊严、追求个性解放、赢得社会公正的奋斗历程,应该说戏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在获得现代性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
然而,无论在本体层面的民族性守护上,还是在价值层面的现代性追求上,当下的戏剧都存在严重问题。
本体层面上,当前戏剧舞台上存在着一个明显倒错现象:新编戏曲力求写实——故事力求实有其事,甚至真人真事,如京剧《廉吏于成龙》强调《清史稿》里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沪剧《挑山女人》强调是发生在安徽五条山区的一个真实故事,《徽州女人》导演陈薪伊说导该戏是为了还愿(她奶奶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舞台美术也一定要再现历史真实,《成败萧何》一定是汉代门廊,《贞观盛事》一定要有盛唐气象,《徽州往事》一定要有白墙黑瓦马头檐,《大唐贵妃》更是将逼真的华清池搬上舞台,歌舞演员充斥舞台;人物造型也绝不允许秦冠汉戴,宋衫明穿,诸如此类,仿佛不逼真不足以有艺术感染力,而将古典戏曲的写意传统与游戏精神抛到脑后。话剧却力求写意——很少看到营造幻觉真实的四堵墙式的舞台,早就接受“空的空间”了。无论舞台设计、人物造型,还是故事讲述、人物塑造,均放弃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严谨写实的传统而追求戏曲艺术的时空自由。林兆华的《赵氏孤儿》、田沁鑫的《青蛇》、王晓鹰的《伏生》《理查三世》,都没有被镜框式舞台所束缚。话剧的追求不仅符合民族性,而且与世界潮流同步;戏曲本来是民族艺术,却长期以来走在反民族性的道路上,而且未见高明之处,不知何故如此、何必如此、何苦如此?
价值层面上,当前戏剧也存在着明显的混乱现象。新编戏曲曾经追求深刻厚重,拷问人性幽微、追问历史真相、直面现实困境,出现过一些好的作品,如上世纪80年代的《新亭泪》《秋风辞》《曹操与杨修》,新世纪的《傅山进京》《成败萧何》《景阳钟变》等,但最终还是走向了道德教化,如《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挑山女人》《程婴救孤》等。话剧本来应该以摹写真实、揭示人性、审视困境见长的,但最近也走到了廉价的大团圆模式、春晚式的煽情模式。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长生》《大哥》《老大》、西安人民艺术剧院的《立秋》、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立春》等。这还是严肃的原创戏剧,那些纯商业的戏剧,则是以搞笑为主要目的了。可见,古典形态的戏曲亦可传达现代意蕴,亦有传达现代意蕴的时候;现代形态的话剧在传达现代意识上或许有方便之处,但也未必都有现代意识。本体与价值、形态与功能并无必然联系,是可以相对剥离,进而优化组合的。
这就要求我们实现最佳组合,探索用民族化的形态表达现代意识的多种可能性。如何运用符合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形态表达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故事,是我们的戏剧创作需要努力的方向。无论话剧还是戏曲,都可以和需要发挥我们戏剧的民族特性,以利于戏剧的传播与接受;无论话剧还是戏曲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赓续的过程。我们需要弘扬我们的民族形式与艺术精神,借鉴西方的现代精神,重铸现代戏剧之魂。
对戏剧创作如此要求,对当代戏剧批评亦应作如是观。应该用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标准去从事戏剧批评。所谓戏剧批评的民族性,是对本民族戏剧文化传统的主体自觉及在批评活动中的自觉运用,具体而言是指对民族戏剧艺术历史的理性认知,对传统戏剧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传统戏剧美学风格的自觉弘扬。所谓戏剧批评的现代性,是指在戏剧批评中要具备和体现既能够接纳优良传统,又能够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现代社会中能被广泛接受、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视角切入戏剧批评,就是要在弘扬戏剧的传统美学和发掘戏剧的现代价值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中国戏剧艺术之两翼,我们无论搞戏剧创作,还是从事戏剧批评,都不应抛弃它。
今天的世界依然是西方主导的,包括艺术审美上也还存在着唯西方是尚的风气。我们现在需要找回我们的主体性,确立自身的艺术评价标准,重新赢得艺术包括戏剧审美上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