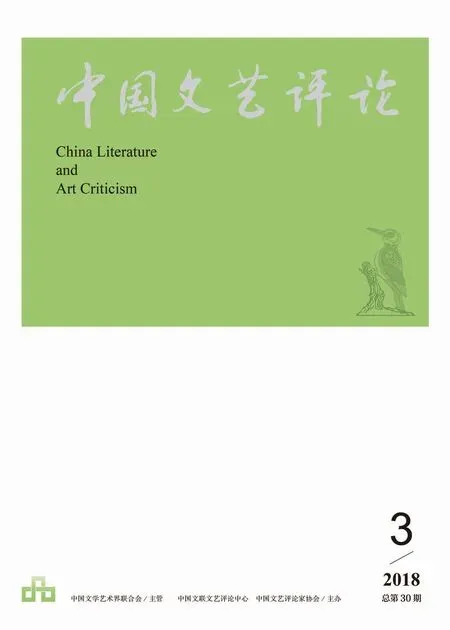“后理论”时代与文化诗学批评思潮的流变
陶永生
作为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事件和标志性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学派能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独特的景观表征出:人们曾如何蹒跚地走过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几多可圈可点的痕迹,或浓墨重彩的印记、或痛彻心扉的遗憾,这其实也就是从直指本心、直达历史深处的终极层面来触摸、理解和捕捉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任何一段精神的历史,即便初始时还很微弱、渺小,甚至往往会无疾而终,倏忽而逝,但对于未来都将具有不可替代的定格和不可磨灭的价值。躬逢其盛,中国传统“诗论”思想博采众长、自我扬弃,同“无论是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阐释语境,还是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批评视域”都生成了一系列的蕴涵交集与视域融通,从而为文化诗学整体形态平添了更多中国元素与中国气派。
似乎再度呼应了“以全球为架构思考,以本土为关怀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流行语,当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多元文化竞相迸发的繁荣格局,为不同区域兼容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双重维度的“国别体”文化诗学批评形态同步粉墨登场准备了时代契机和资源优势。尤其是进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提出的“后理论”时代,落实在“通过比较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的方法论层面上,要实现这些异域及异质文化——包括作为文化范畴中的一种特殊构成的文学形态在内——之间的批评交流与商谈沟通,就更需要我们去寻求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和共性所在,寻找它们之间平等对话和有效沟通的载体与平台。
一、“本土化”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呈现形式中一向以“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集大成者——文学样态”见长,早在孔子兴办私学时即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列为“四科”,高蹈着“诗性精神”的文学形态随喜成为典型的本土话语和固有学科。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明曾几何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其他文化形态、文明板块折服膜拜、争相效尤,“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呈现文学场域的运作肌理”的文论样式,中国“诗论”传统自备一格,而又源远流长,它立足于中国“文学事实”本位,以原道、载道、明道为人文诉求和价值追求,渐次积淀而成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形式。
延至中国文化诗学(China’s Cultural Poetics)一脉,只是增添了些“实证”色彩,它注重感性把握与理性认知结合,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叙述,这一自觉的立场与视角成为了最终融入世界文论潮流的不可或缺的路径选择。体现在“比较视域本体”的方法论层面上,中国文化诗学批评形态本身就具备这种以整体性文化系统为参照系,既学贯中西又融通古今式地包容各种具体文学样态或文化形态的理论质素和学术品格,为实现异域及异质文化之间的交互构塑铺垫了厚实的基石。
毋庸置疑,当下的中国文化诗学确乎受到了西方文化视域下高扬着“诗学理性”品格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思潮,尤其是美国文论家斯蒂芬·格林布莱特首倡的文化诗学批评学派的触发和激励。与前述典型的本土话语“诗性精神”相较,这里的“诗学理性”确乎是个“表征着异己力量和他者身份”的舶来品。探索“他者身份架构及其生成机制”理论形态的意义,从“他者”立场与视角出发,反观自身,“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体认,“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与众多现代性学科的“东方化”发展史相仿,这里也有个如何消除水土不服症状的“本土化”问题。“东方化、本土化”问题域涉及“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和“自我被塑造”(Selffashioned)的双重转化过程,是自我(本我)力量与他者(异在)力量短兵相接、攻防互换的互动过程,互有征服,又互有屈从。只有经历了与中国固有的批评方法与研究路向相结合的“本土化”洗礼的文化诗学批评范式才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事件及文学事态的有效方法和必由之路。
我们认为,“西风东渐”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思潮具有“本土化”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当然,这一切只是“可能”。“可能”,一方面意味着尚未发生的“未然性”,但也同时昭示了包孕着无限可能的“或然性”。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但也正因为没有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无限可能。这一核心判断是基于美国正宗的文化诗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学阐释学以及当代的文化诗学批评学派之间存在的若干重要“相通性”而作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相通性也只是说在两种研究路向之间具有某种相契合的可能性,并非说二者是具有同样性质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更不是对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批评学派的生吞活剥与机械照搬,其诞生及发展是与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文化事象、文学事态万象更新、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是一种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文学现状的研究路向与理论视野,其发生机制、批评视角、批评范式、文本资源、批评对象以及历史趋赴都有别于格氏文化诗学的总体构造。
二、两种文化诗学形态的分殊与互构
“中国文化诗学”作为我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理论创新形态(an innovative form),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审美诗学(aesthetic poetics)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double integration),显示出学术开拓性、前沿性和综合性。文化诗学批评思想在中国文论界的学术倡扬与批评实践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萌芽和兴起期,并且其最初的历史登场还有着较长时间的酝酿,大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般而言,“文学史是当时文学的复原”,是当时文学形态整体性的复原,或言之,它既是当时“文学创作事实”的复原,也是“文学理论事实”的复原。“中国化”的本土文化诗学批评观之所以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出场,并很快融入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潮流之中,正是当时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现实之需,也是当时社会心理及审美意识现实化的必然结果。这里所谓的“社会心理”是社会知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的总和;而“审美意识(aesthetic consciousness)”作为认识、反映和超越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则属于现代心理(思维)科学的构成要素。
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下前面涉及到的两个隶属于“意识(consciousness)”范畴的概念术语,即诗性精神与诗学理性。在梳理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观”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具体而言,从实体性出发达成“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是“精神”意识范畴,而原子式“集合并列”的伦理观和思维方式所隐喻和预警的是深植于西方哲学传统并在现代性中得到极端发展的“理性”意识层面,是“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叙事思维方式还是“从实体出发”的叙事思维方式,或言之,是“集合并列”的思想观念还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的思想观念,是“理性(rationality)”与“精神(spirit)”两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意识形式)的根本区别。
由此,“精神”不仅与“理性”相区分,而且与“伦理”相通。难怪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如是昭告天下:“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由此学会“伦理思考”便从方法论认知工具跃升到了认识论“人类学意义”层面,直接关涉到“人类种族的赓续不绝”。在中国“伦理”文化传统中,“精神”是一个典型的本土话语,明朝大儒王阳明即曾以“精神”一语来诠释良知:“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而“理性”则是一个舶来品。“精神”与“理性”两种伦理观与思维方式,不仅代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内在于个体生命进化史与人类文明绵延史,构成“伦理”思想观念的两种逻辑与历史可能。映射在文学创作形式及文学批评形态的认识论意识形态层面,它们分别对应着中式诗性精神与西式诗学理性两种“诗论”观念。
具体而微言之,首当其冲凸显在发生机制、批评对象和批评视域层面上,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学派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诗学批评观更加强调立足当代社会现实和当下生活世界,尤其要对如火如荼的文学事象和风生水起的文学事态予以文化叙事和审美阐释,力求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学繁荣有所助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虽然力图与旧历史主义整体切割、恩断义绝,但它们毕竟都对“历史语境”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比方说,该批评学派更喜欢将批评对象圈定在某个历史分期的纷繁芜杂的文学事件上,而将其前后的历史流变割裂。比如,格林布莱特对文艺复兴时期“逸闻轶事”类传记文学的厚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与“元历史(metahistory)”等“元评论”(Meta-commentary)的深度缕析,等等。中国文化诗学则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态土壤”上和独具特色的文化语境下诞生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路向,其“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的现实性品格近乎与生俱来。揭橥“文化诗学”内蕴的人文品性和现实特质,就是为了回归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注和诗性剔抉,即进行激情投入式的社会参与和诗性表达一种现实关怀: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所说:“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
其次,落实在历史趋赴、文本资源和批评范式的层面上,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日渐式微不同,中国文化诗学正处于不断生成、持续发展的成熟阶段。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学派的顶层设计缺陷与批评实践弊端早已被中国文论界所洞悉,不少中国文艺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和反思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在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予以纠偏与完善。单从批评方法来看,格林布莱特在具体文本的阐释实践中提出一种“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的新方法:“办法是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小部分具有共鸣性的文本上。”这里更多关注的是形单影只的“一小部分具有共鸣性的文本”这样的单向度文本,彰显的则是自我个体的“这一个”独特性和“全面发展”丰富性。文学文本的共鸣性与自主性源于“自我身份与自我力量”的发现和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从而引发个体“知识逻辑、情感判断、意志指向”的再理解与重新塑造。这点与弗朗索瓦·于连“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的论断不谋而合。
中国文艺批评家则对其进行解放性反思与意识形态化细部完善,更多聚焦在文本集合体和社会群体性上,并毫不讳言地将其标识为自身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切入点和支撑点。而“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现实化的结果”,加之“社会心理”又是“知、情、意”耦合的三维结构体,因此又可将之概括为“重建文化反思语境与社会心理语境”。直面文艺作品或文艺现实,仿佛川流不息在“杂多”文本之间,各种要素在永不停歇地“流通、转换”中积聚、整合,最终内敛成贯通了文本间性(intertexuality)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两大部类”的互文(intertextuality)聚能环。诚如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在《走向一种主体论的文化诗学》等文章中再三申明的:“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文化诗学的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这些理论构想都助推了中国文化诗学最终形成完备的批评形态与独特的批评范式,仅此一点,西方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便不得望其项背了。
就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思潮的发展脉络而言,中国文化诗学批评学派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凸显了文学存在的社会维度,“人文化成观念”,进而向整体性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全面敞开。它对于文化综合研究和文论的“批评化”趋势的精髓都有所汲取:一方面,文化诗学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文化情怀和现实关怀精神,密切关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象和文化事象,并及时予以理论回应。另一方面,它汲取了文论“批评化”思潮的放弃构建理论体系的诉求,转而走向批评实践。有所得兼必又要有所舍弃、有所区别:文化诗学和文化研究的文本无限扩张不同,它主张以文学文本为核心,在各类文本的互文间性关系中展开批评实践;也与文化诗学理论的“批评化”思潮不同,它不再止步于将自己简单等同于文学批评,它是综合性的跨文本、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立交桥式”理论建构。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化诗学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
总体而言,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主张在历史语境和文化架构中研究文学文本,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互文间性关系中理解、阐释文本,解读文学意指系统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内涵。简言之,在格林布莱特的字典里,“文化诗学”这个偏正结构的重心上行(ascending)到了“文化(政治)”上。对此,童庆炳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
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批评流派就作为一种最新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潮进入了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连带着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海 登·怀 特 的“历 史 诗 学(historical poetics)”、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诗学(political poetics)”等批评理论也随喜得到了中国文论界的认可和追捧。他们所联袂恪守的把文本及其作品放回到历史语境和文化架构中进行社会批判和审美阐释的基本批评准则给处于困境及困惑之中的中国文论及其批评观念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只不过翻译到中国的字典里,“文化诗学”这个偏正结构的重心下移(deseending)到了“诗性(人文品格)”上,更多凸显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品格(esthetic ideology theory)。正如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所言,“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充分发扬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建构之中,更是当务之急。”
三、构塑中国“本土”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和话语形式
鉴于我们对于“文化世界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方式和把握方式仍处在变动不居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诗学作为文学艺术批评学科面对当代世界和文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响与实践应答,也必然是处于不断生成和持续对话之中的。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理论形态和实践策略,中国文化诗学必须主动出击、敞开心扉,去拥抱叠彩纷呈的文化世界和历久弥新的生活世界。它既要反思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经验与文学传统,更要积极面对此时此刻的文化社会现实。
首当其冲的是与当下的文化理论形态和文学意指系统展开及时、双向的平等对话,这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话语保持鲜活生命和现实品格的根本所在。正如布鲁克·托马斯指出的,与提倡从“研究历史”去“介入当下”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有所不同,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更明显的是关注新文学史书写如何能够用来适应当下时代,书写新文学史如何帮助提供新的未来”。
其次是立足、扎根于中国文化群落的丰厚土壤,在与中国古代文化事件以及文论“传统”的深入对话中汲取充足的营养,通过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还原历史语境,挖掘中国的文化“传统(tradition)”,从现当代的角度进行新的阐释和探索理解的新意义,进而与当下鲜活的文化现实进行比照、融通,完成重构历史的新阐释使命。传统之谓“传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历史上发生的、一以贯之的、今天仍然存活并发挥作用的。如果只是历史上发生而当下并不具有现实性,那只是文化遗存。前面提及的“伦理(ethic)”概念是多元价值中的“元价值”,“传统”是多元文化中的“元文化”,它们分别成为具有多元凝聚力和历史绵延力的两大文化元素,构成了“文化解读与价值评判”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轴,具有累积价值共识和塑造文化历史的意识形态意义。正如盛宁先生所强调的,“所谓重构历史,从现当代的角度对现存历史文本中史实的等级次序、史实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新的阐释,而是要引出迄今人们尚不曾这样理解的新的意义。”
最后是文化诗学批评观的多学科或跨学科性的综合研究视野,决定了文化诗学必须要与其他学科、理论展开多重对话与交流,汲取它们的优秀成果,不断累积“理解解读经验与价值评判共识”,从而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套路,更好地对中国文学事象与文化事件展开“一种既能够揭示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特殊性,又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诗学范式”阐释活动。“价值共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关联,在“意识形态”概念的首倡者安东尼·德拉图·特拉西创立的“观念学(ideology)”中就已经是题中应有之义。顾名思义,意识形态实之谓“意识”与“形态”的语义合成,因具象化的阐释语境不同,语义重心或在“社会意识”或在“具体形态”,但其真谛如一,即在对“社会意识”的个别性与多样性承认的前提下,进行“形态化”的努力。其中,具体形态有两个维度:一是自我意识的自觉文化类型,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等;二是个体意识的社会同一性或社会凝聚。
要之,“意识形态(ideology)”的真义是社会意识的同一性。“多”中求“一”,“变”中求“不变”,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蕴涵所在和发展规律。由此,必须将意识形态思维的重心由对“多”的承认转向对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的“一”,即价值共识的追寻。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言:“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学艺术现实,以努力发展出一种既能够揭示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特殊性,又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诗学’范式。”唯有如此,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批评形态才能拥有更加诗意的栖居和走向更加广阔的道路,获得“自我力量展示和自我形象塑造”的理论空间和话语形式。
一言以蔽之,无论中西方文艺,抑或现代、传统文艺,还是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之间有怎样纷繁纠结的杂多关系,展开一种延展在审美视野维度上的文艺对话与交流将是人类文学艺术绵延拓展、永续趋升的有效途径和原生通道。要实现这种平等的对话和有效的互动,以期达至文化“情结”的审美自信、审美自觉,最终抵达“向真向善向美而生”的至高境界,就需要当代文化艺术哲学从一种“独白”的艺术哲学范式走向一种“对话”的艺术哲学范式。现在,我们并不是要强制它凝神谛听来自外面的声音,而是要让“会听的耳朵”听出自己内部也有“接着说的粘连音”和“换着说的杂音异调”,从而产生某种新的“多声部”音响效果。形而上学体系内部总有那么一些尚未驯服、别无依傍的要素颗粒,它们内敛聚合,高蹈扬厉;它们吸纳崇高,吐故纳新,而这恰是中国“本土”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始终保持锋芒和活力的充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