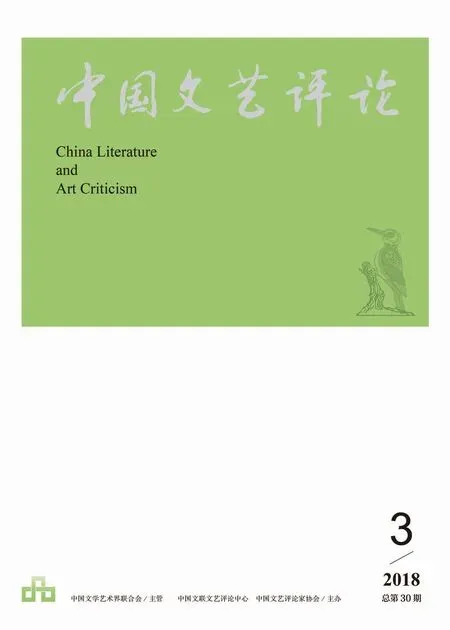本土美术批评古今之变与承继
李昌菊
中国传统艺术中没有“美术”一词,因此也无“美术批评”一说,但大量的画论,构成了美术批评的存在形态。时至今日,现代画家所绘的传统中国画并不少见,传统画论式的美术批评却难觅其踪。评价传统中国画以及其他美术现象的,全然已是一套新的话语方式。这种现代美术批评,既不同于传统画论运用的语言,也有别于其评价标准。其原因在于,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狂飙之势席卷所有文化领域,语言变革推动了白话文的使用,美术革命则掀开了以西画标准审视本土美术的序幕。白话不仅意味语言外观的改变,更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与此同时,对西方画法的推崇,以及西方评价标尺的引入,更从内外不同层面,推动了本土美术批评的现代转换。可以说,今天的美术批评,无论思维模式还是评价标准,均不同于过往传统,它及时顺应了中国文化主体的现代转型要求,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自身,建立起新的形态样式。
20世纪的评论家们依据时代之变,融汇中西、努力创建了现代美术批评,其对不同时期美术创作的推动与审断,充分展现切实的效力。不过,在距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是否需要回顾本土美术批评的前世今生,端详其形质,思考个中变化与遗失?诚然,现代美术批评已取得许多新成就,其话语面目的焕新、知识体量的扩容、方式手法的多样、涉猎对象的广阔,均令人振奋,但传统画论诗性美的失却、传统美术评价标准的退守,也同样引人深思。今天,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尊重的时代氛围里,传统文论(包括画论)诗性的语言特征以及价值标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还能否成为本土美术批评建设的重要资源?笔者不揣浅陋,试以论之。
文言到白话
一个极为直观的印象,今日的美术批评在语言表达上与传统画论迥然不同。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化缘于新文化运动对白话的提倡,使白话跃升为书面用语进入公共言说空间,逐步确立起其话语地位。也即,在开启新的批评文体实践方面,新文化运动是重要推动力与转折点,伴随这股文化革新的潮流,本土以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语言系统开始建立,现代美术批评与传统画论从此分野,前者不断汇入新质,后者逐渐成为具有传统色彩的知识体。
新文化运动后,新的美术批评文体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如“近二三十年以来,欧洲画坛上,更有一种新的进展,他们把以前自然主义的要素都归结在表现感情的状态上,力倡尊重自我,排斥物体的写实与严正。最近表现派绘画,就是这个主张。”且不论其谈及内容,仅表述语言便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文言文,虽然此时徐悲鸿仍坚持使用传统画论式语言,“云林《山水》在其中者,均是精品,古木竹石尤不真,山水幅略有意耳”。又如“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败,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或文白相间为一大时代文化景观。该时期不少眷念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们,仍然运用文言进行美术评价,不过,最终文言渐行渐远,白话文成为现代美术批评的语言主体。
言简意丰的文言终被清晰顺畅的白话取而代之,于美术批评,无疑是接近了读者大众,其播散美育、开启民智之效固然可庆贺,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言说方式转变的,不仅是言辞的外观,而更是内在的思维方式的调整,一种异于本土传统的西方思维模式开始进入国人写作的结构与序列。
传统画论以精练的评点、直接的观点见长,虽然精彩的描述、类比、象征手法也是特色。如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对画作《七贤》的评价:“唯嵇生一像颇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这种精练、隽永的评语,在传统画论中随处可见,又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顾骏之的评价:“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仍是简洁凝练的评点,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通常直接出现在篇章中,却无推理和论证过程。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在描述了壁画情状之后,径直指出绘画的功能。“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之后的曹植在《画赞序》中几乎直接沿用该观点:“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有趣的是,两人均未对该结论或观点进行分析或论证,仿佛一切不证自明,这是今天论者难以想象的。
以上不经推理,直奔结论的情形与西方迥然有别,以西方最早的美术史写作者乔治·瓦萨里对达·芬奇的评价为例,“在大自然的进程中,常常可以看到,上苍降非凡的才能于人们。有时候,以超自然的方式,极度地集美丽、优雅和才干于一人,这样的人的注意力不论转向何事何物,一切行动都是那么的超凡越圣,首屈一指,清楚地表明那是上帝之赐与,而非人类技艺所造就。人类在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身上看到这一点:他,身材健美,任何褒词绝无溢美之嫌,一举一动雍容大方,天资颖异,成年后,任何难题到他手里迎刃而解,全不费功夫。”这一段文字表明了作者对达·芬奇是一个天才的激赏。若在中国传统画论中加以表述,作者一般直言某人是天才,但瓦萨里却在富于文采的表述中展开巧妙演绎推理,举要其内在逻辑,大致为:天才是拥有什么特质的人,达·芬奇身上有着天才的举止与才干,显然达·芬奇是天才。可见,这与中国传统直接说出个体观点极为不同,西方重视逻辑思维,讲求推理顺序,一般采用演绎、归纳与分析综合形成理性认识,将观点建立在对感性材料由表及里、由彼及此的严密论证上。
事实上,自上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东、西方文章在论述和结构方面的不同已为知识分子所觉察,在崇尚科学的时风影响下,西方的逻辑思维作为一种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得到学人的认同,选择其思维与行文方式,便在情理之中。此时期不少美术批评家已开始借鉴和运用西方文论方法和批评术语,在行文中重视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注重通过分析思辨形成观点,这自然与传统画论直呈感性经验判断的思维模式拉开巨大差别。
以此时期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为例,其开篇“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首对“文人画”的说明,体现了传统画论所缺乏的概念界定意识。倪贻德的《艺术之都会化》(1935年)是较早谈艺术如何表现都市的文章,文中作者不仅梳理了西方艺术表现都市的历史,还分析了表现都市的原因(环境变迁、个人主义),指出都市给予艺术家的创作启示(鲜明色彩与运动节奏),以及其他负面因素。该文结合西方美术史和中国都市现实进行分析,材料新颖,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显现出重知性分析、重理性认识的特色,展现了美术批评的现代特色与水准,该时期类似评论并不少见,它们意味着新的美术批评文体在本土的逐步形成。而后累年的延续与发展,更是助长和完善着这种源自西方的文体形式与逻辑思维模式,如此一来,现代美术批评与重直观经验、重个体感悟的传统画论思维方式渐行渐远。
可见,从文言到白话,全新的篇章、结构、段落、句式表达出现在世人眼中,不止于此,文体只是其表,其间悄然发生的思维方式置换才是内在原因,这也正是古典形态的传统画论与现代形态美术批评的本质差异所在。
西法的采用
传统画论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影响,在不同时期各有表现或侧重。从春秋时的“使民知神奸”到南齐谢赫的“明劝戒,著升沉”,再到唐代张彦远的“成教化,助人伦”,重视政教宣传、道德伦理的儒家批评观昭然可见。魏晋玄学开启另一理路,对天地大道的感悟与追求,使南朝宗炳感叹到:“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唐王维认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宋更进一步,逸格被提到首位,外向伦理事功转向了内在怡情悦性,文人趣味渐据上风。北宋米芾推崇“董源平淡天真多……格高无与比也”,元倪瓒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清戴熙则言:“密易疏难,沉著易,空灵难。”道释精神与美学趣味尽在其中,对艺术本体的自由探求也清晰可见。
经儒、释、道审美理想延展出的批评标准与术语是传统画论的特色,前者如谢赫的“六法论”,其中以“气韵生动”领衔六法,为历代重要品评鉴赏标准,到清王翚依然认为“画家六法,以气韵生动为要”。后者如“逸”“神”“妙”“能”等品次格法,兼顾两者是古人读画依循的必要次第。“凡阅诸画,先看风势气韵,次究格法高低者,为前贤家法规矩用度也。”至于技法表现层面,有骨法、赋色、笔法、墨气、位置、写意等,艺术趣味则有精谨、萧条、淡泊、高古、士气、境界、意趣、沉雄、荒寒、明净、空灵等。
传统绘画批评标准一经提出,便千古不移。与之相反,现代美术批评则注意时时更新。自康有为用“遍览百国”后的西方眼光审视中国传统绘画,认为近世之画衰败极也,将传统绘画置于西方标准的要求下,援引西方观点和理论的步履即已开始。随着西画东渐,西方美术批评术语和方法更是源源不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术批评的字里行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再现、表现、写实、抽象、象征、装饰、变形、夸张、素描、速写、笔触、空间、轮廓等词汇已很常见,如汪亚尘写于1920年的《近代的绘画》中,介绍了古典派、学院派、印象派、未来派、立体派、调子、构图、光线、形状、色彩、立体、结构等西方美术专业术语,可谓早矣。
与传统画论的承袭性、稳定性不同,现代美术批评对西方艺术新概念、新方法的接纳姿态是开放的、动态的(大部分时候)。此间,一方面,围绕西洋画展开大量翻译、介绍,将新词汇、新术语快速推送到公众视野,另一方面,围绕美术创作与画展展开讨论、评价,对新术语进行了现实演练。之后,新词长驱直入更成蔓延之势,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直觉、自我、个性、荒诞、全球化、身体、权力、批判、文本、女性主义、公共性、文化记忆、后殖民、后现代等话语流,它们从西方哲学、美学乃至文化学、政治学各个学科领域向本土美术批评高频度地汇聚和扩散。与此同时,对西方现代美术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也令人目不暇接,如贡布里希的视觉艺术心理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化身份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均成为本土美术批评中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可以说,在对西方艺术学理的借鉴中,当代美术批评走向了众语喧哗的多元情境。
美术批评术语、方法的引进,促成了批评学科的体系化,一些相关的教材与著作在新世纪相继问世,如《跨文化美术批评》《美术批评方法论》《艺术批评学》等,这些著述均注重对西方现当代美术批评方法的推介,广泛涉猎美术批评的定义、思维、标准、方法、写作,对美术批评学科发挥了积极建设作用。现代美术批评发展至此,似足以令人宽慰,其流派纷呈、新意迭出昭示了话语的空前活跃,已建立起对艺术创作(如精神分析法)、艺术语言(如形式研究法)、读者接受(如接受美学)、社会文化(如女权主义)等各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对西方艺术理论与方法的吸纳,拓展了本土的文化视野,打破了之前传统画论相对单一封闭的思维格局与模式,使现代美术批评另起炉灶并初具规模。
的确,西方艺术批评理路给本土美术批评提供了多样手段和工具,在作品的读解角度、阐释空间乃至剖析深度方面,较传统画论均有极大拓展。除此,在今日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它还快速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基本保持着与20世纪这个“批评的时代”的同步,较好促成本土美术批评的现代转化。但同时,我们也面对着一个尴尬现实,这便是从术语到方法以及学科体系,几乎完全建构在西方话语的基础上,它与传统画论极为隔膜,缺乏对之的继承发展。如此一来,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评论家们正运用西方话语打造的批评标准看待本土艺术。虽然,借用西方文化成果来发展本土美术批评不失为重要思路与方法,但在接纳与借鉴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参鉴传统画论,以建立更为独立的价值标准与批评原则?
秉承这一思考,我们注意到,面对西方美术批评方法时,本土并非不加选择地被动接纳,遗憾的是,人们忽略了与传统画论的对接,更多时候只是据现实需要为我所用,如本土运用最多的社会学批评、形式批评、文化批评,大致对应着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80年代现代艺术以及之后的后现代艺术等,但它们均未建立在对本土传统画论的继承创造上。即便是自50年代以来,对本土影响最大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知人论世不乏心气相投,“这种社会历史研究法事实上渗透了中国古代重实行、重伦理、重功利的哲学传统,是古代的社会历史研究法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以新的面貌装载在得自西法的方法论框架中,更严密,更完整”。显然,遥接了儒家文化理想的社会历史研究法,凭借的也仍是西方理论框架与方法。事实上,在现代美术批评的话语建构中,西方影响无处不在,传统画论却被冷落一旁,导致西方的价值标准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这一现象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诗性回望
正如前文所述,从文言到白话,本土现代美术批评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画论的语言表达与方法。就语言方面,如果说传统画论偏向感性、诗意、直观、模糊,那么西方则注重理性、冷静、客观、清晰;就方法而言,“中国美术批评的方法是品评,是点悟,是心领神会;而西方美术批评的方法是分析、是逻辑、是层层解剖”。读西方美术批评,我们不禁感慨其归纳演绎的逻辑力量,求真探理的科学态度,而浏览传统画论,则会赞许其行文之简练优美,态度之从容洒脱。尤其后者的语言,以诗性之美成为独具的特色。如谢赫评卫协:“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语调铿锵、朗朗上口,唐代更直接以诗论画,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均有不少品画诗作存世,如该时期诗人元稹曾形容“张璪画古松,往往得神骨。翠帚扫春风,枯龙戛寒月”。到清唐岱谈读书对于绘画之重要,言辞间的诗意依然不减,“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哉?”
中国传统画论的这种诗性话语方式,往往借用拟喻之法,有形象的直观感,如《二十四画品》,将“明净”描述为:“虚亭枕流,荷花当秋。紫葩灼灼,碧潭悠悠。美人明装,载桡兰舟。目送心艳,神留于幽。净与花竞,明争水浮。施朱傅粉,徒招众羞。”作者借花与美人形象比喻画作的境界,继承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的语言风格和美学意境。传统画论语言不仅有形象、音韵之美,更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趣味,如恽格评倪瓒:“云林画天真淡简,一木一石,自有千岩万壑之趣。”至于如何有千岩万壑之趣,文中并未道尽,只是点到为止,需要读者凭借木石意象去体悟、去意会了,这种模糊、朦胧、含蓄的语言表达,较之一览无遗的陈述,更有一种回味不尽的韵味感。也或,正是融汇了儒家的“比兴”文学手法,道家的“得意忘言”情状,以及禅宗的“妙悟”之理,传统画论才拥有了如此情思蕴藉的诗化意味。
传统画论重比拟、感悟、意会的诗性表述,与西方美术批评重抽象、学理、分析的科学表达形成对比。西方从古希腊即开始重逻辑思维,重对世界的理性探究,力求知识的清晰明白。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更为盛行,并成为衡量、判断一切的尺度,美术批评自然也秉持这一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之相对,本土传统画论也论法明理,但以美的诗性的方式抵达。不过,随着20世纪西学的东进,科学主义被推崇到各文化领域,本土美术批评步入西方思维方式的本土操作与实践,求美开始向求真移动。今日的美术批评,“‘始、叙、证、辩、结’的程序,归纳演绎、逻辑推理丰富验证的手法也很使人感到其科学性、条理性和说服力”,虽然批评对象不同,但是语言特性却相当接近,这便是客观、明晰、严谨,总体文风偏向理性。
行走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与传统画论的诗性言说日渐疏远。至此,我们不禁疑惑,难道美术批评只能以学理性方式表达吗?理性言说是否批评文体的唯一选择?“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关于此,作家周作人认为,“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朱光潜则说,“批评本身是另一个作品”,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作品的最有意义的批评往往不是一篇说理的论文,而是题材相仿佛的另一个作品。”可见这些作家、美学家均视批评为一种艺术创造,而不限于或满足于说理分析,展现了对批评文体的自觉意识。
若如此,传统文论的文学文体是否可成为现代批评的重要参照?其感性的诗化语言,或可为文艺批评提供重要启示。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批评家、学者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子恺、傅雷便开始了尝试,如丰子恺对印象派的评价:“注重光色的结果,对于自然愈加亲切,自然的描写愈加深刻,同时对于画的内容意义渐渐轻忽起来,故一堆稻草、一片水,皆可为杰作的题材,这是绘画近于视觉艺术的纯粹绘画的进步,是绘画的独立革命的先声。”行文既鲜活有趣又揭示了本质。如傅雷对拉斐尔名作《西斯廷圣母》的描述:“这是天国的后,可也是安慰人间的神。她的忧郁是哀念人间的悲苦。两个依凭着的天使更令这幕情景富有远离尘世的气息。”语言生动且并未影响见解的抒发,“由了光暗,伦勃朗使他的画幅浴着神秘的气氛,把它立刻远离尘世,带往艺术的境域,使它更伟大,更崇高,更超自然”。同时期宗白华关于中西绘画差异比较的一系列文章,也处处洋溢着诗性美感。如谈中国画“其气韵生动为幽淡的、微妙的、静寂的、洒落的,没有彩色的喧哗炫耀,而富于心灵的幽深淡远”。又如,“西洋油画的描绘不惟幻出立体,且有明暗闪耀烘托无限情韵,可称‘色彩的诗’。”其文章随便拈取皆成妙句,诗性表达被作者推到一个高度。
此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哲学、美学角度读解本土传统美术的李泽厚、朱良志等学者也以独特的诗性写作语言获得学界认可和大众喜爱。
如果说上述学人多在美术史和艺术美学行文中运用诗意语言,今日的美术批评家们,对文辞修饰也不乏重视,但更多表现为行文的平实,语言的准确,观点的精辟。其实,在一个世纪的现代美术批评实践中,我们已积累了大量理性评述经验,若在此基础上对文体再多一些关切,多留心文字的质感、节奏、韵味,多注意援引传统画论的诗性,以拓展语言的另一美学向度,美术批评语言形象一定会为之改观,读者的阅读审美体验也会更好。虽无需以此要求所有批评,但若文章既不失学理分析的深度,又在字里行间流溢传统画论的诗性气质,岂不美哉。
守护与拓新
自20世纪以来,随着新的美术批评体系逐渐建构起来,传统画论的话语方式慢慢淡出人们视野。那么,传统画论的价值标准是否依然行之有效?是如常还是出现变局?众所周知,传统画论涉及绘画的功能、标准、格法、境界、画法、鉴藏以及继承,自成一套价值体系,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画理、画法讨论不断走向深化、细化,评判标准却相对恒定。但自百年前主张革新的文化人物以西方眼光打量后,传统画论的评判价值标准不仅失去主导位置,其命运更是急转直下。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陆续引进,使传统美术价值观一再被挤压、责难、质疑乃至否定,与此同时,维护传统绘画价值体系的学人们,则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抵抗、守护、肯定和学术整理。
在这场世纪之争中,传统画论的评价标准与价值体系倍受冲击,尤其核心部分——文人画与笔墨价值体系。自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1917年)中推崇唐宋之法,贬斥士大夫作画,便开了问责文人画的先河,他追源中国画学之衰败,“以归罪于元四家也”。元代是文人画大发展时期,元四家为其中代表,其批判意图不言自明。美术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不仅讨伐元明清文人画,还开出了改良中国画的方子,“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这些深受西学影响的革新派,往往以西方尺度检视中国画,对文人画以禅入画、抒写逸气、崇尚写意的作法无不排斥。而后,徐悲鸿大力践行写实主义,更提出“新七法”,直接抹去气韵生动,其对传统批评标准的个人改写,显现与康、陈以西方写实主义取代传统绘画价值观的同一思路。
与之相对,珍视传统的学人们则对文人画极尽卫护,以陈师曾为最,其《文人画之价值》(1921年)在认同传统画论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如对六法的遵从),对文人画之优越处大加推崇,“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沿着陈师曾的先声,胡佩衡、郑午昌、潘天寿、丰子恺、俞建华或对传统品评标准(如气韵、意境)加以阐释,或对表现语言(笔墨)深入研究,或对中西画法加以比较,这些坚守传统的学人,一方面有强烈文化危机意识,意识到外界对国画“加以排斥,则直是根本推翻本国固有之文化”,并强调“国画已受世界文化侵略之压迫,宜速自觉而奋起”,一方面对本土传统有高度认同感,认为“气韵一点,为中国画精神所寄,万万不可加以革命”,指出“且知特具和平淡泊的精神之我国画,实占世界艺术之最上层”。总之,通过大量著文与著述,学人们运用西方逻辑思维对传统画论加以理论研究,守护、继承、阐发了其价值体系,深化了对之的认知。
作为重要评价项,笔墨也是论争焦点。传统画论对笔墨极为重视,“骨法用笔”位居谢赫“六法论”第二,荆浩提出,“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此后米芾、黄公望、董其昌、蓝瑛、王时敏、戴熙等历代名家无不论及笔墨与气韵、方法、写意和性情的关系,龚贤说:“画以气韵为上,笔墨次之……笔墨相得则气韵生。”王翚认为气韵“全在用笔用墨时夺取造化生气”。唐岱指出:“气韵由笔墨而生。”可见气韵与笔墨休戚相关,王学浩道出“作画第一论笔墨”。方家均从气韵、笔墨对画进行品评和鉴赏。
然而,笔墨却多次遭遇声讨与否决。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表现现实的创作要求,国画纳入了改造进程,文人画和笔墨价值即被批判和清理。其时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气韵、笔墨等形式主义论文、题词等文人玩艺,都不再是画家追求的方向了”。“单纯以笔墨为批判艺术价值的至上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否定笔墨的论调,一些画家进行了反驳,坚持“在国画创作中‘笔墨’是重要问题”。自此,围绕笔墨争议不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横空出世,继而引发空前热议,该文将中国画笔墨视为“僵硬的抽象形式”,传统画论则为“僵化的审美标准”,认为“评价一个画家在美术史上的位置,主要是看他在绘画形式上是否有所突破,在绘画观念上是否有所开拓来决定的”。可见,与50年代以现实主义衡定传统国画价值不同,作者欲以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价值取代之。90年代,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挑战中国画价值判断,万青力则以《无笔无墨等于零》作了回应,之后张仃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指出“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笔墨等于零》在上世纪末再次引发巨大争议,多位画家、理论家先后参与讨论。
来来回回的激烈论争,见证了传统美术批评在20世纪饱受争议的状况,其价值标准(尤其核心价值)屡次被推至遗弃与守护的两极,滑动于打击与自卫之间。新进的西方批评标准不断越界对其加以估量,并试图取而代之。何至如此?笔者认为,一是特定的时代要求,传统文人画超然物外的价值取向与救亡、启蒙、建设现实格格不入,从出世到入世,将蹈虚导向务实,实在情理之中(如传统品评标准中儒家教化观并未受到攻击),事实上,文人画达到的超逸境界对人格亦有感化之功,所以守护该精神价值同样重要;二是中西艺术价值观的差异,一主科学实用,一主非功利(如文人画),两者发生冲突势在必然,不过,一旦涉及传统画论核心价值部分,本土学人却坚决捍卫,不接受被颠覆;三是中国画革新的强烈要求,创新一方意欲摆脱传统笔墨评价体系或突破边界,面对语言本质的消解,维护传统价值的方阵却明确表示了拒绝。可见,当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两两相遇发生纠葛时,传统价值观(包括艺术)遭受撞击与撕裂在所难免,所幸守护与继承的力量始终伴随,彰显了坚定的民族文化意志与情怀。
那么,传统画论的价值标准还可行吗?除了守护,有无拓展?其当下价值意义何在?事实上,虽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在接纳西方评价标准的同时,本土学人也守护着传统美术批评标准,使之免于剧烈破坏或瓦解。不过,随着现代美术批评的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艺术批评占据了更多言说对象和空间,传统美术批评的话语影响力明显削弱,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令人欣慰的是,传统的一些价值标准依然奉行在中国画创作与批评领域,虽然不完全(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观念混行其中),但毕竟未丧失话语活力。除此,在其他创作领域如油画,传统批评价值标准也拓展出一定言说空间,从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特色”到50年代“中国气派”再到80年代的“中国油画”,不仅意境、传神引入油画表现,意象、写意等也被用以评价当代油画特征,说明传统美术批评标准并非没有延展性。另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传统美术批评从被质疑起便开始得到保护、整理、研究,迄今已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对象,其价值不断得到阐发与认定。
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当下创作形态多样,批评话语多元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吸收传统美术批评价值或标准,将其转换为当代中国美术批评体系的重要部分?对此,已有学者在对其儒家传统、主要范畴、审美标准、批评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呼吁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也有批评家指出,应该将20世纪本土运用广泛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批评与中国传统画论进行整合。的确,在现有的美术批评基础上,如何将“传神论”“六法论”“逸、神、妙、能”等品评原则和标准加以现代转换,使之进入今日美术创作的阐释空间,是关乎如何传承与创新,并在传统基础上建立本土现代美术批评价值体系的现实问题,它尚需更多学人的思考与智识逐步向之汇集。
结语
浑然不觉中,我们已经在运用新的言说方式和方法评价美术作品,对于其中的西方质地习以为常,虽然,传统画论的语言已被替换,但其价值体系依然存留。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传统画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并行的繁杂格局,它们应对着空前丰富的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装置乃至综合材料、新媒体艺术的创作景观,在此起彼落的批评话语潮中,共同构成现代美术批评的多声部。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美术批评已经具备一定方法与规模,但如何更进一步,塑造出更好的文体语言形象,并逐渐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本土美术批评体系,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传统画论的诗性美感与价值标准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们不应忽略的重要文化资源,必可给予现代美术批评重要启示与参照。尤其在当下,中国美术已有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除了艺术创作的开放、包容、多样,打造本土特色的美术话语同样十分重要,在这特殊的时机,传统必将再次释放独特而引人注目的文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