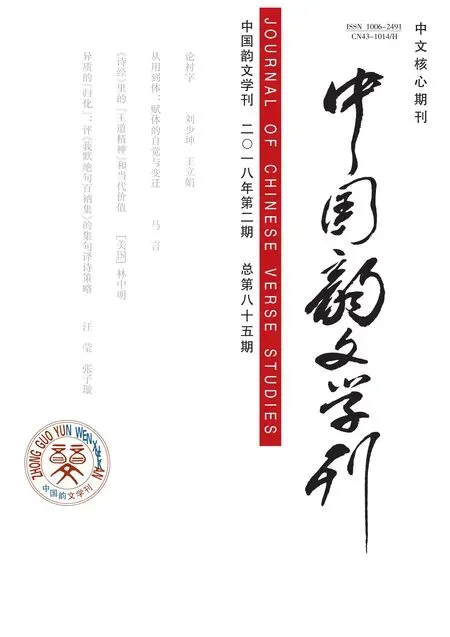清初词中“佳人论”
朱秋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词至清初,题材空前广泛,言志、咏物、怀古、怀友、祝寿等等题材在词中的比例较宋词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艳情与词中女子形象在清初也发生了新变。张宏生《艳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内涵》《〈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日常化与女性词境的拓展——从高景芳说到清代女性词的空间》三文指出清初艳词出现感情真挚、风格醇雅之作,出现了艳情之中融入家国之感的作品,闺阁女子的日常生活题材也进入了词学创作。这些新变都是词史上质的飞跃。在此启发之下,本文联系清初词作及其评点,考察词作中的女性形象。清初词人所写的恋情大量依附于家庭伦理内的寄内与闺词,这与当时江南士族“才子佳人式”家庭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词中女性形象体现了清初追求女子“德才色”与“真情”的佳人论。
一 词中闺阁佳人与清初女性观
唐宋词生成于歌筵舞席,以资欢娱,词中的女子主要是美貌的歌妓舞女(包括青楼与家伎、营伎),词人与她们的爱恋是长盛不衰的主题。词中的恋情多为实有,且发生于词人与歌妓之间,如此柳永、秦观与歌妓,晏几道与萍、莲、红、云,姜夔与小红、合肥姐妹,等等。虽然唐宋词不乏少女思妇的形象,也有李清照、朱淑贞等女词人对闺阁女性的塑造,但与词中歌妓形象相比则数量悬殊。词发展至清初,早已完全脱离花间尊前的生成环境,无需再传唱于檀口皓齿,词人与歌妓舞女的爱恋在词中也几近消失。清词所刻画的女子形象悄然移位于闺秀,言情之作大量出现于闺情与寄内的题材中,这些闺秀形象寄寓着词人德才色兼备的“佳人”观。
歌妓身份卑微,且以色艺事人,词中刻画歌妓易流于艳冶轻薄,对此,清初词人提出批评,自觉地将笔墨转向闺阁女子。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论:“唐人《菩萨蛮》云:‘牡丹滴露真珠颗。佳人折向檐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只道花枝好。一面发娇嗔。碎挼花打人。’此词脍炙人口者素矣,予谓此戏场花面之态,非绣阁丽人之容。从来尤物美不自知之,亦不肯自形于口,未有直夸其美,而谓我胜于花者。况挼碎花枝是何等不韵之事,挼花打人,是何等暴虐之行,幽闲之意何居,温柔二字安在?李后主《一斛珠》之结句云:‘绣床斜倚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此词亦为人所竞赏。予曰:‘此娼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李渔认为这两首词中女子情态似“戏场花面态”“娼妇倚门腔”,失却了“绣阁丽人”的“幽闲”与“温柔”,其实词中佳人即为歌女或青楼身份的女子,词中所写为本真情状,并无需责其不具备闺秀气质。李渔的批评虽然失当,但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清词将着力塑造闺阁女子。李渔对词中闺秀形象提出“幽闲”与“温柔”,基本可纳入对女子德性的要求。李渔《耐歌词》所写女子主要是闺阁,有虚构的闺阁代言,有写其妻妾的闺情、恋情,有与二女淑慧、淑昭的唱和,其词中甚至写女子妨窥,“为闺人写出一段贞节苦心”,仅有几首写歌儿舞女。基本上,李渔的词与词论涉及到女子的德、才、色诸方面,这是清初词坛崭新的“佳人论”,与当时“才子佳人”的文人理想及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末清初出现批判传统女性观的思潮,传统“三从四德”的观念发生了新变,纳入了新的内涵,形成“德、才、色”与“真情”兼备的新女性观,并逐渐成为时人流行的观点。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与戏曲中,佳人都是德才色兼备的美的化身,《玉娇梨》男主人公详述了他心中的理想“佳人”,代表了当时士子的婚恋向往:“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也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当然,“德”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刺绣织纺,女工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守芬含美,贞静自持,行坐不离绣床,遇春曾无怨慕,女德也;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喁喁凉凉,则失风流之韵。”显然,女德仍然是根本。“德、才、色”以及真情,是才子佳人小说、传奇中“佳人”的模式。
这种佳人论出现于清初的词坛,更体现出佳人论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明末清初涌现出大量才子佳人式的婚恋生活,比如沈宜修与叶绍袁,商景兰与祁彪佳,谈则与吴人,程琼与吴震生。这样的家庭生活也出现在普通的士绅之家,词集中极为常见,比如董元恺“家有田园,室多图史,佳妇比肩,并坐鼓瑟。乃至邓尉探梅,段桥踏雪,浮家洞庭之泽,消夏芙蓉之湾,弹琴而看文君,买钗以贻徐淑,李居士书藏金石,管夫人画擅梅花,人生乐事,莫过于此。”又如阎牛叟与其妻情深意笃,据阎牛叟记,其德,“妻屡请纳妾,予不应”;其才,“妻善弈,花下与诸女剧,必招予,予笑谢。于琴不由师授,以意成谱,巧合自然”,“甲申予客金陵,妻独携子女避地吴越,常手书促予归”。甚至也有青年男女因文才而私相倾慕,互定终身的真实恋情,俞公谷《念奴娇》(评残词稿)序言记载沈遹声与杨玉倩情事:“其东家杨倩玉者,名琇,与沈郎结今生缘,私为倾许,且出其诗词杂沈集中,余悉能辨其香慧。”这些女子的出身都很普通,她们均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加之自身的天分,表现出优异的才能。
同时,明末清初涌现出大量的女性作家,闺阁诗集、词集层出不穷,作者有大家闺秀也有贫家女子。富贵之家可以家人传授或为女子延请塾师,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闺塾师的职业女子,寒儒之家的女子,通常是由其父兄传授文学,如李渔的两位女儿、徐石麒的女儿。普通贫家女子也可以有机缘获得学文识字的机会。历来农家女词人贺双卿是真实存在还是文人之虚构,一直处于讨论之中,然,如此女子并不少见,如明清之际邹枢记载其外祖母侍女如意,如意自称:“我南城织户陆氏女,七岁鬻于顾氏家。主怜我聪颖,命我入馆伴读。主母延女师训诸姑,师姓沈,嘉兴秀水人,工诗词,尽心教我,以故诗词颇晓。”这些女词人在词中刻画了现实中的闺阁佳人。
在闺秀文化趋向繁荣的同时,青楼文化开始了衰落。明末是青楼文化最为耀眼的时期,所谓“名妓”,不仅评以美貌,更重在才艺,她们与当时名流诗词唱和,文酒风流,甚至参与社集,在明末的混乱局势中,赋予了政治性色彩。《板桥杂记》即记录了秦淮一地名妓凡三十五人,分为“雅游”“丽品”“轶事”,各擅才艺,突出者如柳如是、顾湄、董小宛、马湘兰等,她们的文学、绘画、书法等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国变之后,江南地区的青楼业一度萧条,余怀《板桥杂记》即是面对秦淮残山剩水,人去楼空的凄凉景状,缅怀往日的繁华梦,悼念过往的王朝。清初词人多有悲悼金陵旧院荒凉败落的作品,如金烺《爪茉莉·过南院马湘兰遗址》云:“青溪佳丽,曾记得、依稀者。只可怜、匣粉炉香销谢。行乐地,菜圃也。”毛奇龄同此感慨,评曰:“南院旧址,不胜蔓草荒烟之感。”战乱之后续以大狱,大量的士族缙绅家毁人亡,赖以生存的青楼业随之而消歇。雍正以后,青楼业更在政策中明令禁止,虽然青楼实际上存在,但政策多少会产生影响,青楼已缺少明末的条件培养出具备才艺的名妓。乾隆时期,青楼恢复繁盛,但青楼女子已大多胸无点墨,不解风雅。
长久以来男性于青楼中追寻情感与艺术的共鸣,心灵的相契,词中的女子大多为倡优歌妓,作为美貌、才华与真情的化身,寄托着词人美好的情愫或慰藉仕途生涯中的失落。当“佳人”式的妻妾可以从现实中寻觅,而青楼的文化色彩逐渐消退,闺秀必然会以理想的女性形象取代青楼成为词中的女主角。
二 德才色兼备的词中佳人
清初词中佳人德才色兼备,女德之中,贞孝、女工是词人描写的重点,并受到词人与评论者的热烈歌颂。一方面是由于词在尊体过程中,原本属于诗文的题材大量进入了词的创作,另一方面是词体脱离音乐后女子身份转变的结果。大量贞女、孝女的形象出现于词中,如佟世临、程大戴、傅世垚梁园唱和,以《哨遍》调歌咏孝女,李根茂评云:“孝女节烈处和盘托出,可与皇甫谧庞娥传并垂不朽。”“曲曲折折,淋漓满纸,为孝女重开生面,真顾虎头传神之笔。”陈维崧则每于贞孝节义处以史笔为词,意在立传,比如他的《满庭芳·吴门管烈妇夫亡殉节,词以纪事》、《满庭芳》(庚氏苟娘)、《大丑·题毗陵海烈妇祠》、《河渎神·题秦邮露筋祠》、《麦秀两岐·为周贞女题词》,等等。评者对这些节烈女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倜诡离奇,洞心駴目,昌黎《南海庙碑》、《湘夫人祠记》,不足多也……可令烈妇吐气。”甚至认为她们的德行胜过了男子,“每念贞孝女之贤似过于男子,读此知人有同情,哪能不湿春衫也?”清初盛行以词祝寿悼亡,其中很多词是为自己与友人的母亲、夫人所作,这些女性更被塑造成妇德的楷模。曹贞吉追悼尤侗夫人的《小诺皋》词即“可作贤媛小传”。与此同时,代表了女子社会职责的女工得到词人的关注,如王士禛、邹祗谟、陈维崧、彭孙遹、董以宁诸人围绕着余氏女子刺绣图唱和歌咏,词作达十九首之多。女工在明末清初已不再是单纯的供给家庭穿戴,它发展为一种行业经济,尤其是刺绣,其精美者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艺术品。李渔曾激烈地反对一些女子专注文才而忽略了女工:“然尽有专攻男技,不屑女工,鄙织纫为贱役,视针线如仇雠,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倩老妪贫女捉刀人者。”词中歌咏女子刺绣,兼具了歌颂女子才能与妇德的双重意义。
相比女德,词人更多地关注于闺秀的才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之间、女性与家族内部男性之间的词学唱和,在清初并不鲜见,女词人的数量之多更远远超越了两宋。比如沈时栋与“一子二女皆工词藻,暇辄分题唱和,子女有好句则回环歌咏以为乐。子即成厦,女即参荇、纤阿也”。《倚云楼词选》则是江兰为主唱,其夫张叔珽、妾徐如蕙和词,结集而成。集中张叔珽、女瑞英及另一妾芳丛,共同参与了评点。女性大量参与词的创作对词中女性形象产生直接的影响,加之社会对女子才华的肯定,女子的“才”“艺”在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晚明以来,思想界肯定女子才能,主张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李贽在其《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一书中曾云:“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清初词对女性才华的揄扬提醒我们,这一异端思想逐渐被文士接纳,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
这些词中才女大部分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女性,来自词人、亲友、邻里的妻(妾)女、姊妹,词人对女子的才华都持赞赏的态度。难得的是,在男性词人笔下,出现了主动追求文才的女性形象。金烺《多丽·春闺倦绣,邀邻女品茶》描写了两位名士一般的女子,她们刺绣闲暇品茗、赋茗,如同士子读书之余的文化消闲。文化修养增添了她们的女性魅力,宗鹤问评云:“随意绘写,曲尽香闺情性。末结更思出云表。又云‘绒舌唾红香’五字,何等香艳。”徐斐成则云:“奇文雅称韵题,然一种娇痴,潇洒风流。跌宕之情,吾不知雪岫如何着想,写得活灵活现,噫,技固神矣。”“潇洒风流”惯常用于评说魏晋名士,“活灵活现”则说明现实中有这样的女子,金烺以传神之笔真实又灵动地再现了这一形象。又如董以宁《鹊桥仙·贺华子瞻花烛》是为友人新婚而作,新人是一位女才子:“呼郎新字,怪郎新字,抄袭眉山因怎。鸳鸯社里面分题,才信道才名相称。”女性对自身的才华充满自信,这样的自信使她们转而对男性提出“才”的要求,董以宁的词或出于对友人的调侃,但无意间透露出当时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对此,男性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女性拥有一定才华,两者能够在艺术情感上共鸣,另一方面女子才华的逾越,削弱了男性的优越感,士子英雄失路式的人生悲伤便无法在原本代表柔弱的女性那里能到宽慰。王士禛评该词云:“此新妇殊可畏。”“可畏”或只是表达一种称赞,但若这位新人的才华果真超越新郎,对于当时男性而言便是真正的“殊可畏”。
佳人的容貌、情态依然是词作的重点,不过清初词作中“佳人”为士绅之家的闺秀形象,较宋词贵族妇女的范围更为宽泛。对佳人容貌、情态的描写以温丽闲雅为美。比如清初马振飞对闺人的描写极为友人称道,其词《蝶恋花·斗草》,评者谓:“与配绣君唱和妍雅,宜其曲悉闺襜如此。”词中的女子应是以其妻为原型:“拾翠寻芳穿野道。幽树深丛,处处啼黄鸟。满掬靑靑红渐少。紫藤筐外花须袅。 嫩绿如茵粘碧草。选叶搜枝,石上铺多少。斗罢嬴输香缭绕。玉人嬴得微微笑。”上阕幽致的景物烘托了女子的品性,下阕本应热闹的嬉戏,玉人也仅以“微微笑”,温婉幽静的女子跃然纸上。黄云孙评陆求可《忆秦娥·闺情》一词云:“温丽中带闲雅,逼似湘真。”陈维崧《海棠春·闺词,再和阮亭韵四首》一词,评者谓:“寻常闺阁中,哪得如许雅致?”词中要集中表现的正是闺中的“雅致”,它来自真实的闺秀生活,而美于现实。概而言之,“雅”是清词描写闺阁女子的准则。
词中女性形象以代表德才色兼备的闺秀为主,体现了词坛尚雅抑俗的审美趋势。自云间词派开始,有感于明词的俚俗淫哇,在词学理论中明确地提倡雅正。对雅的追求至浙西词派达到高峰,论词以“醇雅”为旨归。对于摹写女子的闺襜之作,词人尤其严辨雅俗。毛先舒于《与沈去矜论词书》中云:“大抵词多绮语,必清丽相须,但避痴肥,无妨金粉……且闺襜好语,吐属易尽,巧竭思匮,则鄙亵随之。真则近俚,刻又伤致,皆词之弊也。”彭孙遹早期以艳情词著称,王士禛戏谓其“艳情专家”,其词中有青楼爱恋,也有夫妇之情,不可以传统之“艳词”统而概之。彭孙遹论闺词以雅正为宗:“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以冶淫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正非徒于闺襜巾帼之馀,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兰苓之目也。”清初人论“闺襜”一词常将青楼模糊的涵盖其中,一些鄙亵之词通常是写青楼与优伶,描写闺秀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女子为妾或市井女子时,语言会俊俏一些,但也不落淫邪。对闺襜词雅正的强调,也许正是出于对青楼一类词的排斥,或者主张同样以雅的准则加以规范。柳永词大量写青楼歌妓,其情其态无如闺阁之娴雅,在清初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即可为之明证。如邹祗谟《忆瑶姬》(十五年前事)一词,追忆与一位类似霍小玉身份的女子的恋情,王士禛评这首词云:“元十一和《梦游春》诗无此凄艳。屯田小词,传播旗亭北里间,终不解作香奁绣阁中语也。”
三 “佳人”之真情
清初的小说、戏曲中对情的宣扬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词由于在不断地尊体过程中,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诗化的层面,强调词人的比兴寄托,言情的传统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其实,清初词言情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风”“骚”寄托,一是纯粹的言情之作。后者较之宋词同样发生了新变,它蕴含了至情的思想,宣扬儿女真情。
对于词而言,直接影响其宣扬至情的是《牡丹亭》为代表的讴歌至情的传奇。明人“以传奇手为词”,其曲化导致了明词俚俗而衰微不振。至清初,词人严持词曲之辨,从语言、风格、格律、用韵诸方面将词剥离曲的影响,有效地促使了词学复兴。然清词存留着“曲化”的痕迹,即有意识代言与宣扬至情。明人评词喜以曲比拟,而清初词评很少提及曲,这是词之尊体使然。以曲论词集中于评论词中代言与至情,通常以《牡丹亭》《紫钗记》等比拟,尤其是《牡丹亭》,而至情的宣扬是通过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之作。
《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与“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在以往的文学中从未有过,其感人至深,于当时形成了一股“牡丹亭热”。许多作家都继承了汤显祖的传统,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大量揄扬至情、宣扬真情的爱情剧,如周朝俊的《红梅记》、徐复祚的《红梨记》、孟称舜的《娇红记》、袁于令的《西楼记》、吴炳的《情邮记》、《画中人》等皆是。杜丽娘幽禁深闺的苦闷,追寻真情的渴望极具典型意义,在杜丽娘的身上,女性读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杜丽娘的热烈与执著又给予了她们精神的力量。当时闺阁几乎人手一册,清初程琼云:“盖闺人必有石榴新样,即无不用一书为夹袋者。剪样之余,即无不愿看《牡丹亭》者。闺人恨聪不经妙,明不逮奇,看《牡丹亭》,即无不欲淹通书史,观诗词乐府者。”闺阁女子将刺绣花样夹于《牡丹亭》刻本中,刺绣之暇,时时展阅。男性词人在代言的闺词中,便将杜丽娘的色彩赋予了这些闺秀。
男子作闺音,以代言的笔法描写女子,这本为唐宋词的传统。自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之后,“词中有我”的成分在艳情词、闺情词中得以强化,并且是后人解读唐宋词,评判优劣的标准之一。不过与此同时,男子作闺音仍在词史中延续,至明末清初,词人对词之代言、虚构更是有了自觉地认识。李渔论词中宜分人我,即以传奇比喻,“或全述己意,或全代人言,此犹戏场上一人独唱之曲”。词的代言、虚构实与传奇相通。词人在代言中摒弃“我”之视角、情感,摹唇炼吻地化身为女子来言说。比如沈时栋《隔帘听·深闺闻百舌,步家大人原韵》一词,以女子的口吻叙写面对春光的流逝,引发对青春的珍惜,从而思念远人。黄泰来评之云:“能化身入金闺,临川《牡丹亭》是也。钩深致远,想复同之。”评语所论“化身入金闺”与“钩深致远”,涉及到创作中的虚构,对于这一手法,他首先联想到的是传奇。又如金烺善写闺阁女子,评者赞其“曲体艳情,无不工妙。想雪岫前身乃香妍女子”,也是追求“无我”式的纯粹代言。词的代言在传奇的影响之下得到了发展,使男性词人更能客观的观察与反映女性心理。对于毛奇龄的闺情词,女士商云衣评论云:“读初晴近词,每使人不怡。”又如金烺《更漏子·春情》写一位女子无可排遣的闺情,其真实足使女子同感而泪下,唐实君评这首词云:“世间慧心女子,若见绮霞新词,必掩面悲啼,红泪淫淫下矣。”传奇、小说以“奇”动人,通常有夸饰的成份,词中体现的女性情感,与之相比更为真实。
词中以代言体刻画了大量杜丽娘式的深闺女子,或为闺中少女徒然地渴望爱情,或为深闺少妇思念漂泊羁旅的远行人,“情”是这类词的主题。如陈维崧《番女怨·五更愁》一词:“榕亭一夜残灯警。霜浓虫省。五更风,十年事,无形无影。梅花窸窣惨人听。半池冰。”王士禛赞曰:“入情语,惟临川剧中能之。”《牡丹亭》对词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词中女子形象摹仿了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寻梦与相思而病的情事。词中深闺女子于春光中发现青春的美丽,生发无人怜惜的惆怅,一如杜丽娘之游园。沈谦《踏莎行·恨情》一词:“竹叶香丝,莲花金瓣,月华初满花头绽。纵然端正又风流,十分好处无人看。 钿盒难分,连环不断,相思还寄垂杨岸。前生果是没因缘,如何空积愁千万。”张渊懿评曰:“临川‘三春好处无人见’,同一惋惜。”词中女子由明媚的春光感发“纵然端正又风流,十分好处无人看”之情,很明显来自于《牡丹亭》,其摹仿虽不高明,却可典型的反映杜丽娘形象对词描写闺情女子的影响。又如孔传铎《杏花天·本意》一词,顾彩谓:“便是临川绝妙好词,不特韵似,神亦肖之。”词全文为:“催花御史催花绽。杏腮艳似佳人面。金铃暗护悬枝畔。蜂蝶且教驱遣。 上苑边、斜飞紫燕。曲江外、低垂柳线。玉楼人倚栏杆倦。雨后落红一片。”这位玉人在大好春光中发现自身的美丽,其情虽未透漏,然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其言情的指向不言而喻,故评者赞其与《牡丹亭》神似。
杜丽娘式的惊梦、寻梦在词中很常见,但词写得含蓄蕴藉,以雅为尚。王士禄《昭君怨·楼外》一词,尤侗评云:“‘觑屏山’三字惝恍之极。隐括《牡丹亭·寻梦》。”叶光耀《如梦令·冬夜》一词写出新意,于惊梦、寻梦之外,添加问梦。“外雪敲窗左。惊醒梦儿一个。试问梦中人,谁更多情如我。无那。无那。挨着绣衾还卧。”丁天庵评云:“实甫惊梦,临川寻梦,浮玉问梦,可称三绝。”相思而病是才子佳人传奇的套路,词中之情大略相同。如尤侗《如梦令·病呓》一词写佳人深秋抱病,彭孙遹云:“大似杜丽娘身份,但彼正伤春,而此又悲秋耳。”又《虞美人·怜病》摹写佳人暮春病剧,自怜自惜之态,王士禛评曰:“似《还魂记》中语。”清初女子获得教育的机会较之前代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婚姻方面,依然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法自主地拥有选择“情”的权利。即便父母门当户对的择婿观包含了希翼女子嫁与才品兼优的男子的愿望,但实际上有“情”的婚姻可遇不可求,即便如叶绍袁为其女纨纨精心挑选的人人争羡的婚姻,依然是所适非人。清初闺思、闺怨词截取片断,多侧面地展现闺阁女子杜丽娘式的情怀,出以同情的态度,于当时来说,确为一种人文关怀。
德才色兼备和追求真情是明末清初思想界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新型女性观,于文学作品中,受到关注的主要是小说、戏曲。清初数量众多的闺词同样响应着这一时代思潮。相比于小说、戏曲的虚构性,词更具有真实性,更能客观地反映现实。清初词坛的“佳人论”对考察当时的女性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
[1]李渔.窥词管见[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5.
[2]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3]荑秋散人.玉娇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5]董元恺.苍梧词[M].康熙刻本.
[6]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全清词·顺康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邹枢.十美词纪[M]//香艳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8]金烺.绮霞词[M].康熙刻本.
[9]佟世南等.梁园唱和词[M].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10]陈维崧.迦陵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1]曹贞吉.珂雪词[M].康熙刻本.
[12]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3]沈时栋.鞠通乐府、瘦吟楼词合刊[M].民国刻本.
[14]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邹祗谟,王士禛.倚声初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陆求可.月湄词[M].康熙刻本.
[17]毛先舒.毛稚黄集[M]//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18]彭孙遹.松桂堂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吴衡照.莲子居词话[M]//词话丛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5.
[20]汤显祖.才子牡丹亭[M].吴震生,程琼,批.台北:学生书局,2004.
[21]周济.宋四家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22]毛奇龄.毛翰林集[M]//清词珍本丛刊.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3]张渊懿,田茂遇.词坛妙品[M].宣统辛亥精校石印本.
[24]孔传铎.红萼词[M]//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5]王士祿.炊闻词[M].康熙留松阁刻本.
[26]叶光耀.浮玉词初集[M].康熙刻本.
[27]尤侗.百末词[M].康熙留松阁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