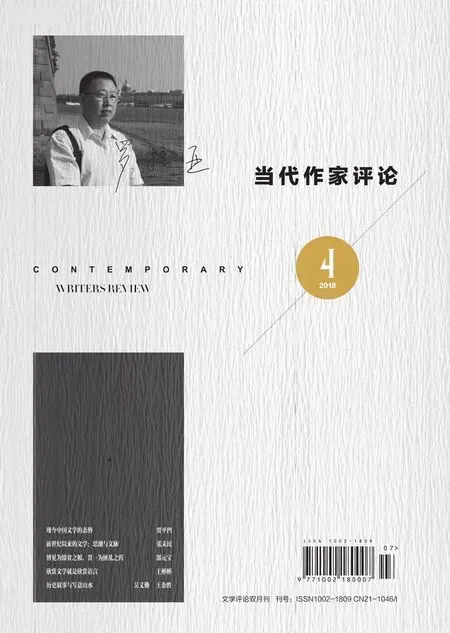做一个诚恳真实的批评家
——王彬彬和他的文学批评
孟繁华
初识王彬彬大约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文艺争鸣》杂志在吉林市丰满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王彬彬和我等应邀参加了会议。那时的王彬彬也就30出头,他穿一件海魂衫、寸头,头发茂密且齐刷刷地怒向青天。虽然身影青春无敌,但已经大名鼎鼎。原因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上。此前,八九十年代之交,王彬彬已经发表了诸如对张炜《古船》与贾平凹《浮躁》的比较研究,对余华、残雪、金庸等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也多有惊人之语,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但还属于“常规性”研究的范畴,在流播层面很难“影响广泛”;而《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甫一发表,迅速传播并被“事件化”。1994年代,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讨论也几乎是“排队划线”泾渭分明。而《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彬彬被推到风口浪尖,“二王之争”也顷刻在大小媒体稳居抢眼位置。王彬彬从此便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文学界或者在其他什么界,要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并非易事。第一,这人要有真知灼见;其次,真知灼见要敢于公诸于世;第三,公诸于世后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有真知灼见的人很多,但敢于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真相就不容易了;一旦说出后,问题便接踵而来。后来的王彬彬说,那篇文章发出后,我吃了多少亏,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后来看到了一些关于王彬彬的材料,特别是他复旦博士毕业留校未果,重返部队后的郁闷心情。这时他写了系列随笔式的文章如《渴望跪下》《所谓事业》以及《尊严像破败的旗》,特别是在《尊严像破败的旗》中他说:
十年后,他已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同学、老师以及一切熟人眼里,他都是一个过于清高的人,一个自尊心太强的人。在有的人那里,自尊心是身上最坚硬最牢固最不易受伤的部位,你一斧头砍下去,斧都卷刃了,手都震痛了,从他的自尊心里却流不出一丝血来。……有时候,你想要伤害他们一下,得费好大的劲。你得事先把某句话磨了又磨,磨得自觉锋利无比后,再向他们的自尊心上奋力捅去,就这样,也才能让他们的自尊心小小地痛一阵。他常常用不解的眼光打量着这些人,打量着他们的刀枪不入的自尊,有时甚至有隐隐的羡慕。与这些人相比,他常常觉得自己的自尊是过于敏感过于脆弱了。
这是王彬彬彼时的自况。那“过于敏感过于脆弱”的自尊,是否也隐含着难以察觉的攻击性格。如果用心理分析来分析《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是否与他那时的攻击性格有关也未可知。但是,此后不久,他在《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中说:
我1986年跳槽到中文系当文学专业研究生后,就觉得,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说点真话,尽可能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边”实在无聊。1987年到现在,我发表的百余篇习作(确实只不过是习作)中,有“骂”,也有赞,即使对同一个作家,也两者都有。……至于《过于聪明……》以及近期的一些短文,我自己并未特别看重,但居然有了这样的“影响”,我没有理由不为此“庆幸”。借用王朔先生的话说,写作么,不就是为了出名吗?索性学一回王朔,庶几能得到某种曲意的蔽护。“王朔不是理论家”,我也不是;王朔是“大腕作家”,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王朔骂人骂得比我刻毒,甚至说“知识分子”是“灵魂的扒手”,而我骂得远不如他。对王朔宽容者,主张对王朔的话不较真者,理应对我更持此种态度。不然,便太令人费解了。
王彬彬这段话中,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说点真话,尽可能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边’实在无聊”一句。这句话也可看作是王彬彬不具有“攻击性格”的一个注脚。他的批判性,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自觉追求。这句话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或敢于在文学评论中践行,是非常艰难的。王彬彬是这样说的,也在一定程度这样做了。他这样做了必然要成为“敏感人物”,后来他的几篇文章也涉及到了我的朋友和曾经的同事,在学界沸沸扬扬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其实,那几篇文章并不特别重要。王彬彬真正的贡献和学术眼光,恰恰被这种有意的“事件化”给掩盖或遮蔽了。在我的印象中,王彬彬确实有几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为了突出他的观点或看法,他甚至不惜以极端化的方式做了表达。比如《〈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这个表述,我宁愿将其理解为王彬彬有意为之的一种修辞术。但这一策略的后果可想而知。他遭到了一连串的质问和批评:《“酷评”难撼经典大树——〈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质疑》《〈红旗谱〉:不应被忽视与诋毁的“红色经典”》等,就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文章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文革”期间他读《红旗谱》,读到“反割头税”时,书被父亲没收并亲自送还。后来他解释说:
现在我该回答“文革”期间父亲为何没收我正读着的《红旗谱》了。那时候,……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对于杀猪先要争取指标、后要“裁税”的事,我很小就知道,且认为既是国家法令,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红旗谱》中,贾湘农和严江涛发动、领导的第一场斗争,就是“反割头税”。所谓“割头税”,就是“杀猪税”。第二十六章,贾湘农给严江涛布置“反割头税运动”的任务:“你见过吗?杀过年猪也拿税,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这就是说,过年吃饺子也拿税,人们连吃饺子的自由都没有了。农民眼看一块肉搁进嘴里,有人硬要拽走。我们以反割头税为主,以包商冯老兰为目标,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于是,严江涛挨家串户,向农民说明政府要收“割头税”的事。农民一听,都义愤填膺,觉得杀猪也要完税,闻所未闻,一个个革命热情高涨——读到这里,联想到当时农村的情形,我一头雾水。我想:现在农民杀猪不也要“裁税”吗?所不同者,《红旗谱》中的农民,只要完税,杀多少都可以;现在则有严格的指标控制,一般农民想交这“割头税”还交不上呢!我把疑问向父亲提出,父亲一听,大惊失色,立马没收了我的书,且严厉警告我,不得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至于《红旗谱》是否虚假和拙劣、王彬彬的“酷评”是否能够撼动经典大树等,终是一时难以说清的事情。而“反割头税”从严江涛时代延续到“文革”,还真是值得一说。生活是老师,它告诉我们的还是比书本要真实许多。他的另一篇文章《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是一篇的确有洞见的文章。这篇文章中王彬彬发现:复出后的高晓声,一直是心有余悸的。他要以小说的方式表现20多年间在农村的所见、所感、所思,他要替农民“叹苦经”,他要揭示几十年间农民所受的苦难从而控诉造成农民苦难深重的政治路线的荒谬,但又担心再次因文获祸,担心自身的灾难刚去而复返。这样,高晓声便必须精心选择一种方式,他希望这种方式既能保证作品的安全和他自身安全,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抒发自己心中的积郁,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几十年间的所见、所感、所思。而“包包扎扎”后再“戳上一个洞”,便是高晓声选择的方式。“包包扎扎”是在掩藏、遮盖真相,也是在为作品和自己裹上一层铠甲。“戳上一个洞”,则是让心中的积郁、愤懑,让几十年间的所见、所感、所思,通过这个洞口得以表现。“包包扎扎”不只是用一些政治套话、一些意识形态话语缠缠裹裹,也包括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搞一点模糊”,还包括以创作谈、序言、后记一类方式误导读者。后来郜元宝教授评论说:王彬彬教授《高晓声创作论》提出一个挑战性观点,他认为高晓声曾被打成右派,新时期又因农村题材小说备受争议,这就使他一直心有余悸,不敢彻底揭露所亲历的农村生活真相,总是“戳上一个洞”,又赶紧“包包扎扎”,“搞一点模糊”。创作如此,“创作谈”也如出一辙。这就很容易误导研究者,而一些研究者真的被误导了,因此“高晓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误解的作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不仅面对作家不敢直言不讳,面对同行也是讳莫如深,久矣夫不见如此大胆真诚的剖析论难了。这也堪称高山流水一段佳话了。当然,王彬彬的文章我更喜欢的是他在《钟山》杂志开设的专栏——“栏杆拍遍”,这是王彬彬式的文章。他获得了第一届《钟山》文学奖。我曾向贾梦玮主编索要授奖词,可惜的是第一届《钟山》文学奖没有授奖词。如果是这样,我想为王彬彬的“栏杆拍遍”补拟这样一个授奖词:
王彬彬的专栏《栏杆拍遍》,以对文史的通识能力,对材料的考据辨识功夫,以老辣睿智的春秋笔法和独特文体,令人拍案惊奇。会心乍有得,抚己还成叹。他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无所不能栏杆拍遍。他的思想、情怀、认知等,道人所未道。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中论短长。见识与材料在正史之余又在历史之中,他是当今随笔世界的独特存在、一大景观。
王彬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多年前,陈武在《散论王彬彬的文学批评》中说:“当王彬彬对现实中道德理想主义的缺失进行批判的时候,‘人文’的形象早就在大众的心目中模糊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商潮中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有不少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脱这个厄运,他们在现实面前表现出的怀疑与失落、惆怅与沉沦,都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对现实世界的妥协与认同,这些表明了‘人文’精神的日渐崩溃和丧失,在这里,物欲改变了失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在巨大的浮躁中偏离了航向。”另一方面:“他在‘道德理想主义’面前所展现出的明智和理性:一方面旁征博引地论述了道德理想主义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阐述了道德理想主义极端化产生的灾难后果,他希望对理想有道德的判断之外,还需要有冷静和节制,否则就如同真理进一步成为谬误,或者乌托邦。”这一评价我看是非常中肯的。
王彬彬在批评界是一个独行者,是一个不大有“现实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敢于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的批评家。据他的学生方岩说:他是“每年都会把《鲁迅全集》拿出来翻翻的人,已经把鲁迅变成了自己文字、秉性、生命的一部分”。鲁迅的伟大,百年来鲜有人能与之匹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人格成就。王彬彬时常读鲁迅,显然有个人的自我内心期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也常被称作“文学批评家”。这总让我羞愧,觉得自己实在不配。我并不因为自己“理论视野狭窄羞愧”,更不因为自己“不能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看待文学而羞愧。……我之所以羞于被称为“文学批评家”,是因为深感自己语言上的天赋不够。对语言的敏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共同的先决条件,对此我深信不疑。后天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但对语言的敏感,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仅有后天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先天的禀赋起着很大的作用。……我最初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诗人。胡乱写过许多诗。这个理想之所以破灭,就因为自己语言上的天赋实在达不到一个诗人所需要的水平。发现这一点,曾让自己悲哀不已。而近些年,我更发现自己语言上的天赋也远远不够支撑起“文学批评家”这样的称号。我之所以越来越少谈文学,我之所以越来越想“退出批评现场”,就因为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配对文学发言。
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批评家呢。后来和王彬彬熟了,发现他是一个简单、纯粹、有意思的人。他日常生活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他说在家里经常走过的地方都要放上酒,为的是便于随手喝上一杯;他说不要锻炼身体,古人坚持“静”肯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生活中的王彬彬也是不疾不徐地走路,手里似乎永远有一支不熄的香烟在他身前身后烟雾袅袅。这或许是他内心从容、情绪淡定的一种外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