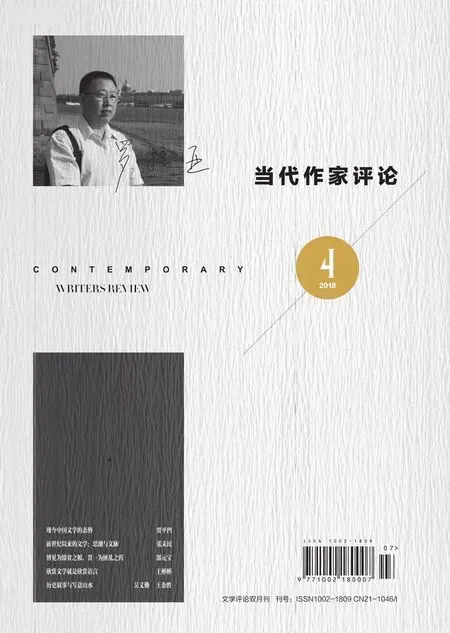无家可归者与一种文学装置:苏童论
项 静
1963年生于江苏苏州的苏童,跟众多同时代作家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一道,创造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异军突起,参与营造了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备受瞩目的中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妇女生活》《红粉》,长篇小说《武则天》《城北地带》《我的帝王生涯》《米》《蛇为什么会飞》《河岸》《黄雀记》等,以流畅而优雅的叙事风格,独特的故事和意象,收获了大量读者。苏童的文学创作被写入各类当代文学史教材,实现了短时间内(1980年代至今)的经典化。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苏童作品的评价是:“多取材‘历史’。对于‘意象’的经营极为关注,尤其擅长女性人物的细腻心理的表现。……既注重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同时也不放弃‘古典’的故事性,在故事讲述的流畅、可读,与叙事技巧的实验中寻求和谐。”但也有对苏童尖锐的批评,认为从《妻妾成群》开始,苏童的“先锋”性实验成分已明显削弱,把红颜薄命等主题和情调写得富有韵味,但“削弱了小说中的创造性的文化内涵”。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把苏童发表于1989年底的《妻妾成群》视作“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文本之一,高度赞赏作品对于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和生存法则的呈现,但隐含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缺席的倾向,认为这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意逃避。
这两套受众面最广的文学史对苏童的观察和评价,基本上都是以中长篇小说为论述对象,充分肯定其语言才华和叙事魅力,批评其思想能力和现实感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苏童的公共认知。苏童曾经懊恼地自嘲在国内背负着特殊职称——“写女性的作家,写老黄历的作家”。苏童懊恼的是接受中间的误差和标签化。首先,他的创作面向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一个写民国、女性和宫廷的作家,他还书写了1960年代生人的少年记忆(香椿树街系列),书写过大革命背景下乡村社会的解体和人物内心的骚动(枫杨树故乡系列),写过历史故事(《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孟姜女》),尤其创作了题材广泛的诸多短篇小说,其叙事才华和艺术构思可圈可点。而近年来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河岸》《黄雀记》拓展融合了原来的写作空间,展现出继续生长的写作气象。其次,纵观苏童的创作,如果以思想能力和现实感为准绳,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苏童本人对这两种意见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他不认同正面强攻现实,而是与现实保持“离地三公尺”的距离,“从青年时代的创作到现在,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当然不停在演变、深化,要说一定要找到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性”。
对苏童的批评与苏童对自我的确认是两个隔离很远的巷道,基本上无法彼此接近。按照程德培的判断,苏童是一个自我阐释能力非常强大和准确的作家,苏童在自己的世界中已经建构起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所以解读苏童需要一个放低的视角,回到他创作的个人谱系和作品内部。而关于苏童作品中语言特征、主题意象、童年视角、女性描写、人性挖掘等研究文章已经汗牛充栋,30年后再徘徊在这些问题上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的无用功。
本文想引入一个接受者和文学后继者的视角。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依然活跃的作家,很多是难以被模仿的,譬如王蒙、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在后继的写作者中很少有自觉的追随者。让追随者却步的原因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话题。苏童和几位先锋派作家却在更年轻几代作家中始终是重要的文学启蒙导师和讨论对象,尤其是苏童。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其作品中可以看到苏童影子的非常之多,比如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张楚曾系统研究过苏童所有的作品和访谈,模仿苏童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我阅读苏童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期,看遍了他所有的小说,梦想着有天能成为跟他一样优秀的作家”。比如“80后”的双雪涛、颜歌都把先锋文学中的苏童、余华作为自己的文学传统,双雪涛说:“我觉得如果我的性格里一直暗藏着某个关于小说的定义,也许这个定义孤悬多年,当我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我发现他们实现了我心头模模糊糊的关于小说的乡愁,然后刺激我自己也来试一试。”
苏童还影响了一些导演,塑造了影视作品对一些重要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比如《红粉》《妇女生活》《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等可以看作是近年来民国戏、宫廷剧的滥觞,它们的基本母题几乎都在苏童所开创的写作空间之内。再比如中国县城、小城镇电影的重要开创者贾樟柯特别喜欢《刺青时代》,“看了那部小说之后唤醒我自己的记忆……《刺青时代》将是我对七十年代的想象,它将不是什么记录,也不是纪实,也没有什么旧可怀,而是对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的想象”。一方面,苏童是电影爱好者,他喜欢欧洲、台湾电影,喜欢费里尼、库斯图里卡、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的作品,苏童的作品跟如上电影有某种承接关系,而很多新生代导演的艺术片或受到苏童的启发,或是跟苏童具有共同的来源。另一方面,当代小城镇文艺片所呈现的核心内容比如人物命运、人性的层次、故事发展,跟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是同一个永恒的母题——欲望、少年血(暴力)、生活的转折和时间的变迁。
在阅读1970年代以后出生作家的作品时,能够让人看到苏童影子的作家还有阿乙、路内、田耳、弋舟、张悦然、韩寒、颜歌、甫跃辉、郑小驴、郭敬明等等,这有可能是种错觉,作家们也不一定愿意被拉进这条太过明显的河流,但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在文学的代际中传播和移动,这种代际之间依然在传递的面目相似的氛围和文学味道,可能就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装置,苏童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发明创造了一种可以跟随时代前进依然被运用的文学装置。
二
把苏童简单地放置到先锋文学或者影视作家的篮子里,或者给予他一个写作标签,对于理解苏童的创作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他所创造的文学装置的当代性表明苏童的文学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及物性,这应该是很多研究者努力避开的方向。苏童的创作及其形式变革,从潜在到显在过程中所附着的社会情感是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问题。把苏童作品的内在情感伦理逻辑放置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能继续对后继者们产生吸附力。
苏童198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在《我与北师大》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感受:“二十岁的人很像一棵歪歪斜斜的树,而八十年代的北京八面来风,我无法判断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对社会有用还是对自己有用,或者对谁都没有用。生活、爱情、政治、文化的变革和浪潮,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歪歪斜斜,但我不会被风刮倒,因为我的大学会扶持我,我的大学北师大,那是我在北京的家。”这个被作家追溯的“家”的意象特别贴切,能够看出一个被位移了的年轻人内心的图景,感受到在时代文化的浪潮中,苏童所感受到的恐慌与无所依傍。对“家”的渴求或许可以对接他小说中虚构的枫杨树故乡,而两部宫廷帝王小说和香椿树街系列这种恒定了空间的写作都是“家”的想象与延伸。纵观苏童的创作,可以找到一条有关“家”的线索:从家园的破败、家庭内部人性的挤压,到无家可归、寻找家园。
枫杨树故乡系列作品在灾异、欲望、死亡腐败的气息之中,有着模糊的时间线索,从《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到《米》,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律动的城乡社会变革时间表。枫杨树系列看起来是一个“地方”,而实际上其核心是时间,是一个被精心选择的时间段。《罂粟之家》中直接出场的也是时间,“三十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罂粟,于是水稻与罂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为乡村的标志”。“一九四九年前,大约有一千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罂粟。”“一九五○年冬天,工作队长庐方奉命镇压地主的儿子刘沉草,至此,枫杨树刘家最后一个成员灭亡。”
枫杨树故乡的时间基本落定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之间,地主的衰荣历史,罂粟种植的开始,都是大时代改变的注解,而在大开大合的革命时间中,过去的一切可能都要被重写。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中国城乡关系处于一种剧烈的震荡之中,这个过程中既有“家”的模型,又有“家”的毁坏,是20世纪中国乡村呈现出全面颓废态势的开始,乡村经济破产,人伦失序,乡村文化调节功能弱化,整个乡村陷入了全面的社会生态危机。除了天灾人祸,重要的原因是“城乡背离化”发展中的危机,“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
苏童以繁丽的写作风格为这个幕后的时间主角制造了层层障碍,让我们去接近枫杨树大地上和香椿树街上的事物之“存在”,它们曾经在黑暗中默默无语,被宏大叙事和现代性“时间”掩盖多年,这是苏童让“时间”开口说话的方式。时代交错的时刻及其内在的张力,是苏童早期风格中最具有容纳力的外观,也是苏童式文学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个内核存在,这种风格就是一种死去的知识。
另外,作为出生于1960年代的中国作家,他的时间主题避免不了对中国革命时间的凝视,不论以何种姿态,“文革”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他写作的一个动力,也是苏童小说中人物命运和故事结构的重要塑造者。苏童有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一直认为60年代的一代人看待‘后文革’时代,由于一种无可避免的‘童年视角’影响,书写态度有点分裂,真实记忆中的苦难感有点模糊,而‘革命’所带有的狂欢色彩非常清晰,这样的记忆,悲哀往往更多来自理性,是理性追加的。”
童年视角来自于时间的赐予,它的轻盈、视线模糊、放低姿态会拉平镜框里事物的参差感,也会制造另外一种均质的时间,而这也是理解苏童文学风格、修辞方式和故事的一把钥匙。由于真实记忆的模糊和后来的理性追加,这种混合勾兑模式,使得苏童小说中的时间容器几乎具有一种共同的特质,无论是作为他亲历生活前史的1930年代到1950年代,还是具有模糊记忆的1960年代到1970年代,都具有了一种敞开性中间悬浮的光彩。比如同龄人张清华就被这种童年叙事所深深打动,“苏童用他自己近乎痴迷和愚执的想法,复活了整整一代人特有的童年记忆。我在苏童的小说里读到了那业已消失的一切,它们曾经活在我的生命之中,却又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读他的作品,仿佛是对我自己童年岁月与生命记忆的追悼和祭奠。”但张清华又警惕地提到这种叙事双重效果,“有效地简化了这个时代,同时也有效地丰富了它,剥去了它的政治色调,而还原以灰色的小市民的生活场景”。童年视角所一直环绕的时间球体,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确具备了某种解放属性,释放了在政治捆绑之中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同时它又是模糊和旋转的,具有脱离时间的牵引力。
可能所有以言语为本事的写作,都有着对于所悖反之物的暗中依恋,苏童枫杨树故乡系列的写作以“逃离”的方式,却又可能是以此来呼应1980年代周遭社会文化的巨大震荡,尤其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改变,还有个人生活中的从南方到北方的移植带来的动荡。比如“1934年”的躁郁不安与新时期以来整个社会的变动转折也具有一种同位关系,作品中遍布的逃亡痕迹,都是巨大变迁人物心灵的一个出路。当然社会学的解读也可能完全是一种后来者的个人想象逻辑,而苏童的内在旨趣可能仅仅在于“一种典型的南方乡村”,一个不透明、漂浮、诗意而又很难被具体捕获的意象或一种内心生活、精神。
三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张学昕《重构“南方”的意义》曾专门论述过苏童的“南方”写作,“南方”是建设性的,它直指地域和生活方式、情感模式,也是一种修辞方式,这也是苏童在接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签。苏童本人对他人给予的南方意象有一种解构的解读:“南方无疑是一个易燃品,它如此脆弱,它的消失比我的生命还要消失得匆忙,让人无法信赖。”“我所寻求的南方也许是一个空洞而幽暗的所在,也许它只是一个文学的主题,多少年来南方屹立在南方、南方的居民安居在南方,唯有南方的主题在时间之中漂浮不定,书写南方的努力有时酷似求证虚无,因此,一个神秘的传奇的南方更多地是存在于文字之中,它也许不在南方。”本人去解构掉“南方”,不可否认是一种挣脱被命名的主观心理,另一方面也是苏童作品中切实存在的“逃离”的愿望,这个“南方”是矛盾的心灵,是在北方求学时期的念兹在兹的怀恋之地,又是真实生活中的厌弃之地,是一直以逃离的心态视之的空间。
这个“南方”有着具体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的外形,但它本质上是抽象的,内在地具有反地方志的呈现方式,比如《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开头有一种煊赫的气势,“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这个想象的家园和故乡,起源于回忆、想象和半夜的梦境,小说中被铺排了众多形容词的乡土,游弋在枫杨树故乡的幺叔和落脚城市的祖父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对峙和牵连。这是一个寻找者和回望者的感性叙事,我们无法获得关于故土的切实知识。
在空间上苏童所呈现的是一种乡镇生活的雏形,介于都市空间与乡土空间之间,就像《城北地带》开头所给出的那个空间,“一年一度的雨季无声地在南方制造着云和水,香椿树街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湿润粘滞起来。当一堆灰色的云絮从化工厂的三只大烟囱间轻柔地挤过来,街道两旁所有房屋的地面开始洇出水渍”。空间是半敞开的,是一个生产性和消费性混合的小城市,依然具有乡土社会的属性,舆论空间持续存在,尤其是少男少女们彼此有着频繁的交往,并且氤氲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或面临爱情和成长的难题,或面临家庭的丑闻和地位的升降。由于成人世界的粗放和整个社会环境对政治的焦虑,他们成为自我教养的孩子,没有指引者,凭借着生命的本能和社会空间中继承来的生存法则左冲右突。
模糊的及物性和抽象的空间使得叙事、语言和声调独成一体,满溢并且去驱散“南方”的实体性。先锋作家群体来自于文化和政治上温和中庸的长江三角洲,与北京和广州文化空间的作家相比,他们显然并未承接太多时代的新风,与1980年代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表述的其他文学相比,苏童和其他先锋作家们显然也没有优势可言,只能寻找“形式”空间,以“个人”为源头,去开拓独异的变形世界,形成了他们把握日常生活的一般形式或纹理。
先锋小说第一次使得文学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强调,开创了当代文学的重要写作空间。苏童写作诗歌的经历,或者他所浸染其中的文学语境,使得语言诗性特质被郑重对待,质地厚实的语感,黏着而绵密的用语方式,轻盈而略带忧郁的语调,跟他所描绘的江南乡村、城镇生活,以及他所聚焦的宫闱、庭院空间形成恰当的互动关系。苏童的语言达到了影视镜头般的意象和距离,对空间的深度聚焦融合了大时代背后的时间秩序,微细情绪细致而旖旎,主导情感酷烈而氤氲,它们膨胀出一个形式的世界遥遥对接时代的内核。苏童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迅速地统摄住那个变动不居时代的感官经验和内心躁动,让它们获得自燃的机会,就像因发酵而膨胀并获得抵达生活深处的愉悦和幻觉,获得模拟了真实的虚张声势的满足感,在隐喻和写实之间巨大的中空处,继续唤醒和填塞社会记忆和个人经历。
结语
苏童的文学装置是1980—1990年代文学遗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依然活着的“遗产”,衰老灵魂的叙事者和内在抒情的自我,几乎等同于现在的“丧”文化,全身而退地躲在历史、枫杨树村、香椿树街的旁边,讲述无穷无尽的故事,那些少年、男女从洞穴中找到了出路,鱼贯而出,面目相似,带着同样的惆怅与坚硬的内核。苏童的文学世界与今天写作者所共享的是,深陷其中的不安定感,城市乡村两个空间的加剧区分,消费主义社会带来的社会阶层断裂,巨大的无物之阵在威胁生命的活力与蓬勃。
苏童及其后继者的写作有一种永恒的青春酷烈面相,形成了比较顺畅有形的自我表达通道,它所回到、看到的都是少年与青春,面对的是内心的极限体验,拒绝寻求答案,而且也失去了聚焦历史和现实的能力。这套文学装置对于一个希望成长的作家来说,它的活力与限制同在,它对于苏童一直希望有所突破的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束缚。《河岸》具有开阔的气象,逃到船上去的库家父子,好像一个逃离了香椿树街的象征,他们终于从苏童熟悉的具有腐败气息的市井生活中逃脱了,但他们依然被苏童用各种熟悉的意象给拖了回来。《黄雀记》这个贯穿更长时间跨度的故事,写了新时代里纵横捭阖的两男一女,改头换面、发迹、离开,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不同的配方勾兑的故事,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熟悉没有悬念。
程德培说:“苏童对束缚自身的东西具有极度的敏感,几十年了,他的创作几经变异,多种探索和尝试,他是真正懂得‘捆绑之后’一个作家该如何应对。”一个好作家最好的应对必然来自于自己,苏童还写过很多外表平实内里锐利的短篇小说比如《肉联厂的春天》《人民的鱼》《一个朋友在路上》等,精致地把时代变迁、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龃龉和交错包裹在叙事中。这些小说几乎是不可模仿的,随意的细节都能得到饱满的传达,小说背后是苏童对具体时空中人群的理解和体贴,因为细节和铺叙,使得行文脱离了习惯性的文学装置而显得放松自然。这一类型的写作对于被“捆绑”多年的苏童应该是一个破除障碍的方向,无家可归者不会轻易获得外在的指引,只有此时此地的自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