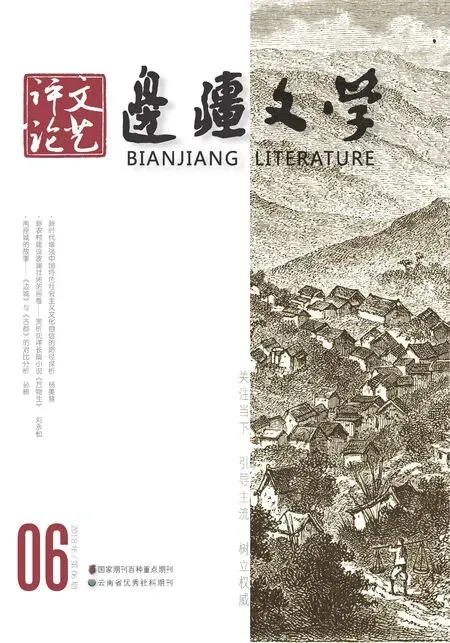叙事的“反叛与狂欢”
——浅谈孙甘露小说的叙事策略
马梦娇
一、人物塑造特点
(一)人物的虚化写法
正如方克强所说,孙甘露的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人物缺乏可以辨认的面目、身份与性格,情节丧失了时间、地点、现实、历史以至神话的提示与参照,环境则逃离现实的记忆而躲藏在梦境的深处。”呈现出一种诗意化的特征,表现为抽离片段式的语言,零碎不堪的人物形象,不完整的故事情节等等,这些使人物的性格呈现出模糊性和朦胧性的特点。在孙甘露早期作品中人物往往是缺少专有姓名的。比如“丰收神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没具体姓名的,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的关联,知道他们的关系;《请女人猜谜》也采用了虚化人物的写法,小说中先后出现的十来个人物都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名字也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故小说的意味的表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人物较多采用“单字”的取名方式,如《请女人猜谜》中男主人公“士”、《忆秦娥》女主人公“苏”、《请女人猜谜》中女主人公“后”、《夜晚的语言》中的丞相“惠”和巫医“泉”;孙甘露还喜欢给人物取植物的名字,如《信使之函》中的女人“温厚的睡莲”,《仿佛》中的人物“时令鲜花”和“夏季藤萝”以及另外一些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指称:“养鸽者”“致意者”“乱世余生者”“六指人”“守床者”等。
(二)女性人物特点
如《信使之函》里名叫“温厚的睡莲”的女性僧侣,“她有无计其数情夫,他们如亡命者般来往于耳语城和域外的荒山野岭。每年的春季,他们如野
兔般从四面八方窜回到她的身边,等候她的垂青。”《忆秦娥》中的“苏”选择的伴侣都是“一类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却又忧心忡忡的男人”……
(三)异化的人物关系
人物多忧郁沉思、多愁善感。在多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包括《呼吸》中的罗克持续沉浸于地对已逝的生活作自我反思;《信使之函》中的“六指人”们具有“细皮嫩肉而又表情呆板的多愁善感”,“他们的思绪生来以一种谦卑的姿态低伏潜行。”;《请女人猜谜》中的“士”神情忧郁又缺乏勇气;《音叉、沙漏和节拍器》中阴郁的家庭氛围,主人公“福亚”神经质的母亲总在指责父亲勾搭别的女人,他常想“只有父亲不在了才能停止母亲的唠叨”。
(四)人物的冥想与流浪
人物总是不分昼夜地行走漫游,包括他们的思绪也是总在追赶无影无踪的概念,即冥想与流浪。无论在《访问梦境》或《信使之函》中,作者高度抽象化地将上海传达给人的最直接、最隐秘、最本质的“人在途中旅行”的感受刻画了出来。“信使”与“访问”,信使始终在途中。如同《我是少年酒坛子》中的诗人,追赶的不是铜钱,也不是发情的骡子,而是一种诗意的幻想。张新颖说过:“像博尔赫斯一样,孙甘露也用玄想设置了一座又一座迷宫。他的想象穿行于迷宫中,一边津津乐道地破继解谜,一边又以破解活动遮蔽了烛照链底的光亮,‘用一种貌似认真明晰和实事求是的风格掩盖其中的秘密’。”
二、叙事特点
(一)叙事时间空间化
文学中时间大致可以分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所谓故事时间就是指作品中被讲述的故事中人物所处的时间状态,叙事时间是指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间。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时间、叙述节奏几乎与故事时间相一致的,遵循的是故事的自然时间规律,即时间是一维性的、线性的。而先锋小说为打破、颠覆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将时间作为反叛传统的一个有力手段,时间成为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独特技巧。在先锋小说中,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不再是匹配的,甚至某些作品本身就无故事可言。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作品就是如此。先锋作家专注于自己的感觉,用感觉心理来自由切割故事的线性时间,然后再通过拼贴技巧将在叙述者的意识与记忆中同时存在的故事碎片重新组合,进而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系列错综复杂、毫无头绪的场景和断片,这样就创造了一种纯心理的时间和空间。孙甘露可以说是一位在文体实验的形式追求上走得相当远的先锋作家,他对时间的认识深受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影响,即认为时间不是一维的、线性发展的,而是多维的,不同时间是可以并存的。那孙甘露是如何实现这种时间的并存呢?
1.“故事套故事”的写法
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利用“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实现了不同时间的共存叙述。同时,受到博尔赫斯关于分叉、聚合、平行的时间观念和博尔赫斯作品《花园》双重文本叙事的启发。在这篇题为《请女人猜谜》的小说中,出现另一篇叙述人自称在写作的《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个故事被巧妙的并列并交织在一起。这种双重文本意图颠覆传统时间的概念以及写作本身。《请女人猜谜》在现代的部分中,讲述“我”与人物“后”之间爱情的忧郁情绪,而作为故事讲述背景的《眺望时间消逝》,是关于过去,讲述人物“士”的怪异和阴森的故事。但两个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在两个不同的文本时空中分割又交融,“后”与“士”彼此交错,过去、现在和未来混淆在一起。通过重叠并扭曲过去与现在,他建构起一个包含多层空间的叙事,这个叙事也并不具备时间上的统一性,时间也不再是直线的,相反,它分裂并叠合,叙述在过去现在未来间自由穿梭,《请女人猜谜》小说每一节都有一个小标题,但小标题与每一节的内容无关,而且每一节与每一节之间的内容也没有关联性。小说题目是《请女人猜谜》,却没有请女人猜谜的有关情节,整篇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无关联的碎片;
这种故事套故事、不受时空限制与文体互文性的后现代叙事手法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作者在一个文本中会写到另一个文本里的故事,比如《岛屿》叙述的是名为《岛屿》的另一部小说集的写作过程,真正的文章与虚假文章完全重合;《信使之函》里写到的《我的宫廷生活》,《仿佛》中写到的辞典《米酒之乡》……
2.叙事主体的非现实化与时间的碎片化
《呼吸》中,叙事呈现为主体非现实化,时间的追忆性和碎片化,主人公罗克没有现在和未来,只有对过去的追忆。罗克将一种厌倦的感知作为他的生存方式,恍惚懒散和忧郁的沉思是他永远的姿态。小说是这样描述人物的厌倦情态的:“他把他的一生看成是一次长假。慵懒是他的标志。他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最后一天。”(《呼吸》p88)他的思想感觉远远大于其现实行动,被定义为“全天候的梦者”“梦游症患者”。他追忆的故事非现实化、人物成为飘忽的影子。
3.人物身份及所处时空的不确定性
《请女人猜谜》中“士”一会是守床者,一会儿成为乔治奥威尔的仆役,一会又是一名医学院的解剖师……对时间的原始秩序的破坏,使人物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超验时间流程中。
《岛屿》不同的叙事单元里,霍德的身份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作家、偷情者,迁徙者或流浪汉……他与少女桦、卡车司机石默的关系也很离奇。脱离了历史、文化的整合性,“整个存在都是虚构的”。《岛屿》还消融了创作形式与批评形式的界限,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写小说,《庭院》也是如此。
(二)穿越时空的叙述者
孙甘露小说中的叙述者具有多重身份,行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夜晚的语言》中,“我”作为叙述者、写作者,一方面是现在文本的呈现者,另一方面又是丞相惠的贴身记录人员,穿梭于古代与现代之间,也存在于故事中和故事外,甚至于还在梦境之中也拥有话语权,还具有评价功能。《天净沙》中的“我”则既是生活中看电影的观众,又似乎是电影中的角色。
(三)追求语言形式、结构形式的创新
孙甘露的小说写作不具备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更不用说情节了,彻底背叛了写作制度。受博尔赫斯影响,孙甘露把博尔赫斯的迷宫理论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的交错和一种语言上的狂欢,产生出一系列神秘的人物、奇怪的行为、矛盾的推理,荒谬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的碎片,无意义的描述、空无的夸夸其谈、抒情的华而不实的言词,模棱两可的思想,没有故事的故事,并试图将极具感性化的诗性语言引入小说之中。
1.例如小说《信使之函》近两万字,但通篇却少有让人读得懂的句子和段落,每一个字或词我们都认识,但就是不能明白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偶尔有一些“通”的句子和段落也不能有效地构成情节和生活场景。比如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诗人在狭长的地带说道: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信风携带修女般的恼怒叹息着掠过这候鸟的天宇,信使的旅程平静了,沉睡着的是信使的记忆。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感的慢跑中徒然苏醒。和信使交谈的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五彩的愉悦是后来岁月的事情。”
所有的语言都没有现实的对应,每一句话之间不管是用句号还是用逗号,都缺乏关联,比诗句更富于跳跃性。展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些不相关的要素的混杂,包括没完没了的空谈,一位僧侣的冥想,神秘怪异的人的日常行为形而上学般的誓言等,作者充当叙述者,以无意义的方式转换叙事角度,通过隐喻或者语法错误,使叙述的声音无所不在。通过对能指的自由操作使完整的故事便朝各个方向发散,形成一个迷宫性的故事。
孙甘露的小说创作完全沉入语言狂欢中,他在《信使之函》中对信赋予了53个定义:诸如“信是淳朴情怀的伤感的流亡。……信是私下里对典籍的公开模仿。……信是自我扮演的陌生人的一次陌生的外化旅行。……信是一次遥远而飘逸的触动。……信是一种状态。……信是一种犹犹豫豫的自我追逐,一种卑微而体面的自恋方式,是个人隐私的谨慎的变形和无意间的揭示……”孙甘露将信的能指意义扩大到无穷尽的地步,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的滑动中,试图将极具感性化的诗性语言引入小说之中,这53个信的定义随意散布在整篇小说中,这样读者对理解小说情节的预期就完全被阻碍了。在这里孙亦表现了自己对纯文学化语言的追求。人物均在语言中诞生又在语言中消失, “士”与“后”的也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转换自如。在孙甘露的小说中,谈话与话语源源不断,他的非历史性陈述,那些莫名其妙的梦呓、忏悔、胡说八道,都表明了他真正追求的是一种语言乌托邦。
2.在《访问梦境》中,孙甘露解构了叙事的结构,仅仅追求一个梦幻世界中的语言狂欢。因为小说叙述的内容是零散化的和精神分裂式的,是梦意识的片断呈示,读者可以感受到叙述正在进行,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叙述内容的关联性。读者再一次看到一个深刻的形而上的思考的世界,人物缺乏可以辨认的面目、身份与性格。主人公“我”和我的想象一直在行走着,来到丰收神的橙子林,又去寻找一个叫“剪纸院落”的地方,根据一本名叫《审慎之门》的书的指引来到“冷兵器纪念堂”,之后又出现一位“美男子”“玩镜子的男人”等人物,作者在文本中穿插了所谓“舞蹈者的故事”、讲述了一本叫《流浪的舞蹈者》的回忆录里的故事……叙述犹如在梦游一般的呓语,花园,尿罐,床垫,丰收神,镜子等意象不连续的,一个一个的进入视线,所有这些都最终指向一个虚构的世界。
3.《请女人猜谜》中的一段描写:“一位丰满而轻佻的女护士推着一具尸体笑盈盈地打他身旁经过。他忽然产生了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中自如飘移的感觉,然后,他淡淡一笑。他认识到自古以来,他就绕着这个花坛行走,他从记事起就在这儿读书。” 孙总是把多个不协调的形象掺和在一起,运用各种出人意料的词语组合,表达不可言说的感觉。炫目的阳光下一位丰满而轻佻的女护士推着一具尸体笑盈盈地打他身旁经过,“他”产生了虚幻飘移的感觉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自古以来”个字使这一幅奇妙的图画获得了超验而神秘的内涵。
4.孙甘露对语言的控制欲望还体现在以下地方:在他建构的非理性世界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违背正常认知的话语。如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调皮捣蛋,叫一个教汉语的老处女一巴掌磐成了个半残废”,语言让上帝变得残缺起来;以及“我生前就是个死者”的表述也不合乎常理。
5.诗意化的叙述体使字里行间流淌着的语言美,如“我无法向过去的日子回复,甚至倾心接近的意象也被自己认作是虚妄,而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场景始终驱动着我,唤起我的追忆,使那些腼腆的,在内心深处无比荣耀的岁月萦回缭绕”(《忆秦娥》)仍然用欧化的修饰性语言营造诗意氛围。
再次,孙甘露的小说的题记的诗意效果也相当明显。孙甘露的小说中基本都有题记,《海与街景》和《仿佛》也引用博尔赫斯,《信使之函》引的是卡夫卡,《请女人猜谜》《此地是他乡》引用艾略特,《境遇》引用萨特,《夜晚的语言》引用叶芝,《剧院》引用查理鲍希,只有《忆秦娥》的引言来自江淹,而《我是少年酒坛子》的“引言”引自《米酒之乡》,而《米酒之乡》是孙甘露小说《仿佛》中的文本(“双重”文本的一重)。他直接承认“我当初是把诗歌当作小说来写的,受叙事体或者史诗传统的蛊惑,其后,我是把小说当诗歌来写的。”表明作者的诗意营造目的。
(四)荒诞的寓言:隐喻背后对人类内心及生存状态的关怀
孙甘露的无边的语言实验最大限度地拆除了小说与诗和哲学的界线,因此孙甘露的游戏文本并没有失掉内在的深度,我们可以在他看似无章的字句背后看到对现代城市生活、人际关系的反思。
如《信使之函》中信使刚踏上征途时,怀中的信函就已经“羽翼般飘落”了,他一下成了空洞的毫无意义的盲目行者,况且他去的地方叫“耳语城”,耳语城充满了荒唐、淫乱、虚伪、狂欢和秘而不宣,他要寻找的收信者最终也消融到耳语城的芸芸众生里。所以在整个时间流程内,信使的徒劳奔走,信函的遗失和被忽略(没有收信人),象征性地体现出人类精神的漂泊无依,一种理想、纯洁信仰的缺乏失去与失落,其间无度的精神紊乱又纠结着内心感情的流放。像“热闹的地方让人倍感孤独”等一类语句也大都隐含着生存现实的启示, 《大师的学生》亦表现了文化的冲突与困境;孙甘露以幽深甚至荒诞的方式直面时代、人生的“真实病症”。
三、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甘露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也是相当边缘化的。难得的是他在执着追求语言、文体形式的创新时并没有抛弃作品的内在深度,在一个“诗意无用”的时代,他对诗意的追求、对语言的热爱应该得到尊重,正如批评家吴义勤所总结的“孙甘露在他迄今为止的一切小说充分地对语言的诗性进行了不懈的表现,孙甘露可以说最为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巨大可能性和诗性。孙甘露的小说没有别的主体,语言就是其文本的主体和一切,在语言之外我们对孙甘露将注定了无法言语。没有了语言,没有了那个活跃在文本中的言语者,就没有了孙甘露,也就没有了孙甘露的小说。某种意义上说,讲孙甘露是中国文学史中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语言乌托邦者不仅丝毫不夸张,而且非常符合实际。”孙甘露的小说往往被很多人认为读不懂而不被接受,但因受众的喜好各异所以孙甘露今日也有他所应该拥有的文学市场,将来他的作品境遇如何则更多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了。
[1]孙甘露.夜晚的语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孙甘露.忆秦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3]孙甘露.呼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孙甘露.上海流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5]方克强.孙甘露与小说文体实验[J].文艺理论研究 ,1999(6):68
[6]张新颖.双重见证[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152
[7]周桦,曹磊.幻影:一切文化与非文化的努力—《访问梦境》与现代主义小说的终极出路[J].当代作家评论,1989(1)
[8]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