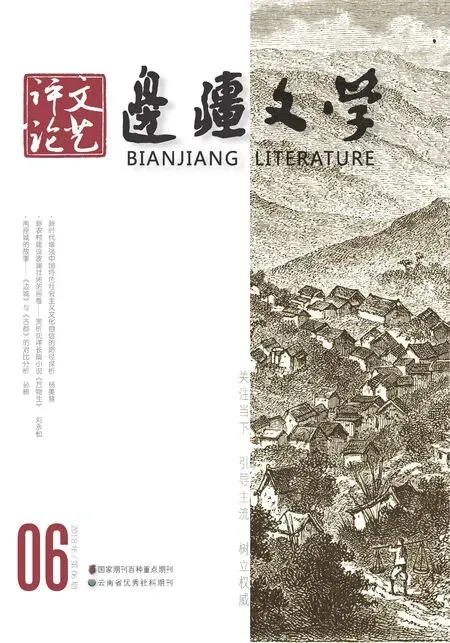浅析沈从文湘楚文化心理对其创作的影响
樊晓燕
文化心理是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走向和精神状态,并以精神文化形式沉积下来,由各类文化陶冶而形成的基本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伦理道德以及价值取向等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环境。文化心理研究是理解作家作品、探究作家思想与精神的重要方法。
鲁迅评价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甚至有学者言:“没有沈从文的现代文坛是不完整的”。许多人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特异的作家之一,探究沈从文的文化心理对其作品与整个现代文坛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沈从文的文化心理主要受湘楚文化以及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这四条文化线索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作者的文化心理。正如凌宇先生所述:“沈从文并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被沈从文接受吸纳,从而形成沈从文自称的‘新道家思想’。”沈从文具有炽热的民族情怀,在其作品中一幅幅的优美“湘西画卷”让我们久久难忘,其创作中带有鲜明的湘楚文化特征更是彰明较著,都深深地打上了湘楚文化的精神烙印。作者的文化心理基础是自小生存的这片土地,他的心理与精神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上。因此,文章主要从湘西文化的视角探析沈从文的文化心理。
什么是楚文化?张正明在《楚文化》中说:“楚人迁居江汉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与他们的祖先作为天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更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形成了南方流派。”凌宇把湘楚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原始的民族忧患意识,炽热的幻想情绪,对宇宙永恒性和神秘感的把握。”由此,楚文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崇尚自然,充满神秘与浪漫色彩,带有原始的民族忧患意识,加之以屈原的爱国情怀为典型代表的楚文化特征。综上所述,文章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炽热的民族情怀以及民族忧患意识
楚人炽热的爱国情怀可追溯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他虽遭谗被疏,甚至被先后流放到汉北和沅湘流域,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楚顷襄王狼狈而逃,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显示了他在流放期间对劳动人民的深入接触,使他深刻地了解与体会到民间的痛苦处境,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也因此,在他的诗歌里我们能看到许多忧国忧民的诗句。又如《招魂》里的名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表现的是诗人远离故国,担忧国家的悲伤情感,这些诗作都蕴藏着他对楚国炽热的爱国情感。
沈从文作品中表现出的炽热的民族情怀,正是对湘楚浓郁的爱国情怀的继承与发展。他始终以“乡下人”的眼光关注着湘西人的生存状况、历史命运,注视着都市的文化生活,他笔下的湘西题材与现代都市题材,形成强烈对照,揭露都市人的“文明病”,他们没有生命活力、人性分裂、毫无血性、腐化堕落,虚伪、无情、狡诈、野蛮。沈从文呼吁的是“健康、优美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他希望笔下的人物充满爱与美,希望他们保有正直与热情,也希望“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长河〈题记〉》)”,以实现民族品格的重塑。
同时,沈从文对湘西民族那段被视作“蛮族”遭受歧视、压迫、同化与屠杀的悲惨历史遭遇寄予深切的关怀与同情,“这地方的一切,虽在历史中也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派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迫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种种限制与支配。(《湘行散记·箱子岩》)”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常常带有隐隐哀愁与无可奈何的痛苦,悲悯心与责任心油然而生。“在谈及自己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一例充满的‘淡淡的孤独悲哀’与乡土‘悲悯感’的原因时,他说:‘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的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湘西散记〉序》)”小说《边城》中天保的死,傩送的出走,爷爷的死无疑给作品留下一抹哀伤的色彩,《萧萧》中作为童养媳的萧萧的命运,让读者感受到丝丝的悲凉。沈从文说过:“我正感觉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长庚》)”他的这份悲悯心与责任心不经之间流露出炽热的民族情怀以及民族忧患意识。在他的楚人血液中,流淌着屈原的因子,爱国,爱家乡,爱土地的精神以及楚人的悲悯意识,坚守独立人格,都体现在他独特的气质上,也处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二、崇尚自然与浪漫抒情的艺术追求
湘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观是史前人类对自然万物原初的理解。先民致力于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自然力和自然现象拟人化或人格化,赋予自然界万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把它们看待成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命和思想感情的对象。”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自然的亲切与尊重,其笔下的自然景物描写更是得栩栩如生,处处充满了生机盎然,就连笔下的人物也带着自然的属性,《边城》中的小女孩“翠翠”宛如一头山水间的小灵兽。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也是自然辖治下的“边城”,那里的人们充满了爱与美的人性,对天命的顺应可看作是一种对自然的顺应,人与自然毫无违和感。沈从文说过:“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水云》)”对湘西民族而言,大自然包孕万物,天、地、神、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都是生命的实体,并且能够生存与共。湘西民族泛爱自然、回归自然的观念,影响着沈从文对艺术的表现方式,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大自然的灵气与生的气息,同样也给现代社会普遍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以深刻的启示与反思。
沈从文与自然的契合在其作品中还反映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多次提到屈原及其作品,屈原的作品中向世人展示了湘楚大地的绮丽风光,比如《九歌·湘夫人》中就得到精彩的表现:“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榜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这样美妙的景色在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中也得以体现:“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长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丫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行文至此,朗朗在目的是楚地白燕溪山崖间自然繁衍的奇花异草所熔铸的一片美丽秘境。可以说,沈从文是明确有意继承屈原对湘楚风光描绘的文学传统,而对湘西的秀丽山水作了大量的描绘,在《边城》《静》《长河》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这类景致的描写,它为沈从文的作品披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形式。(《水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也被定位为浪漫主义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
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善与美的“人性”
“强旺而执着的生命意识,正是楚文化的精魂。”正是因为沈从文身上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他更注目于生命,可表现为他对生命的细致体察,对湘西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如在其散文作品《湘行散记》中能找到很多的例证。他从一草一木上,见出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以及生物求生存与繁殖的“神性”,从小虫上,见到自然的天工之巧与生命形式的多样,自然事物能够使他对人事和人生有所会心。也正是因为他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意识,使得他对自然有着一份崇敬之心,他作品中的大自然的各种声色显得格外的迷人,同时也造就了他作品风格的奇异审美。
沈从文十分关心湘西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在《湘西散记》《湘西》的人物画卷里,妓女、水手、纤夫、兵士、女性、商人、煤矿工人、劳工家庭……他们为生存而不断徘徊在死亡线上,肉体上、精神上都经受着沉重的苦难。水手随时都有可能要下河拉船,时刻面临着被急流卷走生命的危险,为了赚那一天几分钱的工钱;年近八十的老人为生存而去拉纤,对于生存还是那么努力与执着;妇女为了生存,只有靠卖身养活自己;面临着随时可能坍塌、灌水的矿坑,在地狱讨生活的煤矿工人埋头做着他应分做的事情。作者通过平静的叙述,更能我们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忧虑与愤慨的力量。对湘西底层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作者进行了深层的追问,并给予了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反思。即便生存的境遇如此,但作者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群勇敢正直、热情活泼、善良纯洁、坚忍倔强的“乡下人”。他们虽然活得沉重、庄严却又十分执着与洒脱。
沈从文以善、美为审美主体,善与美的集中表现就是“爱”,这是沈从文对生命状态进行理性思辨后铸造而成的。“湘西世界”的构建是他审美理想的总体象征,而善与美是“湘西世界”的显著特征和价值取向,而与它对立的是丑陋的“都市文明”,《八骏图》中的八位教授病态的人生和堕落的生活,《绅士的太太》中的上流社会的男女,生活奢侈,精神糜烂堕落,都与《边城》《柏子》《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人物的善良美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从文在双重的文化视野下展开他对“人性”、对“生命”的理性思考。自然神性和人的神性相交揉,在沈从文的笔下透露出了对于人性以及生命意义的最有审美力量的美学探寻。沈从文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建筑,这种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人性是作者构建“湘西世界”的基础,对湘西和湘西人民的歌颂和赞扬体现了沈从文对理想人性形式的追求,即人性的返璞归真,也体现了他迫切的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湘西精神中“善”和“美”的人性才是沈从文生命意识的最真实蕴藏,才是其创作中对生命形式的认知与哲学思考所在。他呼吁健康人性返璞,追求自然人性归真。最终,在朴实健康、自然清新的“湘西世界”中,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理想精神家园。
四、结语
湘楚文化是影响沈从文创作最主要的因素,其创作在思想内容、悲剧意识、人格精神、文化特色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湘楚文化精神特征。在文化探源上沈从文将自己视为“楚人”,他创作的文化心理与他从小生长在湘西凤凰和自身苗族的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作品独特的审美视角与风格内涵与湘楚文化氛围的浸染与熏陶是分不开的。“关于沈从文青少年时代在辰沅间所处文化环境中精神文化方面的主调已可确认,作为一种氛围状态,熏染沈从文心灵,从而建构了他‘文化禀赋’或曰‘文化情结’的”,“是因特殊的历史机缘长期以活化石形态遗存于辰沅民间的巫风特盛的这湘楚文化!沈从文明白楚人在辰沅的历史,也清楚当地文化主调的性质,故在《湘西·沉陵的人》中视自己故乡人为‘楚人’。而在《长庚》中则说到自己身上涌流的是‘楚人的血液’”。沈从文身上的湘楚文化情节早早在二十一岁就已经形成了,他称自己是“乡下人”,表明了对湘楚文化的认同。而湘楚文化给予了沈从文炽热的民族情怀以及民族忧患意识、影响着他崇尚自然与浪漫抒情的艺术追求、赋予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善与美人性的追求,方方面面都使得沈从文的思想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显得更为成熟、深刻与复杂,也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之一。
[1](美)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J].新文学史料 ,1978(1):237
[2]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文学评论,2002(6):11
[3]张正明.楚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124
[4]凌宇.重建楚文化的神话系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124
[5]董楚平.楚辞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文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7]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邱苑妮.诗性的皈依沈从文自然意识研究[M].漫延书房,2012:19
[10]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