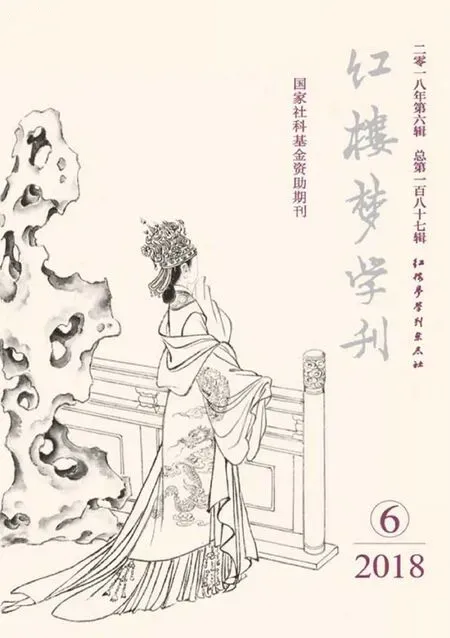张新之“以易解红”诠释理路的再评价
内容提要:张新之“以易解红”诠释方法的选择与使用既是他个人的文化选择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选择。《易经》本身对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影响极为深远,《红楼梦》文本也拥有丰厚的《易经》思想,尤其是清代经学的发展对张新之及其那个时代的文人影响不可小觑。“以易解红”不仅激活了《易经》这一传统的学术资源,同时也拓展了小说评点理论空间。这种诠释理念的转型,既拓展了文本解释理论,又提升了小说评点的话语权力。
一、张新之“以易解红”诠释方法及其评价
张新之自称“寝食以之者三十年”,日累月积,著成三十万字评语,最后得出结论:《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道光三十年,(张氏此作以《妙复轩评石头记》行世后,获得了当时许多学者的极髙评价,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以《易》阐述《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最大的代表作”。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的回末总评、行间夹批以及《妙复轩评石头记》卷首的序文中都较为详尽地阐释了他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大学》、《中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演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大学》、《中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在《妙复轩石头记》的双行批中说:
“通灵,明德也,借通灵明明德也。说石头,`新民也,以《大学》评《红楼》,我亦自觉迂阔煞人。”
“作者固自演《大学》、《中庸》,天人之微,理欲之极,必无中立处也。臣 其君,子栽其父,岂生而然哉”
“曰《中庸》《大学》,作者之意可知矣。一部《红楼》不过是《中庸》、《大学》。”
此说一出有关质疑批评张新之“以易解红”的不绝于耳,这里罗列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①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一书中指出张新之评论的基本观点是:《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全书无非《易》道也(《红楼梦读法》),郭豫适觉得这样异想天开的评论是荒唐的主观猜想。②1985年王先霈、周伟明《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一书中指出“张新之重视小说之命意,但是又不是从作品本身体会作者本来的命意,而是只管按照评点者的想法去推演作品的命意。他从传统出发把《红楼梦》说成是劝惩之作。他的论著从观点上到方法上都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教化说的腐朽和荒谬”。③1999年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说“张新之把儒家经典著作为依据分析《红楼梦》有时未免望文生义,硬拉胡扯,全朝‘性理之书’的角度去加以阐述发挥,似有误入歧途之嫌”。④1997年张庆善在《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浅析》中认为张新之用《易》演《红楼梦》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瞎猜胡扯,指出张新之的失误在于没有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读。1997年他在《红学评点派》一文中提及张新之《周易》评点《红楼梦》的附会,并认为他那些评点是枯燥说教和玄奥的占卦术。2003年杨慧《〈红楼梦〉古今评点谱论》中罗列八家评点红楼梦,认为张新之的评点是对《红楼梦》的误读,认为“张新之是一个带着《周易》沉重镣铐的评点家”。
以上诸种说法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的共同认识,这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张新之误读了《红楼梦》,还是我们误读了张新之?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易经》,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易经》意蕴?张新之“以易解红”真的毫无价值吗?
二、《红楼梦》文本的易学意蕴为“以易解红”提供了阐释空间
《易经》这部书是一个文化奇迹,是中华智慧的源泉,它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发生、发展的历史。《易经》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自汉代开始“易为群经之首”,一直到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头一部就是《易经》,《易经》一直具有群经之首的地位。千百年来,《易经》对文学影响极大,归纳起来《周易》对于文学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文学作品中对《周易》语言典故的借用、对《周易》易象的借用、对 《周易》易理的阐发、易学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艺术结构的启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等。《周易》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是全方位的。从理论到创作,从创作到批评。从文到诗,从小说到戏曲。从简单的使事用典,到作品结构的借用。从“易象”活用到“易理”阐释,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深深影响了大批的文学家创作素材、艺术构思以及文学思想。《易经》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以及《红楼梦》文本中的“易学”内容,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与研究,如梅新林的《旧题新解:〈红楼梦〉与〈周易〉》探讨了《红楼梦》与《周易》——中国文学与哲学史上的两大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探讨“红楼《易》理的文本依据”时,从史湘云“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的说法到贾雨村有关天地正邪二气的议论,“一阴一阳之谓道”,按史湘云的具体解释是:“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这一解释是《红楼梦》阴阳变易论的一个统摄全局的核心论点,毫无疑问,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阴阳哲学的,但又是为红楼世界所特有的杰出创造,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哲理思索与艺术个性。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挖掘“红楼易理”,主要探讨了“红楼易理”的四个方面:阴阳对位、阴阳变易、阴阳还原、阴阳恃论。就是《周易》哲学的核心——阴阳原理。二元对立、四重变奏的“阴阳组合图式”中,既有显性的阴阳对位、阴阳变易,又包含着隐性的阴阳还原、阴阳恃论。四者互相关联,由表及里,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了红楼《易》理的主干。当然,梅文在在最后特意分析《红楼梦》与《周易》之分合,在《红楼梦》与《周易》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对应性的异质同构关系,《红楼梦》与《周易》——中国文学与哲学史上的两大奇书之间内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及其具体契合点,在艺术创造原理上,《红楼梦》也同样吸取了《周易》阴阳哲学而熔铸为独具一格并与从阴阳对位到阴阳悖论相应的对立幻影、符号易位、原型回归与本体象征等四大原则,两者真正的不同在于文学与哲学的不同。除了梅新林之外,郭冬升、佟晓丹《〈红楼梦〉的易学意蕴》也详尽探讨了《红楼梦》与《易经》哲学的契合点,从《红楼梦》的哲学视角(太极视角)、哲学基石(心物一元)、哲学境界(无极境界)、存在论问题、哲学精神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当然,除了以上两篇文章之外,也有不少论文或著作中的部分篇章也涉及相关研究,主要为研究《红楼梦》哲学思想的相关成果。本文之所以不再梳理,主要是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了。引述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足以证明《红楼梦》有丰富的《易经》内蕴,张新之“以易解红”绝不是对《红楼梦》误读,而是在对小说文本充分细读感悟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更不能批评张新之的诠释是牵强附会或荒谬绝伦。这样评价的话,既不科学,也不实事求是,对张新之的学术成果也缺乏足够的尊重。
三、张新之选择“以易解红”的原因
如果说《红楼梦》文本中的易学意蕴为张新之“以易解红”提供了坚实的文本依据的话,那么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比附经史是张新之选择“以易解红”的文化原因。
在探讨文化因素之前,我们先探讨一下个人原因。比如说孙桐生认为张新之其学渊雅,博通古今,著述颇富。可见张新之学识渊博。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说:
遂乐与谈,风晨月夕无不俱,十三经二十一史,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所见大致不径庭,而其谐可喜,其態可畏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新之是熟读《十三经》的,要不然不会“滔滔然,渊渊然,互相考”,而张新之自己也在《红楼梦读法》说: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演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由此可见,张新之的文化素养也是影响他“以易解红”的重要原因。当然张新之个人文化素养的养成以及选择“以易解红”的原因,还有历史与文化的因素。
张新之所处的时代,满清王朝对汉族文人采取了拉拢和高压两套手段。笼络文人方面,大兴儒家思想,提倡经学研究;高压控制方面,大兴文字狱,大力查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张新之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此间的文化政策对其评点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文字狱依然严酷,文人倾向研习经学,清政府采用文化高压政策来镇压具有反抗倾向的文人,文字狱是其中一大措施。清朝文字狱从顺治帝开始,乾隆期间愈演愈烈,至清末依然存在。《清朝文字狱》列举的文字狱中,顺治时期有6宗,康熙朝有13宗,雍正朝有20宗,乾隆朝约有140宗,嘉庆朝有1宗,同治朝有1宗,光绪朝有1宗。康熙晚年数次下旨严禁“淫词小说”,雍正、乾隆也是谨遵前朝定例。因为文字狱的原因,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之口解释此书与时事、淫邀艳约题材小说无关,借此为自己洗白:
(空空道人)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侫、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虽书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而最终的结局是,曹雪芹的表忠心无济于事,《红楼梦》并没有躲过被禁毁的命运: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载:《红楼梦》一书,晦淫之甚者也,安徽学政玉麟首倡禁毁《红楼梦》。汪堃《寄蜗残赘》卷九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嘉庆以后,《红楼梦》屡遭查禁,直到光绪年间也依然被禁。
乾嘉年间《红楼梦》遭到禁毁,是因为政治原因,恐书中有“碍语”,这些因素对张新之不能不产生影响。
张新之“以易解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清朝文化政策有关。统治者们借儒家思想文化系统来巩固政权,安定社会。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其治学以传统的儒家经学为中心。而嘉道之际,学风转向汉学;道光年间,王朝危机,民族危机深重,学术界也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依旧是儒学。张新之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他与五桂山人交谈中主要涉及的是“十三经二十一史”,而在张新之的评点中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可见两人的知识积累、价值取向都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这是用攀经附史的方式将小说地位从“稗官野史”提升到了与经史同等的地位。当然,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界,包括张竹坡、金圣叹等人也是将小说比附经史,以此确认小说有着和经史一样的地位和功能。因为经史中所承载的“仁义道德”“劝善惩恶”“立德、立功、立言”在小说中可以同样得到体现,经史的功能是劝诫示警的道德教化作用,小说同样可以善恶报施,劝惩重诫,通其说者,与神圣同功。张新之以群经之首的《易经》为批评标准和诠释原则,既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又远离了当时的现实世界。这应该是张新之“以易解红”的最重要原因。
四、郑玄“以易笺诗”与张新之“以易解红”
由于研究经学,一个偶然原因,发现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郑笺》里也做过“以易笺诗”的事情。郑玄“以易笺诗”是否对张新之有影响我现在无法找到佐证。但是从清代郑玄研究在经学研究的发达程度上来推测,张新之应该看过郑玄“以易笺诗”的。在这里我们把郑玄“以易笺诗”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两者的诠释方式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郑玄本来以“以礼笺诗”著名,但他还同时进行“以易笺诗”,即以研究易学的思想、方法诠释《诗经》。郑玄“以易笺诗”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涵盖了《风》《雅》《颂》三大部分,但他下功夫最大的是《风》《雅》两部分。
郑玄“以易笺诗”的主要内容有:一是以易学的字义训释《诗》的词语。如《周南·日月》“畜我不卒”,《郑笺》:“畜,养。”源于郑玄《周易注》的《小畜》注。二是“以易”阐发《诗》的意义。如《召南·草虫》“亦既觏止”,《郑笺》:“觏,合也。男女以阴阳合其精气。”源于郑玄《周易注》的《系辞传》注。 《周颂·有客》“有客信信”,《郑笺》:“聘礼毕,归大礼,曰旬而稍。旬之外为稍,久留非常。”源于郑玄《周易注》的《丰》初九爻注等。
郑玄“以易笺诗”的方法主要有:一、以《易》卦爻象笺《诗》。 《魏风·伐檀》“寘之河之干兮”之“干”,郑玄注:“干谓大水之傍,故停水处。”郑玄之所以将干解释为大水之旁,正是来源于他对《渐》卦初六爻辞“鸿渐于干”的注释。二、以《易》来揭示《诗》义。郑玄以《易传》笺《诗》的具体内容来看,他所援引的主要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和《说卦传》五种。如《谷风》《柏舟》《将仲子》《采微》《菀柳》《小星》等。其中尤以《象传》与《系辞传》为主。《象传》是专门解释卦名、卦义、爻辞的文字。
张新之“以易解红”是寻找《红楼梦》与《易经》之间的关联,他评点中对于小说人物、数字等进行诠释的时候,运用有关卦象、数字、五行等易学思想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及其相关意象。
张新之善于将人物与卦象结合起来,由此分析人物性格与命运。在卦象的选择上,张新之费尽心思,在《读法》中就将刘姥姥定位为《坤》卦,刘姥姥孑然一身,无子息,正对应纯阴《坤》卦,随后以元春与《泰》卦的契合为切入点进行评点,张新之按照顺时针流转的顺序,从元春生于一月对应《泰》卦着手,一一解释其他三姐妹与对应卦的关系。迎春为《大壮》之《观》,探春乃《夬》之《剥》,惜春为《乾》之《坤》,并通过卦象揭示入物的性格命运,在整部小说中贯穿十二消息卦的卦象,以《坤》卦始,以《复》卦终,暗示整部《红楼梦》的结局。张新之评点文字中使用的卦象不是单一的,具有丰富的指向性。他善于将人物与卦象对应,以卦象来隐括相关人物命运;在用卦象比喻人物的同时也展现出整部小说的运势。
张新之在用易解读《红楼梦》过程中,特别关注数字,通过数字分析来确定命理的定数。如“八九七十二”这一数字,我们仅取与黛玉紫鹃有关的两例。第八十二回,黛玉生病,觉得自己喉晚中有血腥味,再看到紫鹃露出慌张的神色,也知道自己的病已经非常严重,自己或可能命不久矣,顿时心里凉了八九分。第九十七回中,黛玉病入膏肓,紫鹃去找老太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问人都说不知道,紫鹃已知八九分了,只恨这些人如此狠毒。这两处的“八九分”,八九相乘都是七十二,于是张新之说:“八九七十二,地数也,气数到此一终”。周易的数字奇数为天数,九为天数最大,八为地数最大。七十二是九个八相乘,表示地数尽,黛玉一直拖着病体,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怎么会不清楚咯血之后意味着什么。知道八九分了,指对事情的知晓程度,张新之用“地数”,隐指黛玉魂归大地。此后评点中八九七十二多取“地数终”的意思,多指生命终结,气数已尽。
除此之外,张新之还用《易经》中五行生克来解释人物命运结局。如张新之说,黛玉是木,宝钗是金,这个不难理解,黛玉姓林,本是木,前身是绛珠仙草,也属于木。宝钗的名字是金钗,属于金,她又有金锁,也属于金。从姓上来讲,“薛”谐音“雪”也是杀“林”的。五行上金克木。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姻缘”肯定也会被宝玉和宝钗的“金玉姻缘”所克。金与木在姻缘上也存在对立,宝玉与黛玉为木石姻缘,宝玉与宝钗是金玉姻缘,姻缘相克,命运相克,由此确定了黛玉的悲剧。
我之所以把郑玄“以易解诗”与张新之的“以易解红”列举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新之还通过《诗经》传达《红楼梦》孝道等教化主题。第十七回中,贾政一行人观赏大观园,贾政要宝玉对草堂建筑题对联,宝玉念到:“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菜芹人”,张新之紧接着评:“诗咏《周南》,《颂》升《泮水》,吃紧教化在此,贾兰到矣。”原来“浣葛”的典故出自《诗经·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浣害浣否?归宁父母”。写的是新妇洗干净葛衣才回娘家,这《红楼梦》中喻指元春归省。下联中“采芹”也出自《诗经》,《诗经·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指泮宫之水,泮宫又指学宫。后人把考中秀才入学称为生员,又称为“入泮”或“采芹”,这里的“采芹人”指贾府的读书人。元妃归省重在宣扬孝道,贾府的读书人中除了宝玉唯有贾兰最终考取功名,贾兰也谨遵孝道。张新之归结此对联意在宣扬其教化之功。
根据张新之对《诗经》以及经学的熟练程度,我在这里大胆推测,张新之是接触到过郑玄“以易笺诗”解经方式的。“以易笺诗”直接影响到了“以易解红”。其实,无论是“以易笺诗”还是“以易解红”,都是中国古代对传统经典的一种诠释方式,这种与众不同的诠释方式尽管很难被他人认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诠释经典的方式,也是一种全新的创新,其开创意义不能低估。
五、“以易解红”诠释方法的再评价
张新之“以易解红”不仅在《红楼梦》评点中属于异类,在整个明清小说评点中都是异数,这个特异的文化现象,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扇窗口。
“以易解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历史化、政治化、观念化的道德隐喻解释。其诠释特征表现为将小说评点作为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手段,将文学诠释与个人生命融合为一,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以小说评点这门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在身份建构上体现为儒家价值守护者的角色。
《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离张新之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但张新之依然将其拿来作为解读《红楼梦》主题与人物的理论资源,对他来说也是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激活。
儒家经典诠释学建构了明清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从诠释方法上溯源,经学注疏传统是小说评点方法的源头,“读法”与“文法”则来自文章学。从诠释立场上看,由于受传统经学教育和个人诗学修养的影响,张新之的诠释立场表现为经学与文学立场同时并存的特点。“以易解红”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张新之对《易经》的接受和理解成为他诠释《红楼梦》“前理解”,确定了他对《红楼梦》的认知框架,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阅读体验,他的《红楼梦》评点也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和概念。这些丰富的差异性,对我们理解《红楼梦》文本提供了大量与众不同的新观念。对于张新之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小说批评来说,这些差异和不同往往能够形成“视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小说评点的诠释效力。
张新之对小说文本的诠释,有时用传统经典诠释方法,有时用自标新法去诠释,更有用自创新法去进行评点诠释的。无论是对小说文本的字句诠释、内涵诠释和结构诠释,他都往往驱文就我,以“道问学”与“尊性情”之间,以“才子文心”建构来他自己的小说评点学的知识谱系,成为那个时代的批评异数,他带来一种小说批评观念的更新和诠释向度的转变,他们的评点由直觉、鉴赏式随意评点嬗变为思辨、理论式的批评方式。这种诠释理念的转型,既拓展了文本解释理论又提升了小说评点的话语权力。
也许我对张新之“以易解红”的理解是错误的,不会被广大红学同仁所接受。但如果我坚持认为“以易解红”作为小说评点的异数,他拓展了小说评点的视野,开创了完全迥异于其他评点者的全新视域,希望得到同仁们的认可。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那些完全否定张新之“以易解红”研究者们,没有一个是研究《易经》的专家,更谈不上精通易理,所以他们完全理解不了“以易解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然,张新之“以易解红”到底如何认识、如何评价,还是留给读者去评说吧,接受者的效果是最好的评判。
注释
①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饭社1980年版,第117页。
②⑥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700、705 页。
③ 程刚《〈周易〉影响文学的七个层次——〈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天府新论》2012年第1期。
④ 梅新林《旧题新解:〈红楼梦〉与〈周易〉》,《东方丛刊》1995年第1辑。
⑤ 郭冬升、佟晓丹《〈红楼梦〉的易学意蕴》,《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⑦⑩ 《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2007 年重印),第6、256页。
⑧ 赵维国《〈红楼梦〉毁禁始末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辑。
⑨ 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⑪ 葛培吟译注评《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