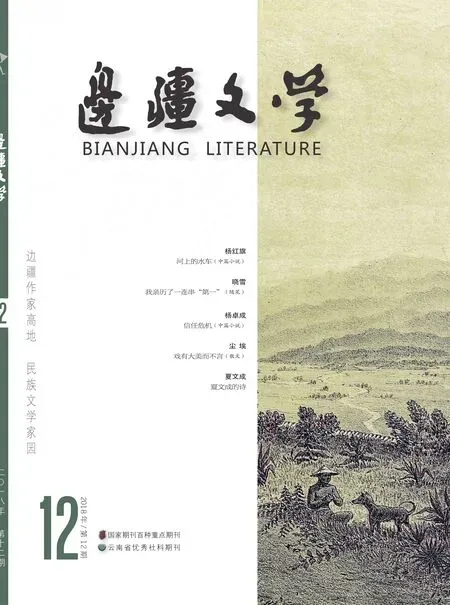戏有大美而不言
尘 埃
她或悲或喜或忧或怨,这些表演都尽在我的意料之中,而她在第三场《登墙夜窥》和第四场《监守自盗》中的演绎才更让人叫绝不迭,董生连演带说地表现各种爬墙、偷听和矛盾的内心活动时,李氏没有唱腔,很少台词,她就用她的表情和内敛的身段动作来征服观众,我记忆最深的一幕是:李氏安静地斜坐在亭子里的背影,充满诱惑、魅力和美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让我心动不已。愁肠满肚的在院中观月时,她突然发现董生又来偷窥监视,不禁窃笑起来(我正思念于他,他就来了),开始隔墙戏弄于他,她的表演让人看出李氏虽说已是个寡妇,可实际上还是个正值青春年华的花季少女呢,她不但有春心,更有玩儿心。她故意唱情曲,夸张的风情万种,这带着一些冷幽默的搞笑表演并不会让人觉得李氏淫荡,反而更觉得她的可爱和可怜。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人们的精神向度,寺庙和教堂是一个很好的去处;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那么去戏院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到泉州我要去的戏院叫:梨园古典剧院。
一、梨园乡音
关于“梨园”一词,我知道的典故是:因了唐玄宗李隆基喜欢在一个叫作梨园的地方教戏、票戏之故,所以后人就把“梨园”一词用以指代戏曲界和戏曲人了,没想到在泉州还有一种古老的地方剧种叫“梨园戏”,已有800年的历史,这比昆曲和川剧还早100多年呢,保留着许多宋、元之古风。
这个活化石级别的地方戏曲剧种,之所以在当今这个戏曲式微的多元化时代非但没有逐渐消亡或是被人们遗忘,相反在近些年却还越来越让全国的戏迷所熟知和喜爱,据说与一位梨园戏表演艺术家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分不开,她就是梨园古典剧院的主人,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团长——曾静萍。
我知道梨园戏也是从曾静萍的戏开始,有一次在网上搜看一部叫《节妇吟》的程派京剧,没想到还搜到了一部梨园戏的《节妇吟》,梨园戏?点开来看看,那熟悉的乡音一下子就让我产生了亲切感,原来是来自我老家泉州的地方戏呀。
刚看时印象并不是太深,浅薄如我这般的初级外貌党戏迷,一开始总是更容易被那些扮相美丽的人物所吸引,而这部戏中曾静萍的扮相算不得很漂亮,另外乡音虽然好听,但对于我来说不看字幕依然是很难看懂的,这让人很分神,不能完全的入戏,可当我耐心地看下去,慢慢发现舞台上的这个女人非常优美。她的美不是在外貌上,而是从她的体态、身段、表演、声音中一点一点体现出来的。我发现梨园戏有个特点,那就是它的旦角的服装不像其它戏曲在演绎传统戏时应用水袖,而且它的手型手势也与京剧中的兰花指、兰花掌不同,看起来非常的优雅柔美,还有她们在舞台上走圆场也与我熟悉的其它剧种有区别,走得好像比较细碎,步子非常小,看起来更像古代的三寸金莲。
这些吸引我又找到曾静萍更为成功的另一部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来看,这两部戏从内容上看似有雷同,都是讲一个年轻的寡妇耐不住独守空房的寂寞,而用情于隔壁书生,只不过对象不同,结局也就大不相同了。然而这两部剧在表演形式上却是各有特点的,《节妇吟》更像正剧,全剧中插科打诨的地方很少,剧情看似不悲却给人许多压抑和沉重感,当然这都是曾静萍把颜氏这个人物塑造得很成功所致,观众都跟着她走进到颜氏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了。
《董生与李氏》却是另一种具有冷幽默感的表演形式,剧情很悲,一来就是死人的场面,可观众看着却发笑不停,因为那将死之人的滑稽搞笑不通情理和绝灭人性的要求和安排,使得观众在不断的笑声背后却又勾出了对年轻新寡的李氏将来命运的许多担忧和同情,剧情按着这种线路发展下去,董生为了要完成李氏丈夫那个已死之人的托付,所采取的行径就显得尤为荒诞可笑和迂腐不堪了,事情滑稽、行为滑稽、表演得更加滑稽,因此舞台上虽然没有什么音效、华丽背景的辅助,一个人的戏、两个人的戏都显得那么的抓人,在这里不得不叹服曾静萍的表演功力了,她的表演风格不是那种很开很放的,而是很柔很细腻含在内的,音调不高,动作不大,每次我以为她就要高声笑出时,她的笑却只是一脸灿烂像朵花似的开在脸上,并不出声;每次当我以为她就要有大的身段动作或是快速舞动起来去表达她的内心情绪时,她的手臂动作却是适可而止的悠悠含在了胸前,有一点感觉像日本艺伎的舞蹈(个人直觉),那种温情、那种魅力、那种含蓄的美也就像春雨一样无声地浸润了观众的心。
她或悲或喜或忧或怨,这些表演都尽在我的意料之中,而她在第三场《登墙夜窥》和第四场《监守自盗》中的演绎才更让人叫绝不迭,董生连演带说地表现各种爬墙、偷听和矛盾的内心活动时,李氏没有唱腔,很少台词,她就用她的表情和内敛的身段动作来征服观众,我记忆最深的一幕是:李氏安静地斜坐在亭子里的背影,充满诱惑、魅力和美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让我心动不已。愁肠满肚的在院中观月时,她突然发现董生又来偷窥监视,不竟窃笑起来(我正思念于他,他就来了),开始隔墙戏弄于他,她的表演让人看出李氏虽说已是个寡妇,可实际上还是个正值青春年华的花季少女呢,她不但有春心,更有玩儿心。她故意唱情曲,夸张的风情万种,这带着一些冷幽默的搞笑表演并不会让人觉得李氏淫荡,反而更觉得她的可爱和可怜。
戏看到这里董生要是再不娶了李氏,我都忍不住想跳上台去娶她为妻了(估计有我这样想法的观众不在少数)可见剧情发展的合理性和演员表演的诱惑性。当演到董生被李氏点醒,彻悟圣贤礼教之精髓和深意后,向李氏求爱,舞台上留下一对红绣鞋时,我以为戏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还有一场《坟前舌争》让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名正言顺和有高度了,也让这出戏更具有思想性和教育意义。那个代表封建绝灭人性礼教的彭员外,从坟墓里爬了出来,斥责董生,并要索取李氏性命,李氏一句唱:“万千事,莫慌恐,由妾一人承担。”让人不禁感动,呆书生一句:“李氏无过,我之过。”更让人动容,可死鬼彭员外却不为所动,执意不肯放过,激起懦弱书生也要一怒为红颜,他拿圣贤书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反击,最终赢得胜利,迎娶李氏,皆大欢喜。
看完这两部戏我终于明白曾静萍为什么能让她的梨园戏,走出泉州、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让那些根本听不懂泉州话的观众喜爱上它了,首先这两部新编剧不但故事性强有很好的文学性,同时还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启示性;其次是梨园戏本身的那种典雅的风韵和鲜明的艺术特点,人都说昆曲典雅、优美,我看了梨园戏感觉其典雅、优美之处并不在昆曲之下;再就是演绎呈现这样的好剧种、好剧本的艺术家的精湛、细腻、准确、生动的表演了。正是这三好合一的好,使得梨园戏得以绝处逢生,再放光彩。
二、泉州好戏
泉州是个包容的城市,早在宋元时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 2018年由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承办的元宵节演出周活动,不但有泉州地方戏的演出,还特别邀请了全国包括:莆仙剧、滇剧、越剧、昆曲、京剧、上党梆子、秦腔在内的7个剧种的诸多名家参与两场《名戏名家唱上元》的演出。十位梅花奖演员齐聚在泉州这样一个小地方演出,那是多不容易的戏曲盛事呀。
《名戏名家唱上元》演出分两场,每一场分别由不同剧种的五个折子戏组成,一般来说我比较喜欢看整场演出的大戏,我觉得大戏不但能使观众看得入戏走心,也能使演员演得入戏走心,因为故事和情感是连贯的,同时也更能够真正、全面地体现一个演员的综合艺术水准和表演功力。不过像这样名家荟萃的折子戏演出,来看看热闹,追追星也不错,何况还有像计镇华和梁谷因这样的国宝级老艺术家出演,现在想要欣赏到他们的大戏基本是不可能了,能看到他们演出折子戏也属机会难得。
第一天晚上开场的两出戏安排得很巧妙,是同一部戏《千里送京娘》的前后两折,《阳送》和《阴送》。由福建省莆仙戏剧院的名家王少媛主演《阳送》中的京娘;《阴送》中的京娘由云南省玉溪市滇剧院的冯咏梅主演,巧合的是她俩不但同演同一剧目的同一角色,她们还是同一届梅花奖的得主。看这两折戏对我来说感觉也是相当的奇妙,莆仙戏的京娘一出场开唱,那久违了的乡音就让我倍感亲切,(我上网查过莆仙戏应该唱的不是泉州方言,可不知为什么,我听得懂一些)活泼可爱的小村姑,一路连撒娇带挑逗,剧情看起来有点像《梁祝》的《十八相送》,只不过赵匡胤不是英俊书生,是个大花脸,京娘也不是大家闺秀。我一直迷惑不解戏里把赵匡胤安排成个大花脸有什么讲究?后来听冯咏梅讲座时还说道:以前老戏里赵匡胤还戴髯口,觉得一个小姑娘去挑逗一个老头子,和他谈情说爱很不般配,所以她们后来排演时做了修改,去掉了胡子。
阳送送完,京娘求爱不得,含羞自尽,但仍痴心不改,开始了《阴送》。做了鬼的京娘在一群闪闪发光的萤火虫的指引下出场,舞台霎时亮丽光彩,为了更好的展示滇剧艺术、得到最佳的舞台效果,冯咏梅这回带了她们团的25名演职员来和她共同完成这次演出,一出场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在遥远的泉州乍一听到用云南方言演唱的戏,于我又是一种更近的亲切,云南是我生活和工作的第二故乡。说来惭愧身在云南,我却很少听云南的地方戏,只看过一次滇剧,可巧,就正好是这部《千里送京娘》。看过许多女鬼,都是白衣长袖,飘飘荡荡很空灵,冯咏梅演绎的这个女鬼没有太多的去应用水袖表演,而是更多的应用唱腔和表情来表现,感觉上像个更接近人的新鬼,这也对,因为赵匡胤一直以为她是活人,回心转意想要与她结连理呢。
第三折戏是我非常熟悉的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一段,而且是由我心目中最好的“林妹妹”单仰萍来演出,看单仰萍的大戏无论多长都不想结束,可这次她偏偏演的最短,都不是一折完整的《葬花》,太不过瘾,可惜缺个“宝哥哥”也是无奈。我一边看戏,一边在心里幻想,如果她去芳华越剧团借个尹派的“宝哥哥”来合演那就太完美啦,那这一版《葬花》将会是无数戏迷挤破头也要来看的精彩。幻想总归是幻想,现实是这段《葬花》比那被葬的花儿还易逝,我还在等着那句念白:“人说我痴,难道还有一个痴的不成?”时,舞台上灯光一暗,林妹妹已飘出了视线。觉得没看够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次日工作坊活动时,主持人不放过她,观众们也不放过她,她只得盛情难却的又清唱了一段:“那一天呀……”才算完。
第四折昆剧《雷峰塔》中的《断桥》,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昆曲名家胡锦芳主演,《断桥》我看过京剧、越剧的,还没有看过昆剧,可当他们一开唱,那昆曲优美的声腔一下子就让我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一般,混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昆曲是越来越让我着魔了!看字幕打出戏名是“昆剧”,我一直有疑问这“昆曲”和“昆剧”有何区别?听着这唱腔明明就是昆曲吗?后来百度了一下,说什么字意的不同:曲,曲调也;剧,戏剧也。其实依我看都是指的同一种戏,就像有一阵子,黄梅戏吵着要改名为黄梅剧一样,概皆是因嫌“戏”啦、“曲”啦的字眼太小,没有“剧”那么上档次,其实在当代人眼里,并不那么较真,什么戏呀、曲呀、剧呀的都统统只是一个戏曲剧种的名字而已,还是习惯于昆曲就叫昆曲,黄梅戏就叫黄梅戏。胡锦芳我不熟悉,百度上查看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艺术家,我很喜欢她的唱和表演,可第二天她却向观众致歉说:这次没演好,因为之前生病,有五六天没有练功,所以她对自己不满意。人说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十天不练功同行知道,一个月不练功观众知道。可现如今不练功的年轻演员多了去了,没想到一个近七旬的老艺术家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五六天没练,连同行也不一定看得出,就更别说我们观众了,她根本没必要当众道歉,可她就这么做了,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第一场名家演唱会的最后压轴戏是由魏海敏主演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的《捧印》一折,魏海敏明明是台湾著名的京剧名家,可打出来的演出单位却是:“北京京剧院/福建京剧院”真是让人搞不懂,还好我以前看过她的戏,对她有些了解,去年看了一出她演绎的现代戏《金锁记》就被迷上了,一发不可收拾地又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她的戏。真是大艺术家呀,戏路宽广、演技高超、擅于变革和创新,有着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和能力。其实这次来我也是为着想看一看她演绎的传统梅派戏,可惜不是整出《穆桂英挂帅》,她那梅派大青衣的气势饰演中年时的穆桂英很有风采和神韵,这折戏身段、动作不是太多,主要就是通过表演来把穆桂英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戏里的唱段相当经典,她唱得透亮圆润,非常好听,可她自己还说有些感冒,嗓音不好。
第二场名家演唱会开场的戏还是莆仙戏,只是换了一个剧团演出,剧目名字叫《敬德画像》,虽然同是莆仙戏,怎么我听起来感觉与头一天的韵味大不相同,不管是发音还是唱法都有些不一样,这场演出演员们的唱很奇怪,就像嘴里含了个东西似的,听着像大舌头,这是他们的特色吗?如果是特色的话,那正常的舌头要唱出这种感觉来还真是不容易,我不懂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就我个人而言是很不习惯听这样的唱法的。我的疑惑剧院没有资料可以解答,百度也说不清个所以然。
第二折戏,上党梆子《杀妻》。“上党梆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戏,所以很好奇,想它会不会是像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那样的高亢激昂呢?实际听上去还算柔和,词也很容易听懂,几乎可以不看字幕,这样有利于观众更好的欣赏剧情,他们选择的这折戏稍微长一点,故事很完整让观众能全面了解整个剧情,一折戏看下来我已经有点喜欢上党梆子了。演出的名家是山西省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的陈素琴。
第三折戏,还是我熟悉和喜爱的越剧,由上海越剧院的方亚芬主演《梁祝》中最精彩的《楼台会》。演这一段,方亚芬本来也可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用个伴奏带唱过去的,可她为了有更好的演出效果,选择了用现场乐队伴奏,自己团里的乐队人员又不方便全拉过来,就只好带上主板、主胡,其他的到泉州来现配,虽然同是乐队,奏相同的曲谱,可不同剧种的韵味还是有所不同,演员和乐队的配合也非常重要,于是她就得非常辛苦的与乐队一遍一遍地合乐。据说才来的那晚排练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一早在工作坊活动中匆匆地讲了几句话后就又去排练了,于是听讲座时,整个剧院都能听到她甜美清亮的嗓音在回荡。晚上演出前,妆化到一半,不放心,约着她的“梁兄”又去与乐队合了一遍。当时我在旁听着,感觉乐队之间的配合还是不太熟练,还蛮为她们马上就要开始的演出捏着把汗呢。然而正式演出时效果非常好!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于演戏来说怎么讲究都不会错,多花功夫也就会多有收获,这段《楼台会》演的凄美感人,以前我对傅派英台的唱腔比较熟悉,现在一听袁派,也非常好听,这次和方亚芬配演梁兄的是上越年轻演员叫斯钰林,扮相很英俊,嗓音宽厚洪亮,范派唱得相当有味道。这一对搭配起来甚是养眼,唯一遗憾的还是太短,也没有把《楼台会》整折演完,不过瘾,太不过瘾。大概方亚芬自己也觉得不过瘾,所以她说希望有机会能带着整出《梁祝》再来演出。
第四折戏是由秦腔名家齐爱云演出《焚香记》中《打神告庙》一折。她才一出场,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一定是个天天练功的好演员。她那身段、她那圆场、她那几近完美的长水袖功夫真的让人叫绝不已,她是我见过长水袖舞得最好的演员,没有之一。她的唱腔高亢、凄凉非常有爆发力但并不让人感觉聒噪不适,也有低回婉转、也有绕指柔肠,虽然与我习惯了的南方雅戏不同,但也很有女人味。秦腔的音乐给人有种悲凉的感觉,特别是胡琴的声音,听上去一股醋味,酸得让人直想落泪(不知是不是因为这部戏本身很悲的原因),演出时她水袖和身段动作的表演首先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和眼球,台下掌声、叫好声一片,还没等我仔细体会她的表演时,这折戏已经结束了,这就是看折子戏的怨念和缺憾啊。还好我看了她白天的排练,那时空荡荡的剧场里仿佛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在台上激情地演,唱、念、做、跑、跳、翻、舞;我在台下安静地看,内心翻江倒海。她和敫桂英融为一体,或哀伤、或悲愤、或疯狂、或绝望;我的情绪也随着剧情起起落落,莫名的就很感动,为剧中人,更为齐爱云。
整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是由两位年过七旬的老艺术家计镇华和梁谷音演出昆曲《烂柯山》中精彩的《逼休》一折,他们的表演自然、精湛、娴熟、细腻,两人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我惊叹于他们在唱腔和身段方面也保持着相当好的状态。这段戏也是以一种冷幽默的手法在演,观众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搞笑的轻松感,可是笑过之后又会对剧中人物的命运产生一种更深切的悲怜感。看来幽默这个元素很重要,演戏如是,写作亦如是。
三、道是无缘恰有缘
自从我与戏曲结缘之后,每次出门看戏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故事发生,这次也不例外。
看演出的那天,我去剧院取票,取完票时间还早,本想到西街去逛逛顺便吃点东西再来看晚上的演出,可谁知像我这样的超级路盲居然就在剧院里迷失了,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口,却转到了舞台上。剧场里有个女声在进行舞台调度和声光调试,光线暗淡,看不清人影,但凭直觉我猜那一定是曾静萍。
仿佛是上天的指引,顺着舞台后的过道,上了楼梯就是化妆间,“后台化妆间”是一个对我有无限吸引力的神奇地方,就像一个魔术师手拿一个苹果,放进一个暗箱,出来后苹果就变鸽子了,“后台化妆间”就是那个“暗箱”,这个地方的奇妙在于它是一个从生活到舞台、从演员到角色的中间状态。一般观众都只是看到了这个“暗箱”的两端,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很好奇,并且百看不厌。
我走进化妆间,如入无人境地,迎面碰到的人都对我报以友好的微笑。已经有演员在化妆了,每个人都一脸白粉,看不出谁是谁,妆台上有贴着每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个看过去,其实我也不认识谁。听到有人说云南话,不用问,那一定是云南的滇剧名家冯咏梅。在千里之外的泉州看戏,碰到了我们云南的艺术家,这让我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我们聊了几句,不知她在异乡看到我这个来自云南的戏迷时是否也会觉得有点亲切?她态度热情,我想拍两张照片,她说:加微信,我发演出剧照给你。我开玩笑说:“我主要是想把自己也框在照片里。”于是她就和我自拍起来,还邀请我以后到玉溪去看她们剧团的演出。
再往化妆台的另一侧走去,奇遇就发生了,看到了我心中的“林妹妹”——单仰萍。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那个打了油彩,又扑了厚厚白粉,正在化妆的人是她,刚才在化妆间旁边的一间房门上看见写着“单仰萍”,我以为她会在独立的化妆间里面化妆,根本没想到她会在公共化妆间里出现,所以当我晃到她妆台边,她从镜子里看到我跟我打招呼时,我看了半天都不敢相信,她会从天而降般地坐在了我的眼前。其实从第一次在苏州偶遇单仰萍开始,我们的每次见面都像奇遇,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戏。我万分惊喜地说:“单老师前两天才看你《焚稿》。”她也很幽默地调侃说:“最近我一直在《焚稿》。”是呀,自从2015年看了她殿堂版的《红楼梦》后,她似乎一直没演什么大戏。我说:“你演那么多次《焚稿》,每次都那么投入,所以我们看了那么多次,每次也不厌倦。”她却说:都演得机械化了。我说:“不会吧,难道眼泪也能到点,一按开关就流吗?”我不信,她不语。其实我能理解她那种总演一段戏的厌倦和无奈,我也能感受得到她对自己现状的些许不满和无助。
单仰萍为这次演出准备好了录音伴奏,可却漏录了一句幕后的伴唱,马上就要演出了,这如何是好?幸好有万能的方亚芬在呀,刚下飞机的方亚芬救急来友情伴唱。方亚芬以前曾说过她演过《红楼梦》里的许多人物,应急时还演过紫鹃。这回可以刷新记录了,还幕后伴过唱,她自己说:“叫金牌领唱。”试音时见她俩在台上有说有笑,还不时嬉戏,可见得她俩情义比别人好。
其实我每次去看单仰萍的戏时都有见到方亚芬的,也单独看过她的大戏,只不过每次都是远观,这一次我和她近在咫尺,机不可失呀,我走上前向她自我介绍,一阵磨叽。没办法,记者有记者证,可以直接上去持证采访,作家没有作家证,想要结识大演员,大作家可以刷脸卡、凭名气,小作者如我这般就只能靠脸皮厚、能磨叽了。看来我的磨叽功夫很有长进,短短的三言两语之后让她记住了我的名字。第二天演出完,我上台与她合影时,她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她叫尘埃。”
每次看单仰萍化妆都似有魔性一样,站在她身后,我的双脚像被粘住了一般不能挪动,眼睛更是直盯着镜子里面的美人,连眨都不会眨了。这种魔性不止幻惑我,我刚站了一会儿身后就围起了许多人,有她的粉丝,也有其他剧团的演员,还有挂着长镜头相机的记者,美就是一个魔,迷你没商量。
忘了吃饭、忘了时间、差点忘了看演出,直到戏快要开演了,魏海敏的助理发信息问我:“票不要啦?”(当天晚上的戏票是请她帮我买的)才醒过神来,赶紧找她去拿票,乘机见见久仰的魏海敏。说来我与魏海敏还有一段奇缘呢,我2017年到上海看她演的《金锁记》,被她的舞台艺术所征服,后来写了一篇观戏的评论文章,当时只是贴在自己的博客上,还没在网络平台上推广,也没在纸媒上发表,更没出书,没想到那篇文章竟然被魏海敏看到了,而且很欣赏。她让助理找到了我,并表达了她对文章的喜爱之情。天啊!太难以置信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虚拟网络,这需要什么样的缘分,才会让这篇文章碰到了那个我最想让她看的人!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缘于戏吧。
进到魏海敏的化妆间,她正在自己化妆,看到我停下手上的活儿跟我聊了起来,时间很紧不便多打扰,我想拍一张她的工作照就告辞的,我知道演员在妆化到一半时一般都不愿意被人拍照,因为那时候不像自己,也还不像剧中人,我试探着问:“魏老师我可以远远的拍一张您的照片吗?”没想到魏海敏却非常善解人意地说:“我和你合个影吧,你那么老远的来。”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站到了她身旁,她却让出了半边椅子让我挤坐着和她留了个影。
拍完照我离开了这间化妆间,没想到第二天又有机缘再次走进这个屋子。第二天在这儿化妆的是齐爱云,话说我与齐爱云也有一段小故事。大约八九年前,那时正流行玩博客,我又刚刚开始对戏曲发生兴趣,就和齐爱云在博客上相互加了好友,其实那时我并没看过她的戏,对秦腔也还没什么兴趣,过了两年大家开始玩微博,我们又相互关注了,就这么默默地关注着,也没有更多的交流,看她的微博,有时候也会在电视上看她的演出,多是一些短的晚会节目,没看过大戏。一次我发了一条张火丁复出演戏的消息,见她点了个赞,心想:她一定也喜欢张火丁。回复一问,果不其然,于是我们聊起了《锁麟囊》,聊到秦腔也演过这个剧,当时就想有机会的话要到西安看看她的大戏。没想到这次终于见到活人了。
第一眼看见她,是在工作坊活动的时候,她穿了一件深绿色的长裙上台讲座,身材看起来蛮纤细,我私下想:“那舞动十几尺水袖的爆发力从何而来?”她开口讲话,声音温柔甜美,我又想“那高亢、豪迈、凄婉的唱腔就是来自这条嗓子?”她介绍秦腔的艺术特色,她讲自己对戏曲程式的理解,还有她的演出和她正为传承秦腔所做的事儿,看得出她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有行动的戏曲人。她说她是个戏痴,其实我也是个戏痴,她演戏痴,我看戏痴,这么说我们也算得一对了。看她走台完,我到舞台上去找她,她刚排演完,虽然看上去气息平稳,不过满脸汗水,有人给她拿了水来,她坐下喝水,对我说:“我等会儿和你讲话。”她的这折戏是这次演出的所有戏中最吃功力,也是最费力气的一出,我知道她一定比表面看上去更累。她的行程安排非常紧,来的当天还在演出,晚上才到,第二天上午排练,晚上演出,演出完马上又回去接着演出,我心想你是铁人吗?虽然我们才刚刚见面,但是我感觉着我们怎么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毫无陌生感和拘束感,当她和音响师讨论演出时要把音量再放大一点的时候,音响师说已经调大了,她说平时演出比这还要大。我想也没想就直白地对她说:“我觉得够大了,刚才我在台下听,你唱到高音时都有点刺耳膜了。”她不再说话。下午看她化妆时,她突然有些担心地对我说:南方戏都很柔美,像越剧,昆曲,不知道这里的观众能不能接受我们北方这么粗犷、高腔的戏。我理解她的担忧,她前面一个戏是阴柔的越剧,她后面一个戏是典雅的昆曲,我说:“应该可以吧,他们的高甲戏腔也很高呀。”我又说:“曾听一个豫剧名家讲过,他们演戏有几种方式,在室外、在农村演就要满弓满调高门大嗓豪放地演,但在城市、在剧场里演就要收着些。这个剧场不是很大,声音的共鸣和回声很响,伴奏声音可能不易太大。”她说:在我们那儿如果不大声唱观众听着不过瘾。我想这就是要吼的秦腔了,不过以前秦人唱秦腔之所以要吼那是因为他们那时没有麦克风嘛。其实我也拿不准这儿的人到底喜不喜欢这么粗狂的秦腔,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那种温婉、细腻、甜美的戏曲。
我也是第一次现场听秦腔,所以她演出时也有点担心,结果却出乎我想象的好,演出结束后她微信问我:“观众对我们秦腔的反应如何?”
我回:“你演得非常棒!掌声热烈!”
她说:“我调整了声音。”
“你调整了声音,正好在观众耳膜能够承受的最佳范围内。”
“听取你的建议晚上特别注意调整声音。感谢你!”
聊到这儿,我内心又惶恐又感叹,像这样有名的艺术家还能听取并吸纳一个普通观众的建议,真是太有智慧了。贾平凹的《秦腔》没能让我爱上秦腔,齐爱云的戏曲艺术和个人魅力却为我打开了秦腔艺术美丽的大门。
这次泉州之行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没能欣赏到曾静萍演的梨园戏。不过舞台上虽然没有看到她,舞台下却时时处处可见她的身影,那天工作坊活动时,听到许多名家发言都盛赞曾静萍的表演艺术,能够为同行所佩服和认可的演员,那才是真的好。我用眼睛在剧场里寻找她,(剧场不大,来了许多观众,坐不下,都站满了)发现她没有和名家们坐在起,她也没有和观众们坐在一起,她就站在后排近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谦逊地微笑着。有讲完了要离开的名家,她就牵着手把她们送出去;有刚进来的名家,她就牵着手把她们引到座位上。此刻她不是一个二度梅在身的艺术家、不是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也不是一个剧团的团长,她只是个服务员,为戏曲服务、为艺术家们服务、为观众服务。
我一天到晚地泡在剧院里,就从早到晚地看到曾静萍忙碌的身影,早上名家活动,她在忙碌;下午泉州地方戏演出,她在忙碌;晚上名家演出,她在忙碌。终于是所有演出都结束了,瞅见她站在舞台的后面,稍有空挡,赶紧上前求合影,她说:我今天穿得……(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羽绒服,非常朴素)话说一半照片已拍了,我又不失时机地赶紧磨叽几句,说到这次没看到梨园戏有些遗憾,她说:“我们演出很多,你可以再来看。”
“再来必得是看您的大戏。”
“好。”
这算个约定吗?就算是我与戏有约吧,有好戏的地方我一定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