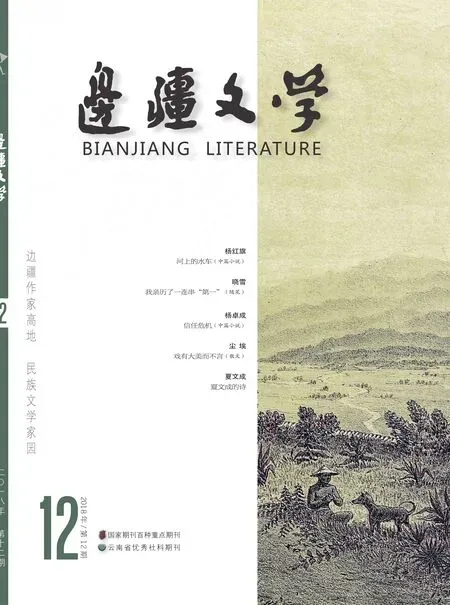夏天的外婆
杨仲淑
外婆已经去世整十年了,可我时常会想起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是夏天镌刻了我对外婆最深刻的记忆吧!热烈的阳光,充沛的雨水,蓬勃的生机——又或者是外婆的品性里蕴藏着这些属于夏天的特质,才会让我在夏天的时候对她的想念格外强烈。
在我七岁还是八岁那年的夏天,家人照例留下在校读书的我,举家到亲戚家做客去了。那时的农村恪守习俗,一场红白喜事起落少则三日多则五日,再加上交通不便,于是遇上路程远的亲戚一去三五天是常有的事。亲戚间的礼数往来必不可少,房舍里还得有人照管,而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最合适的留守人选。
我不记得家人那次去了几天,总之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那是一段特别漫长的时间。说是一个人并不确切,因为每天傍晚,住在邻村的外婆便会来我家陪我。
外婆除了陪我过夜,还要给我煮饭、打扫、喂养猪鸡。她每天傍晚来到后,先是煮猪食喂猪,接着盛一盆清水一瓢苞米召唤鸡只,待鸡们聚拢啄食间清点数目。倘若数目对了,等它们食尽苞米便邀入鸡圈,若数目不对,便拿着瓢把苞米粒颠得啼哒响着,嘴里“咯咯”唤着,房前屋后地找鸡。次日早晨起来,她帮我煮好够吃一天的饭菜,喂过猪鸡,打扫完毕,这才回去干自己家里的活计。
我们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两三里农田,外婆顺着田埂便可走到我家来。水田里蚕豆已归仓等着栽种水稻,旱地里小麦等待收割,视野不受遮挡,所以每次外婆只要一出村,我站在家门口就能眺望到她的身影。夕阳在西边的山上缓缓落下,外婆一颠一颠地披着夕阳走来,像一只在大地上行走的急着去保护雏鸟的老苍鹰。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吃过饭做完作业便守在家门口,一见到外婆的身影出现就激动地飞奔去迎接她。
我们在中途相遇,外婆总是第一时间从围腰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手帕打开,里面包着水果糖、冰糖或者是香蕉干之类的小零食,像是一个流动的糖果店,任我取食。回程的路上,听着连绵不绝的蛙鸣,我一边吃着香甜的糖果,一边采着路边的野花,一天的孤独和委屈瞬间便荡然无存了。
然而,并不是每次飞奔而去都能顺利地遇上外婆。
有一次,我忽然撞见路边草丛里卧着一条蛇。我吓了一大跳,边往回逃跑边惊惧地喊:“外婆,这儿有蛇!”“不怕不怕,水蛇没毒的。”外婆一边高声安慰着我,一边顺手折了一根树枝左右扑打,几乎是跳跃着向我小跑而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婆的身手会如此地矫健,一个小伙子也不会跑得比她更快。
还有几次,我被临时挖断的田埂隔阻,那壑沟是我无法跨越的。我站在这头撒娇似的朝外婆喊:“外婆,田埂被人挖断了,我过不来。”“别急,站在那儿别动,等着我。”外婆扬声回答我。听到她这么说,我就真的不着急了。不一会儿,外婆走到田埂那头。有时,外婆“哼”地喝一声就跨过来了。有时,横在外婆面前的沟坎太长了,外婆也跨不过来。这时,她会一面与我说着话,一面坐下来,麻利地脱鞋,解裹脚布。
没错,我的外婆是老式乡村的妇女,缠足,行动看上去不是很麻利。我的爷爷总是讥讽外婆,说她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可我觉得外婆的裹脚布虽然不短,却一点都不臭。外婆卸下裹脚布,卷高裤腿,提着鞋子,将她形状怪异的小小的双脚蹚进水陷入淤泥,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我紧张地盯着她的小脚,生怕一个不小心它们会使外婆滑倒在水里。所幸,每次外婆都安稳地抵达我这边。那双小小的脚,像钉子一般牢牢地抓住大地。我从来没有看到外婆滑倒过。
爬上田埂后,外婆仍是先掏出装着零食的小手帕给我,笑呵呵地说:“乖孙女,看看外婆今天给你带了些哪样?”慈爱在外婆的脸上荡漾开来,比天上的太阳还温暖。外婆洗干净脚上的泥,重新打上裹脚布。倘若遇上裤子被淹湿了,外婆就不再打裹脚布了,只是随便拧几把裤腿上的水,便带我继续赶路,两道水泽便一路随着我们回家。
一个星期天,外婆中午就来到我家。“你妈她们还不回来,你家地里的麦子干得粒儿直往下落,再不割可不行了。”她进门就找镰刀。我脑海里关于下地干农活的记忆正是始于这一天。那天太阳火辣辣的,天上没有一片云彩,地里也没有一丝风,那金灿灿的麦浪宛若一片火焰,而外婆带着我像是在一点一点地扑火。
割麦子是一件多么辛苦的劳作啊。麦芒扎得人无从下手,握镰刀把的手没一会儿就疼得不行,汗水流进眼睛里让人刺痛难忍。这样的情形下,我又能帮外婆割多少麦子?充其量不过给她做个伴而已。我割倒一把麦子,外婆便夸我能干。我说手疼,外婆就让我歇歇。于是大部分时间里,我紧随着外婆,坐在她割倒铺在身后的麦秆上玩,坐不到两分钟便忍不住要起身瞧一眼还剩多少。令人无望的是,无论我怎么看,那块麦子依然是站着的多倒下的少。我感到那些麦浪早晚要把我们淹没掉,但是外婆倔强干瘦的身影总是挺立在麦浪之上,一片一片地麦子倒下去,身材矮小的外婆不断站起来擦汗,外婆在麦地里显得好高大啊。
骄阳直射,灼热难挡。喝下的水仿佛未及流入腹中便化作汗水从发根直往外冒,接着四下乱流,避无可避,眯得人睁不开眼睛。在麦田里多呆一分一秒都是煎熬,我多么希望外婆能快点再快点,早点割完麦子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外婆这次并未如我所愿。她的动作不但没有加快,反而越来越慢了。而我那时还不明白镰刀使用时间长了,刀口会变钝,外婆想快也快不起来。不仅如此,钝口的镰刀割麦子时常带起麦根上的土块,每次外婆都要反转镰刀把土块敲碎。这样一来,割麦的速度就更慢了。我绝望得想哭。好几次想催外婆,可见她被晒得通红的脸上汗水纵横交错,终年戴着的包头被远远丢在一边,汗湿的头发一绺一绺黏在头皮上,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催她的话我便说不出口了,我又拿起镰刀。
眼前的麦浪还很壮观,但在我们身后铺倒的麦秆也一点点增长。“哎哟”忽然听见外婆一声低呼,接着便见外婆用手捂着额头,稠红的血自她指缝中滴落染红了脚前的麦秆。原来外婆这次敲土时,一不小心镰刀尖刺破了她的额头。我吓得不知所措,焦急地问:“外婆、外婆你会死吗?”外婆不当回事地笑笑,说:“傻孙女,外婆不会死的。外婆还要割麦子哩。”
最后,外婆没有因为那天镰刀割破额头死去,她带着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刀口割完了那丘地里的麦子。可是关于外婆会死的恐惧却成为笼罩在我儿时心里最大的阴影。外婆真要是死了,今后谁来陪我呢?
外公中年病故,所幸身后的一个儿子四个女儿,除了妈妈皆已成家。外婆寡居后,一心一意帮儿女们过日子。不论儿子女儿,遇上哪家活计多人手不够,她便上哪家帮忙。由于外公去世时妈妈还未成年,加上妈妈是最小的女儿,外婆应该是偏疼她一些的。小女儿成家后,女婿常年出外做副业,三个外孙女尚小。每到农忙时节,外婆便来帮小女儿干活,秋天掰玉米、割水稻、点蚕豆,春天捣秧田育秧苗,夏天打蚕豆筛糠、割麦子、挖田插秧。一收一种,一季农活干下来个把月时间就过去了。
加之,外婆是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虽然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但父亲却健在。外婆隔些时日就要回娘家,给父亲也就是我们的外曾祖父送些点心,或者帮他洗衣服洗被子,直到我的外曾祖父90多岁去世。在外曾祖父的晚年,外婆出现在我们村的时间和频率自然更多了。
爷爷那时从城里退休回家,在村里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自视甚高。可他思想守旧刻薄,无视外婆来我家几乎都是粗活重活抢着干,甚至有时外婆回娘家去看望她的老父亲。我爷爷总是语带轻蔑地说:“怎么你外婆又来了?”我爷爷从不待见我外婆,当面对我外婆没好脸色,又时常对孙女们说外婆的风凉话,他说外婆不顾脸面跑来女婿家让女婿养活之类的话。爷爷认为丈母娘死在女婿家是农村里极其忌讳的事,他总说外婆指不定哪天会死在我家。就是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严重的阴影。当然,我倒不是忌讳外婆死在我家,仅只是害怕外婆的死,毕竟“死”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字眼。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外婆不过六十多岁,身体健康,远远还不到谈论死的时候。可是那时我年幼,加上外婆旧时传统妇女的穿戴,便把爷爷的话当了真,认为外婆已经很老了,随时都有突然死去的可能。于是,每当外婆来与我作伴的时候,我又期待又害怕。每天晚上带着忐忑难安入睡,早晨起床,看见外婆好好的,悬了一夜的心才能放下去,到了晚上心又被提起来。这种恐惧伴随了我好长时间,不敢对任何人都提起。
面对爷爷的冷眼和嘲讽,外婆如何会不明白?但外婆对爷爷的刁难不悲不恼,不解释不抱怨,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只是坚持自己要做的事——上要服侍自己的父亲直到送终,下要帮助自己的女儿过日子用尽最后一份力。
外婆一到农忙季节就来帮妈妈干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那时的外婆腰已经完全直不起来了,可是她仍能佝偻着背帮妈妈撑船运送满船的水稻,仍能匍匐在潮湿的农田里帮妈妈点蚕豆。等到再不能干这些重活时,她仍默默地帮妈妈筛糠,糠灰扑了她一头一脸,让我的外婆口鼻莫辨,五官不清。她似乎连抹一把脸的时间都没有。一个总是在忙忙碌碌的外婆,就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
即便是农闲的时候,外婆也不闲着。她提着塑料编织口袋,去野外捡桉树叶。无论寒暑,外婆几乎每天都去捡桉树叶,攒到一定分量便背去熬桉叶油的作坊,作坊按一两分一斤的价格收购。为了捡桉树叶,外婆受尽了风吹日晒雨淋,还经常忍饥挨渴。有一次,外婆在捡桉树叶时被恶狗将她的腿咬得鲜血淋漓,当时外婆都昏倒在桉树下了,又没有人来帮她。天黑了以后外婆被冷风一吹,才自己醒来,然后一瘸一瘸地回家。我现在都难以想象一个小脚女人,是怎样地被狗扑倒,又是怎样忍着腿伤痛独自回家?
儿女们都反对她去捡桉树叶,一是担心她的安全,二是觉得脸面无光,可是外婆根本不听劝,一直到她老到走不动路了才不得不放弃。外婆一片一片的捡树叶,一分一分的攒钱。外婆心中有一个执着的念头,一个伟大的梦想。只是那时我们都不知道。
舅舅是外婆的独子,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他的身体不太好。先是他生病住院,然后被转院到州医院做手术,此后过了没几年出去做副业,高空作业又不慎坠落几乎要了命。正值年富力强的年纪,接连两场病祸,使舅舅的家境异常艰难。而同一时间,原先住在一个院落的邻居纷纷建起新房搬走了。老院落空旷了,舅舅一家六口人却仍挤在仅有一间卧室的老房子里。
孙女眼看着成年了,孙子也一岁岁长大,却连分个床的地方都为难。舅舅的处境,外婆自是无比焦急却又无计可施。不记得何时起,家乡兴起熬桉叶油,外婆也不知从哪儿得知熬桉叶油的作坊收购零散桉树叶,反正从此外婆便把所有农闲的时间都投入捡桉树叶这个漫长的苦差事中了。
桉树并非我们家乡原生树种,是作为经济林木引入,所以不管是山上成片的桉树林,还是道路两侧、村旁舍前的间或几株,都是有主的。外婆家一株桉树都没有,外婆只好遍走山林、道路、田埂、村舍,捡有主的桉树落下的枯叶。寒冬腊月,村人要么卧于暖被窝,要么围着热火炉的时候,外婆正提着口袋拾捡覆了霜的树叶。她说这样的天气才好捡树叶,落叶多啊,多得捡不过来。三伏酷暑,人们不是哪儿凉快待哪儿么,外婆依然提着口袋出门。她总说树荫里凉快着呢不热,可是再凉快的树荫也比不过瓦檐下清闲呀。
对于捡桉树叶,外婆从未埋怨过其中的孤独、枯燥、危险。怕蛇,外婆自己打草先把蛇吓走;被狗咬了,换个地方,下次带根打狗的棍子;昏倒了,醒来爬起继续。少时丧母,中年丧夫,老了还要替儿女背负生活的苦累,外婆仿佛把生活给她的所有苦难悉数都咽下,却又转化出对无穷的对抗苦难的力量。
外婆没把捡桉树叶看作苦差事,反而从中获得乐趣来。一次,外婆兴冲冲地赶到我家来,让我妈把家里的空口袋都找给她。原来,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路上,村集体把路两侧长成气的桉树叶卖给熬油坊,熬油坊砍走成吨的枝叶,不好收拾的零散枝叶遍地都是。“老板说了,那些散叶子他们不要,给我了,让我只管去捡。”一下子,得了这些多额外的树叶,外婆简直像撞了大运,拿了口袋,急匆匆地赶去捡“宝”去了。
外婆常年在附近的村庄捡桉树叶,附近村民大凡都认识她。有好心的人家计划出售桉树叶了,便会提前告知她一声,让她到时去捡零散枝叶。每每遇上这样的好事,外婆都很感激,总是提前赶去帮人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我家门前也有十几棵桉树,桉树叶一年能卖一百来块钱的样子。每年我家出售桉树叶那天,外婆便早早来等候收拾油老板不要的枝叶。外婆帮着妈妈招呼割桉树的工人,提醒他们爬树挥刀小心,也提防他们黑心断了树梢,伤了桉树的元气,轻则影响来年的收成,重则导致桉树枯死。等到油老板结清货款,把成捆成捆的桉叶装车拖走后,外婆便可以收拾属于她的枝叶了。
我家门前的桉树是奶奶和妈妈一起种的,所以奶奶有一半的物产权。每次出售桉树叶的时候,奶奶总会过来拿走属于她的一半桉树叶所得。我们都觉得这理所应当。正如我们觉得外婆得到那一地散落枝叶就足够了一样,妈妈也从未从桉树叶的所得里给过外婆哪怕一毛钱,也是理所当然的。
桉叶油作坊兴起之初,周围村落捡桉树叶的人很多,但一捡十余年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的外婆了。儿子多灾多病,孙儿年幼,自己已然身老,对于何时能建盖新房,外婆肯定也不敢预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一刻也不肯停歇,为遥遥无期的希望默默地坚守着,执着地努力着。
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舅舅家筹备建新房,外婆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四百多块钱,微微颤颤地递给我舅舅,说钱不多,我能给儿帮衬一点是一点吧。四百多块钱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那是外婆历经多少个寒暑捡起的多少片桉树叶换来的呀!一斤桉树叶有多少片叶子?外婆要弯多少次腰,走多远的路?没有人知道;多大一背桉树叶才能卖到一块钱?更没有人算得清。
外婆为舅舅筹建新房,倾囊奉上了她的所有积蓄,更奉上了一个母亲的爱,我仿佛能感受到外婆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她的儿子终于也要建新房了,孙子们也将有自己的房间了,接下来就不愁娶孙媳妇了。有房才有娶妻生子的条件,子孙一代一代便能传下去。外婆该有多么欣慰!
外婆就像是一个被上足了发条的陀螺,永远都在为子孙操劳。不捡树叶后,她便常年帮我表姐也即她的孙女带孩子。我表姐结婚后,头两个孩子都是出生几天便夭折了。我那个时候年少,远远不能体会表姐受到的打击,但是外婆肯定格外心疼自己孙女所受的创伤。等表姐生第三个孩子后,外婆几乎投入了全部心思帮忙带这个孩子。外婆晚年,已经长大成大伙子的重孙待她感情很深厚,经常去帮她拆洗被褥和衣服,洗脸脚,修剪头发和指甲。
儿时困扰我多年的恐惧并未发生,外婆并未死我家。外婆88岁无疾而终。外婆晚年时,儿女们生活都还不错,用她经常祷告的话说是清吉平安。我家由农村搬到了县城。妈妈很多次想去接外婆来我家享享福,可外婆来住了两天便固执地要求送她回去。最后两年,外婆更多地是住在舅舅家里。每次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都靠墙坐在堂屋前的房檐下。她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人了,“谁来了?”她听见脚步声,总是问。“是我,外婆。”我们一出声,她便欣喜又准确地喊出我们的名字。
外婆一辈子都在付出,而几乎没有给人添过麻烦,哪怕身后都不愿给儿孙增加经济负担。弥留之际,外婆摸索出她的小手帕,里面包着三千多块钱交给孙子,交代给她置办丧事用。外婆吃长斋,爱吃的零食左右不过几样,衣物也是至简至朴。这三千块钱都是捡桉叶的收入、后辈的孝敬、政府的补贴积攒而成的。
外婆出殡那天,我鲜少出门的爷爷冒雨去参加了她的葬礼,这举动在爷爷来说真是极其反常的。我无法得知爷爷怀着何种心情去参加这个让他蔑视多年的亲家母的葬礼,但我愿意相信爷爷对外婆的态度早已由轻蔑转变为敬重。
今年夏天,不知为何,我已无数次地想起我的外婆。想起有一次读中学时下学路上遇见外婆在路边捡桉叶,我从自行车上下来喊一声“外婆”,她抬头见是我,忙从沟边爬上来,依然从围腰里掏出小手帕,乐呵呵地揭开四角递到我面前。那块小手帕已经很旧了,看起来脏兮兮的。若是里面包着的是有外包装的糖果,我便拿一颗剥开吃,若是里面是冰糖或者果干,上面会粘有一些灰尘或草屑,我便摇头说不饿,外婆小心把手帕收回围腰里,沟壑密布的脸上依然开心地笑着,叮嘱我要好好念书。
我曾一次次回想最后一次在外婆手帕里拣糖吃是什么时候的事,是什么样的糖果,可我终究是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个夏天里的外婆,伫立在麦地里倔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