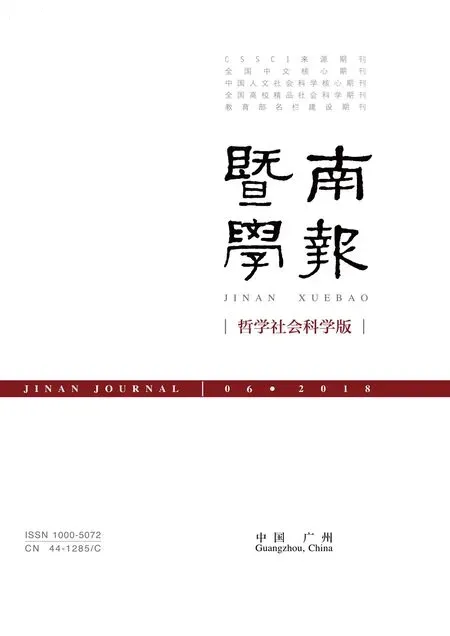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演变
——以央视春晚为个案
洪 晓, 苏桂宁
审美趣味并非无争辩,也非纯美学问题,其根底隐藏着社会各方力量的斗争,与时代文化、阶层变更和社会变迁等因素息息相关。“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每当文化处于转型关头时,便会出现显著的趣味冲突”,且两者的关系成正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各层面急剧变革,大众处于分化与更替中,文化从一元向多元发展。诸多因素影响了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乃至冲突。本文以央视春晚为例分析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演变,特别是主流、精英和大众三种趣味的演变,进而对习性的治理与建构提出有益意见。
一、主流趣味的演变
主流趣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论语·阳货》已提出,“诗可以群”乃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之一。此“群”“应指‘人群’、‘合群’,即人能与群体和谐相处”。一方面见出诗有促进群体关系融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见出儒家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追求“敬业乐群”。这在周代的奴隶社会和长期的封建社会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落后的农耕经济不同于单打独斗的贸易经济,它讲究集体协调合作。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主流趣味能成为主导趣味,还有三个因素:“一是启发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利益及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思想;二是受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集体主义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实践的影响;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总结。”特别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接受国家和集体的治理和安排。80年代改革开放遵循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私营经济虽有发展,但因与“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光明正大的地位,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疑虑重重,小心翼翼。这必然使得长期以来以国家和集体为上的文化传统和主流趣味牢牢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当时的大众文化主调洪亮,以国为主。此时期春晚的主旋律除了号召大家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理想而奋斗外,还涌现了一批赞美党、国和家乡的歌曲,典型的如《党啊,亲爱的妈妈》(1984)、《我的中国心》(1984)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6)。此类歌曲平均每年有7首,特别是1984年有11首。在富有人文关怀的爱情歌曲中,一旦触碰到国家、集体的利益,就表现出无条件的服从和牺牲。如大家熟悉的歌曲《泉水叮咚响》(1984)、《十五的月亮》(1985)和《血染的风采》(1987)等。
主流趣味在政治导向的计划经济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但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入转型,“政治场”的传统势力在削弱,而“经济场”的影响力越发突出。文化生产和消费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由市场之手调节。大众趣味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迎合,主流趣味的主导地位面临重大挑战。强调个体和平民意识的大众趣味与市场经济的匹配度更高,它的发展壮大对于文化版图的构成有重要意义,“牵引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走向,致使官方机构也不得不考虑市民社会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并且对其作出妥协和迎合”。主流趣味被稀释,走向与大众趣味融合和妥协之路。首先,春晚上奏响强音,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之类的高调慢慢落下,余音变为更加平实的共同努力,开创未来之声。其次,对党、国家和家乡直抒胸臆地表达赞美的歌曲大幅度减少,多存在少数民族歌舞节目和怀旧歌曲中。春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不再直接而显露,而是日益多样化。
同样,新世纪初在文化产业的蓬勃兴盛中,在阶层分化的大众趣味影响下,主流趣味进一步向大众趣味妥协、融合和靠拢。春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主要采用“虚饰化”模式,通过营造盛世景象、复归传统和建构和谐社会等谋略来隐喻和美化社会现实。这些模式和谋略相比过去是越来越成熟、完善与软化隐蔽。为迎合大众趣味,主流节目除了人性化处理,还进一步增强了故事性与趣味性。但在爱国主义热潮的兴盛中,也时有高调。如在“飞天英雄红旗颂”系列航天节目中表现出来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2011年以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场的异军突起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在互联网带来的草根文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此时期主流趣味降至最低点。除了相关节目大幅减少,手法也愈加隐蔽。它用文化大国的形象塑造来对大众实现文化认同,寓身份召唤于无形之中。2014年后出现新的拐点,国家意识形态节目慢慢增加。主流趣味在“中国梦”的时代潮流中迅速回升,并于2016年攀至顶峰。
可见,在计划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趣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再风光无限。虽然在“两主一仆”的文化格局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不断地被稀释,走向与大众趣味的融合和妥协之路。近几年在文化治理的加强和新时代风气影响下,主流趣味明显增强。
二、精英趣味的演变
80年代在文化资源体制化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在其传统的“忧国忧民”职责召唤下,在现代化的理想召唤下,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他们并不刻意迎合大众,而是更多地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弘扬和传播精英趣味,对大众进行教育和启蒙。走过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沙漠,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也为精英趣味的传播和吸收提供了深厚土壤。精英趣味与主流趣味相辅相成。在春晚上,精英趣味首先体现为对理想和崇高神圣的追求。节目中号召大众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和歌颂英雄是常见主题。典型的如歌曲《年轻的朋友》(1983)、《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1984)和《我们是黄河泰山》(1988)等。其次表现为对高雅文化和文化知识的推崇。不少节目从高雅文化中脱胎而来,歌曲也富于历史与文化底蕴。语言类节目追求展示才华才智的笑和寓教于乐的笑。再次,体现为批判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对商业的排斥,极力维护文化的纯洁性。不仅节目如此,工作人员也是以身作则。春晚制作靠的是大家的奉献和敬业精神。这种雅趣受到了当时大众的肯定和欢迎,当时《中国电视报》选登的观众评价中,不少人都夸其格调高雅。
90年代,在社会的经济转向中,在世俗文化的包围中,在大众趣味的兴起中,传统精英趣味逐渐被消解和改写。因为大众在世俗化的追求中,“用世俗的物质生活消解神圣的精神启蒙,用细小的现实人生取代遥远的乌托邦理想,在对‘日常生活’本身的肯定中消解‘非日常生活’的崇高感、神圣感和真理性”。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的年代,大众慢慢丧失了乌托邦的激情和对精英文化的顶礼膜拜,日益沉迷于日常生活的感性包围和物质欲望的追求中。相比80年代,号召大家为理想而奋斗的高调在90年代的春晚上大为弱化,推崇高雅文化和文化知识的节目也在大量减少。精英趣味更多地要以兼顾大众趣味的方式而被改写出现。比如涌现出了一批呼唤人间大爱和真情的节目,典型的如歌曲《同一首歌》(1991)。
进入21世纪,精英趣味在消费时代更是日益式微。在世俗的深化中,在快餐化娱乐的追求下,在消费文化的欲望追逐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中,精英的理性、批判和启蒙意识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只有在具浓厚传统文化味的节目和揭露人性与社会问题的语言类节目中能觅踪影,如歌曲《龙文》(2010)、小品《台上台下》(2002)和相声《五官新说》(2009)等。
2011年以来,随着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并日益受到重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的时期,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号召下,精英趣味相比世纪初的式微有了明显提升。在那些旨在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塑造文化大国形象的节目中不难感受到文化味儿的厚重。在一系列赞美大爱和助人为乐、强调职业道德的节目中,皆有精英旨趣的存在。如2012年的7个小品就有五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道德的。
可见,精英趣味在文化繁荣的计划经济时代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当行政文化体制衰落,市场文化体制兴起,特别是在娱乐至上的喧嚣尘世中,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近几年的回升得益于文化治理的加强和时代风气的转变。
三、大众趣味的演变
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大众的审美意识刚刚萌芽。步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日益壮大终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为主,文化为仆的局面,出现了“两主一仆”的复杂局面。在文化权力的慢慢下放中,一种以市场、大众为主导的文化在逐步形成。后者兴起的背后,是对以市民为代表的普通大众的关注和迎合,是对大众利益和趣味的肯定和追求。因“市民社会任何一点权利的扩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了严格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并使得原有的国家权力系统产生权利分化状态”。它在解构和分化的同时开辟了新的独立的文化公共空间,“新的审美趣味由此产生”。这种新趣味乃是普通大众的趣味。它与以国家和集体为上的主流趣味相比,其核心是平民和个体意识,肯定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及其滋生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于是,90年代春晚的流行歌曲风格不再以思家乡爱祖国为主,不再止于人道情怀和抒情曲调,而是日益个体化,更多书写个体心灵感触、爱情体验和青春萌动。如歌曲《水中花》(1991)、《再回首》(1991)和《让我一次爱个够》(1992)等。同时,大量节目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平凡人,鼓励人们勇于追求自身幸福和美好生活。如小品《相亲》(1990)和《妈妈的今天》(1992)、《张三其人》(1993)等。
审美趣味不仅有社会性,且具鲜明的阶层性。随着市场经济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社会分化为上、中、下等。大众审美趣味也大致形成了中产阶层和普通百姓两种趣味。中产阶层处于社会中间层,具有很大的摇摆性。既有对上层趣味的追赶,崇尚符号消费,又有与下层趣味的区隔意识和文化善意。普通百姓则比较传统保守,循规蹈矩且易满足。由于“社会每一阶层都将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模式当作自己最理想、最体面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它靠拢”,同时中产阶层的富裕生活场景更能与国富民强的意识形态幻象营造有呼应效果,因此在21世纪的春晚上,这股中产阶层的审美趣味潮流占据了明显优势。它表现为追求高品质和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推崇消费主义,西化特点明显。普通百姓趣味则表现为追求平实的日常生活和简单朴素的趣味。
与世纪初对于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转变的乐观期待相反,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门槛准入越来越高,代际流动下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固化、板结化,民粹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在“民粹化影响下媒介文化不再是由中产阶级趣味主导的大众文化,而是由受众自己主导”。中产阶层的审美趣味对广大底层受众失去了往日的符号象征和吸引力。它少了激进与西化的一面,表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一面,更多释放出对中下层的文化善意,出现越来越多表现阶层互助和谐的节目。此时期春晚的草根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文化语境中,此时的大众审美趣味开始追求“真、亲、新”。
第一,“真”即真实性,反对假大空。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中国大众对于真实有着特有的偏好和喜爱。此时期春晚,很多反映回家过年和骨肉亲情的节目不断走红,就根源于其坚实的现实土壤。草根上春晚也因其代表了广大社会底层的大众。
第二,“亲”即亲切感,情感真诚,以情动人。艺术创作的重要维度除了求真,就是求善,“在富于感染力的情境中潜移默化地为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且此情应是“真情”而非“假意”。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充斥太多的是“后情感”,大众开始厌恶。于是新时期春晚涌现出众多表现亲情真情的节目,主持人的语态日益亲民化、亲切化与幽默化。
第三,“新”即新意,反对机械的复制模仿。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使大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他们追求新奇特,渴望体验各种不同。托夫勒就认为:“当人们开始富裕,短暂性也开始兴起,人们就不再有旧日的占有冲动时,消费者……开始热烈收集‘体验’。”同时,“个体开始不满足日常生活,而渴望在现实当中体验这种完美的梦境。这种态度引发了人们对于新奇事物的渴望”。这种求新追求也是符合精神追求和人性发展需求的。与世纪初相比,此时期春晚的拼贴、混搭更常见,且越来越有创意,甚至还出现了一批特地以创意命名的节目。2018年的春晚总导演杨东升在受访时表示,今年所有节目都“围绕着‘创新’来创作”。
可见,大众趣味伴随市场经济而生,并随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日益发展蔓延。它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也出现阶层分化。开始主要以中产阶层趣味为主流,而在日益民主化的当下,草根性日益突出。在市场的自由发展下,它也出现了庸俗化、消费化和娱乐化等趋向。2011年后,随着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关注,大众趣味的恶性发展趋势得到了有效扼制。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文化语境中,有了对真、亲、新的追求。
四、审美趣味与文化习性
从40年主流、精英和大众趣味的复杂演变可见,审美趣味构成复杂,它“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范畴,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敏锐地昭示着社会的变迁及其内在矛盾”。在社会剧变中,“各阶层或集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经历深刻的变化与调整,不同的趣味类型也就自然处于错综纠结的复杂关系之中”。它们此起彼伏又相互交织。主流趣味和精英趣味在8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文化资源相对垄断的条件下”,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但90年代后,在“文化资源从中心化控制转向离散状态,特别是以市场机制的运行来调节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这两种文化趣味的相对衰落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面对市场经济的日渐兴盛和文化世俗化、消费化的冲击,精英趣味所受的冲击是最大的。主流趣味虽在“两主一仆”的文化格局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不断地被稀释,走向与大众趣味的融合和妥协之路。强调个体意识和享乐主义的大众趣味则乘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发展势不可挡,并对主流趣味与精英趣味产生极大的挑战。大众趣味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也出现阶层分化。在阶层地位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中,不同阶层的趣味既有差异,又有变化和融合。在市场的自由发展下,它也出现了庸俗化、娱乐化等不良趋向。2011年以来,随着对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和强调,扼制了大众趣味的恶性发展趋势,精英趣味和主流趣味在“中国梦”的时代潮流中迅速回升。但娱乐化的风气已经形成,市场化和媒介化的生产消费环境增加了文化治理的难度。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也在实践中让问题变得不简单。近年央视春晚收视率的下降其实已从侧面说明了问题的难度和任重道远。要回复到80年代的黄金岁月,要让广大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喜欢春晚仍面临诸多问题。
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引导中,重要的是审美趣味问题。“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趣味就是一种人们经由教育等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内在‘习性’。”趣味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和锋利的棱角,涂抹上厚厚的润滑剂,让人沉湎其中。它让大众对某种风格或特点的大众文化产品产生了特有的喜爱和归属感,而在这种日积月累的趣味耳濡目染和浸泡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的感觉方式、情感结构,形成不同的性情倾向系统,重构了习性。“趣味的表征实际上是对规则的一种无意识内化,它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们的‘习性’”。而习性一旦形成后,就会强化和固化与其内在价值观和思想感情一致的审美趣味。正因如此,习性与趣味密切相关。对趣味的引导和培养就是对习性的治理和建构。
伴随着审美趣味的变化,中国人的文化习性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顾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见,在大众趣味对平民和个体意识的强调和肯定中,今日的中国人对于集体和权威,不再盲目服从和膜拜,少了长期专制体制下形成的群体性和奴性,个体性和权利意识在增强,变得越来越独立和自我。同时,这种个体性的增强对以集体为上的主流趣味就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随着大众趣味的兴起,主流趣味在不断地被稀释就说明了此问题。从90年代流行歌曲的个体化、情感化和世俗化到世纪初的消费化、欲望化、快感化可见,在市场的自由发展下,大众趣味极易滑向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此外,在大众趣味对快乐的渲染和追求中,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喜悦中,今日的中国人不再那么容易有落后和自卑心理,习性中多了自信和乐观的一面。但在对快乐的片面追求中,在日常生活的沉醉中,极容易让人丧失崇高理想,并目光短浅,将人导向享乐主义、娱乐至上、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不良习性。这必将削弱中国传统习性中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文化因子。一旦放任,就会让来自西方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泛滥成灾。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在让国人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同时,也为虚无主义和浅薄化埋下了隐患。
五、审美趣味的合理建构
面对趣味的复杂斗争,什么趣味是合乎生命情感和自由意志的和谐发展,有益于习性和国民性的全面健康发展,有益于个体和国家,不仅是审美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在对各种趣味进行辨析后,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建立和谐、合理的趣味结构。既尊重主流趣味、精英趣味和大众趣味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又各取所长,互补互渗,相辅相成。
首先,在加强主流趣味的宣传和培养时,要与世推移,注意“落地”原则。由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一世纪艰苦奋斗历史积淀下的主流趣味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财富。它是国家富强、人民团结的有力保障。它也极好地避免了大众趣味完全走向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渊,有益于提升其品格。但面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大众趣味的汹涌澎湃,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强调集体和奉献精神的主流趣味建设不能再自视甚高,要拿出更多的诚意和说服力来让大众接受。应密切关注时代脉搏的跳动,随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切忌假大空,要充分地贴近和靠拢大众,了解民情民意,接地气,接人气。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尊重大众对于“真、亲、新”的趣味追求,在具体而微处,真实并让人信服地接受。如果仍然一味生硬表达,做席勒式的单纯传声筒,大众会觉得高蹈虚空,了然无味。又或者下手过猛过重,就会导致大众的反感甚至是强烈对抗。2016年春晚的民间差评已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国家虽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但大众不买账,就只能是叶落无声,甚至激起“对抗式”效果。因此,“落地”原则至关重要。
其次,积极加强精英趣味的建设。精英趣味的批判和启蒙意识,对于真善美等理想的追求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如大爱和亲情、友情、爱情是大众文化的永恒主题。人的欲望不是向上升华,就是向下沉沦。精英趣味的理想和崇高追求,可以很好地避免大众趣味中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发展趋势,有助于提升其艺术水准和审美底蕴。知、情、意的和谐发展相比欲望和快感的当下满足和精神虚无,更能让人获得身心的解放和自由。康德的超验美学提倡“纯粹的、无功利的”审美趣味,将审美与现实功利进行了剥离,既巩固了精英趣味的垄断地位,又实现了趣味的文化治理,有效避免了趣味的阶层分化。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加强精英趣味的建设。文化建设者不要以阳春白雪式的曲高和寡为傲,应积极地寻求融雅入俗,追求雅俗共赏。比如近些年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节目就充分利用了各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做得既好看又有深层的意味,非常受欢迎。如果节目浮于表面,为教育而强说理,勉强拼贴笑料,就会弄巧成拙。真正寓教于乐的节目,应该是既在主题上切中时弊、发人深思,又在技巧上合情合理、水到渠成。如小品《扶不扶》(2014)的情节安排合情合理,又很好地引导大家深入思考了摔倒老人扶不扶的热点问题。
最后,引导大众趣味健康良性发展。大众趣味对于平民和个体意识的强调,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意识有相得益彰的效果。恰当的娱乐可以让繁忙的大众获得片刻的休息和放松。但在大众文化生产中,商业利润的巨额刺激往往会让生产者为了市场占有率,为了吸引眼球而违背真正的艺术精神和职业操守,一味地迎合和放纵大众的感官享受和低俗趣味。因此,要对大众趣味加强监管,促使其向乐观进取、健康向上的一面发展,并积极地将主流趣味和精英趣味融入大众趣味。各级文化部门要严厉地从各个审查环节加强监管,坚决杜绝低俗文化产品,净化文化市场的生态环境,引导趣味向健康良性发展。
此外,对于大众趣味中的大众定位要准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非为少数人服务。虽然社会上层的审美趣味对于下层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中下层大众也需要自己的文艺。广大的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市民是中国当前数量最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他们也是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和文化创造繁荣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