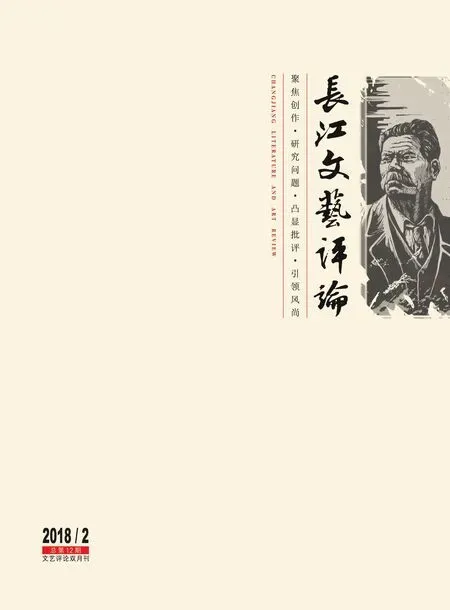身体在叙事中的丰富意蕴
——秦岭小说的一种解读
◎王元中
小说家秦岭的创作多以其老家甘肃天水乡村为背景,他笔下的土地、粮食、水、牲畜、普通农民、乡村教师、计划专干诸等,无不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有关。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生命的存在首先表现为一种身体的存在,这种存在与乡村大地上的历史回声、社会变革、自然生态、生活法则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有着深刻丰富的、耐人寻味的意蕴。
一
秦岭的小说中关于身体的讲述,从对象上看,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关于动物的。这些动物有帮人类运输的牲畜,有为人类提供蛋品的母鸡,有尝试和人类进行心灵沟通的狐狸、骡子等等,它们用裸露的肢体、情状表达着对人类世界的认同与质疑。《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中的主角之一是怀孕在身的母狐狸,它和有着“杀夫之仇”的猎人不共戴天,如果不是猎人的妻子施救,它注定将成为一具被剥掉优质毛皮的尸体。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它冒着风险来到了同样怀孕的女人家里找水。两位大肚子的准“母亲”既惺惺相惜,又彼此戒备。惊惧中的狐狸不小心掉进水缸,女人再次施救,也掉进了缸里。两个“母亲”的死亡,在人兽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应。马是《吼水》中的重要角色。村民董球为了修建自家的水柜,花血本从集市上买了一匹马用来驮运水和建材,超负荷的出力和驮水却不能喝上一口水的窘迫,终于让马心理失衡,狠狠咬掉了主人的一只耳朵,主人的身体由此有了尴尬的残缺。马其实并不坏,它和主人之间曾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它先后两次亲吻了主人的耳根。残疾的主人并没有因此而忌恨它,相反却在水柜修好之后,大老远去马的新主人家,给它送去了一大塑料桶清水。《摸蛋的男孩》里的重要“主人公”是母鸡。在供应制时代,上缴生猪鲜蛋是农户的重要“任务”,产蛋最多的母鸡被称为“英雄”母鸡。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小男孩全全学会了把手指头探进母鸡屁股摸蛋的技术,目的是为了让城里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吃上蛋,然而,一次进城吃蛋遭拒的尴尬,使他发现了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他愤然在母鸡“英雄”的身体上留下了宣泄的血痕。另外,《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中那只莫名其妙的狗,《一头说话的骡子》中那头张嘴就能说话的骡子,它们的身体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信息,而这些信息反而比人类来得真实,来得可靠。
第二类是关于女人的。这一类篇目极多,关于女人身体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但作者不是简单的就身体而论身体,而是在灵魂、精神层面给身体赋予了不同的元素。《幻想症》中,“我”的农民奶奶其实是流落到民间的西路军女战士,她身体最大的特征是残疾——哑巴。她大半生都在用肢体语言代替口语,谁也不知道她是为了免遭政治迫害而装聋作哑。后来由于“我”屡屡听见她的梦话而开始对她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奶奶索性在父亲的协助下割掉了舌头,终于让生活归于“常态”。《一路同行》中,作为计生专干的“我”,“监护”着怀孕的女同学前往镇卫生院做引产手术,实际上,“我”和同学都怀有七个月的身孕,“我”属于正常怀孕,同学属于超生,身体“内涵”的不同让情感冲突、灵魂挣扎显得深邃而悲壮。《分娩》中,迫于生计的孕妇采取在火车上分娩祈求社会救助的办法,不惜将身体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尊严被现实摧毁,身体已无关紧要。在《绣花鞋垫》和《不娶你娶谁》中,当山区女中学生圣洁的身体面对传统世俗,面对未来的无望,面对考学与打工的抉择,身体在少女成为女人的链条中,完全变成了与精神脱离的一部分。另外,在《借命时代的家乡》《皇粮》《烧水做饭的女人》中,女人们的身体或因成为平衡生存与前途的工具,或因成为社会变革冲击传统道德的第一道堡垒,或因成为女人们赢得另类尊严的“武器”。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完全被世俗化、物质化和利益化。比如那位民办教师的妻子花儿,迫于乡上田书记的权力和淫威,索性顺水推舟,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争来了丈夫继续教书育人的资格,确保了山区教育事业的正常进行。
第三类是关于男人的。在秦岭的一些小说中,本该好端端的男主人公常常以残疾的面貌出现,导致他们身体致残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战争、人为伤害、煤窑爆炸、工地塌方诸等。《父亲之死》中的父亲贵为县长,原本身体健康,顶着风雪下乡检查工作时不幸阑尾炎复发,却不愿在条件简陋的乡镇卫生院做手术,最终腹部感染一命呜呼。《杀威棒》中“我”的民办教师父亲,不满知青政策给山区农民带来的严重不平衡,以教育为名用教鞭在班里的知青子弟后脖子上抽打出了“×”型血痕。《硌牙的沙子》中,山区中学生不满教师追随乡政府的干部挨家挨户催粮要款,于是在给教职工食堂运水途中,偷偷在水中掺进沙子,让教师们遭受“硌牙”的痛苦。在《寻找》中,“我”爷爷当年到底掩埋的是红军的尸体,还是国军的尸体,始终是个谜团。当腐烂在地下的“身体”无法证明爷爷的清白时,爷爷用他羸弱的身体漫山遍野寻找了一生。在《心震》《阴阳界》《流淌在祖院的时光》等“地震系列”中,男人们的身体多因地震灾难而变得残缺不全,甚而变成冰冷的遗体,而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均在肉体、心灵的伤口上回旋。而在《马阴阳出山》《皇粮》《分娩》《本色》中,男人们的身体多因各种矿难事故而致残。也就是说,男人们身体的遭际,没有一次是偶然的,所有的根源全隐匿在故事的背后。
二
秦岭有关动物和人的身体叙写,与其说一具具客观的肉体呈现,毋宁看作是整个农村社会肌体的投影。作者把社会肌体上的种种病灶、症候、沉疴巧妙地依附于人与动物身上,既让身体的血与伤折射社会形态中扭曲、变形的部分,又让生理的痛与痒体味人间的真诚、温情与悲悯,这种独特的表达,内涵深刻,意蕴深邃,体现了作家独立的追求和严肃的思考。
第一,秦岭有关身体的叙写,表现为对西部农民生存、生活真相的深刻揭示。人和动物的身体所承载的,其实是农民的困境和境遇。在《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等小说里,赵花瓶、李最美、孙花儿、王精彩与她们的老师,甚至做饭的女工皮见花和校长雷大麻子之间的故事,都是女性身体服从严酷现实的真实写照。妇女身体的表现大都被外在的力量所驱动、所支配、所蛊惑、所制约,从这一特殊的立足点上进一步挖掘下去,一个深层的问题也便逐渐浮现出来:虽然妇女解放的呼声从“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运作之中——直到现在,特别是在那些偏僻的西部乡村社会,妇女的解放——哪怕仅仅是身体意义上的自由,依然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动物的身体也难以幸免,《吼水》中作为大牲口的马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生活负重,嘴唇因为干渴都起血痂了,汗都从眼睛里流出了,但是驮着水的它却被剥夺了喝水的自由。董球的女人当初是因为听说董球有自己的水柜而嫁给了他,但后来又因为家在四川的老板所说的家乡“江”的故事便决然地带着孩子给人家做了二奶。人和动物不同的遭遇和反应,经由“水”这一个聚焦点,生动地显现出了偏远乡村所有生命存在普泛和共有的艰窘与沉重。《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中的母狐狸为了腹内的“儿女”,不惜铤而走险,钻进“仇人”家找水缸喝水,最终溺毙。干旱缺水,是中国西部最为显著的自然特征之一,它导致庄稼无法丰收,农民生活质量无法提高,乡村大地不断消解着农民本该引以为豪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为了表现这一严峻的现实,秦岭别开生面地把一个个动物推到了艺术的前台,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悲剧力量和现实穿透力。
第二,身体叙事在凸显人和自然、人和人紧张关系的同时,视角延伸到了社会的纵深层面。当物质社会解构着传统的乡村秩序,当金钱戕害着延续几千年的乡村美德,当城乡不公伤害到农民作为公民的尊严,谁来关注、倾听农民内心的苦闷、冤情和诉说?这不,《一头说话的骡子》中的骡子说话了,骡子看似是一头非常普通的骡子,其实它是前世的一位普通农民工,他是被玩弄法律的掌权者以“强奸杀人罪”误判后执行死刑而死的,他的死不但在人间拍手称快,而且家族数代被永远株连在岁月的耻辱柱上。他的冤情深深触动了阴间的阎王,破例给他批了转世的指标,可他宁可转身为畜生,也不愿为人。这些年来,我们听到的被错杀、误判的案例不在少数,背后阴暗的逻辑也曾昭然天下,可是,除了有限的新闻舆论,我们还能听到当事人的声音吗?好在我们终于听到了,它就是骡子的声音。我们在这样的声音里,听到了另一种反思和批判,感受到了鞭挞和怒吼的另一种形式。为了强调人的身体和恶劣的外在环境之间的冲突,秦岭非常多地写到了男人们身体的残疾——特别是后天残疾的现象,《皇粮》中岁球球和《分娩》中张平安的矿难成残,《马阴阳出山》中廖姚明的施工事故致残,《吼水》中董球的为马所残,等等,艰窘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对于男人身体的伤害,反过来残疾的身体却还得承受更为艰窘的生存压力。看这一类的书写,读者的心里总是会产生别样的沉重感受。除此而外,秦岭还有一些和权力有关的身体伤害故事的书写。在这些身体的表现中,因为掺杂了复杂的权力因素,所以相关的内容读起来也便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在这里,身体的变化既是社会变革缩影,也是畸形现实生活的反映。
第三,身体作为勾连历史和现实的纽带,构成了反思和批判的有效平台。伤口之痛,无疑来自身体,那么,心灵的伤口在哪里呢?作者非常巧妙地把这些疑问嵌入身体伤口的来龙去脉之中。《杀威棒》看似一段简单的知青历史,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感受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伤口,感受到了压抑在农民身体内部的情绪和愤怒。民办教师曹尚德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挥鞭“教育”年仅十几岁的“祖国的花朵”——知青子弟,他与其说抽打的是孩子无辜的身体,毋宁在抽打一段历史。当用来教书育人的教鞭的呼啸声湮没于漫漫历史,我们从中还想感受什么?是伤口上汩汩流淌的血?还是至今犹存的疤痕。毫无疑问,《杀威棒》告诉我们的,不光是特定时代城乡紧张关系的特殊表现,不光是中国式教育的残酷,不光是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荒诞,不光是历史叙述中真相总是被遮蔽的虚妄,这是一篇需要多角度去观审的小说,其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只能让我们从现实中注目历史。段崇轩认为这是一篇“本年度最具历史反思意味的小说”(《文艺报》2012年2月14日),道理应在于此。同样,反映战争题材的《寻找》、《幻想症》等小说,当事人的身体早已湮没于大地,历史的硝烟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好在,那些曾经来自身体的挣扎、哽咽、声吟通过秦岭的“身体叙事”被录了音,摄了像,拍了照,成为读者前瞻未来,反思历史的窗口。
第四,通过一个个身体的变化,我们能窥视到物质时代人的不平等形态和不同阶层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林霆评价秦岭的小说时说:“对于政治之于中国人生存的巨大影响的切肤体认,使他的小说主题往往超越了道德和文化的层面,达到了一种认识层面的深刻。用艺术的手段展现民众的生存现实,特别是权力之下的生存真相,是秦岭小说的一大特色。”《权力之下的生存——评秦岭的〈本色〉》在日益明显的阶层和等级社会,秦岭对社会心理的观察,由表及里。入木三分。《父亲之死》中的父亲只不过下乡检查工作时阑尾炎复发,却何以死于非命?在条件简陋的乡村卫生院,他宁可虚情假意地把手术的机会让给恰恰也犯了阑尾炎的儿时玩伴,也要故作无奈地在同僚们的劝说下出山去城里的大医院做手术,并不惜全乡上下为他这个惠泽桑梓的好县长清扫出山的积雪。结果丧失了手术的最佳时机,腹内感染,身体变成了尸体,阴差阳错地赢得了因公而死的美誉。这篇小说意味深长的地方在于:父亲尽管是有口皆碑的好官,但他骨子里的等级、贵贱、本位、权谋意识同样根深蒂固,其根源显然来自权力。这一点,在秦岭的《难言之隐》《打字员盖春风的感情史》以及长篇小说《断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当一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所支配,那么,阶层之间的落差、人与人之间的失衡就不容忽视。
第五,秦岭在身体叙写中倾注了可贵的悲悯与温情。在所谓底层叙事跟风逐影的当下,很多作家都以叙写底层苦难为能事,但秦岭的小说区别于当今许多作家喜欢将怨恨、不满等乖戾之气传导给读者的企图,秦岭笔下所呈现的苦难只是一个侧面,或者说只是他展示人物和故事的一个渠道。身体的伤口与心灵的光泽、身体的破损与精神的高贵几乎是并存的,这是他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也完全符合几千年农耕文明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符合中国乡村的形态和现实。《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中,当人兽之间难以弥补的隔阂面临彼此肚子里即将分娩的生命时,以谅解、理解、宽容为标志的人(狐)性之美顿时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媚。《吼水》里的妻子忍受不了干旱之苦,领着儿女离开主人高攀远走,咬掉主人耳朵的马也被卖给“有水的人家”。但妻子和马都不是无情物,当故乡有了生命之水,他们依然踏上归途。诚如杨显惠所言,“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冷峻的目光、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冷静的底层意识,还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民和农村教师命运的忧患和关怀”。不难看出,秦岭总是在借助于人、动物身体的描述,有意无意地去调和人和动物、人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逐渐实现的理解,多侧面地展现他眼中的乡村情义、道德和伦理,并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持久的温度。
艺术是现实的审美反映,任何艺术所描述的艺术对象的特征,其本质无不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映射。秦岭的身体叙事既显现出明晰的现实所指,同时也内含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审视,作者从多种视角观照乡土中国的历史运行过程,并对人与自然、人与政治、人与时代、人与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力所能及、自然也不无深度的反省和叙述,从而兑现了作者在创作谈中的承诺:“我在反思传统,也在反思时尚,归根到底在反思历史、生命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