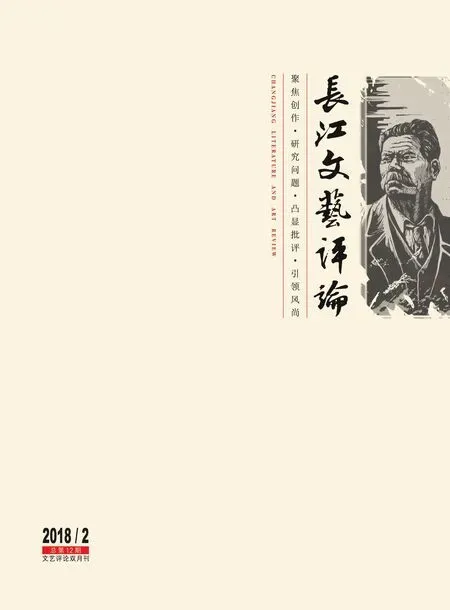光阴反刍:小城叙述的情与物
——读杨章池的《小镇来信》
◎李啸洋
有一部日本电影叫《东京物语》。电影讲述一对生活在小城里的老两口,他们前往东京,探望在大城市成家立业的子女。因工作忙碌,儿子和媳妇无暇招呼小城里来的父母,最后这对老两口只好悻悻而返。这部电影过去60多年了,影像中的温情与无奈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影迷。小津安二郎用著名的低机位镜头,向寻常生活致敬。
“每个清晨,每个囚牢。/我在墙壁上层层涂抹——沮丧。”(《小镇答案》)。诗集《小镇来信》和《东京物语》的精神颇为相似:原来,光阴自有一种力量,小城也可以天荒地老。在与光阴的逐鹿竞跑中,小城余留了一丝温情,也余留了一丝遗憾。在急速前行的现代社会,小城没有与传统社会相隔绝,也没有迷失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氛围里——小城像敦厚的长者,坐在时光的角落,聆听生活布施的语义。
小城叙述:日常时刻与小镇空间
莫言写“高密乡”,梁鸿写“梁庄”。贾樟柯用电影记录县城“汾阳”,杨章池用诗歌书写小城“松滋”。这样的比照固然牵强,但是文学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都曾被弃置于现代性的洪流之外,被启蒙遗忘。
湖北松滋,是诗人杨章池的故乡,这里有他的童年记忆,也有宁静的诗学空间。松滋既不像长安、扬州、成都,有可以清晰识别的文化记忆地标;也不像香港、深圳、广州,地理上错杂交织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诗歌中的松滋,不具备江湖和历史的含义。松滋,是自然和地貌学意义上的松滋,在诗人的笔触下,它只有人类最简单的居住功能。它尚未进入公众视野,尚存留着私人记忆的边界。这是一种隐私策略,也是一种被心灵保护、被现代化大潮遮蔽后的幸运。
杨章池书写松滋的“小镇之暖”和“庸常之细”,在童年与中年的往返之途发现了“时光之镜”。松滋的地理位置,构成了杨章池的写作心态:平和,而不激烈。贾樟柯在《县城与我》中写到:“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卖菜的,卖豆腐的,卖书报的,银行里头的职员,对面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你都认识。”杨章池关于松滋的叙述里,也有着类似体验:照相馆、理发馆、马戏团、县医院、澡堂、学校、五金水暖门市部,逃学、钓鱼、吃饭、洗澡、被大人骂……作者对旧日器物流连忘返,每一棵香樟树,每一块时间切片,每一粒灰尘和树叶,都叠合时光的影子。
作为原乡,松滋小城有杨章池的成长经验,也是他在地书写的灵感来源。松滋存留的日常时刻,唤出诗人幽邃的中年情态,成为私密的记忆档案。杨章池像一位地方志作家,他在诗歌的现场,用第一人称现身说法,来记录地方记忆。松滋从一种地方性的话语表述中转换成一个抽象的词语符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辐辏点。杨章池用诗歌勾勒出小城地理,用词语重组往昔的零碎生活,用私人体验来佐证一段地方记忆。
松滋是一座小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小城松滋完成自己的角色定位,它没有与乡土错位,也没有和现代化脱节。在历史性的演进中,松滋静候光阴的恩典。在杨章池的诗歌书写中,小城空间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小城空间给人以安定和幸福感,也提供了可以庇佑的保护感。作为生于兹长于兹的松滋人,杨章池通过小城叙述省识出诸多现实问题。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用时序错置(Anachronism)和空间位移(Displacement)来分析原乡的成因。王德威认为,原乡关注的不是对原来故乡现实主义写实,而是作者在原乡图景丧失后对故乡的眺望与追溯。原乡是杨章池诗歌的书写主题,因为没有迁徙,没有返乡历程,诗人对原乡的描述始终平视而宁静:“月亮注视人间,人间如此寂静。”(《巨月之夜》);“阳光越来越慈祥了。/我们喝完汤,开始午睡/窗帘摆动,桂花香里掺着婴儿的哭”(《秋声》);“1970年代的星光下。/屋前溪声和无休止的虫鸣,凉床上我们唱歌,一支接一支。”《二胡:夏夜怀堂兄》)。诗人笔下的原乡,既不像鲁迅在深冬时节返回的《故乡》,弥漫着落败、荒凉的气息,也不像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里“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变成故乡的客人和陌生人,故乡不是影子不是断肠愁,故乡松滋一直以现实主义的身份在场,杨章池也一直是自己乡土的主人。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诗意地栖居。”松滋为杨章池的诗歌提供了栖居的土壤,这种切实的在场和在地书写,决定了杨章池诗歌作品的基调:它与诸多的返乡作品不同,也不会遵从返乡叙事的惯有路径。或以桃花源式的想象追缅往昔故里,或感喟都市人情薄凉以期从返乡历程中获得安慰,或感伤于变迁时境将原乡作为归隐寄托——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小镇来信》迥异于大陆文学中熟悉的返乡描写,它直陈在场的原乡,用原乡的现时风貌解析乡愁。地方性的在场藉由日常生活片段串联起来:搓澡、理发、串门、逃学、上街、过生日、练太极拳、家庭趣事……这些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构成原乡生活场景的基本风貌,人间烟火藉由此在作者笔下窸窸窣窣展开。
许多乡土书写沦陷于苦难和无止境的怀念表述中,于是乎,故土给人一副消逝的面孔。杨章池诗中的故乡,没有背井离乡,没有外出打工的血泪史,只有朝九晚五和家长里短,有寂静的光阴和世俗的生活:“清洁工人的笤帚和拖车远去了,/ 冬天重新从地底下长出来”(《后半夜》),“摇车陈旧,婴儿熟睡/她嘴角动一下,就变成一朵花。”(《塔桥路口》),“洗澡后我换上儿子的绿色卫衣/坐在他常霸占的电脑前,玩/他爱玩的游戏”(《扮儿子,装孙子》),“两声,三声,鸟鸣贴切得/像我自己叫出来的……/这是我在安心桥/每天的早餐/一切多么美好,我要向世界/再做一个鬼脸”(《安心桥之晨》),杨章池的诗歌中缺乏一种迁徙想象,所以光阴能完好如初地保存,这种时间感就像侯孝贤的电影镜头一样耐人寻味。
学者耿占春在《地方与叙述》中写到:“小地方小人物,他们的事迹不足以名留青史,然而也不是没有痕迹,他们的性情与故事留在地方性的话语谱系之中,他们在地方性的叙事里得到恰当的小历史和小叙事的位置。”杨章池用诗歌为湖北松滋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系列的档案记录,在这个私人记录的谱系里,可以看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可以看到众生相:乡村理发师、田螺姑娘、戴眼镜的老人、拉二胡的堂兄、送葬队、清洁工、盲人、搓澡工、烧电焊的人……旧日肖像导引出地方记忆。德勒兹在《运动——影像》中认为,物品自身构成了质——力量,因为与事物的状态和起因有关。日常时刻的书写,小镇记忆以物的形态,进入到诗歌的书写序列中。这些记忆中的物象经过诗人的交换、回忆与复现,构成一种精神性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到诗歌的生产中来:碗筷、钟表、门神、旧衣、窗户……由家庭、师生、亲缘和工作关系凝集而成的松滋与地方性,让南方的音调与地方叙述变得糯软起来。原乡就像一个自带光源的能量器,它充满了“边缘的活力”,不断地为诗人的写作蓄积能量。
实景记忆:童年想象与父亲身份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曾说:“正是在梦想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事实的层面上,童年在我们心中才保持鲜活,并且从诗歌的角度来说是有用的。”恒久的童年,杨章池在诗歌中封印了永恒的童年,他的诗歌是一道护法,保持了往日时光的光晕。对童年的记忆,使宇宙得以向诗人重新敞开。
杨章池打开了记忆的橱柜,童年的气息扑面而来:“假装我们是……/两个四岁的强盗,在广场中央密谋/脸庞绷紧,眼神不可一世。”(《两个强盗》),“你一定从来没有爱过我,爸/当你低吼出“滚开”,嫌恶的语调/浇透我:灰尘满身的家伙瞬间变成泥猴。”(《泥猴》),“那头猛虎又开始咆哮时/儿子突然发现我这些年几乎没有吼过,‘你是不是把苦都吞掉了?’我却记得夏天的怒斥,甚至十年前的巴掌,/当他还是一个幼儿。”(《便河书》),这三首诗歌里,童年空间是重要的陈述对象。顽皮、玩耍、挨骂,三重记忆交织出童年生活。
父子关系的表达颇为微妙。杨章池的诗歌中,父子关系不是油画,也不是印象画派中大块浓艳的色彩,诗人不会浓墨重彩地去描绘父子之情,而是用中年的眼光来进行细致观察,尔后做出关系的比照:父亲—儿子、儿子—儿子、自己的童年和儿子的童年之间介入了中年的眼光,最后形成一种关系勘探。这样的心态比照,在杨章池的诗歌里比比皆是:《相互拨通没有应答的两部手机》,描述的是一部用过的旧手机,手机里储存了儿子对父亲的亲切慰问:“揿开,拨通,那翠绿屏幕自动跳出两个字:‘爸爸’。/哦,爸爸。我的心跟着跳了两跳。”再比如《与子书》:“你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这些词还要渐渐增多,扩大直至/整句话、整段话都来自火星。”在比如《喊成父亲》:“在墨轩之前,我确信我有过/好些小孩/他们有的叫贝贝,有的叫嘟嘟,有的叫小蓓/有儿子有女儿,有的性别不详/这些又虚幻又真切的小孩啊/从脉管中,心跳中,喊我爸爸”,在这几节关于父子关系的描述中,读者恍惚又看到了朱自清的《背影》里那个疼爱的父亲形象,杨章池将童年置于想象的放大镜下,他将属于或者不属于的过去,都抽成一根根丝线放进诗里,尔后被时间编织在诗歌中,镂出了中年人对童年的接纳和喜悦。
杨章池在纸上留下了童年丰富的触角,也留下了一道温情的人类学景观。他对于父子关系的描摹,并非浓墨重彩,而是像版画一样勒印出记忆轮廓,这其中有时间的镂空感,也有光阴的一缕亮色,而这种亮色又是以中年心态的灰色作为底衬。
阿玛蒂亚·森认为,身份与认同感和身份选择密切关联。身份是环境对自我的形塑,是一种完整的自我感。身份赋予人们“一种共同历史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力量,并在此历史基础上形成一种归属感。”童年指认出时间的过去,父亲身份则是一种精神体认。在杨章池的诗歌描述中,父子关系的表述,常常以某个瞬间起兴,尔后遁入到时间的沉思与寂静中。《互相拨通没有应答的两部手机》,以与海外留学的儿子通话为触感,感喟异乡带来的沧桑感;《喊成父亲》里,作者追忆似水年华,追忆当年初为人父的喜悦;《吼叫》的第一节,父亲形象似乎以一种忏悔和观罪的形式出现,到了《长在头顶的儿子》,为父的温和与严厉、力量与弱小,疼爱与无奈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动人描述:
我只有这么高
一米七二的男人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在小小县城,做平凡的事
拿最一般的工资
不会开车,只有一所简单的房子
除了你,我只有你妈妈了
儿子,其实你仔细看,我已经
渐渐老了,白发丛生,病痛缠身。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把你举过头顶
让你更接近天空。
我用全身力气站稳自己,拽紧
你的脚
以后,星星你自己摘
月亮你自己摘
这是一首情感复杂的诗,它让读者久久徘徊、感动。“举过头顶”的动作,其实暗合了一种人梯精神:几乎每个中国父母节衣缩食,盼着子女出人投地,自己默默奉献,子女长大了,自己就变老了。这何尝不是中国千千万万的父母心?这首诗没有太多修辞技法,没有晦涩的隐喻,没有思想的锐度,却有着寻常人家的物与情。再回到父子关系的讨论上来。在杨章池的诗歌里,父亲身份是什么?是心脏与阑尾。谓心脏者,乃是因为父亲的中年身份,让作者对光阴有了更多的感触;谓阑尾者,乃是因为光阴留不住,父子情会在光阴颠沛流离的过程中隐隐作痛。
光阴的刻度:中年心态与启悟
评论家罗勋章认为,“杨章池的诗歌在表现形式上,以叙事化的场景及细节建构诗歌空间,其叙事性背后凸显的是身处后情感主义时代依然葆有的传统时代的情感本真。”“情感本真”,正是杨章池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承载了感觉与经验,风格总是隶属于“领土性”。父子关系、家庭空间和血缘关系等等,正是杨章池诗歌里的“领土性”,然而“新事物恰恰是要忘却领土性。”
何为杨章池诗歌中的“新事物”?答案可能是中年心态和这种心态带来的生活启悟。作为生兹在兹的松滋人,杨章池的生活一直平和而朴素,他的生活里没有上海等城市诗人的前卫和先锋,也没有农民进城的血泪与辛酸,他的履历就是松滋这座城。这座小城给他的,是故乡的概念。杨章池说:“(松滋)环境的相对安静,空气和水的相对洁净。”从小踩着泥土长大,从县城到荆州完成求学历程,没有背井离乡。在故乡松滋,没有雄心,也不期待远方。正是这种相对稳定、安逸的环境,才造就了他诗歌的平和风格。
一个稳定的故乡,外加一个稳定的中年。两重稳定,加固了杨章池的诗歌主题。他的新诗集里,有诸多描述中年心态的诗:《蝉蜕》《梦惊呼》《今夜是可行的》《冬夜不要随便回忆》。“我无耻的中年开始露头/鼾声,一天比一天茂盛”(《梦惊呼》);“我们每天做很多事,使自己/仍有价值。我们背过脸吞下不同的空气和药/凑到一起何其快乐。/我们互称爸爸,妈妈/像两个易碎儿童。”(《蝉蜕》);“一个人在冬夜,背负太多,往事浮一件,衣服加一件”(《冬夜不要随便回忆》);“一百个原谅排队聚成莲花宝座,凭此我能泅渡中年的大海?至少今夜是可行的。”(《今夜是可行的》)……
中年是什么?《论语》里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中年就是这三种情态的合并。“你有你的卑微药房,我有我的辛酸公务。”(《窸窣》)在杨章池的诗歌里,中年是易碎的、消逝的、敏感的,中年是和生活继续叨叨絮絮,夜半鼾声四起。中年是扮演、蝉蜕、抑制,它像一段报废的历史,等待记忆的重新修葺。
如果说中年“痕迹”在他的诗歌里尚不足以构成警示,那么“死亡”主题的复奏则打开了另一重原乡视景,它与温吞的中年情态并不相同,死亡的描述尖锐、凌利,而且无处遁逃。《预习》《靠岸》《病中》《送葬队之约》《十年前的录影》《春天火葬场》《最好的时刻》等诗歌中都提及或者描述了死亡。与悲恸不同,杨章池诗歌中的死亡有着莫可名状的沉默。诗人没有停留于死亡悲情的表层,而是从形而上对死亡进行哲学观照:“说到火葬场,我们常常指的是/悼念厅:城西一带,月光/都不愿停留之地。”(《春天火葬场》),“茫茫无际的秋啊,茫茫无际的/安魂曲/车队开来,电影散场/黄裱纸在飞,鞭炮在疼/我曲行着,躲开迎面飞来的/一张脸”(《送葬队之约》),“这是最好的时刻:/ 父母轻声谈论着一个人的死。/他们已经衰老,但没有崩陷。/儿子一秒钟变少年但还有童音。”(《最好的时刻》)
童年、中年、老年,这三重身份在杨章池的诗歌中完成光阴的叠印,这三重时间在不同的场景交织,一起辐辏在字词与光阴间:“我们习惯在正午,/从明晃晃的阳光中潜入阴暗后厢房:/由两条旧板凳扛着的它,一头高,一头低,/在不可知的深处,山一样巨大。/贴着棺板和棺体的缝隙望进去,/憋住呼吸,用耳朵捕捉/细微窸窣,/然后在一阵尖叫中跑开。”(《预习》)。在死亡与中年之间,还隐藏着一块阴暗的腹地,这块腹地便是衰老。诗集中也不乏描写老的篇目:《县医院》里“晚年的寂寞越来越老。/多少人都这样来去匆匆,被它牵挂/但对它午夜的钟声不置一词。”《南方声调》中“这么老的父亲,居然年轻过。”他熟悉的邻居,《张志桃都老了》:“不认输的女人,慈祥地老了/她走在一场停不下的雨中”,《即景》里,诗人悟出:“我中年渐老,才长出心和肺。”孟子曾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论是亲人的衰老,还是母亲的学生张志桃的衰老,老自有遒劲。苍老和中年一样,它是生活的提词,是诗人自己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启悟。
除了童年、中年、衰老和死亡主题,杨章池的诗歌中还有一些诗歌直接指涉哲学。《老门神》和《被判决的黄牛》因物感兴,书写光阴之无情;《情欲的诞生》和《劈柴赋》翦除了情感的维度,让诗歌走向纯粹的哲学思考;《气候转凉,秋天回到内心》和《渴》追寻世界本相,试图从哲学化的叙述中寻找到精神的纹理。这些诗歌题材从静物到节气,从描摹到隐喻,从空物中开凿出哲学丰富的褶皱。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这样阐释在家的感觉:“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原乡的意义肇始于失落或者改变,也暗示了原乡叙述行为的症结——叙述的本身即是一连串的“乡”之神话的转移、置换与再生。对杨章池而言,童年的松滋回不去了,松滋和中国其他的县城一样,裹挟在现代化和全球性的双重语境中。虽然回不去了,但小城叙述无疑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考。诗歌和小城给诗人杨章池带来无量的幸福,它成为抵御时间洪流的堤坝,也是诗人抵御“中年心态”的坚实基座。小城的物与情,提供了在家的感觉,也提供了世俗语境中精神回乡的路径。松滋,光阴年复一年。对于杨章池的诗歌读解,不妨用《旧巷子》中的一句作结,这句话和他的诗学理念最为熨帖:“多少年了它终于等到我:/用静静的闪耀。/正月初三,老光阴。”
注释:
[1][10]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226页。
[2]耿占春:《地方与叙述》,《天涯》2007年第4期,第21页。
[3]【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谢强、马月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4]法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卡萨洛瓦写过一本书《文学世界共和国》,他将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首都”与“边疆”,它们并不总是与世界的政治版图相吻合。“边缘的活力”,说的是地方性文学具有的文学活力。参见刘大先:《文学地理、空间生产与边地文学——2016年10月30日在四川师范大学的讲演》,微信公众号“大西南文学论坛”,2017年9月11日。
[5]【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6]【印】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7]罗勋章:《情感主义时代的小城经验——杨章池诗歌创作论》,《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9]【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