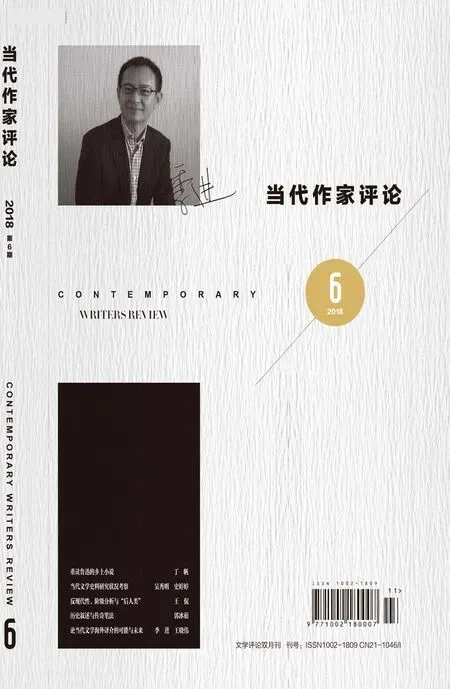如何历史,怎样现实
——叶兆言历史题材小说读札
黄 玲
2017年,叶兆言在《钟山》上发表了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刻骨铭心》。这距1987年他同样也是在《钟山》上发表第一个历史题材小说“夜泊秦淮”之《状元镜》,正好过去30年。看似巧合的背后,是叶兆言30多年来对历史题材持久的写作热情。从“夜泊秦淮”系列、《枣树的故事》,到《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再到《一号命令》《很久以来》《刻骨铭心》等等,历史题材占了叶兆言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并在近年有持续爆发的势头。《刻骨铭心》的出现,让我有兴趣对叶兆言过去30年的历史题材小说进行一次整体回顾。
一、历史是一枚悬挂小说的钉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叶兆言的小说就被评论家们作为“新历史小说”来谈论了。《刻骨铭心》出版后,各路媒体又纷纷把这部作品视为“‘夜泊秦淮’后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但叶兆言其实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作家。研究者面对一个作家时总是试图概括,而叶兆言却是一切言之凿凿的结论的自觉抵制者,他的写作总是在求变。他曾被归为“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但这些概念用在他身上其实都并不准确。叶兆言从来不是一个追随潮流的作家,他对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追求,用任何既定的概念去指认或阐释他都注定是一场误会。
叶兆言的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都不一样,既不追求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也不追求重写某一段时期的历史。他甚至反对人们将他历史题材的小说称为“历史小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对记者说过: “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历史追求真实,小说强调虚构。两者之间相距很远,是很难扯到一起的。”叶兆言尽力撇清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无非就是想让小说回归文学本位,不被历史绑架。
客观上说,历史与小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小说是可能发生的事。但实际上对小说家们而言,他们每一次提笔面对的,无非就是历史和现实。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它所描绘的生活就不可能回避历史这一维度。关键的问题在于:历史在小说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法国作家大仲马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在这里,历史是小说的工具。那么,历史能否成为小说家的目的?我的答案是宽容的。因为从中西方小说发展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在有着“重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谁都不可能扼制住无数小说家们的历史野心。至于小说能否真正反映历史的真相,能否真正带我们重返历史,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愿意把所有“意在历史”的小说称为“历史小说”(无论是传统历史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把那些将历史视为材料和工具的小说称为“历史题材小说”。叶兆言的小说属于后者,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也是我对其这类作品理解的起点。
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叶兆言并不迷信历史,但依旧秉持着传统的历史观,对历史史实怀着最大的敬意。《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后记中,他曾说:“说起来真让人感到惭愧,我的案头堆放着一大堆史料,我写作时坐的椅子周围都是书,除了当研究生写论文,我从来没有为写一篇小说,下过这样深的资料功夫。我一次次地去图书馆看旧书,翻翻当年的旧报纸旧杂志,那些陈旧的东西,让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错觉。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种错觉是十分必要的。”其实,对读者来说,这种错觉也是非常必要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必须有真实感,要让人觉得是真的。如果读者失去了对小说基本的信任,那么他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信任是小说和读者之间不可或缺的契约”。创作中的实证精神,使得叶兆言小说中涉及的历史细节均是真实准确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一号命令》《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中都涉及了一些真实的史料,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间穿行,由此让人在阅读时获得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真实感。如果说历史是一枚钉子,那么正是叶兆言写作中诚恳的实证态度,使得这枚钉子敲得异常结实,足以悬挂起他的小说。
二、讲故事的人
真正优秀的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在回答别人“为什么要写小说”这样的问题时,叶兆言总是说,没什么,就是想写,想表达。叶兆言的表达方式从来不是咄咄逼人的观点抛售,而是讲故事。这是一个天生就喜欢讲故事的人,对于津津有味地给他人讲故事这件事本身无比着迷。
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也许是由于历史时空距离自带的传奇色彩,叶兆言常常会显得更加沉迷于对故事的讲述。至于其他,似乎都可以让步。比如结构。叶兆言小说的结构相对来说都比较松散随意。中短篇还好,也许是因为字数的限制,结构上还是比较紧凑精致的。但到了长篇小说中,结构就显得相对松散随意很多。《刻骨铭心》中讲一群人的故事,故事多头并进,旁逸斜出,作家讲得行云流水,读者读得云山雾罩,得不断地回溯才能在散乱的叙述中找出线索。再比如主题。他在《一号命令》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自白:“有读者看了这部小说,写信给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尾。……这样写究竟是何用心,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实说,自己也没太想明白,大致情况就是写着写着,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于是便这么结束了。”无独有偶,《很久以来》的后记中他又说:“很多朋友问起这小说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所有这些真说不清楚。”“没太想明白”、“说不清楚”,叶兆言总是这样回应着读者关于小说意图的疑问,这不是谦虚,更不是故弄玄虚,恰恰反映了一个讲故事的人随性自适。
另一方面,对于信奉故事为王的叶兆言来说,如何把故事讲好,如何让所讲的故事深深吸引住读者,无疑是他首先要考虑的。与那些高傲的小说家相比,叶兆言从来不掩饰自己对读者的争取,这表现在他的小说写作实践中,就是对叙事方式在技术上持之以恒的痴迷与探索。本雅明认为,讲故事的方式是一种工艺,或者说手艺。一门手艺要日臻精进,需要手艺人不断的切磋琢磨。叶兆言小说写了30多年,小说技艺方面也就琢磨了30多年。
以历史题材小说来看,叶兆言80年代初登文坛时,一篇《枣树的故事》就充满了实验性。小说中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转换、叙事的节奏与结构的变化等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运用得很多,形式感很强。这在当时看来相当前卫,叶兆言也因此在当年被评论者们认定为“先锋派”。确实,如果我们不把“先锋派”的定义局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那场狂飚突进的先锋实验热潮的话,叶兆言一直都是“先锋派”。90年代“先锋小说”退场之后,叶兆言没有放弃小说叙事方面的探索,并且把这种探索精神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及至最近的《刻骨铭心》,每位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有一个“冗长的开头和一个仓促的结尾”。对于自己在60岁上捧出的长篇大作,叶兆言并没有选择四平八稳的叙述策略去展现他30多年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而仍愿做这样大胆的形式尝试,这种创作风格,真的很叶兆言式。
叶兆言是个彻底的小说实验主义者。30多年来,从小说技艺角度讲,他一直是位不懈的探索者。他喜欢一切形式的实验与探索。他说,“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先锋的姿态。我起码坚持这个原则——宁愿写坏了写砸了,也不追求轻车熟路。”对于一个特别热爱讲故事的人来说,一个故事轻车熟路的讲法显然太容易了,但叶兆言却对创作中的轻车熟路充满警惕,每一次都是主动增加叙事难度,以竞技般的专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每一部作品有所创新。这对于一位写了几十年的作家而言,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当然,我并不认为他每一次探索都是成功的。今天回过头去再把他的小说仔细研读一遍,甚至会觉得,他小说中叙事方式上的各种努力很多都并没有达到技艺上的炉火纯青,相反,我们还总是能在这些作品中看出小说家的一丝刻意。但是,在我看来,这不算什么。既然是探索,就肯定有成功,也有失败。既然是实验,它本身不就是一种刻意的尝试吗?叶兆言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内心从来没有包袱,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每一次写作都当成从零开始的出发,轻装上阵。不惧失败,却对一切成功保持警惕。能有这份清醒,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叶兆言的观念里,写小说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是一项发挥个人才智的有趣活动。既然是游戏,那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好玩最重要。“写作是很寂寞的,也很虚渺。既然写出来未必有那么多人看,那写作本身的快乐就很重要,写得好玩才有意义。”带着游戏的轻松心态一往无前地投入写作竞技,这或许是一个小说家最好的创作心态。
三、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
“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菲兹杰拉德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一部小说的卷首语。确实,历史往往都是关乎大自然的演变、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以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宏观而又抽象。有关历史具体而微的细节和肌理、温度和质感需要小说来完成。小说通过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图景,对枯燥历史作有效补充。米兰·昆德拉认为,“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真正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与命运的,是小说家。叶兆言说,“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叶兆言正是持着这样低微的叙事姿态,从零碎的、个体的小故事出发,用普通百姓的视角去开始他对历史的书写的。纵观他所有的历史题材小说,这几乎是他进入历史的固定方式。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是一个最典型的文本。我们对于“1937年的南京”的历史想象中,一定有战场的硝烟弥漫,有百姓的流离失所,有敌人的血腥屠杀,唯独不可能有爱情。因为爱情是面向个人,面向内心的,在草菅人命的战争年代,微茫个体的生命都是朝不保夕的,何谈生命内在的情感呢?叶兆言就从我们历史想象的空白处落笔,用小说给那些粗线条的历史认知纠偏。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是这么写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五,天气晴朗,来自北方的寒流刚刚过去,气温有些回暖。虽然国民政府已把阴历称之为废历,但是阳历的新年气氛,在民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强烈和热闹。”在这样如普通日记一般平静安详的叙述中,整个小说的基调定下来了:1937年,与前面和后面的每一个年份都一样,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来说,它平常得如同每一个昨天和明天。
确实,无论多么重大的历史年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永远都在继续。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儿女情长、爱恨悲欢,这些看起来是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小事、俗事,但千百年来人们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所以,“历史讲的多是变道,但小说所写的其实是常道。”历史代表的是生活的变数,小说反映的是恒常不变的世道人心。叶兆言所有历史题材的小说都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人物都是普通小人物,故事也都是微小个体的故事。
当然,历史在叶兆言小说中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背景,同时还是一种隐在的叙述力量。比如《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当这个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这个特殊的时空位置之下,爱情就变成了传奇,小说叙事一下子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动荡的乱世,不仅让不可能的爱情变成了可能,也能让人性得到更好地凸显。《没有玻璃的花房》写“文革”时期一代人的成长。小说从一群孩子密谋批斗其中一个孩子的奶奶开始拉开序幕,写下了混乱时代中一代人的残酷与迷乱。小说中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欲望诱惑,我们看到了个人身体里的欲望是如何在混乱中被煽动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看到了荒唐年代里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庸者之恶”是如何让人间变成了地狱。在叶兆言的这些小说中,历史被运用成一种助推力量,更为纤毫毕现地呈现了特殊时代人们真实而隐秘的内在生活。
无论是爱情、婚姻、家庭,还是青春、欲望、人性,这些都是生活永恒的主题。叶兆言通过对那个时代人们琐碎日常生活的叙述,要触碰的是人心和人性的真相。他说,“好的小说永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好的小说永远试图表现那些永恒的东西。”小说终究应该与什么相关?哲学家蒂利希说,艺术无论如何应该“与我相关”,小说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写历史题材、历史人物的小说,它们看起来似乎与我们当下生活毫无关联,但事实上这些小说无不让我们洞察了某个人人生的形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它们的成长与犯下的错,停滞与漂浮”,而这些,正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有着各种形式的关联。
小说家低微的叙事姿态的另一个表现是,无论写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事,叶兆言都只是叙述,从来不加以评判,也不讽刺与怜悯。“我是那种不太会有讽刺感也不太会去怜悯笔下人物的作家,因为我觉得讽刺和怜悯都有些居高临下。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个老百姓,写到值得讽刺或怜悯的事情,我产生的是一种庆幸感——这样的事没发生在我身上。”正是这样的平易使他关注到了历史褶皱处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幽微的内心,由此抵达了历史感性、隐蔽、柔软、恒常的部分,为一切严肃的历史宏大叙事作了有力的较正和补充。
四、道路在雾中
叶兆言历史题材小说最终关心的,最终想借助小说表达的,是他关于人与历史的思考。或者说,历史就是叶兆言观察人的存在境遇的一种方式。虽然这些小说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没有十分明确的主题,但是当我们置身于这些故事中,置身于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人物们的命运里,读着读着,内心就会升起一种超越历史的苍茫感。慢慢地,会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境遇有一种形而上的感知。
在叶兆言的很多小说中,他总是在不断强调人对自己置身的时代的不了解,对时代里自身命运的不自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他说“一九三七的南京人还不可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历史悲剧,他们活在那个时代里,并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因此,故事中,1937年的上半年,男人们还在谈天说地、喝酒嫖娼,女人们还在谈情说爱、争风吃醋,日子如常。人们并不知道即将影响每个人命运的战争正在逼近。下半年,战争来得非常突然,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开始遭受空袭,余克润不幸阵亡,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最终失守,继之而来的是大屠杀。风暴来临,而人们往往并不知道。《一号命令》中也是,赵文麟随着时代的潮流考军校,上前线,投笔从戎,在当时看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选择。事实上他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的正义性又在哪里,更不可能知道,战争会给自己和初恋情人沈介眉的人生带来多少起伏的际遇。历史,有时候真的就是人类无意识的、普遍的、随大流的生活。
米兰·昆德拉说,“对于身处某一历史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既不了解历史的意义,也不知道它未来的进程,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行动的客观意义,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行犹如人在雾中前行。”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既然前行的路上充满雾霭,那我们能否通过清晰回望过去人们走过的道路,从而规避掉我们当下的一些命运漩涡?我们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人们眼中的历史,如果我们可以从历史故事中对自己当下的存在处境有更清晰的认知,那么在明天的人们看来会不会少一些痛心的悲叹?
然而事实上,对于后面一代人而言,很多时候他们对历史并不买账。《很久以来》中的小芋,是欣慰的女儿。自小因为被母亲寄居在舅舅家遭受了太多委屈,内心对母亲一直心怀不满和隔膜。她不理解母亲的一生,也不想去理解。因此当欣慰被枪毙后,公安人员让小芋表态时,她能说出“竺欣慰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这样的话来。这令欣慰的同龄人、好姐妹,一直抚养着小芋的春兰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后来即便欣慰平反了,小芋对母亲的冷漠依然没有改变。在小芋看来,欣慰是她一生的阴影。为了逃开这种历史的阴影,后来她不惜一切代价地出国去了。最后作家借叙述人之口无比悲凉地说:“我努力想消除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希望她们能够在文学中和解,在艺术中达到沟通,可是事与愿违,这种隔膜看来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消逝。”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在《一号命令》中同样触目惊心:国民党军官赵文麟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当然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所以面对“一号命令”,想到可能又要到来的战争时他感到无比忧虑。但下一代的孩子却陷入了对战争的狂热之中,妞妞自制红缨枪要激动地参加国庆游行,女儿天天不顾一切地要到缅甸参加游击战,沈介眉的儿子死活都要去参军。关于战争,两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赵文麟“他觉得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跟女儿说,他想和女儿说一说当年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印度作战之事,说一说野人山的森林,说一说当年牺牲的五万多远征军将士,可是千头万绪,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了宝贝女儿也不会相信,他根本就不可以说服她,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历史的真相并不存在”。
由此我们不无悲伤地发现:上一代人几乎没有办法通过回望历史,来为下一代人拨开他们前行道路上的迷雾。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的命运图谱,所有该经历的迷狂、不幸与叹息都必将经历,无可幸免。作家在《一号命令》后记中说,“这是我写作以来,最有疼痛感的一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情不自禁便会流泪。有一天吃饭,跟女儿说起正在写的一个情节,说着说着哽咽了,说不下去。”之所以如此动情,正是因为小说家有一种明明看清了历史却依然对人类命运无能为力的悲怆。每一个置身于今天的人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所有的年轻人对于昨天的故事永远都是那么不以为然,所以人类前行的道路注定永远在雾中。
当然,即便这样,我们也不会因此放弃对历史的理解和追问。就如小说家叶兆言,即便对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他还是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这个世界越是毫无意义和凶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是不可能置身历史之外,越是不能拒绝竭尽我们所能,为世界留下一个理智和人性化的痕迹。”在我看来,这也是叶兆言历史题材小说最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