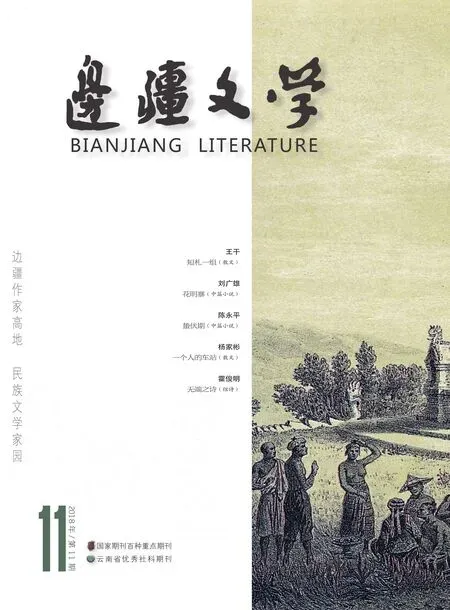无端之诗(组诗)
霍俊明
中途
风吹过时
那些深绿色的玉米就瞬间
压低
并有了亮光
一个女人在车厢里
不停地打电话
我只记住了一句——
“这趟车六十三块五
要是买四十块钱那趟车
就更好了”
我现在有些后悔
如果我的行李和别人的挤一挤
她刚才就不用费力把自己的大包
放到过道面对的行李架上了
我再次看到了
她深绿色的行李
它看上去
更重了
山中
我也曾远足山中
只是为了
看一眼
曾经栽过的一棵雪松
最终
我错过了它
不知它早已被砍伐
还是
长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乌蒙山的雪
现在是秋天的乌蒙山顶
时间的冷和词语的冷刚好相遇
时断时续地雪
却带来一条确切的消息
一位友人刚刚亡故
那时中原的庄稼被砍落一地头颅
雪阵回旋的下午
人们正忙着灰蒙蒙地呼吸
如果偶尔想起了一个人
可以在这样的大雪弥漫的时刻
可以在一些缓慢的事物降落之后
可以在那些越来越快的消失和溶解之前
行者
北方的行者
远来山中
背着中途死去的人的骨灰
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
高过人头的杜鹃
鲜血正在深秋里甩干
心生怨念的人
还是个孩子
正在修习的年轻僧侣
刚刚懂得
明天开始不必再去理发
叶柄
雪不会再来了
湖水早已结冰
冬泳者深插钢钎迸起一阵阵冰霰
手掌般的落叶扑打着看不出材质的护栏
那些小广告,我第一次留意它们
更多的树叶落下来
好像是为了强调时间是一个大磁铁
野鸭子飞起来再降落
只有五秒钟
男人在教女人儿时玩过的游戏
叶柄和叶柄的较量
它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最为粗大的
有一个注定是失败者
成功者穿着白衣
红砖的屋顶刚好被几棵树遮挡住了
他们曾经一起读过一本外国小说
书里的情侣一直躺在床上做爱
也不说话,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事可做
红花结莲蓬,白花结藕
北方一场暴雨
我在回程的火车上
母亲打来电话
她好久没主动打电话给我了
她问我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上
她声调突然高了许多
像年轻时候
她在傍晚扯着燃烧的嗓子
喊我回家
她让我少出差
显然她刚看到了新闻
西南地震,南方台风
是的
此刻我正在暴雨中
她突然说
你堂哥没了
老板给他一百块钱去清理烟囱
雨很大,掉下来了
这时已是黄昏
此时我没有感受到
车窗外面的雨是热的还是冷的
刚刚拎出来的叹息
这是一个城市的南城
街道的一侧刚刚修补一新
胡同里挂着一些节日的必备品
仿佛人们刚刚进城,欢呼也刚刚结束
“哎”——那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正在铁丝上挂着湿漉漉的衣服
铁器在滴答中黑亮
两只白色的油漆桶
堆满了黑色的灰色的衣服
这时已经是冬初
油漆已干,衣物正湿
那一声长长的叹息
仿佛刚从油漆桶里拎出来
滴答在已经不易速干的路面上
那片屋顶空了出来
几分钟前
那里是一群鸽子
远远看去
那里是白雪一片
只是偶尔转身
或短暂起飞
那些灰黑色的尾羽才展现出来
更多的时候
它们在下午的阴影里
那些白蜡树
叶片早已落光
声音也被带走了
它们咕咕的叫声
仿佛喉管里塞着小石子
或者一小把棉絮
红色的爪子贴着瓦上的轻霜
它们什么时候踱出笼子
又是什么时候飞回去的
我们并不知晓
复活
赫拉巴尔的墓园和故园
离得太近了
生死
只隔了两英里
红色拖拉机正在垦荒
椴木上刻着陌生人的名字
米黄风衣的女子侧身在十字路口
风不大
却吹乱了她的头发
一辆蓝色的乡下班车会晚点开来
一半光亮一半阴影的墓园
一只猫突然翻墙消失在树林里
在我看来
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复活
无端
就像今天
总有些无缘无故
无缘无故的
头疼、牙痛、半张脸浮肿
无缘无故的
暴雨来临
无缘无故的
那么多人在车站没有地方落脚
无缘无故的
一个人在黄昏抽身离去
无缘无故的
人们都不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无缘无故的
一个人的骨灰落水
无缘无故的
如此刻
暴雨来临
如此刻
人们在白天也点着蜡烛
如此刻
不信佛的人们双手合十
如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