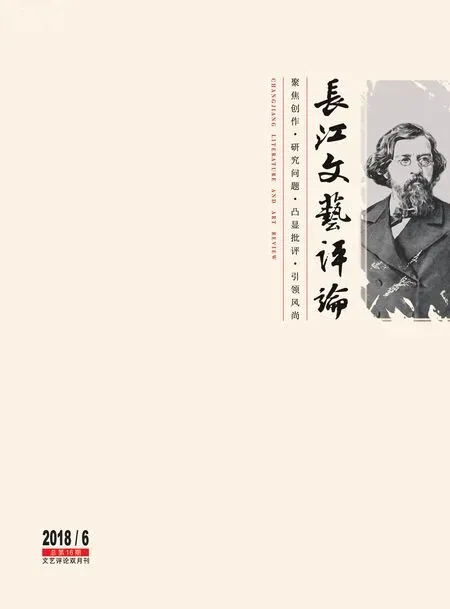2018:回溯“银屏”之旅,求索“文苑”之道
——从仲呈祥的一篇旧文谈起
◎ 苏米尔
历史是真理最忠诚的守望者。在历史浩如烟海的卷帙浩繁中,总有一些闪耀着真理之光的篇章能够汇入时间的长河,滋养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2018年恰逢中国电视剧60周年,站在这一历史节点,尝试着探寻一段关乎中国影像的历史回响,不觉间想起了仲呈祥于30年前撰写的《1988:中国影坛的两个热门话题——“娱乐片”与“主旋律”之我见》。这篇文章对当时影坛的“娱乐片”与“主旋律”这两大话题从概念界定、现象成因、功能发挥等视角予以了鞭辟入里的阐述。仲先生所述之影坛问题也适用于荧屏创作。再次品读,愈感历久弥新;抚卷长思,备受历史启迪。于是,我们立足今天,为了明天,回溯昨天,这亦为撰写本文之源起。
一、重温历史:从“二元对立”到“执两用中”
30年前的影坛正处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预备期,在此新旧交替之际,人们站在不同文化立场、秉持不同思想观念,都渴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在意识形态上难免形成一种彼此对立、一触即发的状态。这种现象投射于当时的影坛,形成了不同哲学思潮的碰撞。针对当时的影坛思潮,仲先生从“娱乐片”和“主旋律”这两大热门话题着手,探究了其背后深层的学理机制。由此文联想其几十年来一贯的哲学思维,不难洞见,该文所涉“娱乐片”与“主旋律”的关系在哲学层次上正是“二元对立”之单向思维与“执两用中”之哲学智慧的一场思辨。对于30年来这种哲学思维的博弈,我们可以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从三个层面展开诠释。
其一,是作品娱乐功能与多重艺术功能的思辨。在原文中,仲先生指出,“所谓‘娱乐片’显然是按影片自身的属性、观众作为接受主体的属性及其所属的文化环境的属性等多种复杂因素所共同制约的社会功能为逻辑起点,来抽象划类的。既如此,按照这种抽象的逻辑去推理,是否还应有与之相应的‘教化片’‘认识片’和‘审美片’呢?”诚然,娱乐功能的单一化和艺术多重功能之间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不仅使“娱乐片”的概念称谓难经推敲,亦使创作实践往往陷入“唯娱乐化”乃至“娱乐至死”的窠臼。究其根源,与三十余年所谓“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原则难脱干系。从理论上讲,“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属于创作美学范畴,二者的统一其实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统一。“观赏性”则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欲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并列统一,从逻辑学上违反了事物逻辑起点一致的统一前提;欲使“观赏性”问题在创作美学中得以解决,从范畴学上则违反了同一范畴的问题在该范畴内解决的原则。从实践上讲,“观赏性”的理论映射于创作实践便直接导致了“唯票房”“唯收视率”和“唯点击率”的“唯娱乐化”现象。如果说1988年“娱乐片”初探时期的电影《摇滚青年》《顽主》《疯狂的代价》还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和艺术水准,那么当娱乐化走向极端时,近年来伪现实主义的电影《小时代》《泰囧》《心花路放》则充斥着“小悲欢”式的纸醉金迷和拷贝美国“公路片”式的东施效颦。30年来在“观赏性”这一口号的误导下,“娱乐片”成为架空现实、偏安一隅的“乌托邦”,援引鲁迅先生的话予以评价,即“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其二,是对“主旋律”认知上“窄化”与“泛化”的思辨。就“主旋律”作品的“窄化”而言,实质上属于“画地为牢”的“题材决定论”。其实,古今中外文艺创作早已印证了题材绝非艺术价值高低的决定因素。一些重大题材在平庸者那里被诠释为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政治图解”。特别是“文革”时期提出的人物塑造“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的刻板原则严重抑制了艺术自由,违背了艺术规律。相反地,一些日常题材在高明者那里则被开掘出巨大的艺术魅力。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一件小事》以人力车夫撞伤老妇人的小题材折射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大主题。就“主旋律”作品的“泛化”而言,实质上属于“主次不分”的“题材一统论”。笼而统之地将任何作品都冠以“主旋律”之名,就丧失了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特色。大国前进犹如江河奔涌,在历史进程中有主流亦有支流。恰如仲先生文中所言,“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就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这个主导方面,就成了主潮。”对于这个“主潮”,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主旋律”应当多视角呈现。鉴于此,在防止“窄化”与“泛化”的单向思维中,以“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掌舵”,坚持“多元一体”的“主旋律”创作航向,方能抵达“主旋律”审美化的理想彼岸。30年前,正面讴歌改革开放的《T省的84、85年》,表达改革中人们意识嬗变的《野山》、鞭挞改革外在阻力的《血,总是热的》,展现改革者自身革新观念的《老井》,为当代改革家树碑立传的《共和国不会忘记》等电影都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旋律”。30年后,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农村经典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表达了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中农民精神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我们不会忘记,在那个文化八面来风的年代,《北京人在纽约》对盲目西化、崇尚出国心态的反省和对文明冲突、文化交锋现实的深思;我们不会忘记,在世纪之初问世的《长征》和《亮剑》以磅礴的史诗情怀和崇高的审美格调让新时代的我们重温那段相去不远的抗争岁月,铭记历史,继往开来。这些经历了大浪淘沙的经典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遥相呼应,汇入了“银屏”主导的中国“主旋律”之影像长河。
其三,是“主旋律”与“娱乐片”的思辨。二者之间绝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主潮”与“支流”的关系。“娱乐片”是市场兴起后适应市民阶层闲暇娱乐的产物,以反映都市日常生活为主,这与美国市场环境孕育的“肥皂剧”十分类似。“肥皂剧”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肥皂洗涤类企业投资广播剧而萌生的广播剧种。当电视媒介逐步兴起后,“肥皂剧”进入荧屏世界。“肥皂剧”所描摹的那种诙谐幽默的生活转移了“大萧条”时人们的注意力,营造了一个充满喜感的“乌托邦”。如今,中国的市场竞争激烈,城市的工作节奏紧凑,“娱乐片”可以缓解劳累、释放压力、带来欢笑。然而,恰如先哲柏拉图所言,“过度的快感会扰乱人的心智”。过度娱乐甚至“娱乐至死”只会养成一个只会笑却不知为何而笑的民族,何其悲哀!诚然,“娱乐片”具有市场环境下存在的合理性,但不能本末倒置地替代“主旋律”,以“支流”置换“主潮”。这是由于,一部中国影像史,就是以审美手法抒写的中华民族发展奋进的历史,影像长河应该映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同时也映现出这个民族的情感、思想与文化。否则,影像就不能成为人类全面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也难以担当审美而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重任。
二、审视当下:从“秩序紊乱”到“宝塔重置”
由以上三个层次的影坛思辨引发的是关于“宝塔重置”的探讨。在一种“执两用中”的哲学智慧中,“娱乐片”本可以综合发挥艺术的审美认知、审美教育、审美娱乐和审美组织功能,“主旋律”本可以在多视角呈现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主旋律”与“娱乐片”也完全可能在“主潮”与“支流”之间彼此贯通,相得益彰。然而,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产业的资本逐利本性扩张至文化领域,使文化生态受资本逻辑的影响颇深,表现为“文化宝塔”秩序的紊乱。仲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论及的“宝塔喻”中曾把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比作宝塔,置于塔顶的应当是仲先生常说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及其经典之作,因为这些艺术家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和文化深度。前些年,由于过度追求“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等商业指标,产生了个别只求养眼、不求养心的娱乐明星占据“塔顶”的现象。这些娱乐明星做出的文化贡献固然不容抹杀,但在一段时间媒体将这些创作人员当成向观众抛出的“诱饵”来追求商业利益,造成文化秩序紊乱,值得反思。
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近两年随着自媒体的崛起,“直播”成为普遍现象。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从媒介功能的视角阐发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与网络媒介让世界变成“地球村”的著名论断。然而,令麦克卢汉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媒介的演进,感官世界的丰富与精神家园的荒芜反差日益加剧。自媒体本是顺应历史的时代产物,但在方兴未艾之际,也为文化生态带来了些许困扰。当前许多所谓的“网红”通过“直播”传播的尽是带有情色意味的话题、格调不高的观念与消极愚昧的思想。较为典型的是,2018年2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了网络直播中的不良现象,并点名批评了一名李姓“网红”在直播中宣扬色情与吸毒等话题的行为。为了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官方随即全网禁播了李姓“网红”的直播内容。如果说前些年的影视娱乐明星们在艺术创作上仍有值得肯定之处,那么李姓“网红”所传内容实属难以归为艺术。网络时代异军突起的“直播”媒体已经强势地占领了大众传播的媒介空间,一些近乎蛮力的网络文化对亟待重置的“文化宝塔”是新一轮的侵袭。那些传播不良内容的“网红”点击率之多、覆盖面之广、关注度之高、影响力之大竟然需要中央媒体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思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强化管制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引领,因为文化管制只能“治标”,只有文化引领才能“标本兼治”。所谓“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以美塑人”,这种文化、艺术、美学对人的沁润滋养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作为创作者,理应尽量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佳作,净化文化氛围,实现“宝塔”重置。在我国“文化宝塔”中,仍有一些精良之作,在产业资本深度逐利的今天,仍然坚定“主旋律”航线,而非随波逐流,它们如同一颗颗跃动的音符,奏响了新时期中国影视艺术的“主旋律”。
比如,在2018年4月揭晓的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名单中,去年“现象级”的作品《人民的名义》《海棠依旧》《鸡毛飞上天》都榜上有名。其中,《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在荧屏和网络引起轰动效应,并非仅仅因为该剧突破了内容限制,揭露了高官腐败,更在于真切地体现了人民性。创作者有意着墨于形形色色的普通民众,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官场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主人公侯亮平作为人民检察官,被戏称为“猴子”,正如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般,侯亮平“大闹汉东”展现出了敢与官场腐败现象抗争到底的人民公仆形象。侯亮平身上不畏强权、机智敏捷的品格正是人民所赋予的勇气与人民智慧的凝练。《海棠依旧》则以意象化叙事讲述了周恩来总理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崇高一生。剧中毛主席和周总理托物言志,二人于海棠树下未雨绸缪,把新中国比作“雨中的海棠”,此时的“海棠”象征着两位伟人不惧风雨的胸襟气魄,是伟人的精神化身与审美意象。剧终海棠花雨漫天飘洒,既是周总理壮丽人生的谢幕,也是国人缅怀伟人的泪雨,更是新中国美好明天的诗情写意。《鸡毛飞上天》以浙江义乌的陈江河与骆玉珠这对商人夫妇从青年到白头的人生创业历程折射出义乌商人在改革开放40年间满怀憧憬又历经坎坷的创业史。“鸡毛换糖”的物物交换方式早已被时代淘汰,但其中蕴含的勤劳质朴、诚信交易、敢想敢拼的精神内蕴流淌于义乌商人的血脉中。该剧以一对夫妇的爱情和事业为“小切口”,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义乌人民商海沉浮的“大世界”,这正是新时期“主旋律”表达的一种典范。应该说,优秀的“主旋律”作品既能规避教科书式的刻板“面孔”诉诸宣教,也能将流俗的感官娱乐转化为高雅的审美娱乐。《海棠依旧》描摹伟人形象尤为成功,使“主旋律”不再是刻板宣教,而是意象寄托;《人民的名义》中被戏称为“猴子”的检察官侯亮平,在工作之外开朗幽默,不乏生活喜感;《鸡毛飞上天》在表达波澜而艰辛的创业历程时也通过柴米油盐的家庭日常拉近了宏大主题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以上三部作品讴歌“主旋律”均以具象化、生活化、情感化、意象化完成叙事,寓教于乐,宜人性情,化人养心,符合创作规律。
如果说寓教于乐作为“主旋律”创作的一种共识在30年间一以贯之,那么30年以来文化生态的巨变则带来了全新挑战。30年前由于媒介技术尚未发达,文化生产能力尚待提升,所以文化生态较为单纯,即使出现了一些造成精神污染的低劣之作,也能及时处置。30年后的今天,网络日益发达,电影、电视、互联网“多屏互动”,文化生产能力在技术助推下突飞猛进。特别是当前文化包容度提升,也使一些《小时代》式的电影、宣扬人性恶的“宫斗剧”、历史虚无主义的“抗日神剧”,以及不良的网红直播有了可乘之机,正在侵蚀我们的“文化宝塔”。因此,需要优秀的“银屏”精品作为“主力军”来净化文化生态,重置“文化宝塔”。在“主力军”中,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则是“尖锐精兵”,需要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激发人们的开拓精神,陶冶人们的审美情操,在“宝塔”重置的宏伟工程中可谓任重道远。
三、未来景观:从“美学基因”到“品格独立”
对“文化宝塔”的重置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特色、美学基因的深刻认知,更需要我们对“主旋律”作品之美学格局、独立品格的不断求索。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文艺创作者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与艺术交流中不断探索着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中国特色“文苑”之道。一些富有担当而格局开阔的艺术家,即使是对美国“肥皂剧”这种“娱乐片”的引进,也能够以中国独有的“美学基因”实现解构与重构。
一个极具镜鉴价值的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一方面,就思想价值而言,该剧以本土特色之现实主义手法,以一个北京六口之家为社会“横断面”,观照了90年代经济转型期人们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这种精神世界的变化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对观念上层建筑发挥的重大效应。展现一个时期人民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以及社会思潮的变迁正是我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所在。所以,《我爱我家》虽为“娱乐片”,却以电视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喜剧手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旋律”,其经验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就艺术价值而言,虽然《我爱我家》是对美国“肥皂剧”和情景系列剧的借鉴,但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语言风格方面,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审美格调。与欧美荒诞、怪异、滑稽、错乱、追求视听刺激、有违现实逻辑的风格不同,中国化的“情景喜剧”趋近传统相声与舞台小品的结合,具有讽刺、调侃、犀利、贴近现实、发人深省等艺术特征。90年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在人们的意识世界中,充满了新奇、未知、彷徨、矛盾,《我爱我家》正是通过日常化、平民化、喜闻乐见、亲切自然的语言形式来展现这场思潮的激荡与碰撞。
恰如仲先生在原文中的论断,“优秀的‘娱乐片’创作,也完全可能汇入‘主旋律’”。这正是以“执两用中”来克服“二元对立”的表征,从中我们不难洞见一种具有思辨性的儒家智慧。儒家的“兴观”美学为当代“主旋律”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美学启示,是“主旋律”创作重要的美学基因。在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之中,所谓“观”者,乃是体察世情与社会百态,荣获1983年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的《蹉跎岁月》以三个下乡知青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使人在一种冷峻笔调下反思“文革”,这正是以现实主义笔触反观历史、直面人生的“主旋律”佳作;所谓“群”者,乃是一种凝聚人心和审美组织功能,作为2001年建党80周年献礼的电视剧《长征》,以长征这一人类奇迹唤醒沉浸于“都市童话”与“自家悲欢”中的人们,使人萌生了久违的民族崇高感与凝聚力;所谓“怨”者,乃是艺术的宣泄和净化功能,《人民的名义》成为“现象级”作品的一大缘由,是因为该剧打开了党和人民痛恨贪腐的情感“闸门”,使人获得情感宣泄之后深长思之。值得强调,将“兴”置于首位,强调了艺术的“感兴”特质,只有触动人心、令人感动,方能发挥艺术的其它职能。“主旋律”创作应当秉持“兴观群怨”的儒学思想,继承美学基因,奏响时代旋律。
毋庸置疑,当代肩负历史与时代重任的研究者与创作者必须合舟共济,探索富有中国特色、大国气派、东方神韵的“主旋律”创作之审美格局。这理应是一种以“崇高”为审美底色、多重美学范畴“多元一体”的格局。“崇高”被康德纳入美学范畴后,表现为数量无限大(量的崇高)和力量无限大(力的崇高)。当作为“崇高”客体的限度超出主体能把握的范围时,随即否定了主体,同时也激发了主体的对抗理念,在对抗中由否定主体到肯定主体,从而产生崇高。这种崇高之美,正是对多难兴邦的中华民族(主体)面对历史上重重险阻(客体)时最精准的美学表述。历来的文人墨客对壮美河山、民族英豪挥毫泼墨正源于此。崇高是由庄重、肃穆、沉静、威严复合而成的审美范畴,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高度美学凝练。2018年,中国电视剧走过一个甲子,中国电影已逾百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须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创作原则,以崇高为审美底色,融汇优美、飘逸、沉郁、空灵、悲剧、喜剧等多重中西方美学范畴,形成“多元一体”的“主旋律”审美格局,并以这种独立的审美品格坚守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家园,迎来中国影像长河的诗和远方!
注释:
[1]该文系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先生所撰,并于1989年1月3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收录于《文苑问道——我与〈人民日报〉三十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