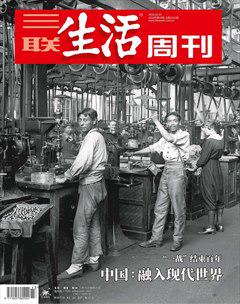专访李沧东:我不知道《燃烧》算不算一部好电影
宋诗婷
从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度上来看,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数量之少令人费解。
1979年,村上春树的师弟日本导演大森一树买下了《且听风吟》的小说版权,第一次将这位学长的电影搬上了大银幕。那是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情节松散,语言在生活化与后现代主义金句间跳来跳去。大森一树显然低估了这部小说的改编难度,当年的票房和口碑双双证明,《且听风吟》电影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像是打了个糟糕的头阵,《且听风吟》之后的30多年,村上春树的七八部长短篇小说又先后被改编,这些电影无一不陷入票房、口碑双失的困境。在李沧东的电影《燃烧》亮相戛纳电影节之前,村上春树的作品已经八年没出现在大银幕上,最近一次改编还是2010年上映的《挪威的森林》。那部电影一度被寄予厚望。原著是村上春树最畅销的长篇小说,越南导演陈英雄又拿过戛纳金摄影机奖,并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强强结合的电影版《挪威的森林》却令人失望,它将村上春树作品里忧郁缥缈的情绪渲染得过于矫情,电影又失去了陈英雄作品特有的生活质感,最终和其他改编作品一样,也没能逃脱“双失”的命运。
时隔八年,又一位非日本籍导演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搬上了大银幕。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韩国导演李沧东的作品《燃烧》成了大热门,尽管最终未能拿奖,但它还是以3.8的场刊评分成为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无冕之王”,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村上春树小说改编电影”。

电影《燃烧》剧照
小說是容器
这次成功的改编要先从李沧东的履历说起。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曾是位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沧东坚持了10年纯粹的文学写作,直到90年代初,韩国导演朴光洙邀请他担任新作《星光岛》的副导演,他才算正式转行,进了电影圈。
难得的是,李沧东很快就打通了文学与影像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他擅长将文本的诗意和情绪影像化,这种在文学性与电影美学之间取得平衡的风格很受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国际电影节)偏爱,前几部作品《绿洲》《诗》和《密阳》都收获过三大电影节奖项。
作家与电影导演的双重身份或许让李沧东更能理解村上春树和他的小说,并找到文本与影像的转化方式。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烧仓房》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作品,全文不过七八千字,以一个三十出头的男性视角,讲他结识的一个女孩的故事。女孩是那种饭局或聚会上偶尔会遇到的类型,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不知道背景,也没有固定营生,穷,却生命力旺盛。小说里,女孩结交了个20多岁的男朋友,是菲茨杰拉德笔下“了不起的盖茨比”那种类型,同样不知道背景,探不清营生,却过着奢侈的生活,有数不清的财富。小说的情节性很弱,甚至都算不上是个完整的故事,村上春树式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贯穿始终。
“乍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改编电影的作品。”接受采访时,李沧东同意大众对于《烧仓房》这部小说的认知。当初,合作的编剧吴正美向他推荐了《烧仓房》,吴正美喜欢这部小说的留白和神秘感,作为编剧,她觉得自己有很多能发挥的空间。李沧东看了,同样被弥漫于整部小说的不确定性所吸引。“女孩存不存在?仓房代表什么?男孩杀没杀死女孩?一个个谜团会引出更多谜团。”李沧东说,他找到小说改编的灵感是从两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的场景开始的,一场是女孩惠美黄昏跳舞的戏,一场是结尾男主角钟秀杀人、烧车的戏,那两场戏让他有了填补小说留白的信心。
在以往的村上春树改编电影中,几乎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导演、编剧过于尊重作家的风格,电影很难跳出作家构建的氛围和价值体系。在这方面,李沧东是有魄力的,他赋予了原本平淡的小说更深的社会意义。在平遥影展的大师班上,他曾说,拍完《密阳》之后的很多年,他一直想探讨一个议题,那就是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尤其是年轻人的愤怒。在遇到《烧仓房》后,他觉得,这部小说的文本是个很好的容器,可以装下这些年他对“愤怒”以及当下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思考。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李沧东调整了原本小说的人物设置。第一人称视角的男主角钟秀从30多岁的已婚男人变成了20多岁的穷小子,20多岁的有钱男孩变成了30多岁的“盖茨比”,女孩惠美的人物设置基本不变,两个男性角色年龄的调转和阶级差异的进一步拉大,让人物之间有了更强烈的矛盾冲突。
在村上春树的原著小说里,出场的三个人物都是模糊的,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信息。但在《燃烧》里,每个角色都更立体了。尤其是男主角钟秀,在刻画这个角色时,李沧东引入了另一位作家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也有一部与“燃烧”有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烧马棚》与钟秀的生活相呼应,小说里,男孩有一位愤怒的父亲,总是用烧马棚的方式来解决与雇主、邻里的冲突,这导致了整个家庭不停地搬迁,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男孩为父亲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又不得不为了维护父亲做假证,保全家庭的利益。钟秀的生活与小说中的男孩如出一辙,他也有位无法控制自己愤怒情绪的父亲,电影一开场,父亲就因与人动手陷入了法庭纠纷,钟秀感到无奈,但又不得不到处奔走,帮父亲求一封请愿书。
钟秀要应对的生活负担,以及他可能遗传自父亲的不稳定情绪成了电影那根随时可能点燃的导火线,也切中了李沧东想要探讨“愤怒”的初衷。

电影《燃烧》剧照
填补小说的缝隙
原著小说的魅力在于神秘感和不确定性,这种感觉很难用影像传达,李沧东在电影中加入了很多符号和线索,来引导观众,强化这种感觉。原著小说里,惠美学习哑剧,为“我”表演假装吃橘子的情节完整保留了。“别想着这里有橘子,忘掉这里没有橘子就行了。”一句台词让电影里人物和情节的真真假假都有了能被解读的空间。
李沧东还把钟秀的身份设置为写作者,在这个角色身上,他投射了村上春树和自己的经历,而这个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设置,也模糊了电影故事真实和虚幻的界限。电影快结束时,钟秀坐在房间里写作的一幕直接衔接他出手杀人,结局真实发生还是男主角笔下的想象就见仁见智了。
在以往的改编里,大部分导演和编剧都放任了村上春樹小说情节性弱这个特点,电影表达侧重情绪,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的改编作品热衷于旁白的原因。在日本导演市川准改编的《东尼泷谷》里,电影画面甚至沦为了村上春树文本的附庸,与其说电影是电影,不如说,电影是村上春树小说的MV。
虽然是作家出身,但李沧东很清楚,具有商业性的电影归根结底是要讲一个好故事。作为导演的李沧东从来不是那种无视观众的艺术家,当年《绿洲》上映时,电影被批评女性角色太弱,沦为导演讲故事的道具。李沧东听到类似反馈后很上心,在接下来的两部电影《诗》和《密阳》里,女性成了电影的中心。
为了让电影抵达更多受众,李沧东要提升《燃烧》的观赏性。他为原本很弱的故事披上了一层悬疑片的外壳。“盖茨比”Ben究竟杀没杀死女主角惠美?原著中“烧仓房”被本土化成烧塑料大棚,惠美消失后,一直没有烧的塑料大棚,Ben卫生间里的电子手表,突然多了的一只猫……线索和证据似乎让钟秀一步步接近真相,但早先埋下的无法被确认存在的人和事又让所谓真相不那么确定。
爱情和性是提升电影商业性的良药,原著小说里没交代太多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李沧东却让男主角钟秀爱上了女主角惠美。两个人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做爱,被从首尔塔反射进房间的“二手阳光”温暖着。李沧东用大量类似的细节将钟秀对惠美的情感建立起来,Ben作为第三者加入后,对方的多金、自由和价值观一次次冲击着钟秀,在他心中积累着愤怒。
尽管对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但李沧东保留了《烧仓房》中最核心的部分——Ben对于社会与人的价值的讲述。在小说和电影里,这个情节都被设置在夕阳西下的乡村,惠美已经睡去,都吸了大麻的钟秀和Ben坐在夕阳里喝啤酒,各自聊起自己的经历和思绪。Ben聊起自己烧塑料大棚(原著中是烧仓房)的爱好,那些无人在意的废弃的塑料大棚等着他去烧掉。在这里,“废弃的塑料大棚”像是在隐喻惠美,以及和她一样没有亲人、朋友,消失了也不会引起注意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和物,Ben所代表的一类“盖茨比们”有着纳粹式的价值观。
不仅保留了小说中的核心情节,李沧东对于当下年轻人精神世界和阶级差异的探讨更进一步,他引入了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两个概念,前者指生理上的饥饿,求的是温饱,后者指精神上的饥饿,追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电影对Ben一样的年轻人未做过多道德判断,反而揭示了他们内心的空虚。
看完《燃烧》,观众感受不到太多村上春树原著小说的气息,这是一部完全李沧东风格的电影。对于村上春树的粉丝来说,这或许有些冒犯,但对于电影本身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探索。
——青年记者“走转改”水墨画般的村庄书写着别样的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