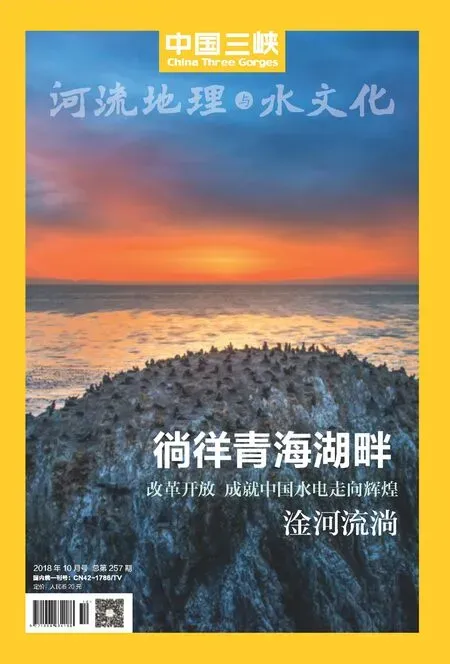宗喀巴与塔尔寺
◎ 文 | 耿占坤 编辑 | 孙钰芳
情人哟!神佛哟!
我依恋情人,
却牺牲了佛缘;
我入山修道,
又违背了情人的心愿。
天哪!天哪!
我愿隔世陷落丰都,
片刻也不离开情人的倩影。
——青海藏族民歌
日月山公平地将落在山头的雨雪之水一分为二,一半向西形成倒淌河,穿过广阔的草原流入青海湖;另一半则逐天下流水而东去,在窄峡宽谷之间汇集成黄河上游一条最大的支流——湟水,于是沿途地名就有了“湟源”、“湟中”这样的称谓。
湟水河的南、西、北三面山峦环绕,向东一面敞开,直奔黄河,从而营造了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大的河谷走廊。这条走廊所创造的人类文化,被史籍与黄河上游文化并称为“河湟文化”。
湟水流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彩陶文化博物馆。1973年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距今4000多年历史,已成为中华彩陶文明的象征。
止贡巴·贡却丹巴然杰在《安多政教史》中,曾引用乃东·曲吉尼玛尊者如此充满激情的描绘:“这里有‘恒河之妹’的湟水,河水滔滔向东。其南北两岸的广大土地,美丽富饶,人称宗喀。南部的积石山脉逶迤磅礴,伸向遥远的天边,被誉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就在这逶迤壮丽的山脚下降临人世。”《圣地颂》中赞道:“此地形似八瓣莲花,天空宛如八个转轮;后山雄伟而优雅,前山象谷物堆就。”
被尊为“第二蓝毗尼园”的塔尔寺就座落在这朵盛开的莲花之中。六百年来,它由一片美丽的山间牧场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成为千千万万信徒们的身心归宿。
“第二佛陀”诞生
1357年,这里的人们总是不经意地看到,已有三个孩子的藏族妇人香萨阿切几乎每天都背水走过这片山间谷地,她在负重途中总要在一块石头上靠停下来休息一阵,因为那时她已怀有身孕。到了金色的十月,香萨阿切顺利地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就在这片草地上,她剪断脐带,几滴鲜血悄然渗入草下的泥土。听着婴儿的呱呱啼哭,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此时的香萨阿切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绝对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成为一位至尊的圣母。直到第二年,那脐血滴落的地方生长出一株翠绿的菩提树,十万片叶子上每片都呈现一尊狮子吼佛(释迦佛第七化身)像,因此取藏语名为“衮本”(十万佛身像)。虽然大家都欣喜地相信这是一个吉祥之兆,但并没有谁清楚它真正意味着什么。
香萨阿切这第四个孩子于七岁时出家,在距家乡以东数十公里的夏琼章(今化隆县查甫夏琼寺)授于沙弥戒,当时的寺主、藏传佛教高僧敦珠仁钦为其取名罗桑扎巴,密号顿月多杰。这就是一代宗师宗咯巴。显然,宗咯巴的称谓是他后来在西藏取得很高地位之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宗咯(湟水河畔)人。
宗咯巴不仅具有聪慧无比的天资,他对佛学更具有一种敏锐的悟性。在他僧人生涯的最初十年里,师从敦珠仁钦,到17岁时,他在佛学方面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就在这一年,受敦珠仁钦的鼓励和资助,宗咯巴赴西藏游学深造。

湟水河 摄影/张国财
也许宗咯巴注定要成为一代宗师,他在西藏求学期间并不始终依附于一个门派之下,而是广学博采,显密并修,终于博通显宗、密宗技法,成为一代高僧。宗咯巴于29岁时受比丘戒,此后开始接收门徒,讲经弘法,他敏锐的思维、严密的逻辑、独到的见解在同各派的辩经中屡战屡胜,在藏传佛教界以及民间逐渐获得声誉。到40岁前后,宗咯巴对显密教经论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他继承阿底峡所付龙树的中观思想,吸取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手印法和宁玛派的圆满法等各派法要,形成了自己的佛教思想体系,并进而展开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活动。从43岁到53岁的十年间,宗咯巴集中撰写了阐述自己思想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他一生著作达一百七十部之多,因而被称为“百部论主”。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宗咯巴还积极进行宗教改革活动,主张僧人应严守律戒,广学经典,先显后密,显密双修等。1409年,宗咯巴利用他的影响发起不分教派和地区、有万人参加的拉萨祈愿大法会,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传召大法会之创始。大法会的成功,使宗咯巴获得了西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同年甘丹寺建立,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形成。格鲁派形成后迅速扩展实力,在中央王朝、西藏地方政权和信徒的支持下,很快就超过原有各教派,成为在藏族社会长期占领导地位的教派,并逐渐集政教权力于一身。因格鲁派僧人戴桃形尖顶黄色僧帽,世俗又称其为黄教。
宗咯巴于1419年圆寂于甘丹寺,他的一生充满了种种神奇。
1378年,22岁的宗咯巴在西藏收到了母亲托人带来的一绺白发,并附信说“吾已年迈体衰,望儿务必返里一晤”。宗咯巴对母亲和家乡充满思念之情,望着母亲的白发,他仿佛看到了母亲那深切期盼的目光,但最终他还是决意学佛不返,让人给慈母和姐姐带回血绘的自身画像一张、狮子吼佛像一轴,并在信中说:“倘若在我出生的地方,以十万狮子吼佛像及菩提树为胎藏建一佛塔,则如同亲晤儿面。”第二年,宗咯巴的母亲依照儿子的嘱托,将由脐血而生的菩提树用绸缎包裹,与印成的十万尊狮子吼佛像共为胎藏,建成一座莲聚宝塔。据说,最初的菩提塔只是砖石结构,塔身很小。

酥油花雕塑 摄影/董宁生

塔尔寺唐卡珍品 摄影/殷生华
莲花中的珍宝
一百多年后的1560年,静修僧仁钦宗哲坚赞来到这片幽静而神圣的山间谷地,他在距莲聚宝塔不远处修建了一座供其诵经坐禅的参康(禅堂)。寒来暑往之间,僧人的慧眼终于观悟了这净地的胜妙之处。从莲聚宝塔环望,四周由八座平缓的山峰环绕,每座山峰均呈莲花瓣形。夏秋季节山色一片青翠,山间流水潺潺,高空云雀啼鸣,一派幽静祥和,几座青山衬映在蔚蓝的天幕之中,呈现一个巨大的优波罗(青莲)花状;冬春时节山峰白雪皑皑,一片静穆圣洁,超然世外,八座玉峰又组成了一朵劳陀利(白莲)花状。座座山峰之间碧空高远,瑞气凝霞,光芒劲射,犹如八根辐轮,恰似法轮常转,传播着永恒的妙谛。
于是在1577年,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弥勒佛殿在菩提塔南侧正式建起了,藏语合称为“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弥勒洲”。以后四百多年间,佛寺不断扩建,菩提塔也几经修缮装饰而被置于殿内。据说因为先有佛塔尔后有佛寺之故,便有了“塔尔寺”这个汉语俗称。
今天的塔尔寺已经形成了一座占地40多公顷、汉藏建筑艺术相互辉映的古刹建筑群。我无法猜测,当年香萨阿切带着对儿子的深切思念而建起那座简朴的佛塔时,是否预知这里将会成为多少善男信女、多少圣贤和凡夫俗子身心向往的圣地呢。当年那些在这山间背水的女人、牧羊的少年一定没有意识到,那株由宗咯巴的脐血而生长的菩提树,会给这偏僻的山隅带来一座佛国圣城。

塔尔寺如意八塔 摄影/殷生华
塔尔寺的中心是大金互殿,是覆盖于莲聚宝塔之上的塔殿。寺中主要建筑还包括:小金互殿、大经堂、文殊菩萨殿、释迦佛殿、祈寿殿、印经院、如来八塔、依估殿、遍知殿、花院以及供僧人学习研究天文历法、舞蹈艺术、医学、密宗、显宗等学识的“扎仓”。还有众多依山而建的僧舍。
作为宗咯巴的诞生地,塔尔寺无疑是青藏高原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但它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寺院珍藏的经卷、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不同时期、不同风俗的雕刻与壁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宗教法器数不胜数,更以精美的壁画、独特的堆绣和奇妙的酥油彩塑“艺术三绝”而著称,从而使它成为一座文化艺术宝库。数百年来藏族社会政教合一的历史,又使塔尔寺成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等世俗权力于一体的中心,是一部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寺中各种金玉珠宝琳琅满目,仅它们的商品价值就难以估量,更不用说那赋予它们无限身价的宗教与文物价值了。塔尔寺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根据三世达赖和四世达赖的要求进行大规模扩建,此后,第五、七、十三、十四世达赖和第六、九、十世班禅都在此驻锡。清康熙以后,历代帝王都对它格外重视,多次向塔尔寺赐赠匾额、法器、佛像、经卷、佛塔、金银珠宝等,从而使塔尔寺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更加深远。据说在塔尔寺全盛时期曾有建筑物近万间,僧侣3600多人。
对于所有现代的观光游客来说,塔尔寺只是他们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惊讶。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知半解地听完导游一成不变的解说词,脑子里留下一片辉煌、一片神秘、一片空白,然后这一切在他们的生活中很快就淡漠了,假如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有机会偶尔接触到这个词语,他们或许会说:“噢,塔尔寺?我去过。”
对于数不清的信徒,那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塔尔寺、宗咯巴、佛祖、玛尼等等,这一切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来到这里,不在于追溯它的历史,也不在于欣赏它的艺术,而来到就是目的。他们匍匐于金瓦之下、红墙之间、佛殿之前,他们转经、祈祷、唱颂,他们将自己的灵魂、肉体、财物和自己的来世无条件地交付到这里,从而获得身心的解脱和抚慰,达到宁静与幸福的境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了佛祖,没有谁注意他们、记得他们。
走进塔尔寺的两种方式
我有机会一次次地来到塔尔寺。假如我是一个观光客,我早已厌倦了;假如我是一个信徒,我也许多少也该获得某种佛缘了。然而我既没有丝毫倦怠,也没有半点得道,我只是一次次到来、观看、感受。我体会到,进入塔尔寺的内在之处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走进大金互殿或大经堂,在幽暗的光线下仰望大银塔或在数百名僧人的诵经声中悄然伫立,当我在无意识中屏住呼吸的那一瞬间,我进入了它的奥秘。另一种就是远远地观望,在这种状态中我能够轻松地吸着香烟甚至哼着优美的曲调。

夏日塔尔寺 摄影/张国财
塔尔寺宏大的建筑使你相信那些殿宇中有足够的空间任你的精神飞驰,然而当你一旦进入,那想象中的自由就立刻不存在了。在所有的殿堂中我都深切地意识到,这里的时空并不属于我。高大庄严的佛像、威猛狞怖的金刚、神秘的灵塔与佛龛、壁画和悬挂于间堂的布画、各种吉祥物与装饰物占据了宽阔的殿堂。殿堂内光线低暗,几乎没有来自外界的自然光线,一排排的酥油灯长明于佛像之前的供案上,灯光闪耀跳动,使殿内的一切都处于忽明忽暗的氛围之中,佛像的金身、镶嵌于各处的珠宝发出奇异的光芒。偶尔有一两个僧人无声地走动于殿堂之中,却更增添了气氛的肃穆。这时我感到,时间在这里早已凝结了,如果它存在,也只能以“劫”来计算,对于我来说,这无疑代表一种永恒。因为在这里,我们世俗中一切显示时间存在的事物都消失了,阳光的游移、风的吹拂、水的流淌,更不要说钟表的摆动。这时候,我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像信徒一样五体投地,但我的灵魂早已匍匐在地下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欢乐或痛苦都无法独立而自由地存在,它们被一种超然的力量统摄着,继而被彻底消解转化,变成敬畏之感。这种敬畏消失之后,我便进入了一个空寂的宁静状态。
多数时候,我总喜欢爬上寺院北面的一座山包,静静地坐下来去纵览眼前的一切。这使我再次成为游客与信徒之外的另一种人,因为游人难得这样充裕的闲暇,而对于信徒,这种居高临下无疑是一种罪过。
与在殿堂中的感觉完全不同,在这里我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可以随意开始或停止看、听、想等一切行为。在蓝天白云覆盖下的这片山峦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我凡俗的目光无法分辨山峰的莲花之形,它们平凡得如一支牧歌,但它们宁静青翠,的确很美,也美得如一支牧歌,没有任何令人身心厌倦的雕琢之痕。山峦之间是塔尔寺宏大的建筑群,在阳光照耀下,最醒目的是几种交相辉映的色彩,金黄色的殿顶,班禅行宫和大殿的红色,灰色的飞檐屋角,洁白的墙壁。

塔尔寺大殿广场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跳欠法会 摄影/殷生华
塔尔寺的建筑群中汉式歇山顶和藏式平顶共存,建筑物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不追求宫廷式的严谨与对称布局,而是在变化中求和谐,显示了藏传佛教寺院与汉传佛教寺院完全不同的特点。汉佛教寺院大多采用轴心对称的宫廷式建筑格局,各大殿前后排列、相互对应贯通,层层升高,体现了与封建王权相一致的严谨、刻板和不容打破的规则,充分表现了对世俗权力和世俗文化的趋同。而藏传佛教寺院在布局上则保持了更多的自由,在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寺院建筑努力以一个中心为基点,呈四周辐射状态,犹如各大部洲环绕着神圣的须弥山一般,仿佛在讲述一个佛教的创世故事。像塔尔寺这样地形条件不具备的寺院,建筑风格更加丰富多样,不要求对称或统一,殿宇随自然地势而建,遥相呼应,显示了一种变化中的和谐。
塔尔寺的外观与殿内形成了鲜明对比,丰富多变的色彩和高低错落的殿宇,或隐或现于山间植物的葱郁之中,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这个时空不是凝固或僵化的,而是开放性的,使得人的思绪和情感与佛的精神和奥义之间能够交流,将世俗与圣境两个世界沟通起来。由于山、水、云、树这些自然事物的参加,使得塔尔寺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人文事物,它与自然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景观,建筑物和各种色彩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山水与树木又成了人文不可缺少的成分。我深信这种构成绝不是一种巧合,它体现了自然精神、宗教伦理和人类情感的交织和相融。崇尚自然的我忽然间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六百多年以前的多少个世纪,这些山峦、这片绿色以及这条小小的溪流,它们是多么孤单和寂寞。我觉得,塔尔寺的奥秘就在于体现了这种神、人、自然的三位一体。
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寺院的幽静只能在早晚的时刻才会出现了,多数时候,道路和殿宇之间运动着的色彩已不再是以暗红色的袈裟为主,而更多的是男人们的西装革履,女人们各色各样的长衫短裙。从殿宇之中仍然有法鼓长号和深冗的诵经声不断传来,但它们常常被汽车的轰鸣和游人的喧嚷所淹没。在我的印象中,始终如一的依旧是那些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和她们悄然地匍匐在每一座殿堂、佛塔和每一块砖石之前,一步一叩,五体投地,全然不去在意汽车扬起的尘土和游人匆忙的脚步,除了心中的佛祖,他们身外旁若无人。
在这个山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佛界与尘世之间难以隔绝的联系。塔尔寺西面一个山包之隔,是一座最初依托塔尔寺而兴起的名为鲁沙尔的小镇,目前是县政府所在地。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小镇的发展也格外快起来,餐饮、宾馆、娱乐设施不断增加,楼房到处生长。一条经过多次扩建的宽阔道路从县城中心直通到塔尔寺的山门,道路两侧无例外地是一间间出售宗教用品和以藏族风格为主的各式旅游纪念品的小商店。有趣的是,在这个佛教中心从事相关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回族,他们毫不含糊的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物质与精神、商品与文化就这样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又微妙地分离着。象征释迦牟尼一生八件大事的如来八塔所在的广场,现在是各种旅游车的停车场。一直令我费解的是,几年前的一次维修中,原来的八座旧塔被彻底替换了,取而代之的是八座装饰鲜艳的新塔。它们真的比以前那些显得破损的旧塔好看多了,我猜想,当游客以此为背景照相留影时,彩色效果一定更胜于原来那些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旧塔。然而每当我站在这里时,我总是很强烈地怀念那几座旧塔,因为这些新塔不对我说话。
塔尔寺同西藏的布达拉宫、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共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中心寺院,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它们既是神权、政权和财富的象征,精神与物质的体现,更成为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汇集之地。在六大寺院中,塔尔寺是规模较小的一座,但它的地位无可取代。
宗咯巴对藏传佛教的贡献远非只是创立了诸多教派中的一种,而是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格鲁派的地位
十四世纪后期,西藏佛教各教派处于混乱低落状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代宗师宗咯巴已经把显密宗各派的教法全部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他渊深的学识和敏锐的思想无人能比,享有极高的声望。针对西藏佛教界的种种弊端,十五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宗咯巴通过讲经、辩经、著书立说等一系列活动,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因得到民众的拥护、地方政权的支持和宗教界的响应而得以顺利进行。宗咯巴在噶当派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因而当时又被称为“新噶当派”,格鲁派发展起来后,噶当派归于格鲁派。“格鲁”意为善规,直接道出了这个教派的根本特征。

格鲁派僧人服饰 摄影/殷生华
从宗咯巴两位弟子传出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全称“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是一个梵、蒙、藏语组合的名称,意为精通显密学识如大海一样渊博的至圣大师。被认为是观世音的化身。班禅,全称“班祥额尔德尼”,梵、藏、满语组成的名称,意为珍宝大学者。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两个活佛系统均在其五世时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1751年,清政府下令由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权,从而格鲁派正式取得对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长达二百余年。
宗教拥有对信徒思想和精神上的绝对统治是不言自明的,而藏传佛教所以同时能取得世俗权力具有特殊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藏族社会没有世俗教育,寺院就是教育中心,进而也就成了文化中心,藏传佛教寺院掌握着历史、哲学、文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所有知识,从而也很自然地控制了经济、贸易、农事、畜牧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力,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宗教的依赖还包括:医病、占卜、择吉、念经、念咒、祈福、 攘灾、超荐亡灵、祈雨防雹等等。另一方面,佛教在藏地传播之初便是自上而下,即从王公贵族开始的,到后来,许多封建领主本身就是法台或寺主,寺主、活佛拥有庄园和领地,不仅拥有教徒而且拥有农奴。同时,自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均极为重视和推崇藏传佛教,不断对其宗教首领进行册封和赏赐,使他们的世俗地位和权力不断提高与加强,最终使宗教领袖得以“大皇帝”之名行使世俗统治权。

几位藏族人在塔尔寺磕等身长头为家人祈福。 摄影/刘浪/视觉中国
藏传佛教的众多寺院中,生活着大量的僧尼。僧尼们的生活因其等级地位、职业分工以及教派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僧尼的生活充满神秘,他们既食人间烟火,又守持种种律仪;既向往宁静超脱,又追求成就和幻想。他们跋涉于世俗和神界之间,既可转身成为丈夫或妻子,也能够潜往深山获得超凡的瑜伽神力。
僧人生活与我们生活之间的距离远不只是相隔一道山门或一件袈裟,实际上他们与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和精神世界。而他们那个世界我无缘进入。于是,更多的时候我转而去努力接近那些朝圣的香客。
塔尔寺的香客以安多藏区最多,还有不少来自西藏、四川和云南藏区,也有来自内蒙的。信徒以藏族为主,也有大量的蒙古族、土族和汉族等。我常找机会和这些香客聊天,同所有好事者一样,我有时会因为语言不通或者对方不愿交流而被一阵沉默或一个微笑回绝,有时也能谈得很投缘。
与香客的对话
我一直记得在塔尔寺遇到的来自云南迪庆的一家人,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孩。那时她们正围绕着寺院磕长头,坐在如来八塔附近休息。我走过去同她们答话,没想到她们的汉话竟说得很不错,当我知道她们来自云南中甸时,我高兴地说,几个月前我去过中甸,还去了松赞林寺,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我的话把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她们用惊讶而欣喜的目光看着我,气氛顿然融洽起来,因为她们的家就往在中甸县城附近。于是我在她们对面席地而坐。她们问我到中甸去干什么,我回答说,同你们一样。这使她们疑惑起来。当我简单说了我在中甸到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后,我看得出来,她们相信我没有撒谎,但她们纠正我说:你那是旅游。我们都笑起来。这是祖孙三代,老妇人大约五十至六十岁之间,她的女儿三十来岁,外孙子十岁左右,我问她们的名字,老人只告诉我她女儿叫拉姆,男孩叫扎西。在一种同乡的感觉中我们聊得很融洽。老人十几年前按照当地一位活佛的卜算,曾同她的丈夫一起来塔尔寺,那时她们在宗咯巴大活佛面前祈过一个愿,这次是专程带了女儿和孙子来还愿的。我不好问是个什么愿,因为那是她们同佛祖之间的秘密,但从老人的话中我猜想那一定与女儿和外孙子有关。我问她们给了寺院什么布施,拉姆说因为路途很远,带不了什么东西,只有一点钱。我问有多少钱她却笑而不答。
拉姆一家在中甸以农业为主,她说这些年生活很富裕,所以出门很方便,一路坐车,晚上可以住价格不高的旅社,而十多年前,她的父母出来时却历尽了艰辛,夜晚无论多冷都露宿在墙角树下,白天要转经磕头,还常得忍受渴饥,现在就不用受那些罪了。老人对这话似乎有点不太满意,她表情严肃地说,可佛爷在保佑我们。拉姆知错地吐了一下舌头。拉姆告诉我,她们这次的旅程非常遥远,等离开塔尔寺后,她还要和阿妈与儿子一起去拉萨,这次朝圣她们计划两个月完成,她们刚离家十几天时间。虽然现在交通很方便,但我能够想象她们未来的旅程仍然会十分艰苦。

青海湖风光 摄影 / 东方 IC
祖孙三人又要起身继续磕头了。我问拉姆,为什么不到大金互殿那里磕头。拉姆很风趣地笑着说,还没排上队呢。
我默默地望着她们一叩三拜地朝前而去。藏传佛教信徒这种独特的叩拜方式对我的心灵产生一种震撼的力量。我曾在青海湖畔的草原上尝试过这种磕长头的方式,虽非出于信徒的虔诚,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游戏,它使我体会到了五体投地的那种谦卑之感,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我已感到腰酸背疼。我从心底由衷地钦佩信徒们那源自心灵的意志和力量。有时我这样想,一个人在一种超然宁静又满怀感恩的心态中,进行如此的身心旅行,岂不是一种对精神的升华、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砺?未必这不是佛祖为众生赐福和禳灾去病的妙法。
透过信徒们宁静的表情和他们谦卑的身影,我深深感到,不是黄金和珠宝、也不是香萨阿切和他非凡的儿子创造了塔尔寺,而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男女创造了它。宗教除了是一种信仰、一种寄托,更重要的是一种与他们的身心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集纳了无数男人和女人的希望、欢乐和爱,集纳了他们的真诚与智慧,塔尔寺才成为一块闪射着人类精神光芒的物华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