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贫穷遮蔽的爱
宋先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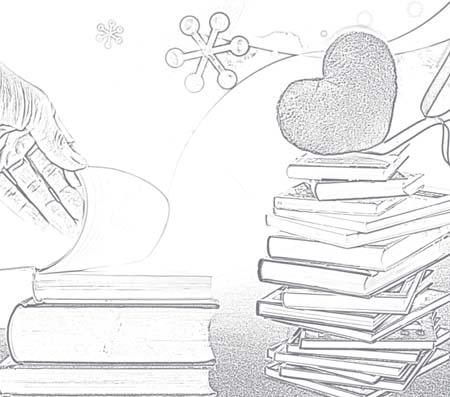
曾剑的这部小说其实并不像它的题目“净身”那样显得多义、可疑甚至令人浮想联翩,它就是一部关于贫穷的叙事,关于贫穷如何限制爱的确认、爱的表达的故事,也是一个少年终于战胜贫穷带来的羞辱感而对爱的接纳的故事。因此,净身不是阉割,也不是光着身体,只是故乡红安为死人洗澡的一个丧事仪式。“我”拒绝见聋二到虔诚地为死去的聋二洗澡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去除对聋二爱的遮蔽的过程。
像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一样,贫穷一直是曾剑回望故乡的作品中的背景、抒情底色和叙事动力,它不仅奠定了作品的叙事基调,也塑造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格局。这些都在曾剑的《净身》中有很好的体现。
贫穷中的成长
整部小说的主线是“我”——四郎的成长故事,因为贫穷,所以四郎的成长故事又与寡汉条子聋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整部小说的线索很简单,就是“借宿——蹭饭——送学费——过继——辍学——当兵”。四郎家儿子多,住处少,所以父母就将九岁的四郎送到窑匠聋二的茅棚中借宿,不知是母亲故意还是偶然将晚饭做得很迟,所以借宿又多了蹭饭。当四郎因为无钱交学费,面临辍学时,又是聋二手掌中的“坚硬”的新票子把在教室后排罚站的四郎领回了家。四郎的父母为了让四郎在聋二家“吃住用”得理直气壮,并让四郎能够读书,就决定把四郎过继给聋二。虽然因为聋二的嫂子葵花的撒泼式的阻挠,过继仪式并没有得以顺利举行,但这并不妨碍聋二承担起了四郎的“吃住用”。虽然四郎是棵读书的苗子,但天灾——一场大雪夺去了聋二牛犊的命,也断了四郎当年学费的来源,四郎终究还是辍学了。在走投无路之际,聋二拦住了欲去武汉打工的四郎,劝其当兵,“去吧,去当兵,考军校,当军官,光荣,将来也好说媳妇”。
所以在四郎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生他的父母,也有一个养他、爱他的聋二。只是因为贫穷,“我”与聋二的关系中爱的真挚和无私与贫穷和农民的算计紧紧纠缠在一起,成了“我”不敢回望的痛。
贫穷中被遮蔽的爱
表面上被中断和取消的是改口仪式,但深层里却是贫穷状态下对爱的遮蔽和犹疑。
首先是父母之爱的被遮蔽。对“我”父母而言,他们忙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儿子们的情感需求。“我的父亲,他热衷于种地,成串的儿子在他眼前晃荡,他很少过问,他或许对我们不在乎,或许对我们这种散养的状态很满意,或许他根本就没发现我们在他面前多一个或少一个。他要么在田地里闷头干活,要么坐在八仙桌前抽烟,喝酽茶”,“夜里,我到父亲母亲床上去睡时,父亲的眼睛瞪得像电灯泡”;母亲呢,“天黑时,家里养的猪没回屋,鸡窝里少了一只鸡,母亲都会找,她却不找我”,晚上吃饭,母亲却让我上窑场找聋二,“我是她的儿子,她竟然把我甩给聋二,甩得这么干净”。母亲难得的一次表达对我的疼爱,是在决定把“我”送给聋二的时候,在这里“疼你”成了送子的最好的借口“娘是疼你,才把你给聋二。咱们家供不起你读书,把你送人,娘心里也不好受。话说回来,给谁当儿子,你还不是咱老杨家的血脉。”如果说送人是为了能让“我”继续读书,但“咱老杨家的血脉”和父亲的“以后让他养你老”真正显示出了这种爱具有农民式的狡黠——凡事只讲实际利益。这似乎与母亲坚持“过客”——“形式上的东西还是要的,这样才名正言顺”有点悖论,而当母亲说出“你当他的儿子,吃得仗义,住得有理由”时,才觉得葵花说的“只知道生,不知道养”不是完全没道理。
在“不顾”和狡黠的爱中,“我”不仅对父母的爱有犹疑,不止一次觉得自己“在那个家里是多余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学校,家,哪里都容不下我”。而且我对聋二的爱也满怀惶惑。聋二无疑是真心地喜欢我——四郎春野的,但是面对聋二的爱,“我”却充满了惶惑,甚至在“懂事”之中有几分讨好。“我心里一暖,同时有些惶惑”“饭后,我懂事地抢着洗碗”。在父母和聋二正式谈到过继,当聋二沉默时,“沉默像一把无形的刀,一点点切割着我的自尊。”“我想哭,却没有泪。”当听到聋二说“我愿意四郎当我的儿子,我喜欢他”时,“这个声音,像一声春雷,将我内心储存了整个冬天的阴霾驱散”“我像解压的弹簧,从床上弹起”。
贫穷中的爱
在一般的生存欲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读书是奢侈的,简单地爱和直接地表达爱也是奢侈的,因此聋二对“我”真诚而不图回报的爱成了“我”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担。
聋二竭尽所能地爱“我”。
他给了“我”在家里很难吃到的食物。当“我”到聋二窑上借宿时,他像招待客人一样,先用鸡蛋和面条给我“烧下午茶”,让“我”觉得“这是有记忆以来,我吃得最饱的一次”,接着又给我做夜饭。
他给了“我”安全感。“我”年纪小,怕黑,怕鬼,聋二“睁着眼睛,等着我睡,我觉得他比我亲生父亲还亲。我往他后背挨过去,贴着他温热的肌肤。”“我将身体挨上去,把脸贴在他的脖颈上,肚子贴上他的脊背,腿也紧挨着他。我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紧贴他,感觉到他的存在,那恐惧才慢慢地弱下去。”
他尽最大努力供“我”读书。当“我”因为没有学费被罚站,并濒临辍学的边缘时,聋二带着“坚硬”的新票子到学校里;上中学以后,聋二送我上学,为我交学费,让我周六回家,到他那里拿米拿菜。最后,聋二卖瓦的钱被葵花要走了,牛犊子又被冻死,这就彻底断了“我”读书的路。尽管如此,聋二还是拦住去外打工的“我”,把“我”劝上了当兵、考军校的路。
而这,并不是像村里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以后“养老”“将来能沾他的光”,而是“我只是觉得四郎是棵好苗,窝在山里可惜。就像一株好树苗,长在荒坡,眼看着缺少水分,就忍不住想给它松松土,浇点水。我不图回报”。
即使这样,爱的真诚和无私也无法战胜乡村的贫困,也无法让“我”通过读书这条途径走出乡村和贫困,也由此割断了聋二和“我”的情感联结和情感发展。也就是说,因为贫困,聋二的爱仅仅止步于食物和安全这一基本生理的层面,无力支撑“我”向精神、成功等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当“我”探亲回来,聋二的贫困和苍老不仅阻止了“我”和聋二情感联结的恢复,而且唤起了“我”对昔日贫穷带来的无力和耻辱的记忆,而聋二作为“我”的保护者的光芒熄灭在眼前的脏乱之中,留存在我记忆中的温暖也冷却在相逢的尴尬和困顿中。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在探亲之时,“我”还没有足够强大到战胜过去贫穷带给我的无力感和羞辱感,或者强大到去改变聋二当前的困顿,实现“在这片窑场盖起三间砖瓦房”的理想,以致将过去的贫穷、将聋二对“我”的爱都视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贫穷带给“我”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竟然将爱也视为一种负担,羞于接受,也耻于表达?
结语
凈身仪式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释放,是聋二与“我”父子之情的回归,也是被遮蔽的爱的释放。在这个仪式中,“儿”与“爷”的对称是对多年前过继的最终完成,也是对不是父子却情同父子的关系的确认。聋二不图回报的爱最终得到了一个干净的身体、排场的丧礼和“我”的追思。聋二在“我”怀抱中带着“天真与幸福”走了,“我”在“爷”的高呼中“如释重负”。可是,另一个寡汉麻球呢,他在哭聋二的同时,也在哭自己。可见,贫穷的阴影和遗留依然在,就像葵花对聋二财产的追问一样。
只有聋二对“我”的爱是简单、明了、真诚而不图回报的。
聋二对“我”的爱的两面性:一方面不图回报,有希冀;另一方面,最大的希冀是找到媳妇。贫穷限制认知,爱的淳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