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经验、地域特色与历史书写
郑润良
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呼吁青年军旅作家必须寻找军营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结合点,提升作品的文化和思想底蕴。“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二摇篮(包蕴了部分军营文化的一个团,一个连乃至一个班),便必须再把它溶化到一种地域文化(军营驻地或生活基地的特定文化背景) 中去,和那儿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生活形态、人物心理相契合,形成一种有地域色彩的军旅文学。”在70后新锐军旅作家中,卢一萍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评论家施战军指出:“盧一萍围绕南部新疆这个场域创作的一批小说,对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地域有时候与一个作家的经典作品关系并不大,但好作品必须在特定场域才能产生。我觉得卢一萍找到了这个时代变幻中相对缓慢的‘场域。”小说集《父亲的荒原》收录了卢一萍近年创作的六部代表性军旅小说,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在特定地域文化与军旅文化精神之间寻求融合的努力。
卢一萍的这种文学追求与他自身的独特军旅经历息息相关。“1996年6月,20出头的他在面临毕业去留的问题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奔赴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哨所。在校时,他作为班长、最有潜质的创作人才,是北京各大创作团体的首选对象。但他婉言拒绝了在很多人看来千载难逢的留京工作机会,执意要回到‘世界屋脊的寂寞中去,与士兵们一同感受生命的尊严与牺牲的快意。半个月之后,卢一萍抵达南疆军区政治部报到……而后,他又借着下连蹲点的机会,一头扎到了艰难困苦的红其拉甫哨所。此后,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卢一萍始终没有离开过海拔5000多米高的边防连前哨班以及季节性的执勤点。”从2007年完成的《帕米尔情歌》开始,一系列以西部边疆生活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渐次成形,构成了卢一萍军旅文学创作的主体内容,卢一萍找到了将地域文化与军旅文化融合的独特方式。
小说集中的《七年前那场赛马》就是这两种文化经验融合的结晶,既书写了草原文化,也延伸到军旅文化的思考。一方面,这是一曲草原文化、骑手文化的挽歌。骑手文化的精髓,用老骑手海拉吉的话说就是人马同体同德:“你必须能够驾驭自己的骏马,这仅靠勇敢和技艺是不够的,还要向马展示你的智慧和爱心。马性强而不倔,非常好强而争胜,能逆风而上,无争名图利之心,你看畜群贪恋水草,但你屁股下的坐骑依然昂首阔步,对丰美的牧草视若无睹,这是因为它有一颗高贵的心——你也看到过,即使是几匹马同拴一个槽头,它们也不会像猪狗那样为争食而龇牙咧嘴,它们的用心不在槽枥之间,而在千里之外。马的德性如此,骑手也要如此,人马同体同德,血脉相通——即使你的马是一匹普通的马,你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但这种骑手文化已面临失传的境地。马木提江之所以不想让久别七年的老朋友军官卢克来看自己,是因为草原上再也不赛马了,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来满足卢克再赛一场马的愿望。七年前,同时爱上萨娜的马木提江和卢克决定通过草原上古老的赛马方式来决定谁留在萨娜身边,最终马木提江凭借一个马头的距离获胜。七年后,马木提江、卢克与年老的海拉吉大爷在酒后完成了草原上的最后一场赛马。马木提江在赛马后告诉卢克当年自己曾想故意输给他,让萨娜跟着有文化的卢克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出于骑手的本性,马一跑起来,什么都忘了。小说彰显了草原骑手的豁达、豪放与淳朴,也流露了对功利的时代氛围中草原文化、骑手文化没落的伤感。同时,小说有相当的篇幅讲述少女萨娜与塔合曼边防连中尉军官卢克的恋情发展,其中也寄寓了作者对军旅文化的思考,表现了军地文化的融合,抒写爱与美的理想状态。中尉卢克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同化,他对待草原、骏马乃至爱情的态度与草原骑手事实上是一致的。小说中人物性情的淳朴与草原景色的美好是互相对应的。美丽的草原景色,青年男女心灵的碰撞,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优美地展现,勾勒出一幅爱与美的理想图画,体现了军地文化的完美融合。
借助于“这个时代变幻中相对缓慢的‘场域”,卢一萍发现这里的山川草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使得人们更加敬畏自然、敬畏传统,更加脆弱也更加坚强。20世纪80年代,军旅作家唐栋曾以《兵车行》《雪线》《雪神》等一系列“冰山”题材作品饮誉一时,在极致化的“苦”与“难”的自然环境中塑造军人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超凡力量与伟岸形象。他笔下的普通边防官兵在漫天冰雪的喀喇昆仑深处承受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孤独,心理上却从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和怨言,随时都被一种高于一切的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支配,这种叙述虽然有利于营造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氛围,但这种对“崇高”的刻意追求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被作者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力度。与唐栋相比,卢一萍在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上做了重要的探索。卢一萍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凸显他们的伟岸形象和超凡力量,而是展现他们普通、平凡乃至不那么光辉的形象,展现军人追求职业理想路途的艰难与代价。《白色群山》中天堂湾边防连六号哨卡的凌哨长在强大无比的大自然面前,感觉到自己还没有真正交手就失败在雄奇壮阔的群山中,连自己作为一星尘埃的重量也感觉不出。在这种辽阔的景象面前,生命渺小得几近于无。小说记叙了他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长达八个多月的心路历程。作者描述了他在得知哨卡已撤、战友牺牲的情况下内心产生的种种矛盾、波动,以及在长期与孤独、寂寞、无聊的斗争中出现的幻觉、精神几近崩溃的各种真实情状。经历了各种精神的困境乃至绝境之后,凌五斗终于挺了过来,专注于为战友们堆雪雕。这一行为绝非单纯地打发时间,而是说明凌五斗已经重新意识到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个体。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翔实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军人追寻职业理想所经历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塑造了血肉丰满的当代军人形象。
《白色群山》中出现了因为高原反应突然死亡的冯卫东,同样,《光荣牺牲》里的军校毕业生杨烈也是因高原反应而死,并且是以最不优雅的姿势在如厕时倒下。小说在军人追寻职业理想的艰难的主题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推进一步,表现现时代军人追寻职业理想和英雄梦所面对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巨大阻力。在我看来,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杨烈,而是营长徐通。徐通是杨烈的未来。营长徐通当初和杨烈一样,满腔热血来到高原,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他唯一的想法是早点下山照顾老婆和十三岁的白痴儿子,曾经的英雄梦早已凋零。英雄梦缘何容易凋零?原因至少有二:一、军营不是象牙塔,社会的趋利风气难免侵袭军人,加之和平日久,保家卫国的奉献意识有所淡化,而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抬头。这种普遍的功利氛围在小说中处处体现。比如,“毕业分配这一步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谁都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经济发达、条件优越、驻地在城市的部队里去,谁都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不用说边海防了”。细究起来,杨烈到边防的动机也并不是那么纯粹,“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不管他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会被分到条件艰苦的部队去。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申请去算了。”这样还能被树为典型有利于未来的晋升。杨烈猝死后,营长担心此事影响自己提升,团长和团政委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为此事定性不影响自己的前途,为此明争暗斗,而一条年轻生命的失去却不在他们的重点关注范畴。在这种普遍的功利主义氛围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行径很难被理解。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和平环境中成长的军人个人权益意识增强,为“大家”舍“小家”的意识有所弱化。但同时,“对生命的尊重一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课程,但我们至今没有学会”。对于边防官兵权益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关注虽然比起以往有所改善,但现实环境对保护和滋养边防军人的英雄主义热情还是存在很多欠缺。比如,小说中的杨烈连基本的高原生存的常识都没有,就被送到高原。再比如,如何理顺边防干部的任职机制,使得营长徐通这样的人能够兼顾国防事业与家庭,如何滋养当代军人的英雄梦,这是小说提出的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因此,卢一萍的小说切中了和平环境下军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脆弱性,拓深了军旅文学的思想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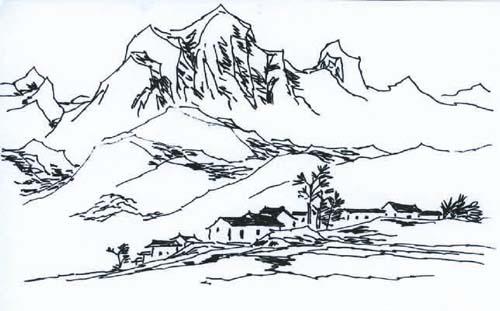
除了现实军旅题材,卢一萍以边疆为背景的历史军旅题材小说也颇为人称道。著名作家周涛指出:“卢一萍的目光常常聚焦新疆南部荒原,让我们得以听到‘那块土地上最初的爱情的战栗。他的小说总会有一个遥远的背景,使其表达的视域变得豁然开阔,意境也变得更为深邃。”作品集中的中篇小说《父亲的荒原》可谓代表。小说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索狼荒原为背景,主要塑造了一个类似于关山林、李云龙的硬汉形象——绰号“王阎罗”的垦荒部队营长王得胜。与关山林、李云龙不同的是,这位硬汉粗中有细,铁骨柔情。他因为摸黑送洗脚水给新来的女兵柳岚,被神经高度紧张的柳岚误当作土匪黑胡子开了一枪,伤了耳朵,却一笑置之。 他虽经组织硬逼,和柳岚勉强成了亲,却绝不强迫柳岚。柳岚对他没有感觉,但女遣犯薛小琼却爱上了他的粗犷豪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小说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人物革命意志与情感的较量,也展现了作家纯熟的叙述技巧及其对历史、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