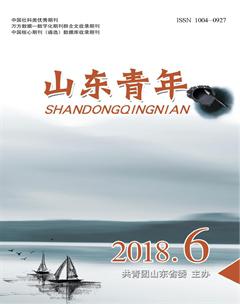土崩瓦解
刘立磊
摘 要:
我国的革命,自古代的农民起义开始,基本上一直沿袭着相同的方式:某地区的农民武装战胜当地政府的力量,接着侵吞其他邻近地区的土地,之后一步步扩张,最终打败原有的中央政府的势力,最后一统全国。可是辛亥革命打破了这一规律性的做法:它只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城市偶然成功后,南方各省便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然后由独立的各省重新开会,成立与北方清政府对立的,新的革命政府。放眼世界,这种革命形式也是极为稀少的,除了荷兰当时的尼德兰革命和我国的辛亥革命有点相似之外,基本上算是独树一帜了。而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是偶然的。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紧密相连。
关键词:辛亥革命;独立;地方主义;新军
地方绅士权力的膨胀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由武昌起义开始,然而一场起于武昌的兵变能够演化为孙中山所说的“风云泱动,天下昭苏”,则大半是在八方呼应造成的八方坍塌中实现的。张一麐后来说,“辛亥之秋,武昌事起”,继而北军入鄂,连战连捷,“汉阳既下,鄂事垂定,而湖南、陕西、云南、山西、贵州、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安徽、福建、四川、山东各省,皆追逐湖北民军之后,或就其都会,或一郡一邑,或一省而至十数处,宣告独立,纷纷设军政府,人心已去,大势瓦解”。这些“追逐湖北民军”的省份以各标“独立”的方式汇入了辛亥革命,以沛然莫御之势促成了最后一个王朝的“大势瓦解”。
辛亥革命成功的如此迅速,这与各省的绅士权利代表立宪派脱不了干系,而立宪派又以各省的咨议局为代表。19 世纪50 年代开始的镇压太平天国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地方官为筹饷募兵所困,不得不广引绅士相助,从而不得不把绅权扶起来。有此一变,于是而有后来五十余年里地方绅士越来越主动地进入赈济、河工、团练、助饷、民教冲突,设厂开矿、维护利权以及开新守旧之争等等地方事务和国家事务之中,并因之而获得了一种不断伸张的绅权,同时又形成了一个不断积聚活力的绅界与绅权的伸张相为表里的,是自发的地方意识正在演变为自觉的地方意识。而这种由自发到自觉的演变,与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同步发生,则又成了新陈代谢中的一种历史内容。宣统年间以咨议局为主体集群而起的赴京请愿“速开”国会的失败,使得立宪派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进而由失望转向了愤怒。他们已经走上了清政府的對立面。稍后“武昌事起”,因清末新政而获得深化、固化和组织化了的这种依省而分的地方主义,便无须过度地合流于其时“亡国之速,未有如是之奇” 的土崩瓦解之中,在革命、光复、反正的种种名目下,以各自的次第“独立”助成了最后一个王朝在碎裂中的倾覆。
军队中革命力量的渗入
曾任军谘副使的哈汉章说:由于袁世凯从小站练兵开始已“取材于武备学堂”,致“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有此势力,则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归来者遂只能以“分散各省”为出路。在奉旨编练新军之际,他们很容易进入各省主持新军事务的督练公所那一脉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既从日本带回了革命的意识,也从日本带回了革命的身份。例如入京的吴禄贞,以及在湖北的蓝天蔚、在江西的李烈钧、在山西的阎锡山、在云南的唐继尧等等。因此,当朝廷中的主兵事者正为“争夺军权”而借重士官生的时候,士官生容易伸展,革命也容易伸展。迨筹备立宪而改官制,练兵处遂变为陆军部而取代了旧日的兵部,之后由陆军部派生的军咨处(府)又后来居上,手臂远伸四面八方。在这种兵政的一变再变里,以北洋为对手而开始的自上而下“争夺兵权”,已一路广罩南北,演变为朝廷与各地督抚之间的重重觕牴。这时,军队已经与地方化的趋势发展了。军界的地方性融入了绅界源远流长,并正在因时盛涨的地方主义之中。在这种曲折里,革命实现于独立,而与之俱来的却是每个省份都以自己的独立呼应其他省份的独立,同时又因其他省份的独立所映照出来的彼己之界而自立主体,并各以地方互相分区。
地方权力的膨胀
其实,军队逐渐地方化,脱离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并非是从现在开始的,往前追述,可以说从“东南互保”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征兆了。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同时宣战 。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而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闻此讯,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 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
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往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称东南互保,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帝敕令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故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东南各行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
总结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土崩瓦解,是地方绅士权力和军队权力发展的结果,也是清末新政以来地方化趋势的反映。革命的力量逐渐深入军队,“重文轻武”时代的终结,各地军阀的崛起,这一切,不仅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现状,也对辛亥革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国强,《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学术月刊》,2018年2月第50卷.
[2]付金柱,《依违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梁启超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抉择》,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8月.
(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