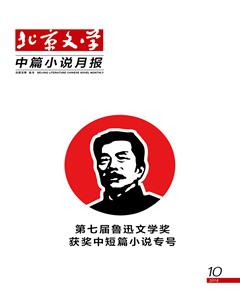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羞脸鬼,羞脸鬼,端个瓦盆要浆水。
这是我们编的顺口溜儿。
快做晚饭的时候,二奶奶来了。她个子小腿短,走路慢悠悠的,微微撇着脚。她的鞋永远是不会穿起来的,不管是烂鞋还是刚上脚的新鞋,她一律将后跟踏倒,像拖鞋一样耷拉着。奇怪的是她这个样子走路,竟然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只猫儿在轻轻走过。我也曾将自己的鞋子故意踩倒试过,一迈步鞋子在脚后跟上拍打着,呱嗒呱嗒作响。有一回她脱了鞋坐在我们家炕上和我妈说话,我乘机穿了她的鞋走路,还是呱嗒呱嗒响,像一个饶舌的妇女跟在脚后聒噪。可见二奶奶她这穿鞋走路已经练出了境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她还会在裤脚上挂一根乱线头,要么是几点碎草屑儿,这一路轻飘飘拖拉拉来了,身后跟着最小的女儿玲子,像一个小尾巴长长拖着。
二奶奶来了还会有什么事儿呢,肯定是来借东西了。我们的目光习惯性地去看她腋下,看见一个瓦盆夹在那里。这就对了,又要浆水来了。
我们的浆水卧在一口大缸里。
秋天萝卜挖回来后,将叶子全部切下来,拣好的串起来晒干菜,为以后卧浆水埋下伏笔。
总是奶奶在做这些事情。
一个头戴白帽的老奶奶,坐在一大片绿叶丛中,用一个冰草绳子串菜叶。这种绳子必须用冰草拧,最好是连根带叶拔起来的那种冰草,韧劲大,才能承载一大串菜叶的重量。
冰草很常见,只要有黄土的地方它们就会生长,无孔不入,顽强不屈。
奶奶自己扒一抱冰草,拧出两根绳子,后面不用她再忙活了,我和姐姐早就跟在她身后也各自拔了一大抱冰草,抱回来坐在萝卜上搓绳子。冰草绳子很好搓,我们一会儿工夫就搓出一根给奶奶。奶奶将萝卜叶子一把一把整理好,放在草绳上将草绳打一个结,一大把菜叶被草绳拦腰捆住了。再整理一把,再打结。不大一会儿工夫,身边堆出一大串串起来的绿叶。深绿的萝卜叶,草绿的冰草绳,一堆绿色还在不断膨胀。奶奶两手沾满了绿汁,站起来,提着草绳一头抖一抖,索拉拉提起了一大串,这种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很沉,母亲过来帮忙,和奶奶抬着菜叶子搭到了早就准备好的木架子上。架子很简单,是两个巨大的长条板凳上支一根扁圆的木棍子。自然,这棍子是榆木的,结实。
半个下午,母亲把所有的萝卜叶子切下来,将萝卜运进后面窑里储藏起来。奶奶也串了十几串萝卜叶的干菜。其实还没有干呢,但是我们已经将它们叫干菜了。好像这些绿叶一上绳子就和散堆在地的叶子不一样了,有了特别的意思。
奶奶还要串,母亲喊,够了够了,多了咋吃得光呢?
奶奶小声反驳说,你们年轻人就爱偷懒,怕麻烦!我们多多地串点,到了冬天卧一大缸酸菜,看你们咋吃呢!奶奶的口气是肯定的,那意思就是你们想咋吃就咋吃,由着性子吃,没人会给你限量。
秋风干爽,艳阳高照,萝卜叶子很快就干了,比原来萎缩了很多。奶奶一串一串取下来挂到后窑墙上的木橛子上去。
我们宽大高深一直寂寞的后窑顿时变得拥挤热闹起来,显得很富足。墙上的干菜串子一串挨着一串。地上堆着农具和一些很破旧但还是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本来木橛子上还留着几串去年的老干菜,对比之下,老干菜更像是一串串破抹布。上面落了尘土吧,在窑洞墙上吊死鬼一样挂了一年吧,总之是面目陈旧得让人伤心。我过去摸一摸,拽一下,干爽枯衰的叶子顿时碎了,化为粉屑,扑簌簌往下落。手碰到一片,就碎一片。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下枝干挂在那里,光秃秃,孤零零。空气都变浑浊了,有点呛人,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从尘屑团里抬起头来喊,奶奶,奶奶这还是我们去年挂的那些干菜吗?咋老成了这个样子?奶奶很忙,不回答我,我也没十分渴望她回答。因为我记得十分清楚,这些干菜除了我们去年此时挂上去,难道还会自己冒出来吗?
木橛子数目有限,要挂下所有的干菜明显有困难。奶奶歪着头想,像一个贪玩的孩子面对着一道不确定答案的选择题。她终于下了决心,动手往下取旧菜,取一串旧的,挂一串新的,一番新陈更替后,所有的木橛子上挂满了新鲜的干菜。
旧干菜串子被堆积在门口,一串一串死尸一样恓惶地躺着,奶奶看着它们有点作难,扔吧,舍不得,再收起来?没地方放了嘛。这取舍真是成了一道难题,横在那里把奶奶挡住了,去年的时候她用双手把它们一片一片择出,一束一束捆扎起来,现在又由她的手来扔掉,好像在叫她扔掉一些贵重的东西一样作难。
我用脚踢着干菜串子。它们实在太陈旧了,好像叶面在失去水分的过程中,颜色也跟着蒸发、褪掉了。
奶奶弯腰把它们提起来。我看着她提了两串不怎么重,就也过去试着往起提。它比我的身高还长,干枯的菜叶子轻飘飘的,一串干菜很轻易就被提起老高。我吓了一跳,踮着脚尖再往高提,还是那么轻。当初那些重量都哪儿去了呢?刚串起来的菜叶子奶奶一个人拿不动一串。现在奶奶提了三串还不重,又往左手里再增加了一串。
奶奶叹一口气,十分惋惜地说:拿去给牛吃吧。我们就真的放进了牛槽里。
新鲜的菜葉子挂在木橛子上,一天天变干,终究也会变成去年一样的干枯吧。就像我有一天终将会长成奶奶一样的衰老。时间是一把刀子,悬在头顶上,一点一点地削切着我们的生命。虽然这刀子隐藏得很深,可是它削砍的结果确确实实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有一天,家里没酸菜了。不等我母亲动手,奶奶已经坐不住了,她先换了一个大水,坐在炕上梳了头,就去沟里担水了。头发没干,把帽子弄湿了,裹在帽子外面的手巾也透出一坨子湿痕。她顾不上管,小跑着去担水。奶奶一辈子都是跑着干活的,好像不抓紧干,活儿就会自己消失了一样。所以得尽快地干,干完了才能坐下歇缓。
腾缸是一件麻烦事。水缸自然好清理,把残余的水舀出来,拿净抹布擦了缸底,再舀一马勺清水冲一冲就成了。麻烦的是另一口缸。那是专门装浆水的缸。吃到最后,酸菜捞完了,缸底里残留着最后一点浆水,里面飘满了白花。奶奶趴在缸沿上看一下,吸一口凉气,先去后窑里取来两串干菜。秋后挂的干菜,已经泛出旧色来了。混杂在菜叶中的偶尔残留下的萝卜头的白顶儿也干了,一片一片,抽搐收缩得像老人的脸,皱纹里落满了尘土。奶奶坐在门槛上往下解冰草绳,当时那么新鲜的冰草也枯旧了,黄黄的、松垮垮的。很快就解下来了。堆在地上,像一团解剖的肉,再也回不到当初赖以生长的骨架上去。锅里水开了,奶奶动作节奏加快了,一边洗干菜,一边往开水锅里投。一会儿满满压了一锅。盖上大草锅盖,往灶膛里加紧烧火。
奶奶一辈子没啥本事,针线茶饭没一样能拿得上台面的,只有这卧浆水是她的拿手活。我母亲那么能干的女人,可以包揽锅灶上所有吃吃喝喝的活儿,但是到了卧浆水的时候她自动退到一边去了。她很放心,不用进来看一眼,奶奶能顺利独自完成所有的工序。
水汽大起来了,从方圆升起,渐渐地包围了锅顶,直到地方完全包围了中央,形成一股很明显的合力,森白的气体打着旋儿离开热腾腾的草锅盖,扑向屋顶。大的檩子小的椽子交错、竹席泥巴凑合垒成的屋顶变得朦胧了,奶奶早就褪尽了软柴,灶膛里架着几根硬木柴棍,火势也形成了合力,嘻嘻哈哈笑着,像个瓜女子在傻笑。那口缸终究是要清洗的,奶奶忽然下了最大的决心,本来就有点下驼的脊背弯曲下去,用大马勺往出舀那些残余的浆水,倒在一个盆子里。刮干净缸底,用清水洗缸的底部和側壁,将笨重粗黑的家伙搬斜了洗,里外都洗了。缸像一个蒙垢已久的女人,忽然换了一个大水,同时那里外的衣裳也给换了,穿得一簇新,要不是缸沿上有一个豁口,它就是个刚买回来的新缸了。焕然一新的水缸边,那半盆子浆水的陈旧让我心里直翻跟头,浅灰色的表面上那层白惨惨的颜色和霉味,都是沉甸甸的。我赶紧把鼻子缩回来,奶奶,奶奶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吃的浆水啊,咋这么难看?还臭烘烘的?
奶奶将灶火门口快要掉下来的木棍往里推一下,伸手赶苍蝇一样赶一下我,快耍去,这是剩下的一点缸底,才两天没吃就臭了!你那个懒婆子妈,就知道等着吃现成的,一缸的酸菜浆水吃光了,还等着我拾掇缸底哩——
伸右手在锅盖顶上甩几下,赶散了一团白汽,一把揭了锅,一团白得发黑的汽哗啦一声腾起来,奶奶消失了,被血盆大口吞没了。可是我不会喊人来救命,因为大口又把奶奶吐出来了。她的脸上挂了一层绿油油的水雾,用大勺子翻搅一番,盖上盖子又开始烧火煮。大团水汽很快消散,只留下一股菜腥味不散,往黄土墙壁、椽子檩子和更细小的泥皮深处渗透。也钻进我的鼻子眼儿耳朵碗儿头发丝里来了。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一根被煮得湿塌塌的干菜了。可我不走,绕着锅台打转。奶奶把缸底腾出的坏浆水端出去倒给老牛喝。
这会儿干菜煮好了,用铁笊篱大马勺搭出来泡进凉水里。黄得发白的菜叶在水里一泡,散开了,颜色慢慢变成了深绿。清水也跟着绿了。我瞅准一个白中泛绿的萝卜片儿去抓,凉水也被泡热了,烫手。我嗖地收回手,萝卜片儿夹在手心里,吹一吹,就往嘴里送。老萝卜的那种苦味儿被开水煮透过滤了,咬一口,柔韧筋道,熟得很好,一点不硬。闭上眼慢慢品尝,呵,像鸡爪子,像羊蹄筋,还是牛耳朵?
奶奶倒掉煮菜水,又烧一锅开水。然后蹲在地上捏菜里的水。捏出一疙瘩一疙瘩熟透的干菜叶子,垒放了半个案板。
我乐坏了,趴在案板边捡萝卜片儿吃,大嚼大咽。奶奶不骂,拉一把我胳膊,说:把菜弄脏了!我才不怕她呢,她从来不会打娃娃,连一巴掌都没有打过我。我把手伸进泡过菜的水里扑晃一下,捞出来,湿淋淋举着喊:看看,我洗手了!
奶奶顾不上理我,将菜疙瘩往那口腾出的大缸里投,我也抱一个菜蛋,从奶奶胳肢窝下钻过去,双手举着砸进了缸里。缸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案板上渐渐地空了,缸里满上来,奶奶将那锅烧开又晾了一会儿的开水倒进去,再抓两把荞麦面,用长擀杖慢慢地搅散在缸里。清水浮上来,菜叶沉下去,面粉打散了,水不那么寡淡了。一层温暖的乳白冒着热乎乎的水泡儿浮在最上面。奶奶剥两根葱,不用切,囫囵个儿投进去。已经能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儿了。
下午的饭跟平常一样,洋芋面。但是那饭舀在碗里显得寡白寡白的,等吃进口里,更是寡淡。调一筷子盐,再调一筷子头辣椒,还是不香,饭嚼在口里一股面腥味,汤喝进嗓子眼里痒痒的,咽不下去。我们的饭量都比平时减少了,爷爷有点懊恼地质问奶奶,为啥把饭做成了这个味道?
奶奶理直气壮地说,没浆水了嘛。爷爷一拍筷子,那就快卧一缸啊。没浆水还叫人咋吃这个饭?
奶奶还是不惊不慌,说:卧上了,后晌就卧上了。爷爷响亮地唉一口长气,无奈地端起碗来,继续往嘴里填碗底的那些饭。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奈地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爷爷都没话可说,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浆水就是这样,旧的吃完,到新的做成,有一个交替的等待的过程。这期间我们肯定有好几顿饭是缺失了浆水和酸菜的,因为我们只有一口卧浆水的缸,没有人提议再添一口进来。日子一直这么过着,浆水也一直是这样的卧法,这样的吃法。没人想过要改变它存在的形式,因为它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总是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只有新旧交替这几天中,我们才感到了浆水在我们生活里是多么重要。它就像家庭里的一个女人,这女人长相一般,挣不来大钱,养不了家,所以大家很容易忽略掉这个女人。忽然一天这女人没在家里,大家才发现这个家没有她真是不方便,饭谁做呢?脏衣服谁洗呢?鸡和狗饿得乱跳,窑洞门口的干柴和牛粪乱成了一团糟,这个家的细微的秩序完全混乱了。这一混乱的乾坤男人自己是无法扭转过来的。
第二天吃干粮的时候爷爷发了脾气,瞪着眼问奶奶咋没有酸菜?奶奶照旧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慢悠悠说:浆水昨天才卧上嘛,还没酸呢。女人生娃娃还都有个十月怀胎的过程呢,你急的啥?爷爷神情一呆,默默地吃一口咸菜,放下筷子,早饭就这么草草收了场。我们都没吃好,因为本来就单调的早饭中少了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拌酸菜。
晚饭时候奶奶不敢四平八稳地等待了,把我妈刚烧开的面汤舀一些,掺点凉开水,然后均匀地投进浆水缸里,再用长擀杖耐心地搅动。这一过程叫投浆水。
投浆水看着轻松,其实很累人的,奶奶双手撑着擀杖,像老渔翁在划动一艘沉甸甸的木船。渐渐地,热面汤被均匀地搅散到各个角落里,奶奶的鼻梁上挂了一层毛毛汗。
我说,奶奶咱去旁人家要点浆水吧,没浆水的饭,甜死人了。
奶奶有点犹豫,要不要去呢?
其实要浆水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二奶奶不是动不动就拿着瓦盆来我家里要浆水么。奶奶每卧一大缸浆水,可以说都被我家和二奶奶家平分着吃掉了。二奶奶要是有三天时间不来我家要浆水,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反常了,心里反倒会不踏实了。
这不,不等我们做出要不要到外面去要浆水的决定,二奶奶已经来了,短腿上的裤子有点长,拉到了脚后跟上,给人感觉她只穿了半截鞋,就脚尖跳着,所以她不能更踏实地走路,一步一步都走在了泥坑里。我们的目光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牵引,去扫她的腋下,那里果然夹了一个东西,鼓鼓的,胳膊窝被撑开了,有点害羞地露出一个瓦盆羞惭的脸面来。
羞脸鬼,端个瓦盆要浆水!
果然又来了。
二奶奶本人却比她的瓦盆放松一些,她在嘴里蓄积起一口痰,扭着脖子吐在了脚后跟处。一只鸡看见了,点着头飞快跑来捡痰吃。瓦盆从二奶奶腋下探出脸来。二奶奶懒散,这种瓦盆要是被勤快人经常擦洗,一定会长久保持一种锃黑明亮的光泽。可这个瓦盆就像个没娘娃,猛一看和旁人家娃没啥区别,细看,脸有点臟,衣裳有点烂。它主人的懒散,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瓦盆来体现。其实我们的二爷爷是一个很爱干净的男人,他的衣着要比我爷爷讲究,只是他的女人在不断地拖他的后腿。
有时候,爷爷看见二奶奶又端着一盆浆水走出门去,他就不无幽默地感叹:真主呀,世上的人要是能活活懒死,最先完蛋的可能非得是这个女人了。
二奶奶自然不会因为懒惰而死,相反活得好好的。因为好吃懒做,她的面目显得远比岁数年轻。把她和我们的奶奶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艰苦的劳作,对一个女人容颜的损害有多可怕。而相对的懒惰就能稍微避免这些东西。
二奶奶在她家里耍奸溜滑,地里的活儿更是很少参加也就罢了,针线上缝缝补补、锅灶上洗洗刷刷的活儿她也不好好干,坐在炕上指挥着女儿干。女儿才有多大呢,站在地上比炕沿高不了多少。她这些行径我们真的很看不惯。不过也只能看着在心里犯嘀咕罢了,我们管不着,那是人家家里的事儿。
然而说起这要浆水,就不仅仅是她自家的事情,她这么天天天天地来向我们要浆水,我们就不厌烦吗?卧浆水是多麻烦的一件事,担水烧火,累人,费柴火,不是件轻松活儿。我们辛辛苦苦做好了,她就来吃现成的。况且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十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谁受得了啊?
我妈受不了了,凉着脸接过瓦盆放在案板上,不说话,只是薄薄地笑着。二奶奶不说话,从这笑的神态里闻出了和平时不一样的味道,她走过去自己揭开缸盖,踮着脚往里瞅,哟,新卧了浆水啊?
一股煮干菜微微发酵后的酸味儿飘散了出来,谁都闻得出这是真正的浆水味儿,只是还没有发酵好,浓郁的菜腥味还没有消退。
二奶奶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她悻悻地夹上瓦盆离开了。
这是我们家唯一能理直气壮地拒绝二奶奶讨浆水的理由,说出来不怕得罪她。
平时我们是不敢这么直接回绝这个二奶奶的,爷爷和二爷爷是亲兄弟,他们从小没娘,兄弟间的关系要比别人亲厚得多。爷爷常在强调,要我们对二爷爷一家好一点。二爷爷手头紧困的时候就来向爷爷借钱,爷爷每次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回。
有一年,爷爷缝了个二毛皮大衣,穿着去寺里礼拜,看见二爷爷穿着单薄,冷得脸色都白了。兄弟两个边走边说话,走到家门口,爷爷脱下皮衣披到兄弟身上,说送给他了,自己再做一件就是。
直到第二年冬天来临,爷爷也还是没能够穿上新做的皮衣。因为二毛皮很贵,我们家宰的羊皮一般拿出去卖了,就算留下两张,也还得再请毛毛客去做,那一笔手工费很高呢,家里哪有那么多闲钱去干这个。
多年后,奶奶说起来还有着怨言。其实心有怨言的不止奶奶一人,只不过那第二个人没敢说出来罢了。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她十分有意见呢。
一来这皮衣确实贵重,是我大舅舅亲手做的。大舅舅干了半辈子皮毛活儿,说到后来只要闻到硝水泡皮子的味道就恶心得直想吐。所以他早就洗手不干这又脏又累又差的活计了。但是他又重操旧业为我爷爷做了一件皮衣,我不知道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但是能叫他重入江湖,可见他对这件皮衣是何等的重视。爷爷一时兴起,将皮衣拱手送人,这件事让我母亲觉得尴尬,她将事情瞒住了不叫传到娘家人耳朵里去。你说真要是传到了舅舅的耳朵里,舅舅会怎么想呢?所以爷爷还能开口让舅舅给他再做一件二毛皮衣吗?
自然是不能的。这些年爷爷就一直穿着那件黑棉袄去寺里做礼拜,清真寺的大殿里冷得站不住脚,奶奶疼爷爷啊。
二来嘛,二爷爷一家人拿去了我爷爷的二毛皮大衣,却一点感激的意思都没有,好像这本身就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不值得他们记恩。所以二爷爷穿着那件二毛皮衣走亲戚、出远门、去寺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都觉得心里酸酸的,有点不是滋味。
要知道这样的二毛皮大衣穿在身上,会让一个男人马上变了样,他的架子一下子就立起来了,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显得高大、尊贵了起来,被一层富贵的气息笼罩了。所以穿了皮衣的二爷爷和爷爷走在一块儿,给人感觉他的气度风范俨然就是兄长,而爷爷反倒成了猫着腰的兄弟。这一份像样的衣着带来的体面就这样被爷爷拱手让给了他的兄弟。
奶奶是个老实人,但是为着这件皮衣,她很多年都耿耿于怀,说起来就忍不住抱怨爷爷。
还是说浆水和酸菜吧。它们是同一口缸里待着的,但不是同一个事物。从浆水缸里捞出的菜,就是酸菜。泡着酸菜的水,就是浆水。可见酸菜和浆水是骨肉相连水乳相融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中两口子的关系,就像我家和二爷爷家的关系。
爷爷以一个长兄的耐性和宽厚呵护着二爷爷一家人,我们就得忍耐,二奶奶来要浆水的日子就一遍又一遍,永无止境。而我们的忍耐一再地纵容了二奶奶懒惰的性子,所以她从来没有产生自己动手卧一缸浆水的念头。
晚饭还是白水洋芋面。面汤刚翻了一个滚儿,奶奶就舀出半盆子热腾腾的面汤来,晾一晾,投进浆水缸里。
饭桌上爷爷终于无法忍受,拍着筷子不看奶奶,说,家里有两个女人呢,连一口浆水都做不好,要你们是做啥的?
奶奶一看这场面,气短了,一点都不敢犟嘴,给爷爷调一筷子油辣子,说,新磨的胡麻油,滚滚的热油泼的辣椒,闻着都香!你不尝一口?
爷爷气哼哼端起了碗。第二天的干粮时节,除了煮洋芋、蒸馒头,爷爷拿起一个馒头念一句:必思敏俩习——掰开了刚要吃,奶奶端着一大碟子酸菜上来了。碟子一落桌,一股酸菜伴着胡麻油的清香味道散开了,白生生的萝卜条、翠黄的叶脉、碧绿的菜叶,杂拌在一起,上面还抹了红红的辣椒油。不用吃,光是看着,口里就泛起一层水,喉头很响地抽搐起来。昏睡的肠胃被唤醒了,蠢蠢欲动。
爷爷眼神不好,没看清是什么,但是抽了一下鼻子,酸菜吗?酸菜成了吗?呵呵,你这老奶奶,酸菜已经成了咋不早说呢?
边说边夹起一大筷子,一口馒头,一口酸菜,吃得滋味绵长。两个馒头不见了,一碟子酸菜也消失了。
奶奶不高兴了,你咋一个人把酸菜吃光了呢?也不知道给我们留点。
爷爷放下筷子。朝阳的光从向东的窗口照进来,光斑洒了爷爷一脸,他一脸金黄,很快这层金色绽开了花,冰面破裂了。爷爷笑呵呵说:没了再调一碟子嘛,你这死老奶奶,吃酸菜还能把家里给吃穷了——
说着端起碟子,把最后残余的一筷子菜也吃了,连碟子底里那点汤水也喝了。
奶奶彻底不高兴了,嚷了起来:谁叫你把汤也给喝了?
爷爷摸一把胡子,呵呵笑个不断,站起身拍打一下屁股,溜下炕去,他要收拾一番骑着骡子去赶集了。
奶奶再去捞一碟子酸菜,这一回舍不得拌清油了,多多地撒了一点干辣子面,然后一口洋芋一口酸菜地吃起来。
我和姐姐在院子里跳绳。被我们绕着跳来跳去的草绳,正是串过干菜的冰草绳。它们和萝卜叶子绑在一起后,一起变干了。现在干菜卧出了酸菜,草绳没什么用处了,我们每人一根,在院子里乱舞着。惊得鸡不敢到房门口巡逻了,远远地躲在大门洞下,用小眼睛偷偷窥视着我和姐姐的疯狂举动。
我们终于跳乏了,感觉没意思了,将草绳搭在牛圈门上,看着牛一点一点往大嘴巴里叼。牛很笨,明明已经吃进去了,可是舌头在那里乱搅,忽然又吐出来,只能又往进吃,白白长了个簸箕一样的大嘴巴,连一根草绳都不能吃得利索点。
姐姐抓着手里残余的一点草绳头儿不丢,看看牛已经吸进了嘴里,她忽然发一声力,双手拼命往后撤,刚才已经咽进肚子的绳子却又从牛嘴里拉出来了,沾满了湿漉漉的草末子。我们的惊讶不亚于看见从一个人的肚子里抽出了他那原本盘卧着的热乎乎的肠子。
老牛嚼出了草绳的滋味,舍不得就这样松口,姐姐就像也要吃这根绳子,牛和小女孩较上劲了,两个隔着一道木框门拉锯。草绳子全被拉出来了,它在牛肚子里走了一趟,竟然没有断,但是颜色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刚才那灰沉沉的旧绿,变成了浅黄的新翠。
奶奶吃完了,端着洋芋皮要倒给老狗。老狗眼睛一直盯着她手里的碟子,跳着脚催促,神情迫切极了。
奶奶看着老狗可怜,干脆捞一碟子酸菜倒进了狗食盆子里。老狗欢快地呜咽一声,大口狂吞,喉头深处发出咣咣咣的吞咽声。
姐姐终于没心思捉弄老牛了,懒懒地松开了手心里的那最后半截草绳,拉上我的手,走,上山拾呱呱牛去。
据说这个被我们喊作呱呱牛的东西有一个学名叫蜗牛。耕过的山地里随处可见白色的蜗牛壳,小指甲壳大小,上面盘旋出一圈圈好看的螺纹。
呱呱牛,海巴巴,爷爷把奶奶揣一把。
谁发明的谁又流传开来的童谣呢?不知道。像北山上的风,你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刮到哪里去?
我们每人捡一大把呱呱牛,回家坐在屋檐下抵仗。姐姐拿一只,我拿一只,互相抵住了最尖的部分,然后同时用力,像斗鸡或者斗蛐蛐儿。总有一只会破裂的,肚子里流出一摊碎裂的沙土。蜗牛早就爬走了,这只是被它们丢弃的一个壳儿。
我们边破坏着呱呱牛,边高声喊叫:呱呱牛,海巴巴,爷爷把奶奶揣一把——
母亲在初冬的风里晾晒破布。这些破布都是从旧衣衫上拆下来,洗了一大堆,一片片晾晒在一片塑料布上。她要用这些布,在这个漫长的寒冬给我们一家人做出明年一年的鞋子。
呱呱牛,海巴巴,爷爷把奶奶揣一把——
干燥的风里含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刀刃,把我们的手和脸划开了无数细密的小口子,手背和脸蛋又疼又痒,但是这有什么呢,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从我们离开娘怀在地面上爬行的时候,开始在土院子里一步一步学步的时候,风吹日晒的自然磨砺就开始了。我们早就不是娘肚子里初次出来时候的那个娇白细嫩的模样,而且我们还知道,终有一天,风刀子毒阳光,会把我们变成母亲一样的女人,再后来,肯定也会雕刻成奶奶那样的老婆婆。
母亲转过脸来,眉眼跳跃着,有点坏,说:你爷爷把你奶奶揣一把?揣哪儿了?你们看见了吗?
她的口气有着纵容我们的味道。
我们顺杆子往上爬,姐姐想也不想,脱口飞出一句:看见了,揣沟子了!
我欢快地应和:呱呱牛,海巴巴,爷爷把奶奶沟子揣一把!
我们得意得忘了形。一串蹄声踏进门槛,哒哒哒,脆生生的,喧闹又寂静。爷爷回来了。我们还在喊:爷爷把奶奶揣一把——爷爷把奶奶揣一把——
母亲赶紧狠狠咳嗽两声,试图用咳嗽声压制我们的放肆。
我们疯了,像春雨后的麦苗子,噌噌噌往上蹿。母亲镇压不住,慌了,丢下未晾完的湿破布仓皇逃进屋去。奶奶迎出来,脸红红的,她好像年轻了十几岁,简直和她的儿媳妇一样的年轻了。
爷爷还骑在骡子背上,咳嗽一声,喝道:胡喊啥呢?大人都哪儿去了,娃娃没人指教吗?不要怪我用皮鞭子帮你们指教了!
皮鞭咣一声丢在台子上。我们嘻嘻哈哈笑着,不喊了,跑过去拉骡子接爷爷。很快地每人口里噙上了爷爷送的一颗糖,甜到肺里去了。
爷爷进门上了炕,有点吃力地靠住被子,伸手敲着窗玻璃喊:老婆子啊,快给我舀一碗浆水来,渴死了,心都干透了——
奶奶双手端一碗清凉凉的白水來了。我们家的蓝边粗瓷碗,像一个清爽干净的女人,肚子里荡漾着一池清凉,看得炕角的猫也动了心,薄刃片一样的红舌头一亮一亮舔着小巧的嘴唇。
奶奶双手一直递到爷爷面前,爷爷不接,埋下头就在奶奶手里牛喝水一样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碗。喝完了摸一把胡子上的水珠儿,长叹:从头发梢儿舒坦到脚后跟了啊老婆子——这一趟啊,可把我老汉一把老骨头累散花了——
他完全地松弛下来了,身子像一串从干草绳上解下来的陈旧干菜,全身慢慢地散开了,连下巴上的那些皱纹也都舒展得平平整整的。
我和姐姐的心思完全在桌子上的那个黑挎包里。那里面还有糖吗?还装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鼾声响起来了,轰隆隆——轰隆隆——这声响完全压过了猫儿的呼噜,它可能觉得太吵,懒洋洋爬起来,四个爪子叉开了撑住,将腰身慢慢地伸长,拉松紧一样往长拉。就在我们担心快要拉断的时候,它毫无征兆地打一个哈欠,噗——跳下炕,一眨眼就溜走了。
爷爷鼾声如雷。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串干菜一样的身躯里会发出这么震天的轰鸣巨响。
姐姐手快,已经从包里摸了两颗糖,我们捏上糖往外溜。跨过门槛,姐姐忽然回过头来看着我,目光怪怪的,问:爷爷那么老的人,会摸奶奶的沟子吗?我们是不是唱错了?
我的目光飞一般抓一下爷爷的手,是啊,那手比老干菜发霉的菜帮子还旧,还会和风花雪月有关吗?
出门撞上奶奶端了一大盆浆水,她这是要给隔壁的二奶奶家送去。
每次新的浆水卧成,奶奶都要这么送一回。一来叫二奶奶一家赶紧尝一尝新浆水;二来等于在告诉二爷爷一家,可以继续来我家要浆水吃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缸浆水的馨香滋养两个家庭的日子又开始了。
原载《长江文艺》2014年第8期
原刊责编 吴佳燕
本刊责编 吴晓辉
获奖感言
马金莲
说实话,获奖消息传来后,我的内心交织着喜悦和酸楚。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我从2000年开始写作,那时候十八岁,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也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多远,只是因为发自真心的喜欢,从此就踏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甚至可能需要用一生去丈量,但是我无怨无悔地走着,因为文学带给我的丰足和幸福,实在是大过了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十八年来,我先后在各级文学期刊发表三百多万字的纯文学作品,坚持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真挚的情感,紧紧贴着地面,捕捉着、书写着、表达着西部乡村最底层广大普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图景,构建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画面,呼唤人性深处的明亮与温暖。
一路走来实在不易,这些年得到了很多良师益友的鼓励、呵护、扶持和托举。从青涩之年到年届不惑,我铭记着所有给过我温暖的美好心灵和善良面孔。
我始终在一个叫作西海固的偏远地方生活,西海固的土地养育了我,更为我提供着源源不绝的文学资源。这次获奖,不是对我一个人的嘉奖,更是对我们西海固文学现象、西海固作家群,甚至是对我们宁夏文学和宁夏作家群的一个肯定和鼓励,希望西海固文学、宁夏文学,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
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始终保持内心的清醒和宁静,不躁动,不媚俗,不迷失自我,向着既定的方向继续书写,始终扎根在西海固深厚的泥土里,用一颗赤子之心,热爱、感恩、拥抱养育我的土地,写这片土地上回汉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温暖人心的坚持,对内心信仰的坚守,对美好人性的守望,对幸福明天的向往;写这片土地上,最普通大众的生存百态,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写时代变迁中乡村世界的悲欢与离合,疼痛与坚守,撕扯与坚韧,泪水与欢笑,光明与希望。人生的路很长,文学的路更长,书写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自己的一生能是和文学始终相伴的一生。
据说我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八零后作家,所以我更深感荣幸,谢谢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和各位评委老师,谢谢如此大的荣誉和鼓励。
马金莲,女,回族,宁夏人,80后。在各类刊物发表作品300余万字,
部分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并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有作品译成英文、法文介绍到国外。
出版有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长篇小说《马兰花开》
《数星星的孩子》。中国作协会员。魯迅文学院第22届高研班学员。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