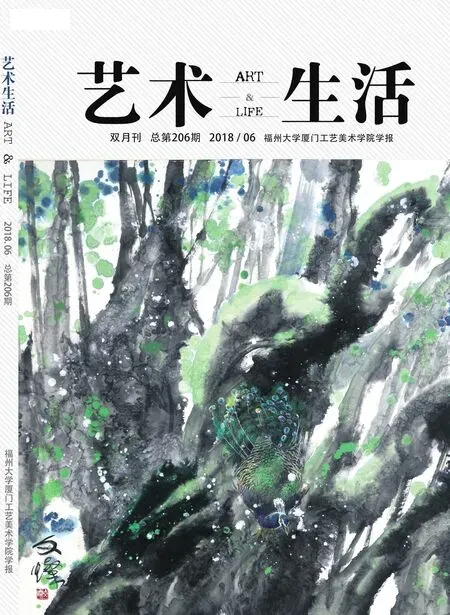伤痕美术连环画的情感嬗变
张 伟
(天津美术馆,天津 300201)
一、引言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励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环画艺术达到了最顶峰,当时几乎所有的画家都进入到了连环画的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经典的连环画作品。1951年到1956年6年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一万余种,累计印数达到了2.6亿册。[1]仅仅在上海一地,连环画出版就由1954年的522种1882万册印数增长到1957年的949种2897万册[2]。1966年到1976年间,连环画出版虽然没有停滞,但从艺术独创性来说连环画人物造型模式化、构图呆板化,题材内容上也十分单一,艺术形式完全服从于创作内容。
1979年,首届全国美展“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与之前人们熟悉的“积极”和“健康”的作品不同,观众在展出的四川美术学院的几个学生的作品看到了悲剧性的主题和灰暗的情绪,[3]作为当时最受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连环画——率先出现了一批具有“伤痕美术”风格的作品。传统的白描、工笔重彩形式的连环画虽然在出版数量上占优势,但是从艺术风格发展来说,“伤痕美术”连环画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取代了传统技艺的连环画,成为“新时期”连环画的代表风格。从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的连环画《伤痕》开始到孙为民、聂鸥创作的《人生》,艺术家对于社会风向与艺术形式的发展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到“85美术运动”之前,连环画的创作和青年艺术家的美术探索是处在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模式下。“伤痕美术”连环画作为“伤痕美术”运动的一部分,短短几年的时间完完整整地呈现出了当时人们微妙的情感变化,同时也把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再一次地推向了高峰。
二、批判与共鸣——自我情感的宣泄
1978年12月25日,“华东六省一市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美术展览”草图观摩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行了讨论。会议对关于“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提议,表示了由衷的赞同,并认为这“说出了广大美术工作者早就想说但不敢说、多年压在心底的话”。[4]一些画家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口号”,并且呼吁美术作品要表现情感,表现生活情趣,表现个性和形式,描绘历史真实。[4]之前那种以英雄、领袖为中心的“三突出”创作模式慢慢发生变化,画家们开始思考人与周围世界、周围人的关系,不再进行模式化思考、模式化创作,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人”价值的思考,预示了新时期美术的正式开始。
“伤痕”主题的艺术创作,几乎是在各个文艺领域内同时展开的。[5]从文学到美术再到影视等等各种艺术形式,均出现了“伤痕”风格的作品,即反应1966年到1976年间色调灰暗、悲剧性的作品。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小说《伤痕》是“伤痕”艺术的开端。当时的人们的情感需要宣泄,在艺术上需要找到情感寄托的港湾,文学与美术是由人们的情感需求直接诱导的,是受当时的思想解放的大环境相影响,特别是1978年提出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方针政策,促使人们在艺术创作上进行反思与批判。

图1 陈宜民、刘宇廉、李彬《伤痕》

图2 陈宜民、刘宇廉、李彬《枫》第18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伤痕美术”的先声是从连环画开始的,也是从表达自我情感开始的。根据小说《伤痕》改编的连环画出现过多个版本,其中包括1979年8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利禄、陶雪华版本,1979年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淮、徐育林、章毓霖版本,影响最大的是首发于1979年《连环画报》第3期由陈宜明、刘宇廉、李斌合作的《伤痕》(图1)。紧接着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人再次合作,于1979年第8期《连环画报》发表连环画《枫》(图2),讲述的是一对相恋的青年学生,各自加入一派,且势不两立,最后一个倒在了血泊中,一个被处死刑,在捍卫“正确思想”的激烈战斗中双双成为这场动乱的牺牲品。
连环画《枫》的三位作者曾说:“对于人物和环境,我们安排了一些对比的处理,造成了一些戏剧性效果……这些记忆中本来固有的东西,当年甚至视之漠然,可是今天看来,却特别令人痛心。”[6]的确,连环画《枫》的成功还在于构图与色彩的戏剧化运用,是1966年到1976年间一元论的美术创作思想慢慢开始向多元发展的开始。尽管《枫》的艺术表现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我们仍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式的结合。《枫》的第27幅(图3)描写的是“他打开语录本,拿出也是并蒂的两片枫叶,只是早已干枯。那是去年十月,‘造总’和‘井冈山’还没有分裂的时候,丹枫送给他的”[7]。画中最前方的人物头部并没有完整显示,这在中国以往的连环画中是不多见的,作者消减了画面边缘,使画面中人物与情节得以延展,渲染出了人物的阴郁的情绪,突出描述了回忆的内容,两个处于不同时间的情节被组成了一个画面,两个时空画面分别用不同色系、不同明度的色彩代表,形成一种强烈的不和谐感,具有蒙太奇的戏剧艺术效果,而恰恰是这种构图与色彩的不和谐感,最大化地体现出主人公的伤痛情绪。
除了运用“蒙太奇”的构图方式,《枫》还运用了隐喻、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段。《枫》的第27幅(图3)中间的革命口号“誓死”两个字赫然醒目地在画面中心,“死”字在画面中连接着男女主角,暗示着男女主角正是这种革命口号下导致的悲剧,画面中的革命口号元素“誓死”在现实与虚幻中游离,这种游离感不由得使人们深深地伤感与反思。这种“生与死”命运的强烈对比不仅仅呈现在独立的画面中,也有采用多幅画面、相同主题元素的穿插对比,来强调情节的转折和生死的无奈。在第4幅中(图4),背景中枫树的火红树冠温暖厚实,似乎充满了阳光和流动的空气,身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的丹枫显得格外动人和可爱,画中暖红色同样充满抒情色彩。当这幅画面与第25幅(图5)躺在枫叶上的女孩尸体相对比的时候,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便显得更加激烈和突出。

图3 陈宜民、刘宇廉、李彬《枫》第27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图4 陈宜民、刘宇廉、李彬《枫》第4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在连环画出版前曾经遇到过阻力,有人指责《枫》的作者是向后看,甚至《连环画报》1979年第8期也一度被停售了几天。《枫》的三位作者曾说:“我们在这组画中,对林彪等不加修饰的直接表现,是为了便于揭露他们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极大的欺骗性,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不可缺少的前提。”[7]1979年《美术》一篇文章曾提出:“而更重要的是还要努力纠正某些人为了蒙骗人民而培植的那套认识方法;坏人一定是衣衫不整,凶眉恶目,面色青绿,神情鬼祟;好人份定是军装笔挺,气度轩昂,手拿语录,胸佩像章……艺术应该在教导人们认识真理的同时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8]反讽艺术手法运用,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人物“三突出”模式塑造的认识,颠覆了非黑即白式的人物塑造的艺术观念,告诉人们在“黑”与“白”处理人物方式之间还有“灰”色地带,即那种层层掩饰的人物塑造方法。

图5 陈宜民、刘宇廉、李彬《枫》第25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图6 尤劲东《人到中年》第1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从连环画《枫》中我们看到创作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每一张张连环画的主题都是艺术家的自画像,每一段段的故事都是自己痛苦的经历,连环画《枫》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对主人公丹枫的深切同情,用悲剧收场的爱情故事对那段特殊时期的批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画面情感是寻求共鸣式的批判,只有经历了那一段痛苦的磨难才能体会到特殊时期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与不能抚平的伤痕。“伤痕美术”的艺术家们大多都是在1966年到1976年间成长起来的一代,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位作者都是由江南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东北农村生活了十多年,在他们身边不乏《枫》主人公式的人物,经历过类似的艰辛境遇和坎坷命运,他们经历的苦痛与压抑的情感都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体现。陈宜明、刘宇廉、李斌曾经提到:“从认识论的角度,通过现实场景的真实感触动人们的隐痛,通过直观将我们这一代青年当时的纯洁、真诚、可爱和可悲,用形象和色彩,用赤裸裸的现实,把我们这一代最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7]这种情感表达把特殊时期的伤痛艺术化,把很可能掉进自然主义的死亡诗意化,连环画画家的感情表达是直白、不加掩饰的。
连环画《枫》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划时代的艺术巨作,作品中的艺术手法和情感表达在那个时代都是激进与前卫的,这种激进使得观众和连环画《枫》产生了一定的艺术惯性空间,人们并没有从1966年到1976年间的艺术思维中走出来,在当时《枫》必定是和读者有一段鸿沟,而这段不可逾越的鸿沟冲击了建国以来的艺术创作模式,使人们——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读者——产生了全新的艺术语境,即“伤痕”语境。1980年吴冠中对形式美的表述引发的争论,《枫》的影响也是其重要的源头之一。[6]《枫》引发的艺术形式与内容辩证的讨论至今都在延续着,小小的连环画艺术甚至影响到了中国新时期美术发展的走向,在1979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无论艺术形式、情感表达都有《枫》的基因与血脉。
三、由批判到反思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慢慢从特殊时期的伤痛走出来,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具有批判性的绘画作品。“无论‘伤痕绘画’或‘星星美展’,对所批判的现实的理解都有表面和狭隘之处,似乎现实的批判意义仅在于将结果归罪于某些人和整体环境和氛围。”[9]特殊时期的伤痛是一个民族共同造成的,整个民族包括你、我、他中的每一个人,所以不能仅仅是哀怨、批判与控诉,应该要进行个人价值的思考,所以这一阶段的连环画兴趣则指向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关注平淡的生活,这些美术作品的主角涉及社会各个年龄、各个层次,其心理基础则正如路德所说:“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主还高些。”艺术家们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现实心态进行艺术创作,这种普爱情感的作品有广廷渤创作的油画《钢水·汗水》、尤劲东创作的连环画《人到中年》等。这时期的连环画作品的脚本多数是改编于“伤痕文学”,是“伤痕文学”和“伤痕美术”连环画产生的互动。
1981年,尤劲东创作的连环画作品《人到中年》在《连环画报》发表,讲述的是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虽是业务骨干,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她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全身心地为患者排除病痛,直至因超负荷的工作晕倒在手术台上,仍无怨无悔。尤劲东曾说:“像《人到中年》里所描绘的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和北京的生活环境,我是熟悉的。但在我动手前我坚持再去体验生活……通过观察,常使我感到陆文婷那样的大夫的现实存在,像同仁医院眼科大夫,她们作风严谨、细致,病人在她们面前,不管是老人、男子汉或是干部似乎都成了孩子,成了需要母亲照料的孩子,这一切使我很受触动。”[10]尤劲东还谈到艺术创作要“奴隶般的忠于生活”,这显然是对于“三突出”艺术模式的彻底的反叛,对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再思考。我们再看连环画《枫》的人物塑造还有“三突出”英雄主义的残留,而连环画《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就是我们身边一位普普通通的女性,并没有因为是主角的原因而在创作时进行美化。通过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物,发掘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形成记忆或纸面记录,然后就创作的需要进行组织安排或艺术加工,创造出一个新的整体。[11]由于小说原著对于陆文婷形象的文字描述不是很多,而“三突出”手法或者连环画《枫》里面悲情的丹枫形象都是不适合表现陆文婷的,所以尤劲东根据陆文婷知识分子的身份结合一位出版社女编辑创造出了陆文婷的形象。从陆文婷的形象可以看到,连环画的创作向普通的、一般的、概念化的“人性”意识转移。
1980年7月16日,北京“同代人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了15位青年画家的80余幅作品。展览注重形式风格,代表作为王怀庆的《伯乐图》和张宏图的《永恒》。其中《伯乐图》那种平面化、装饰化的风格在连环画《人到中年》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装饰性的风格与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绘画风格十分接近。《人到中年》的第1幅就展示出了画家运用克里姆特的艺术形式语言来表现陆文婷因体力不支昏迷的状态,图6又增加了一些细节内容,如一些流动的边缘的描绘,在连环画的第1幅就表现出了陆文婷的艰辛生活,这也是这一阶段“伤痕美术”连环画共用的手法,以“悲伤”开头,以“无奈”过度,结尾给人以想象回味的空间。《人到中年》中的第9幅(图7)叙述陆文婷童年、大学、工作三个时期的成长经历,第15幅(图8)以象征的手法叙述陆文婷在病床上产生的幻觉,这两幅画面运用了三段式构图,将不同时空的内容融入到一个画面之中,打破了以往一图一画的模式,在构思上则与脚本之间若即若离,更偏重对思维想象的开拓,[12]使连环画读者自觉地寻找与画面的共鸣,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增强了连环画的可读性和烘托情感的深度。
连环画《人到中年》之所以感人,主要是成功地塑造了以陆文婷为代表的一些忠于祖国为四化献身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13]《人到中年》对社会中年知识分子的深度挖掘与艺术创作体现出了20世纪80年代连环画作品中普爱的主题,爱的关注对象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向读者传递的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职业、不同阶层都有存在的价值。“伤痕美术”连环画情感表达由《枫》那种自我的感情宣泄转向普爱的人文关怀,是动乱导致的“伤痕”渐渐伤愈的表现,也是渐渐开始了关注人的价值的反思。

图7 尤劲东《人到中年》 第9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图8 尤劲东《人到中年》 第15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四、无奈与希望——新乡村题材的产生
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产模式开始改变,对于许多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知青来说,动荡的十年带给他们的是痛苦的回忆。高考的恢复给这些知青带来了希望,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很多人仍然愿意从农村的角度来观察作为艺术的创作素材。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在1981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是美术创作上“伤痕”的情感表达转向乡村题材的开始。这时候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为连环画创作提供了文本素材。在美术与文学作品“伤痕”风格的带动下产生了像《人生》《乡场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连环画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的艺术家对于创作的题材与情感传递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与艺术自觉性,从连环画《人到中年》那种人文主义的淡淡忧伤转到了乡土的依恋,共同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艺术创作的“伤痕”语境。
1984年,孙为民、聂鸥创作的连环画《人生》在《连环画报》发表,讲述了民办教师高加林被权势挤回到老家种地,后来又被调到县委大院工作,城乡的差距使他渴望改变命运。为此,他竟背弃了在困境中给他力量的姑娘,但最终命运扔将他抛回了黄土地。画家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现故事的伤痛与悲苦,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14]随着高加林的起起落落,同时又伴随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意识到了人生道路的曲折与复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社会的一个缩影。连环画《人生》开篇使用了倒叙的方式,同《人到中年》处理方式一样,把一个无奈与悲伤的画面放在了作品开头。图9第1幅画面交代了无奈的结局:男主角被迫无奈地回到了陕北老家。陕北沟壑的群山占据画面的大半部分,宛如北宋巨嶂山水画一般,主人公在群山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但是,《人生》的群山是一种无奈,一种对于以后农村艰辛生活的迷茫,压在主人翁身上喘不过气来,开篇第一幅画面就如此荒凉与沉重,奠定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压抑与无奈。一望无垠、遍布沟壑的山谷与渺小的人物形成对比,编织着曲折的人生故事,也是对蹉跎人生无奈的抱怨。

图9 聂鸥、孙为民《人生》第1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图10 聂鸥、孙为民《人生》第20幅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批画家从艺术创作上受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影响,连环画的创作出现了“孤寂”与“自然”的情绪,通过对萧瑟画面的真实描写中凸显了作品的矛盾情绪。在一篇评论连环画《人生》的文章中讲到:“那广阔的黄土高原,卖烤馍的农村集市场面,晾晒瓜果柴草的农家院舍……无不散发出独有的乡土气息,给人‘不隔’得亲切之感。”[15]孙为民、聂鸥通过对熙熙攘攘的乡村集市的深入刻画,图10为读者理解高加林卖馍时内心的窘迫提供了具体、直观、可信的依据,作品的容量因此扩大,所反映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厚度,高加林内心的矛盾在写实风格的画面中毫无遮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高加林的描写体现出这个阶段连环画对人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人性的表现上,这种人性表现在连环画上以农村题材和小人物为重点。《枫》《人到中年》关注的是“我”和“我们”当时或之前的伤痛的经历和平淡的人生,而关注农村题材连环画的作者表现的是“他和他们”的生活。
同样是农村题材与农民的塑造,连环画《人生》创造出的情感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连环画所表达的情感完全不同。建国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农民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形成了“工农兵”社会阶层排序。这阶段连环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是正面的、情绪是积极的,当时农民的满足感远远超过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时期的优秀连环画作品就能体现出出来,如《流动的小哨兵》《海花》等。1978年以后,随着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制的推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有过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乐观时期。但这种单纯靠土地上的劳动获取农产品收入的模式很快遇到瓶颈。大批中青年农民扔下土地,跑到广东深圳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寻找新的生活空间。中国美术中的农民形象,从欢乐转向期待,乡村中的“守望者”形象成为主流形象[16]。《人生》第5幅(图11)描写的是高加林受到打压后颓废了近一个月的情景,执拗地思考着人生,但并不想从此消沉下去。画面中高加林坐在床上,以侧面的形象烘托人物的情感、和沉思的状态。连环画《人生》中的人物形象与情感表达与前期作品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着社会巨变农民地位的变化,也体现出那个时期农民的无奈,但是《人生》中高加林在受打压后并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在为人生做着努力,对生活还是抱有一点点希望。这个时期的小说、连环画、绘画包括电影,共同构成了乡土的艺术语境,作为改革开放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窗口,乡土艺术语境甚至影响至今。现在我们偶尔还能听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就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那种落后与贫穷,这种烙印就是来自当时形成的乡土情怀的艺术作品。
五、结语
20世纪70年代末到“85美术运动”前这段时间新旧艺术思想的碰撞不亚于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美术问题的争论,连环画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见证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连环画作为最受欢迎、最为普及的艺术形式,许多画家都投入到了连环画的创作,这导致连环画中的一些作品,如《伤痕》《枫》等,直接影响到了美术创作,这使得连环画中批判、宣泄的情感彻底冲击了文革期间作品“三突出”的艺术模式和积极向上的情绪,这种艺术风向与情感表达奠定了上世纪80年代美术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次,一批“伤痕”文学的出现影响到了“伤痕”风格连环画的情感语言,特别是小说《人到中年》对于人性的关注,使得连环画《人到中年》受到了极大的成功,而后电视剧《人到中年》也取得了极大成功和反响。随着“人的价值”问题的深化,在美术界出现了许许多多描写各个阶层的绘画作品,而后聚焦于农村和农民,这一阶段连环画出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与文革期间农村题材的作品呈现出的情感形成巨大反差,形成了新时期的“乡土情怀”艺术风格。
在连环画《枫》影响下产生的“乡土情怀”与“85美术运动”所掀起的现代主义绘画探索成为20世纪后期中国美术发展的两条主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美术的本土化还是西方化的讨论至今都没有结束,那么对“伤痕”风格下连环画情感嬗变的研究有着追本溯源的意义。

图11 聂鸥、孙为民《人生》 第5幅原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