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渺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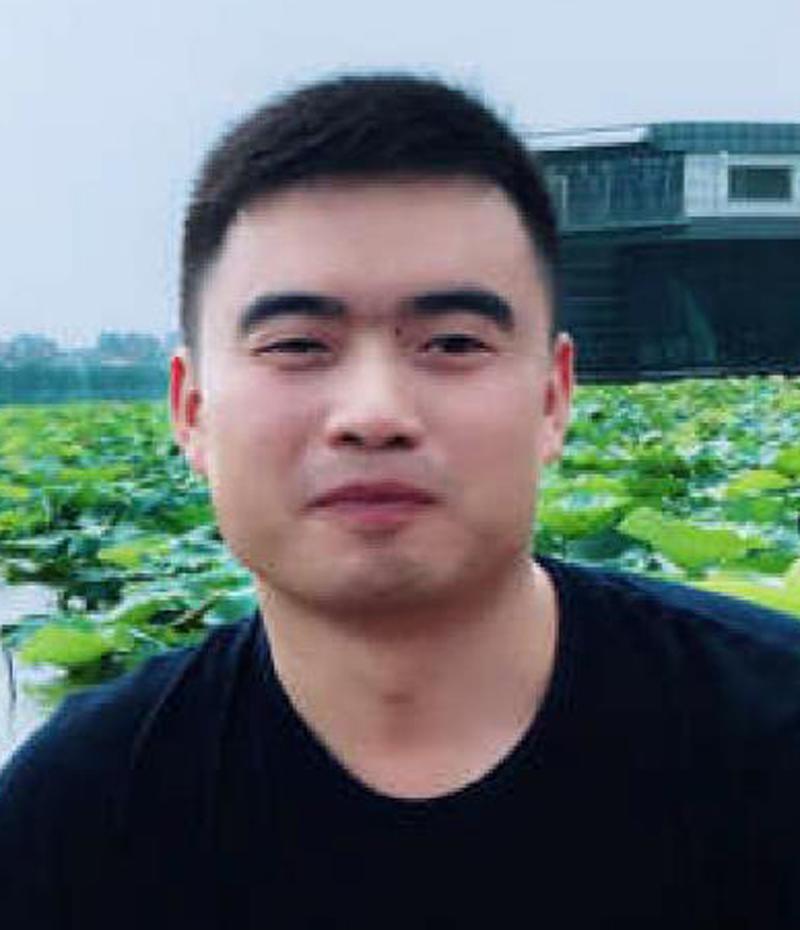
张岩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曾在《政法论丛》、《民间法》、《人权》等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业余写作。
母亲生日那天,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叽叽喳喳地聊着生活中的琐事。母亲在一旁安静地听着,或是面露惊讶,或是轻声叹息,或尴尬地笑笑。我深知,几近古稀之年的母亲怎么能够清楚成年儿女们的生活呢?她只不过是怕扫了我们的兴。酒过三巡,我试图寻找一些母亲感兴趣的话题,所谓母亲“感兴趣的话题”不过就是老家那些经年旧事罢了。回忆多与贫穷相关,当我们一遍一遍翻看时,最后竞犹如小时吃过的一种药糖,嚼着嚼着有了丝甜味。母亲说那时候,一到夏天热得无法入睡,她就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面铺一张席子,我们姐弟四个躺在树下,听着树上的蝉鸣度过一个又一个盛夏。
枣树……记忆中的四棵枣树就像是守望着我童年的四个巨人。它们栽种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们倒下的时候,我已走出了那个村庄。母亲说,那四棵枣树,在她跟父亲结婚前就有了,至于是谁栽的,就连她也记不清了。
我们四个人当时是按照什么规则认领的枣树,也已经无从记起。
我认领的那棵枣树已经模糊得犹如挂在树上的那个风筝,消失在午后刺眼的阳光里。那是我唯一的一个风筝,刚买来就被缠在了树梢,当我抬起头看那个被风吹得不像样子的风筝时,阳光在树叶间灼灼逼人,我揉了揉双眼,关于枣树的记忆就被炙热的风吹走了一半。依稀记得那棵枣树伫立院子正中央,与其他枣树不同的是,它有着速生杨一般笔直的主干,且无旁枝,仿佛拼命要把树梢探出屋脊,伸出院子,最后插进云霄里。可是,那棵枣树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结过果子,我一度怀疑那到底是一棵杨树还是一棵枣树。在它被砍倒的那个下午,我清楚地看见了枝丫上的枣针和长圆形黄绿色的枣叶。
大姐认领的那棵枣树有着大伞般的树冠,温静地站立在院子的西南角。每年秋天树上都会挂满小枣,清脆甘甜,由于枣树生长的位置临近猪圈,每年收获小枣前,母亲都会用帆布将猪圈给覆盖起来。竹竿打落的枣子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帆布上,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像是几十面小鼓同时在敲响,敲得人心里痒痒的,听声音就感觉今年的枣子比去年更脆更甜。收获的小枣一般来说会分成三份,一份由我负责分给左邻右舍尝鲜:一份被拿到集市上换钱:一部分被均匀地铺撒在秋日的阳光里晒干,然后被母亲仔细地装进网兜,放进碎花布遮挡的门龛里,保存到春节以备蒸年糕使用。
二姐那棵枣树生长在院子的西北方位,枝干粗壮,每年结出的果子又大又圆,可是每到秋天枣子成熟的时候,树上的大部分枣子都会率先干瘪溃烂,被南来北往的各种鸟类啄食。
至于三姐的那棵枣树,生长在南门附近,南门低洼,枣树常年浸泡在积水中,树身出现了大幅度的倾斜。树叶常年稀疏,呈现出一种营养不良的黄色,但是每年都会在近三个月的雨水浸泡中生存下来,并且还会结出果子。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家里的四棵枣树,除了大姐的那一棵每年秋天都会有一种收获的仪式感之外,其他三棵枣树似乎一直并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如果哪一年生出了果子,一般还没等到收获就被我们几个孩子和各种鸟类分食掉了:如果哪一年没有生出果子,我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失望,只是心里都默念着,只要树还活着就好。
谷雨一过,枣树的枯枝开始慢慢地生发出一点点鹅黄。随着气温持续上升,枣树上热闹了起来,一簇簇枣花像女人头上佩戴的花簪,斜插在鹅黄色的枣叶之中,甜香充溢着整个院子,蜜蜂嗡嗡着穿行在四棵枣树间。春季是沤肥的最好时机,由于父亲常年在外面游荡,对家庭事务几乎不管不问,家里家外的农活家务便由母亲一人担了下来。母亲从田里回来,换下衣服,穿上雨靴,拿着铁锹进入猪圈,开始清理猪圈。她矮矬的身躯站在将近两米深的猪圈里,将一锹锹猪粪扬到猪圈边缘,然后再将猪粪沤起来,等到芒种,便是上等的绿肥了。每次母亲清理猪圈时,我都蹲坐在枣树下面,看着猪圈里不断扬起的铁锹,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总是感觉那是大姐的枣树在漫长的冬季过后重新获得了力量,粗壮的根幻化成一只巨大的铁锹在帮着母亲。
每次母亲干完活,浑身如同洗过澡一般,靠在大姐的那棵枣树上喘着粗气。我站在枣树下用蒲扇给母亲扇着后背,枣花扑簌簌地掉在母亲头发上,花粉伴着母亲的汗水从皱纹里冲刷而下。年幼的我不知道枣花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姐弟四个当中,大姐从小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是最为认真的一个,颇受长辈和老师们的夸赞。后来大姐上了初中,每周回家拿一次馒头,一家人节衣缩食,就是为了能让她回家都能拿上白面馒头。那时我天天吃窝头,以至于别人在我面前一提起窝头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干呕。
中考报名的前夕,大姐竟然“毫无征兆”地辍学了。大姐在院子里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跟着父亲投奔了一个远房的亲戚,卖起了凉皮。记得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时常会走到枣树下面踹几脚枣树,恨它们为什么是秋天结果而不是夏天,那样我们卖掉小枣就会有钱,大姐也不会辍学。长大之后我忽然明白,当年除了大姐之外,更有一个人在日日夜夜的自责中受尽煎熬,那就是母亲。直到现在,一提起当年大姐辍学的事,年近古稀的老母亲仍然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抽泣地说不出话来,她总是一遍一遍地说,哎,如果当时能借到那几十块钱的中考报名费,大姐也不至于断送了前程……
后来,二姐也辍学了。她的辍学跟她的性格有关,而根源却是她注定无法逃离的这个家。父亲的不务正业和家庭的贫困让性格刚烈的二姐在学校受到了同学们的欺负。她辍学时,母亲哭着央求她回到学校,甚至当时颇有威望的老村长都被请到了家里劝说二姐,然而无果。二姐的性格和这个家庭的卑微最终形成了一股隐秘的合力,导致二姐决绝地走向了生活的另外一条路。
二姐辍学以后,跟着母亲下田劳作,回到家里再帮着母亲把这个家打点得干干净净。她一直希望有一天这个家能够有所改变,能够不再被歧视。她常常咬着牙发誓说,以后我们一定要赚很多的钱,让这个村子的人都羡慕我们,而不是嘲笑。她在家里养了几只羊,几只兔子,还有鸭子。院子比较小,二姐就在西边小小的空地上亲手垒了兔窝和鸭圈,而旁边就是二姐那棵粗壮的枣树。到了夏天,枣叶繁茂,青枣满枝,一些树枝被压弯,像是紧绷的弓,随时都有可能将箭射向天空。几只山羊借此机会两腿撑地前腿扶着树干直立起身体啃食青枣和枣叶。时间久了,二姐那棵枣树靠近地面的枝叶变得光秃秃的,整个树干被山羊啃食得斑斑驳驳,就像是院子里那三间土屋经年剥蚀的外墙。可是那棵枣树的生命力却让我们惊讶,它每年依旧像是一串巨大的风铃,秋风一起,枣子在枝葉问叮叮咚咚地响个不停,不仅被我们孩子们采摘,也被即将南下的候鸟分食。
二姐对生活总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也是她极端性格的根源。父亲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块乌云,他每天都会醉醺醺地回家,然后跟母亲吵架,把家里折腾得一片狼藉然后又出去游荡。父亲的游手好闲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年年算都算不清的外债,每年母亲养的猪仔、二姐养的羊羔和兔子都会被讨债人洗劫一空。记忆中二姐做过两次极端的事,一次是因为父亲酒后,在家里用女人的“妇道”问题无理地挑衅母亲,母亲被气得放声大哭,正在喂兔子的二姐气得咬牙切齿,她的头在那棵斑驳粗壮的树干上不停地撞击,正在树上分食枣子的候鸟惊得四散开来。鸟群像是一朵黑白相间的花,在二姐和母亲的哭声中绽开,然后又变成了小黑点消失在远方,树上凹瘪的枣子、黑色的羽毛、黄绿色的枣叶纷纷落了一地。
另外一件事也是我亲眼所见,记得那是一个午后,我从学校回家,家里异常安静,房门开着,我进了屋子看见二姐躺在床上睡觉,我叫了她几声,没有回应我。然后不知过了多久,她半睡半醒地问我要水喝,我给她拿了水,突然她从床上起来踉跄地跑到枣树下面,扶着枣树吐了起来。鸡鸭旁若无人地伸着脖子在地上四处觅食,黑狗蜷缩着身子在树荫下打盹,公鸡扑闪着翅膀飞上西边的院墙叫了几声,梳理起自己的羽毛,此刻的枣树则安静得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一动不动地撑着虚弱的二姐。二姐呕吐完后没有漱口便踉跄地回到床上又睡了过去。后来听二姐说,父亲跟母亲吵完架便出去了,母亲也下地干活去了,她觉得活着没意思,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她服用了安眠药试图自杀,幸亏服用量较少,没有出什么事。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瞳孔里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窝头,同时将一块黑咸菜梗默默塞进嘴里。那年,她十四岁。
对于我和三姐的枣树,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
只记得当时由于我的枣树生在院子的正中间,影响院内通行,且这棵树从来都没有结过果子,被父亲砍掉了。三姐的那棵枣树何时消失的我们也都记不清了。那棵枣树的消失就像是门前积攒的雨水一样,我出了一趟门的工夫,再回來就没有了。
但是三姐那棵枣树在我的记忆里却奇怪地跟一种美食——油条——画上了等号。三姐的枣树以前算是我家院子的南门。90年代的鲁北农村鲜见水泥砖瓦垒砌的院墙,每家每户在自己院子的四周栽种一两棵树或者堆放一点柴草作为界标,一个院子便形成了。傍晚时分,油条货郎的叫卖声便富有节奏感地从大街小巷响起。那个时候各种形式的串乡买卖盛行,所谓串乡,就是货郎以自己的作坊为中心,用牛车或者自行车载着自己生产的货物在周围的几个村庄进行叫卖的一种交易形式,主要包括人民币交易和以物易物两种方式,例如早上的豆腐、中午的馒头、晚上的油条、一天不定时叫卖的水果、糖葫芦、酱油醋、辣椒酱、小鸡仔、虾酱等等应有尽有。不同的货物有不同的叫卖声,不同的音高、音色和节奏,例如卖豆腐的货郎通常都是不吆喝的,他们的自行车把手上会捆绑着一个竹制的圆柱形器具,手里握着一个木制的梆子,每隔几分钟敲三下。想买豆腐的人听到敲梆子的声音都会提前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票子或者端着盛放黄豆的簸箕,要不就先打发自家孩子到门口把货郎叫住,再提着称好的黄豆,不紧不慢地走出门来。卖油条的货郎可就不同了,每天傍晚,他们炸好了油条装进柳条筐中,骑着自行车喊着“卖果子嘞”,“卖”字往往会刻意地加重语气并延长几秒,最后的“嘞”字往往要提高几个音高,貌似在夸赞自家的油条更加美味。
我们家孩子多,对于油条这种美味自然是难以抗拒的,可是家里债台高筑,每年一入冬粮食就不够吃了,开始东家拼,西家凑,勉强度过寒冬。至于油条这种美味,一年也就只能吃一次,那就是麦收的时候。
刚刚打下的新麦运回家,给政府交完公粮,还一部分陈年粮债和父亲的酒债,母亲往往会拿出几斤小麦给我们姐弟四个换几根油条解馋。到了傍晚,母亲提前称好小麦,我们姐弟四个便端坐在院子里,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叫卖声,心里担心油条作坊那天突然有事不出工了,或者又担心麦收了大家都在买油条,到我们家门口就卖完了……总之从开始等待到声音响起的那一刻,心里都充满了焦虑。随着声音由远而近,我们的心情慢慢地由焦虑变为兴奋,货郎的自行车从南边的路口一转,再往北走五十米左右便到了三姐那棵歪着身子的枣树下,也便是我家的南门了。我就会兴奋地跑到枣树下,蹦蹦跳跳地喊着我们要买油条,母亲这时也从屋里端着小麦出来,跟货郎寻问着价格,讨价还价,货郎也比较好说话,能便宜就给母亲便宜。
交易完成,我和三姐就会抢先从母亲手里拿过一根油条靠在枣树下慢腾腾地咀嚼起来,一是为了想慢慢地享用这人间的美味,二来则是为了让邻居的小伙伴看见我家也能吃上油条,来满足一个儿童与生俱来的虚荣心。每当此时,母亲都会满脸愠色地赶我们回屋里,有一次甚至用枣树枝打了我。我们当时非常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大街上吃油条。事后母亲教育我们说,咱们家左邻右舍还有还不完的债,能吃上一口饭就很不错了,怎么还能吃油条呢?我明白了,母亲是怕被债主说闲话,才让我们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吃油条这种“奢侈品”。油条母亲从来都是一口也不吃的。
再后来,我们姐弟四个也都离开了那个村庄,三个姐姐远嫁他乡,我来到了首都,年迈的父母也都被接到了姐姐的身边。记得大姐的枣树被砍掉了,那棵枣树曾经晾晒过衣服、悬挂过春节的鞭炮,也做过剥蚀兽皮的承重架,这些都是一个农村家庭关于生活几乎所有的想象:二姐的那棵枣树在前几年完成了关于四棵枣树传说的最后的守望,在我们姐弟四个离开家乡后的某个夏天,生了一场虫灾,第二年的春天就再也没有发芽:三姐的那棵枣树承载了我童年对美食的很多幻想,有时候我的梦里依然会出现那一棵站在南门泡在水里的枣树,一动不动地坚守着一年年的旱涝和那几个在枣树下买油条的孩子:我的那棵枣树虽然没有结过果子,却最终成了一根优质的檩材。
它们都死了,我们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