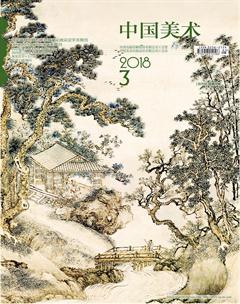暮云春树渺愁予
耿晶
一、从《桃花渔艇图》到桃源涧
恽寿平《南田画跋》中有《为周太史画桃源》一则:
桃源,仙灵之窟宅也,飘渺变幻而不可知。图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独契灵异,凿鸿蒙,破荒忽,游于无何有之乡,然后溪洞桃花,通于象外,可从尺幅间一问津矣。吾友王子石谷语余:“自昔写桃源,都无真想,唯见赵伯驹长卷,仇实父巨帧能得此意,其辟境运毫,妙出匪夷,赋色之工,自然天然。”余闻斯语,欣然若有会也,因研索两家法为《桃源图》。
据行文可知,恽寿平《桃源图》的创作,汲取和融合了南宋赵伯驹、明代仇英两家画法;王翚的心得给予他很大的启发,戚戚焉若有所会,遂欣然操觚。恽寿平为周世臣所画《桃源图》流传不详,而王翚的《桃花渔艇图》却幸运得多。此画见于恽寿平、王翚《花卉山水》合册,为十二帧中的第七帧,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青绿设色,古雅妍丽,其画幅虽小,但构图与布景别出机杼,颇得开合疏密、动静虚实之妙。一条山溪自左侧上方s形斜流而下,愈下愈宽,一小小渔舟沿溪而下,渔人坐于船头,神态怡然自得。崖巅荦确,树石苍翚,桃林夹岸,落英缤纷,云气氤氲腾涌,直接天际。王翚自识:“曾见鸥波老人《桃花渔艇图》,设色全师赵伯驹,偶在房仲书斋背临,似与神合。”王翚由赵孟頫上窥赵伯驹,取法的重心在于赵伯驹融文人笔墨于青绿画法的开创性(董其昌将其归入“北宗”,却也不能不承认他“精工之极又有士气”)。恽寿平对王翚青绿山水的评论也有所印证:“青绿设色至赵吴兴而一变,洗宋人刻画之迹,运以深沉,出之妍雅,秾丽得中,灵气洞目,所谓绚烂之极,仍归自然,真后学无言之师也,石谷子二十年静悟,始于秘妙处爽然心开,独契神会。”
在另一幅江寒汀旧藏,王恽合作《桃源图》中,王翚同样表达了对赵伯驹以及仇英的仰止之意,款题曰:
然自古图绘家多好为武陵桃源,以为闻其说,宛然在心目间若可游索,而惝恍变幻不可知,故往往借笔墨而问津焉。昔赵千里曾作长卷,十洲仇氏亦有临本,皆能得惝恍变幻不可知之意。宛然如在者,可按索而游,故足传也。余为图时,与羽人相遇于泠风之上。图中一阖一辟,别有世界,千里、十洲恍惝奇幻之意,庶几得之,未敢为呼吸可通仙灵也。庚戌(1670)寓白云精舍,鸟目山人王翚画并题。
此题识与上引恽寿平《为周太史画桃源》一跋文意呼应,颇足相互阐发。据吴湖帆鉴考,此画主要为王翚绘成,题语虽款署王翚,搦管者实为恽寿平,并断言“可证当时王恽冶垆于一,无分尔我也”。
王恽合作《桃源图》作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早于王翚《桃花渔艇图》约两年。是年王翚、恽寿平分别为39岁、38岁,正值盛年,论交也几逾二十载。“王恽冶垆于一,无分尔我”所指,当然并非仅为创作中的“合璧”形式及相互之间的切劘,两情契洽、心交神融,才是隐含其中的关键词语。恽寿平与王翚的“桃源问津”,既是对古人的礼敬,也是对传统的溯源,同时又隐约寄托了希世高蹈、超越尘累的向慕。他们笔下的桃花源,既不是士文化中以用指代理想邦国的象征符码,也不是遗民情境中用来表达拒绝政治认同的生存象喻,而是一个并非实有、但又无处不在的意象世界与心灵境域。其“惝恍变幻不可知之意”,稍纵即逝不可捉摸,但又是美轮美奂、难以言说,王翚款题中的“与羽人相遇于泠风之上”倒是可以仿佛一二。唐人韩愈曾执拗地研考桃花源的真实性,说是“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韩愈《桃源图》诗),未免胶柱鼓瑟。对王恽二子来说,“桃源”為性灵的远游与精神的高翥提供了象征性的皈往之所,与武陵人不同,王恽二子因了彼此的把臂同行,“吾谁与归”不再是一个落寞的问号。
“桃源涧”则是一个真实而可居可游的所在。自王翚二十岁移家于此之后,这一个位于虞山北麓的毓秀佳胜之地就不时影现于恽寿平的笔端。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九月南田草堂送石谷应栎园周司农之招》组诗其一云:“我在南田蔽绿筠,错刀天畔寄愁频。三秋丛菊花边梦,半绕桃源涧里人。”在恽寿平的描述中,桃源涧“窥庭如在山,探山山晖閟。有时风雨来,襟带乱空翚”。此外,它又是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应闻天鸡鸣,或与猿鸟值。出入径寸问,森然万象植。云物敢秘精,造化同得意。玄黄改橐龠,阴阳无根蒂。振冠干载上,浩荡骋灵辔。”现实中的桃源涧仿佛与“惝恍变幻不可知”的桃花源交融叠合,浑然一体,成为恽寿平的梦萦魂牵之所。
在康熙初年恽寿平致王翚的书信中,有这样一番倾诉:
每闲行游,看一山一水、一树一草、一片云、一拳石,无一不思吾石谷也,即若与石谷子相对。又观石谷之墨痕笔精,奇理百变也。故虽与石谷形迹阔绝,无时无日不与石谷同室而聚居也,又岂在区区形迹之间哉。弟令春凡三四束装,俱为事累所束缚。已闻北郭好事者韩氏,致书币相招,知石谷不可却。此间有正叔在,知石谷定能勿却也。石谷既来矣,把臂有期矣。而正叔方苦逋粮,日与践更胥吏为缘。望虞山若在云汉之表,非仙人御泠风,乘飞龙,断不能至桃源涧,即弱水秦人舟至遭迴风处也。弟已久坠泥中,虽钻皮不能出其羽。悬拟石谷来时,未知何以洗刷我,而俾我通灵,使修然霞举乎!
“望虞山若在云汉之表,非仙人御冷风,乘飞龙,断不能至桃源涧,即弱水秦人舟至遭迥风处也。”一句中的“桃源涧”,一语双关,所指显然不仅是现实中王翚居处之地。彼时恽寿平正处在疲于应付逋欠的焦灼与困顿之中,他渴望涤肠换骨,把那些热恼与愁闷疏瀹一尽。似乎唯独他的“桃源涧里人”拥有如此神奇的能量——“石谷既来矣,把臂有期矣”!即便无视信的前半段纡徐不迫而又细致入微的那一番告白,仅此一句,也足见恽寿平期盼王翚到来的热切与所求如愿的欢喜,直令读之者会心一笑。
关于王翚与恽寿平,我们已知的是,二人平生交好、嘤鸣相召,自韶龄订交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恽寿平辞世,三十年“道谊同心”。王翚的绘画和技艺为恽寿平极尽赏叹,为之一题再题,络绎不绝,“王画恽题”堪为清代绘画史的一隅胜景。志洁行芳的“恽高士”,其画名远播大江南北,也与王翚的一番导扬不无关系。那么问题是,王恽之间的交游史料并不匮乏,对二人交游行迹作追踪、梳理者也所在多有,脉络清晰、事实明了,似乎不存在什么遮蔽之处。然而坦白说,二人关系何以如是、何以至此,仍令人有迷离惝恍之感。据实言之,王恽之交的历史图像,大半是依靠恽寿平各种文体形式的撰作来构建的,或诗,或文(题语),或书信,等等。《南田诗钞》本就是由恽氏散佚过半之后侥幸存世的诗作编次而成,即便如此,与王翚相关的篇什也占有相当比例。然而在王翚,甚少见到他完整的回应,即便有,也显得平静无波、相当克制。当然,除了王翚不能诗,缺少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之外,可能还与其个人性格有关。
顾祖禹序《瓯香馆集》,有云:“世有独至之人,而后有独至之诗。夫得于天者为性情,出于身者为行谊。存之为学识,发之为文章。性情不真,行谊未笃,而学识未正,徒欲以诗文夸诩天下,天下其许我乎哉?”将“独至”作为恽寿平的个人标识符号,是实至名归的,不论人品还是诗格、画格,还是交游行谊,王恽之交正堪为恽寿平的“独至”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同时互为客体的王恽二子在交游中互为镜像,又成为后人赖以识鉴的依据。
而王恽之交的这份“独至”,似乎并没有被充分认知。印象化的书写一再重复,诸多细节与肌理却在时间的磨蚀中渐渐流失了。恽寿平曾在致王翚的书信中说:“客中与二三赏音谈议笔墨,必言石谷先生云何。王郎姓氏,真如芝兰芳草,出口有香气,人所乐得而称道之,正不知其所以然也。”恽寿平之于王翚的知己之感终生如一日,对王翚的倾怀结想一往而深,难道也只能用“不知其所以然”来归结吗?本文是一次尝试性的写作,如果必须敲定一个学理化的动机,可以表述为:进一步的“知人论世”可以为绘画风格以及作品鉴定等研究建立新的基础。
二、王恽之交的情感质地与美学气象
比照王恽二人的年谱资料,二人自论交之后,或斟茗快谈、联床共话,或泛舟登临、流连花月,或偕三五画俦诗侣往来赠答,种种胜游高会、赏心乐事,即便后来的读之者也不免色艳神飞。然而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聚时少而离时多,才更接近本来面目。从感觉而论,恽寿平交王翚之后,他的生命形态,仿佛就定格在了不是与王翚(或偕朋辈)畅怀游处,就是在床前月下徘徊瞻望的状态之中。“方从天畔忆琼枝,何事春莺出谷迟。青鸟竟违前岁约,碧云深负故人期。”在恽寿平的叙述中,他对王翚的“向慕系思”,甚至并非为王翚所能全部了知。倾怀结想,念兹在兹;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类文字在《恽寿平全集》中俯拾即是。比如信札:
意乌目先生具在虞山枫林红翚之间,未易即得晤言,弟又汲汲将去阳羡,竟不能再登西城草堂,快聚十日,此中恨恨,真不可堪也,不可堪也!
一日不见,念吾兄时发于梦寐。
正月初正欲遣介来相候,因水涸,道路阻塞不通,无计相闻。忽从友人寄到尊翰,喜甚!快甚!弟日夜念吾兄,知吾兄必念弟,异地同心,声相应也。一月望后,悬榻以待,引领以望矣。
时时出阶下望天色,其苦恨可知。手札来,不觉神情欲飞,问天气暮矣,无缩地之术,恨杀。期在明早,即雨,亦当著蓑笠来叩水庭之扉,一呼石谷先生也。
恽寿平“嗟我怀人,有如饥渴”的自我塑造,未有比如下一则更能刻画入微:
自兄来此,弟素狂不怯人,今乃不能著一笔,间持笔,辄念石谷,念石谷百遍,稍稍得一两笔,得一两笔后,辄又虑吾石谷他时或见之也,复为踌蹰久之。弟与兄庶几称肺腑矣,而忍视我坐颠倒想中过五十小劫耶!
正所谓“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每闲行游,看一山一水、一树一草、一片云、一拳石,无一不思吾石谷也,即若与石谷子相对”,“弟日夜念吾兄,知吾兄必念弟,异地同心,声相应也”。这种确信源于灵犀的感通,原非逻辑分析所能把捉。康熙十二年(1673)秋,客居杭州的恽寿平热切盼望王翚亦来同聚,当得知王翚已往扬州,愿景成空,遂以书致之,水远山长之慨尽托于辞:
人生聚散有定数,江山胜赏,良友盘桓,人间乐事,无有过此。然必有造物妒之,定不易得。焦岩销夏,前期如梦,二十四桥明月,王郎独夜闻箫,知此际定难为怀耳。长兄在广陵,必时时念我,弟亦同此一日三秋。正所谓人非形影,安能动而辄俱?一室嗒然,不能不隐几坐驰,伫想天末。
所思“王郎”独立二十四桥明月之下,瞻望弗及,徙倚何依?恽寿平以“玉人”隐喻王翚,浑然天成。所谓“隐几坐驰,伫想天末”,“坐驰”意即向往、神往,“天末”按字面理解,是天际、天边之意,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让人想起杜甫那首著名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恽寿平高自标置、又复深情缱绻之意,尤堪揣想。最为洞彻肺腑的倾吐,当推此则:
不佞弟与石谷以缟丝之雅,兼之翰墨相慕悦,知人所不及知,而赏所不能赏。而称相知,较他相知不啻什倍,宜乎形迹密迩无间隔之恨。而间隔形迹落落,较他相知亦且什倍。若此则相知之心盖已疏矣,而此心则愈密。每闲行游,看一山一水、一树一草、一片云、一拳石,无一不思吾石谷也,即若与石谷子相对。又观石谷之墨痕笔精,奇理百变也。故虽与石谷形迹阔绝,无时无日不与石谷同室而聚居也,又岂在区区形迹之间哉!
他叹息的是:“你我的相知,比其他的相知胜过十倍,本应形影相即,相反却不时暌隔,相比其他的相知也不啻十倍。”恽寿平感慨彼此相知之深,更感慨二人形迹的阔略,在无奈中又转而为心灵的不隔而感到释怀——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慰藉。“知人所不及知,而赏所不能赏”,试想,还有什么比此句更能概括王恽之交的质地呢?“缟纻之雅”无须解释,所谓“授缟芝以托心,示兹诚之不谬”;至于“以翰墨相慕悦”,不可否认艺术是二人相互“慕悦”的直接因素,此种“同调结契”尤其为恽寿平得意惬怀。最现成的依据,应当是他“先生之珍图不可无南田生之题跋,敢云合则双美,庶非糠枇播扬耳”的自白,表现出的自信与当仁不让的确让人印象深刻。此外,还有恽寿平自许知音极致化的表达:“所经营绢素,当更得奇宕险怪之想。然南田不在,即得意,有誰能称快绝者。即有之,想吾兄亦何屑听其妄为评论,使苍蝇声之入耳也。”这是何等的一份自负!与此相类,恽寿平《赠乌目王山人》组诗其四云:“画苑谁称绝代工?兴来摇笔撼崆峒。何知我辈千秋业,万国莺花闭户中。”诗意表明,恽寿平对友情的珍视与对自我的珍摄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于对艺术理想(“千秋业”)的求索之上。再如下则:
今之操觚者,昧昧然索之丹粉,索于颖墨,剽窃唾剩,假借畦径,以涂人耳目,激倡时风,其于古人笔精,相去已不啻千里万里。而况欲出入化机,抉天地之秘奥,而画象之哉?昔顾骏之构层楼为画所,登楼去梯,家人罕见其面,其高致何如也。吾与足下,正以千古自命,亦何肯让之。
大有元好问式的“谁是诗中疏凿手,管教泾渭各清浑”的气势。王恽二子彼此惺惺相惜、睥睨时流,“何知我辈千秋业”,也正是“吾与足下,正以千古自命”者。恽寿平赞叹王翚“洗尽时人畦径”,王翚称许恽寿平“随笔写胸中逸气,而一种幽深淡远之趣,近世画史所不能梦见也”。恽寿平说:“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王翚则认为:“凡画唯在闲适时深参造化,乃得一种意外之趣,而后能合古人。若以刻画求工,遂为时俗谬习,终成下格。”所论桴鼓相应,正蕴含了这份共同的期许之意。
然而,这一点可以佐证王恽之交的所以“独至”,却并不能充分解释恽寿平对王翚的“向慕系思”之深。清晰的因果逻辑有利于保证结构的完整,却常常是以滤除细节和肌理为代价的。恽寿平的“向慕系思”,或许更宜归因于“向慕系思”本身,它不需要理由,也不关乎目的,出于本心,复归自性。他对自己与王翚这份行谊的超乎寻常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七言古体《送王郎还琴川诗》题下自注:“犹记予从南村走东郭,时已就瞑,不得复见,宵分徒倚庭隅,索句既成,明日书扇,舟次诵诗唱别,同人见予与石谷交谊如此,近世所无,莫不叹息。”其诗云:
海云沉山云不飞,吴川落月霜满衣。
折残桂枝怨秋冷,葛屦山人归未归。
锦衾宵寒崇兰湿,茭芦雪浦飞鸿人。
芙蓉渡口饮君酒,鲤鱼风起秋涛急。
吴娥坐鼓蘋花楫,满船都载丹枫叶。
此诗意象迷离要眇,色境浑融,将李贺“化质实为空灵”的表现手法与李商隐哀感顽艳的抒情特点熔为一炉,不言一别字而离情别绪盎然纸墨问,表现力与感染力让人过目难忘。
《送王郎还琴川诗》中的超现实意蕴在古体长诗《梦与石谷画游鱼既寤咏诗为图寄之》中的体现有过之而无不及。“落花游鱼”是恽寿平喜爱的题材,除了“濠梁之趣”这一常规解读,还可以形象地指代精神的自由以及一种空幻灵动的美感。他的诗句,是那么意象纷繁、辞藻典丽;他的梦境,是那么瑰丽奇幻,不可方物;梦中王翚的出现,让他感到无比怡悦和安宁。“若有王郎倚绣茵,墨花暗染蘋花趣。芙蓉雨,蒲塘路,荇带青可怜,修鱼影相聚。莲叶田田不可数,锦石云漪渺难渡。”梦填补了现实的缝隙,抚慰了他的孤怀与愁思,也激活了他的想象和灵感。
王翚入梦索诗,这一情景在恽寿平的记述中不止一次。《甲子秋将游虎林作此简寄与石谷先生》组诗就是其中之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52岁的恽寿平爱子痘殇,沉浸在悲伤之中无计自遣,遂离家作西湖之游。道经无锡,夜宿客馆,梦中王翚来索近诗。梦醒之后赋七绝五首,附书寄之。题下注云:“相别一载矣,去虞山百余里,音问悬隔。嗟我怀人有如饥渴,秋窗梦寐,惝恍晤言,觅句奉寄。”其一云:
东望停云结暮愁,千林黄叶剑门秋。
最怜霜月怀人夜,鸿雁声中独倚楼。
同写虞山剑门,恽寿平早年曾有诗曰:“年年芳草怨离群,有梦如何隔断云。此夜若随明月去,剑门岩畔定逢君。”相比之下,他的吟讴不再那么意气风发,而变得顿挫和沉郁。再看第二首:
秋风萧瑟赋愁予,久断琴川别后书。
白首兄弟相见少,莫因沦落弃前鱼。
第一句撷取《楚辞》中《九歌·湘夫人》意象:“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众所周知,《楚辞》中思公子、怀美人的比兴传统在屈原之后就获得了文学与美学的某种象喻资格。顾祖禹《西田独赏序》云:“先生(王时敏)于石谷,如骚人之怀美人、思公子,得见则喜,不得见则离忧,倚徙欲暂解于中而不能。呜呼!石谷何以得此于先生哉?”实际上,这句话若用于恽寿平之于王翚,比王时敏来得更贴切。“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南田诗本就深得《楚辞》之风神,“南田五言古体,上裔《离骚》,中参苏、李,下括建安七子,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七言古体追逐青莲,又复酷肖奉礼。五律专师浣花,绝句脱然畦封,直与龙标诸贤白战于变风境上”。朱良志先生说《楚辞》具有寂寞无可奈何的美学精神,恽寿平就深有会心于此。尽管其悲凉哀飒、怀抱激楚之作亦复不少,但整体说来,他的诗风俊逸澹宕而又迷离杳远,风姿绰约而又渺然难寻,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萦回不去,在幽思中自怜,在自怜中完成自我的珍摄。这是恽寿平诗歌的基本格调与气象,也形成了王恽之间的情感节奏。其四云:
山水空留太古琴,一生能得幾知音。
半园已去西庐杳,剩得南田是素心。
为王翚梦中索诗而创作这一组七绝诗时,恽寿平的生命只余短短六年。此时老境侵寻、知交零落,清定鼎已久,眼看复明已成泡影。绮梦既阑,壮心已已,又复感慨身世、俯仰今昔,对王恽来说,还有什么比拥有对方这样一个平生知己更能感到慰藉呢?他在随诗信札中说:“举家哀伤,触目恸心,无人生之乐。胸中无限心事,非吾至知,无可告语者。弟命薄如此,将焚笔砚作方外游,不忍者,唯吾石谷长兄先生。”
恽寿平以王翚为客体的吟咏与讽诵,一唱三叹,回环往复,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读其文字,不由感叹他那春蚕吐丝般的绵渺深情,熔铸了热烈与高寒、澹宕与沉郁的气格声调,的确有常人不能效仿者。然而如其所言:“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笔。所谓天际真人,非鹿鹿(碌碌)尘埃泥滓中人,所可与言也。”
真可谓“求仁得仁”,恽寿平又何怨乎?
恽寿平的离世过于匆遽,仿佛朱弦玉磬,戛然而止,遂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如其之于王翚,若“弟日夜念吾兄,知吾兄必念弟”者,由不胜思念而设身处地转换角色,想象对方于自己的思念,当以杜甫《春日忆李白》最为人称许:“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仇兆鳌注:“公居渭北,白在江东,春树暮云,即景遇情,不言怀而怀在其中。”在此之后,“暮云春树”或“春树暮云”成为借以表达离情别绪的经典使事语码。元人宋襞《燕石集》有《送章生还江陵》绝句,诗云:“南国相知音信疏,暮云春树渺愁予。东风解办含情句,代作长江双鲤鱼。”借以为题,庶几可得南田之心哉?
三、作为镜像的王翚
王恽身后,论之者往往并置其人,言下也多有轩轾之语,纷纭络绎,难以尽述。然而,认为他们之间的友道超越当时,将其与“古人”比类,如吴修“论交真与古人同”的说法,成为普遍袭用的修辞。实际上,也就是象征性地表达一种稀有难得、可堪向慕的价值态度。
范玑《过云庐画论》云:“若南田高自位置,其低首在同时之石谷者,实未可企及矣。人谓:南田力量不如石谷,特高逸過之,故工细之作,往往不脱石谷之法。但取境之超,安知石谷非亦得南田之益多也耶?”并且引据阎立本与张僧繇、黄筌与徐熙之间的嫌隙,来反衬王恽之间友谊的可贵:“所谓服之真,知之真;妒之深,亦知之深也。呜呼!岂独绘事为然哉?然如王恽之气谊,已驾古人之上,况其他乎?令人思而颜汗。”范玑明确提到了王翚与恽寿平在绘画技法与取境上的相互借鉴,但他也注意到了恽寿平在王翚面前的刻意低首。赞美他们的气谊的同时,实际上对王恽二子仍有不同的评判。范玑的态度代表了其时一个较为普遍的倾向,整体来讲,去当时愈远,则愈以南田格调高于石谷,石谷不能及为主流。沈德潜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南田山水神品逸品兼善,后恐掩石谷名,故专为花卉,以逊让友朋,此种心胸,近人不易有也。”此种判断似乎纯粹出诸感觉,与其《清诗别裁集》将恽寿平“比之天仙化人”一样,未知何据,却仿佛有无可置辩者。
当然这不影响问题的实质。不论对他们的艺术水准与品格高下持何种判断,都没有人对他们的友情表示怀疑。如戴熙就曾公然表示其追慕之意:“以南田之空灵,积成石谷之深厚,虽山樵、大痴不足慕,徒抱钜愿,愧不克偿知己,何以导我。”这一前提下,通过他们的交游及彼此映像,或许能获得对王恽二子更好的认知,尤其是相对来说面目不那么清晰的王翚。张庚以为:“正叔与石谷为莫逆交,讨究必极其微,石谷画得正叔跋,则运笔设色之源流,构思匠心之微妙,毕显无疑。”这里的“必显”是就王翚的绘画创作与画学思想而言,相形之下,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人”仍模糊得多。
恽寿平的艺术史形象,历来是十分确定的。“清如水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独立高步。”虽论画品,完全可以视作他的自我写照。相比来说,王翚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直至今天,有关王翚人品的看法仍然大相径庭。就个人而言,我的确倾向于相信王翚汲汲于荣利的表现与其笃于孝友、敦伦砥行的传状形象不相抵牾。但直觉与灵感并不能作为一种结论,行迹可见,心迹又复谁人能见?当王翚将画作呈与钱谦益或王士稹时,他是单纯地冀望知遇,还是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声誉?无论倾向哪一个,都不能仅凭材料支持论定,所谓辨析、剥理,多少系于个人经验乃至趣味,有时候,“知人论世”很容易与“推己及人”混为一谈。当然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背后隐藏了识力与格局之类看不见的力量。但无论如何,恽寿平心目中的王翚,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荀家鸣鹤又南飞,天下王郎见应稀”——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一种确信与不疑。
但有些事的确让人感到费解。恽寿平不断向王翚索画,又持续落空,就是其中之一。康熙九年(1670)围绕王翚《溪山红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记叙是通过恽寿平的两次题跋展开的。被他赞为“涤荡陈趋,发挥新意,徊翔放肆,而山樵始无余蕴”的这幅画作,先是被王时敏激赏,后为恽寿平爱不释手,却不过是“摩娑十余日,题数语归之”,最终以归于一位潘姓盐商了局。当恽寿平在买家那里与这张被王翚宣称“十五城不易”的《溪山红树图》重逢时,他表示“既怪叹,且妒甚!”又说:“不对赏音,牙徵不发,岂西庐、南田之矜赏尚不及潘子哉?米癫据舷而呼,洵是可人韵事,真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见西庐、南田,何以解嘲?”恽寿平驱遣《石林燕语》所载米芾以非常规手法获取王羲之《王略帖》的事典,表述饶有趣味。那么问题来了,王翚果然是如王时敏所说,“此君艺固独绝,利上最重”吗?若果如是,又怎么定义这位让恽寿平平生“低首”者的品格?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王翚毕竟是一位职业画家,鬻画维生是他的本色,原本无可厚非。张庚说:“(王翚)性孝友……石谷家本寒唆。以艺享盛名,受知圣主,取润笔致裕,而其根本固如是,此所以为石谷欤!”这是忠厚者之论。顾祖禹在《瓯香馆集》序中说:“叔子少弃举子业,无所事。又伤其家之贫,无以致甘旨于其亲也。闲绘山水以给旦夕,识者争欲致之,一帧可易数十缗。”“事亲至孝”的恽寿平,为了能让父亲享用“甘旨”而出售画作,不会不理解“性孝友”的王翚为家计而奔走经营。更何况,还有“赖石谷周其空乏”这一说!再者,恽寿平的题语也未必没有小藏狡狯。说他有为王翚鼓吹的嫌疑,恐怕也难以辩驳。不过恽寿平希望拥有王翚的画作,倒是真实无伪的。他曾对彼此交二十年却“箧中未尝蓄盈尺小幅,而寻常面交,长绡巨帧累累”的状况表示不满,并提起自己以藏墨换取王翚画扇的话头,让北宋王诜与苏轼上场,用他们的故事来提醒和叩击王翚早日兑现承诺。“夫王晋卿因东坡遭贬谪,其交深矣,然爱其书不可得,犹以缣素易之。因知笔墨赠贻不能独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怨而不悱、似怨而慕,这般自我纾解足以令人生起敬意,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关于友道“忠恕”的诸多话题。
此外,费解的还有关于“直谅”的话题。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爱才若不遇娄东,那得名成一代中。更有南田能责善,论交真与古人同。”自注:“南田极推重之,而与王翚手书,屡劝其勤学,每见画问题语未善,则反覆讲论或至呵斥,务令其自爱其画,勿为题识所污。”这段话措辞严厉,如果真如吴修所言,那么,接受这样的批评的确需要一定的气度。但在王翚一方,没有留下有关于此的雪泥鸿爪,是否存在有意识的取舍?恽寿平出身世家,学识淹博,这一点远非王翚可与伯仲。既为挚友,适当的提掇也在常情之内。王翚以佳图授之,使题识殆遍,足以说明对他对这位友人的同等信任和服膺。其实恽寿平的“责善”之举,并不限于艺事。比如他曾在书信中表示某种忧虑:“此中人见石谷之画,无有不洒然变色者。与其候候于龌龊富贵之场,孰若曳裾王门为上客,而乘车蹑珠为快意乎?此足下所当留意者也。”这封信天然注定了不能编入《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命运,不论王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恽寿平的劝勉。
由此也可以摄取关于王翚性情的某些印象,可能是沉稳、老成,或许心思缜密,与恽寿平的天然率真相比,可能还有一点世故。然而所谓“了解之同情”,其可贵就在于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或境遇。王恽二人的家世、經历、出处,乃至后来的生活状况都大为不同。恽寿平少年经历丧乱,论者以为“艰危奇变”,所交多遗逸、奇士,后隐于乡里,蓬蒿没身,又一度积极筹谋奔忙于秘密反清活动。王翚是一个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用世之心,但是他理解恽寿平的志向,也同情他的遭际。康熙十四年(1675),抗清志士吴鉏至武进联络谋划举义事,寓于恽家,王翚也来同聚,并于其间作《砥柱图》以赠吴鉏。尤其罕见的是,不工诗的王翚竟然一反常态,以六首绝句题画。二十年后王翚重见昔日墨迹,为之慨然不已,有云:“思当时揽辔澄清之志虽未遂而已不朽,因作《砥柱图》并题短句以赠于东山人,志感也,抑以犹冀也。”“思当时揽辔澄清之志”云云显然是南田声气,但却也足以窥见,王翚对恽寿平的理解与同情,是何等的倾其全力。但这又难免令人想象,王翚一生三度北上,第三次入京是在恽寿平辞世的当年(1690),就是这第三次入京,令王翚“布衣之荣,至斯极矣”。似乎不太容易设想如果恽寿平仍旧在世,会给予他何种建议,王翚又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与此相似的思路还有关于画风的。冯超然题王翚《仿古山水图》册(1680,南京博物院藏)云:“南田翁为耕烟交契最深,中岁之作,往往神气相通,故耕烟视为畏友。倘南田同享遐龄,而耕烟画格或为之一变也。”也一样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最不忍想象的,是假如石谷先南田而殁,恽寿平又会怎样以全部的心灵来哀恸与怀想呢?那样的歌哭,只怕是不忍卒读的。与恽寿平相比,王翚在其生前很少公开评论他们的行谊,题跋恽子画作也不太多,尽管评价很高,比如“南田子拟议神明,真得造化之意,近世无与敌者”。在跋语中他称恽寿平为“笔墨交”。这种内敛的表达在恽寿平卒后有所变化。恽寿平辞世之际家贫子幼,身后事无人主持,王翚赠以厚赙,并委托董珙(恽寿平友人、同里)等为之营理殡葬。董珙显然深为感动,他在致王翚书札中说:“要以南田良友如先生,亦足见南田之生平大概,而南田于是乎不死矣”,“古人云,一死一生,交情乃真。不谓当今世而犹得见古君子之大义高风,卓绝寻常万倍如先生其人者也”,不胜唏嘘之感。以“生死”来印可一份友情,这样的情境太过悲凉。而王翚复信中的叙述则平静得多,他说:“弟与恽先生真性命交,一旦长逝,遂令风雅顿坠,人琴伤感,理所应尔。”所谓“性命交”,应当是撇开了诸多杂染与分别的概念,带有超越性。王翚的义举为当时艳称,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情感质地与内在逻辑。赵园论乱世友道,以为:“但也应当说,发生在人间世更为常见的,既非‘刎颈之交亦非反目为仇的故事。至于友情在时间中的销磨,以及因了思想歧异而致的磨损,更是人生中寻常一景。人生的缺憾之感,不也系于此种场合?”就此角度而言,尽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王翚的义举最终为王恽之交作了堪称完美的注脚,但更为可贵的“独至”之处的确不止于此。
———《“意境”如何实现———恽寿平意境观念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