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与“文化间性”
□ 周建国

元杂剧《赵氏孤儿》剧照
古代丝绸之路,也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是经济贸易之路,也是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之路。它是双向的、多元的、多维度的,并且都要经过新疆。新疆是个大熔炉,是个孵化器。所以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新疆四千年》前言)汇流到新疆的各种文化艺术,有的继续东传,就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比如说狮子舞、柘枝舞、剑器舞、胡旋舞、胡腾舞等,有的是继续向西传到了欧洲等地,比如元杂剧《赵氏孤儿》。《赵氏孤儿》是纪君祥的一部名剧,不但改编成了多个剧种,也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实,它还是我国最早介绍到欧洲的一个剧目。早在1731年,它就被精通汉语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译成了法文,1735年发表在耶稣会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期上。他的译本是把唱词全都删掉的。因为他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说来,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转引自斯坦尼斯·于连《赵氏孤儿序》)。就是根据这个没有唱词、只有念白和舞台动作说明的剧本,1753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在巴黎国家剧院上演,它的服装、道具、布景全是中国式的,由当时著名的男女演员出演主角,轰动了巴黎。伏尔泰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剧呢?因为他认为“这出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同时代的作品的。”“戏剧诗之发达,则莫过在伟大的中国和雅典。”“《赵氏孤儿》虽然有不近人情之处,然而却充满了浓厚的情趣,情节虽不免于复杂,而线索脉络却清晰分明。情趣而易懂,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文学创作的两种美德。”(引自《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赵氏孤儿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文学》)。只是他不理解东方戏剧的结构,更不理解孤儿的报仇行动。于是,他把故事从公元前五世纪移到了十三世纪,把屠岸贾改为西方人熟悉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搜孤,曾经心仪的伊达梅藏孤。只要伊达梅离婚嫁他,即可赦免孤儿。刑场上伊梅达与丈夫宁死不从。成吉思汗深受感动,答应由他们抚养孤儿。
《中国孤儿》的改编和轰动巴黎,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成功的一个例证。既保留母体的精华、基干,又尊重、适应、融进传入地区人们的欣赏理念、文化艺术元素,这是能够被人接受和喜欢所必须要做的。从而也便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作品,甚至一个新的艺术样式。这个规律,适合于过去,也适合于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10月20日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里提到“文化间性”的概念,“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的可能性。”我想,《中国孤儿》可能也是这种“文化间性”的一种形式。
有所采用,也便有所舍弃。马若瑟舍弃了《赵氏孤儿》原有的曲牌和唱词,或许也是无奈。“唱词”难译难懂,“曲牌”就更加难记,遑论理解了。但是,元杂剧是歌、舞、诗、白的综合艺术,曲牌和唱词恰是元杂剧作为戏曲的明显标志。没有这个标志,元杂剧就成了欧洲“话剧”了。而我们从《赵氏孤儿》曲牌的深度窥视中,发现《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一样也具有“文化间性”的特征。比如,为救孤儿不惜献出身家性命的公孙杵臼就有一段《梁州第七》的唱段:“他,他,他在元帅府扬威也那耀勇,我,我,我在太平庄罢职归农,再休想鹓班豹尾相随从。他如今官高一品,位极三公,户封八县,禄享千钟,见不平处有眼如蒙,听咒骂处有耳如聋。他,他,他只把那好谄谀的着列鼎重裀,害忠良的便加官请俸,耗国家的都续爵论功。他,他,他只贪着目前受用,全不省爬得高来可也摔得来重,怎如俺守田园学耕种,早跳出伤人饿虎丛,倒大来从容。”除了《梁州第七》,《赵氏孤儿》还有《菩萨梁州》《小梁州》的曲牌。王国维在《唐宋大曲考》里指出:“梁州亦作凉州。洪迈云: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这些曲牌又与佛教音乐、与西域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年在法国演出时的雕版画像
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在公元前后就已传入新疆,经由新疆传入内地。这是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途径应是由印度传入东南亚再传中国南方。(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佛本生故事》为泰国多部舞剧提供了素材,显然应是通过这一途径。)佛教发源于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是佛教流传地,也是梵剧重要诞生地。这里与和田毗邻,历史上就有来往。和田古代曾有“瞿萨旦那”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印度语“地乳”的意思。印度辛哈·班纳吉所著《印度通史》载:“迦腻色迦帝国(贵霜王朝国王,约2世纪初叶—引者注)包括了阿富汗、大夏、喀什噶尔、和田和莎车。”所以和田是新疆最早接受大乘佛教的,以后才传到了疏勒、龟兹(库车)等地。
佛教的传播是借助于艺术形式的。黑格尔曾说:“意识的感性形式对于人类是最早的,所以较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133页)他又说:“宗教却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真理,或者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分服务。”(同上,130页)佛教也是这样。在新疆,它要建佛寺,建石窟,要在里面雕大佛,绘壁画。另一重要传播方式就是由高僧大德向信众、准信众们宣讲佛教教义,宣讲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这种宣讲,已不是单纯地讲翻译的佛教经典,而是经过了法师们的加工创造,把艰涩的佛教经典、佛本生故事演绎成信众容易接受的“变文”的形式了。法师们也不是枯燥地讲述这些“变文”,他要用一定的语调讲说散文故事,还要用韵文把散文内容再唱一遍。开讲之前和讲唱中间,有乐队演奏佛曲,两旁还有帮唱的。这些音乐,原本全是印度的,当用来演唱翻译过来的唱词的时候,就套不上了,必须有所改变,而为了使新疆人、中原人爱听,就自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音乐元素,这样的音乐,就叫“梵呗(bai)”这种韵散相间叙述长篇故事的形式、说唱相间的表演形式,在我国文学史、艺术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推动了我国讲唱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戏曲文学的形成。
唐代的寺院里有很多知名的俗讲的讲唱者,比如长安右街的僧人文溆子就是其中之一。唐敬宗(825—826)都去兴福寺听他俗讲,“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依其所唱改编的乐曲《文溆子》,传至宋代成为诸宫调和地方戏曲音乐曲牌之一。
这种俗讲、变文的形式,除了讲佛教故事,后来在民间也有了非佛教的题材,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促进了唐代传奇文的兴起。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聂隐娘》《柳毅》《霍小玉传》等,后来也都被改编为戏曲剧目。
伴随着佛教传入新疆,印度的音乐舞蹈也传入了新疆。印度音乐舞蹈是很丰富的,这从今天印度的电影、电视剧就能看出来。唐朝时传入新疆、传入内地的音乐大曲《天竺乐》,就是来自印度。《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前凉张重华据凉州时(346-353),就有天竺男伎来我国。其后,天竺国王子以出家人身份来我国游历,传入了《天竺乐》。唐代时候,该乐部有歌曲《沙石疆》、舞曲《天曲》。演出用的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筚篥、横笛、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等。乐工12人,着乌丝布头巾白上衣、紫绫裤、绯帔。舞伎2人,辫发,身穿朝霞袈裟,缠裹腿,着碧麻鞋。《隋书》《通典》对《天竺乐》也有记载。可见,他们在南北朝,在隋唐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乐器,也留在了我国,经过漫长时间的艺术实践,在适应我国民族乐曲和民族乐人的弹奏中,也发生了种种的变异和改造,但其影响依然存在着。比如印度五弦琵琶,在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都必不可少。在库车克孜尔石窟第8窟中就有两组弹奏五弦琵琶的飞天,风姿绰约,令人驻足流连。唐朝诗人韦应物、白居易的诗作里,都有对五弦琵琶、对琵琶演奏的描写。如“古刀幽磐初相触,千珠惯断落寒玉。”如“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在现今,琵琶已被视为我们的民族乐器了,在戏曲剧团乐队里,在民族乐团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乐器。
“五旦七声”理论是通过龟兹乐队的苏祗婆传入内地的。时间是在公元568年。这一年,突厥阿史那公主嫁北周武帝,从突厥王庭来到长安。西域诸国也来祝贺,来时都带着本国最好的乐舞,《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今布哈拉一带)、《康国乐》(今撒马尔罕一带)等再一次东传长安,苏祗婆也随着龟兹乐队来到长安。苏祗婆出身于音乐世家,“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他家学深厚,是琵琶高手、龟兹的著名音乐大师。到了长安以后,应中原艺人邀请,苏祗婆在长安倾情教授、传播龟兹乐舞,引起极大反响,“举世争相慕尚。”这期间,他讲授了西域流行的“五旦七声”音乐理论。并且在他的琵琶上找到了这七声,用这七声勘校中原流行的七声,冥若合符。解决了当时中原地区争讼不已的难题。因为从公元220年曹丕篡夺东汉政权,魏、蜀、吴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到581年隋朝立国,360多年里,中原一直战乱,礼崩乐坏,山河失色。隋朝建立以后,急于恢复礼制,重整雅乐。但是,锣齐鼓不齐,老乐师们死的死,散的散,“七声”总是搞不对。苏祗婆解决了这个难题。五旦七声的乐制,意思是有七声音阶,使用多种调式,“旦”即中原的“均”,现代术语叫音列,就是一个调式由七声音阶组成。“五旦”就是五个调式。应用多种调式,标志着音乐的发达。因而才带来中原乐律、乐制的变革。这七声是:一曰娑陀力,即宫声。二曰鸡识,即商声。三曰沙识,即角声。四曰沙侯加滥,即变徵声。五曰沙腊,即徵声。六曰般赡,即羽声。七曰俟利箑(sha),即变宫声。隋代柱国、相府长史、音乐家郑译(540—591)用五旦七声校勘雅乐,幷以七调与十二律相乘,推演出八十四调,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汉族的传统乐律理论,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那么,“七声”理论源自哪里呢?可能来自印度。在玄奘《大唐西域记》里,他曾记下沿途各地的见闻。和田“国尚乐音,人好歌舞。”“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龟兹是“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就是说,龟兹使用的是梵文,稍有改变。如果要学经教律仪的话,只能从梵文学。“苏祗婆”这三个字,也是梵文的音译。“七声”的名字也是借用的梵文。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是629年到645年,如果上推60多年到568年或者更早——苏祗婆父亲的时候,可以想象也是这种状况。龟兹又是“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那么它的“管弦伎乐”与印度有很大关系这是可能的。这个音乐变革的重大意义也受到了现代戏曲史家们的关注和肯定。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评论说:“自从南北朝以来边疆各族入居中原,也就带来了丰富的音乐财富,这给原来汉族的音乐传统也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首先在乐律的运用上引起很大的变化,从苏祗婆的琵琶八十四调理论的形成,到燕乐二十八调的实际运用,这一系列关于宫调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戏曲唱腔的结构规律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后世戏曲唱腔中的‘宫调’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其次在乐曲形式上有了很多创造,如‘大曲’,各种舞曲和歌曲,这些曲调对后世的戏曲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曲调后来经过若干变化就成了戏曲曲调中的组成部分。”这个评价也是对龟兹音乐的很高评价。龟兹音乐不愧是西域乐舞的优秀代表,它为中华民族奉献的不仅有优秀的艺术作品,还有杰出的音乐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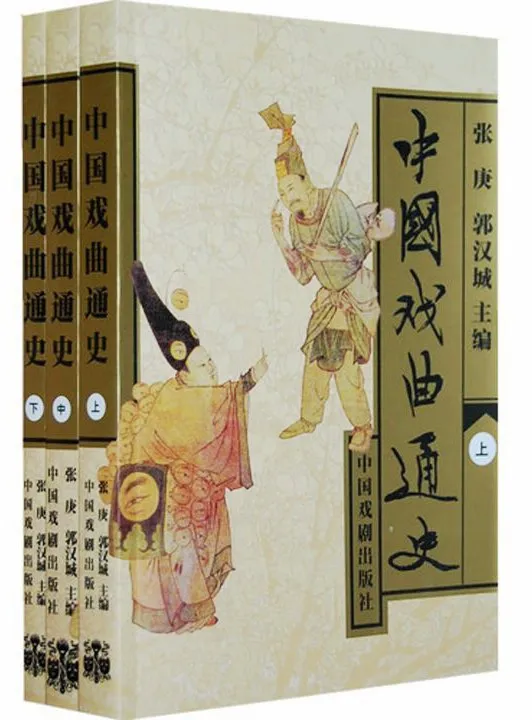
《中国戏曲通史》在高度肯定五旦七声理论对中国戏曲唱腔结构规律形成的贡献的同时,它还指出,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丰富的音乐财富使中原音乐“在乐曲形式上有了很多创造,如‘大曲’,各种舞曲和歌曲,这些曲调对后世的戏曲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有许多曲调后来经过若干变化就成了戏曲曲调中的组成部分。”如果查一下历代戏曲曲牌,的确可以看到这种蛛丝马迹。“大曲”是指曲式结构庞大的乐舞而言。最早的大曲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摩诃兜勒”即大曲之意。唐代大曲为数颇多,一直传到宋朝。王国维在《唐宋大曲考》里说:“大曲之名,虽见于沈约《宋书》,然赵宋大曲,实出于唐大曲;而唐大曲以《伊州》《凉州》诸曲为始,实皆自遍地来也。”《稗史汇编》一一四卷也说:“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凡此诸曲,惟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唐宋大曲除了以州名者,还有很多。大曲的结构,说法不一。因为大曲的确是包含了多种结构的乐曲形式。一般认为,它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序奏,无歌,不舞,由乐器独奏和合奏,称散序。第二段以歌为主,乐器伴奏,称中序或拍序。中间穿插的器乐间奏曲称为“趋。”第三段歌舞并作,以舞为主,节拍急促。这种结构也可叫艳、趋、乱式大曲,例如《霓裳羽衣舞》《春莺啭》。十二木卡姆的琼乃额曼,与这种结构很相似。琼即大,“乃额曼”即“曲调、乐曲。”除了这种结构形式,关也维在《唐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还归纳了联曲式大曲,它是合尾式的、变奏性的。比如《移都师》。《移都师》是6世纪突厥初入新疆时的“玉都斯”,在现在库车和焉耆之间。它的地方音乐传到了长安。天宝十三年(754)宫廷将音译的外国、外族乐舞名称统一改成汉名,把《移都师》改成了《大都仙》。它的音乐是龟兹乐和突厥音乐融合而成的大曲。它的第九段是宫廷迎送宾客的音乐,后来吸收到京剧唢呐的曲牌中,用作出将入相的音乐。还有混合式大曲,如《武媚娘》,它既非完全艳、趋、乱式的结构,又有联曲式大曲尾句相同的特征。
作为燕乐的大曲,人们最为熟知的是《霓裳羽衣曲》了。它是唐玄宗参照和改编了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婆罗门曲》而成。在曲中描写了开元天子与月宫仙女相会的故事。从其由《婆罗门曲》改编而来,可知《霓裳羽衣曲》中包含有印度音乐的成分。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也完整地描述了乐曲节奏的特点。它也是舞蹈。虽然杨贵妃的舞姿无从得见,但是白乐天“虹裳霞披步摇冠”的诗句却令我们抚诗悬想,而类似的舞蹈在戏曲舞台上目不暇接。此外,还有《甘州》《浑脱》《柘枝》《胡旋》《胡腾》等等的健舞的舞曲,还有些比较柔曼的软舞的舞曲,如《六幺》(绿腰)、《春莺啭》《伊州》等。《伊州》即今哈密地区,因为该地唐代受北庭都护府辖制,又称《北庭伊州》。它的舞蹈结构是先有散板起舞,然后中板,舞蹈四遍,边歌边舞,结束在五遍快板节奏中。
隋唐九部乐、十部乐的西域乐舞都是歌、舞、乐一体的大型套曲,它们也是由隋唐相沿至宋的“大曲”的组成部分。包括天竺乐、疏勒乐、龟兹乐、于阗乐、安国乐、康国乐、伊州乐、西凉乐等。所以综合来看,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大曲是非常丰富的,它们本身就包括了歌曲、乐曲、舞曲,包括了歌唱、器乐演奏、歌舞戏,还包括大量的舞蹈。这些艺术形式都对中原戏曲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各民族的民间小调、俗曲、民歌的传入,也满足了中原一般群众对异曲新声的好奇和喜爱。群众的艺术欣赏,总有求新、求变、求奇的心理。各民族的民歌小调迎合了这种需求,被吸收到戏曲音乐之中。这很像王洛宾改编的新疆、青海风格的歌曲,很受内地欢迎,在各种音乐会上都可以听到。有书记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京师的街巷民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士大夫们也都在学。《六国朝》曲,后来成为元杂剧的曲牌。
这些大曲,这些乐曲、舞曲被吸收为戏曲音乐是要有“若干变化”的。但是它的根在,音乐的元素、基因在。戏曲当中是少不了音乐舞蹈的。中原戏曲的音乐舞蹈当然离不开中原本土的音乐舞蹈,但是各民族的、西域的音乐舞蹈又丰富了、充实了内地的音乐舞蹈。而在它被纳入戏曲艺术当中的时候,它又经过了若干的改变。因为戏曲与歌舞是两种艺术形式。歌舞音乐也有叙事,但主要还是抒情的、情绪性的。戏曲音乐也有叙事和抒情,重点在于它是为人物的急剧变化的情感服务。所以,西域大曲以及歌曲、乐曲、舞曲,为了适应内地人们的喜好,是需要有所变化的;当它转而作为讲唱形式和戏曲形式时,就要再作变化。
唐宋大曲的特点是相同宫调的多曲联缀,同一宫调和同一曲调反复演唱,次序固定,唱词固定,这就难免缺少变化,枯燥乏味。大曲偏重情绪的宣泄,这就难于演唱有头有尾的故事和不断变化的人物情绪。民间杂曲又过于短小,也解决不了这个困难。而在俗讲、变文发达之后,人们既想听故事,又要求满足比俗讲、变文更高的听觉、视觉的欣赏需要。这就产生了诸宫调。诸宫调继承了大曲曲调丰富的长处,同时又将各种音乐、唱腔按照声律高低归入不同的宫调。演唱时,根据情节、人物的需要,选用不同的宫调。同一宫调的若干曲调组成一套,若干套不同宫调的曲子共同完成一个曲目的演唱。它的情节更复杂,人物更丰富,描写更细腻,乐曲结构更精密和严谨。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每个唱段唱完后有简短说白,以便另起宫调接唱下个曲子。它打破了唱词五、七言的限制,可长可短,比较灵活。它的唱腔组合也较自由,可以单曲演唱,也可以双曲演唱,或者组成同一宫调的套曲演唱。
据说诸宫调书目有22种,最完整最有价值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董解元是金章宗(1189—1208)时人。姓董,是乡试第一名,其他信息就不知了。他的诸宫调《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独特的作用。从讲唱文学来说,他把俗讲这种外来形式,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新高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完整的说唱文学作品,后世各类讲唱曲艺形式都从它汲取了无尽的教益。从中国戏剧史来说,它在俗讲和戏剧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为元杂剧的巅峰之作王实甫的《西厢记》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王《西厢》正是在董《西厢》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从西域乐舞来说,董《西厢》大量保留、融合、吸收了西域大曲、乐曲、歌曲、舞曲,扩充了中原地区原有的曲牌曲调,为后来元杂剧的唱腔音乐、过门、间奏曲提供了宝贵音乐素材。我们看到,董《西厢》的曲调,采用了般涉调的柘枝令、苏幕遮,正宫调的文序子、文溆子缠、梁州缠令、凉州三台、凉州断送,仙吕调的六幺令、六幺实催、六幺遍,大石调的伊州衮、伊州缠令,中律调的古轮台等。王国维《唐宋大曲考》云“衮则当就拍言之。”“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在元杂剧里,也很容易看到《六幺序》《小梁州》《梁州第七》的曲牌名字。它们的根源其实都在西域乐曲,虽然其旋律已多经变异。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本文的开头:元杂剧《赵氏孤儿》的音乐曲牌《梁州第七》《小梁州》等,都是东西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扩而大之,元杂剧中的许多音乐曲牌、艺术元素也都是在中原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博大的胸怀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艺术元素从而达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这是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的赐予,是不同的文化艺术通过平等、互动和相互尊重结出的丰硕果实。今天,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引领下,当我们在新时代、新高度上重构21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我们相信,只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创造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本文图片由周建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