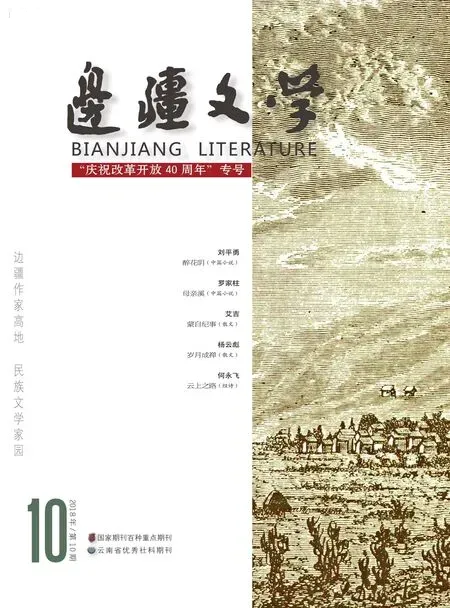八奶的鸽群
安 庆
一
村里人说起八奶就会说到她的鸽群,更津津乐道的是八奶和男人的荤事,八爷的死亡或失踪。如果不是八爷失踪或者死亡,那些男人就没有觊觎八奶的机会。
关于八爷,他们说到一个叫莲的女人,莲就住在火车站西边的兰村。八爷频繁地往车站跑时,八奶还蒙在鼓里,当八奶闻到风声,八爷已经给莲打起了伙计,挣来的钱和粮食一半都给了莲。村里人说,八爷就是这时候去充了壮丁,那一年壮丁的名额轮到了老塘南街的田大户家,田大户放出了诱人的价码,八爷用壮丁的身价换来了几亩薄地和八石粮食,以及一些银票。
八爷一走却杳如黄鹤,让八奶也成了寡妇。
八奶找过莲,莲没让她进屋,莲的屋里已经躺上另一个男人。八奶高大的身架站在莲的面前,和八奶相比,莲显得瘦小单薄,剪短的头发像草一样拂动。她发憷地看一眼八奶,后退几步,扶住了一棵椿树。八奶玉树临风,挥了挥长臂,你逼走了我的男人?莲说,我没那个本事!八奶说,你让他去用命换钱?叫莲的女人说那是他自己的事,这个年月没有比替人充壮丁挣钱更多。八奶说,你就逼我的男人?莲的另一只手又扶住了椿树,椿树上落下几片叶子,院子里的椿树让她想到脚下是她自己的院子,话里增加了一些硬气,你怎么能这样说,我能挡得住一个男人?八奶没有软下去,朝椿树走近几步,一片树叶落在了她的鞋尖上,问莲,去找过他吗?莲说,没有,去哪里找,他已经死了。八奶忽然泪如雨下,一把拽住了对方的前襟,你怎么能这样说,寡妇真是心狠。莲挣脱着八奶,说话不得不伸长了脖子,她的脖子又细又长,还算秀气,嘴朝天上嘟着,说,他不回来,不是死了又是怎样?兵荒马乱的打仗死了多少人。八奶拽着她的手又抖了抖,女人的脚踮起来,脸上出现了胀红,八奶另一只手揪住女人的头发,一只脚踩在莲的脚上,可你拿什么证实?莲喘着气,头抵在椿树上,两坨屁股朝上鼓,几声咳嗽从细小的喉咙里咔出,说话声断断续续,我,我不用证实,你,你自个的男人,自个找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奶奶想象男人最后为家里挣来的几亩薄地,换来的粮食一半留给了她和儿子,临走前和她们母子守在一起。八奶坚信,这个男人还有良心,和那个女人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
八奶在地里搭起了窝棚,白天黑夜地守在地里,她相信男人如果从部队里逃出来,一定会来看看他用命换回的土地。不断有挎枪的兵从东边的大路上走过,从东南的渡口坐船到对岸上去,也会听到零星的枪声。她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但知道兵也都有家,如果八爷从这里过,即使家不能回,也会跑到地里看看,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地里站上一会儿。那时候是深秋,过了霜降,小麦苗从地里拱了出来,干冷的小风一阵又一阵地刮起,枯黄的树叶和草梗顺着风在地垄里出出溜溜地攒动,天往冷里走。八奶砍来了树枝和干草加固了草棚,晚上睡觉再用一捆干草堵在门口,风挡在了门外,棚子里暖和一些。八奶睡得很迟,她在地头的路上走来走去,不远处就是老运河,还偶尔有船过去,抓鱼的鹰船从河上游一直往下游漂流,舢舨上的船主带着几只老鹰,老鹰听他的浆声钻进水里,在下游露出头时,叨着一条草鱼。八奶小时候就看老鹰船,鹰船还一直从河上过。她和八爷十八岁成的亲,十年了,儿子已经八岁。她和八爷看过鹰船,八爷扑通跳进水里,一直跟着鹰船过了马营桥才爬上岸,顺河滩跑回来,身上的水还没有抖干,八爷手里抓了两条鱼,鹰船上的人送给他的。那时候八奶有了身子,八爷让八奶炖鱼汤喝。八奶每天都想着离开她的八爷,想着八爷的好,想着这地可能和一个大活人的命有关,想着想着就又去了运河边,坐在河岸上发呆。她去算过卦,给八爷算,八爷的生辰八字她熟记着。算卦人姓魏是个瞎子,在宋村。她从马营坐船到宋村,魏瞎子坐在院里的枣树下,枣树上的叶子掉光了,树皮厚厚的,翘着皮块。她坐在魏瞎对过的一方石头上,对魏瞎报了八爷的八字。魏瞎的指头在嘴上沾了沾,仿佛要用指头翻动书页,其实什么也看不见。瞎子说,我知道你算什么。八奶不说了,等魏瞎子说。魏瞎子说,如果一春一秋回不来,怕就难了。八奶听出来了,如果一年不见人影,凶多吉少。八奶嗯了一声,他在哪儿?魏瞎说,西南。远不远?魏瞎说,不远,也不近。八奶说,那我等着!魏瞎不说话,听她的脚步快走出院子时,又迸出一句,红颜薄命。八奶扭过身,顿住脚,魏瞎说,你是个美胚子。八奶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她凭着信念,一直等着八爷,傍晚的时候去看河,就又想起老鹰船,又看见八爷的身子。
在地里守了一个秋天又一个春,夏天来了,麦子到了收季。村里的几个男人过来帮忙,八奶给帮忙的男人做饭吃,也打些零酒,活干完了,她把男人早早地往家撵。男人说,八嫂子,夜里不害怕吗?八奶说,快滚。男人说,不用给你暖身子?八奶掂起木杈,男人们带着酒气悻悻地离开。
这年冬天,八奶搬回了村里,搬回她的小土楼。八奶回到小楼的那天是一个月的初一,八奶在案上烧香,叨念,对着燃起的香烛说,看来,我得出去找一找,不找这个冤家,他不会回来。我要告诉他,兰村的疯女人随后就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
二
我想象不出那些鸽子怎么形成了庞大的鸟群,为什么会集结着朝八奶的楼上飞,悠扬的鸽哨那样诱人,那么多鸽子是有一个鸽子王,还是八奶就是鸽子的王,一定藏着什么秘密。八奶像一个神,夏天穿一套白色的衣裤,旧年的粗布,纯朴,干净,耐穿,犹如她衰老仍显姿色的皮肤,她站在楼上像一尊雕像,从来不管楼下遥望她的男人。她闻到了从村外飘来的庄稼的气息,土地的潮气,各种复杂的气味卷入村西的老沧河,混杂着野兔、野狗、牲畜交媾和死亡的气息,往下游漂流,流过很多村庄,汇入更宽的河。她的目光越过村庄,听见了火车哐哐啷啷的奔跑,火车停下来的喘气,那是八爷花心开始的地方,也是八爷离开她的地方。她在那里等过火车,想等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佝着腰回来,抓住他的手,拉着她回家。可是,很多年过去,她的等待成为虚妄。之后,她每天登上楼顶,她的期望变成一种固定的姿态。每天,看着楼顶的羽毛,她俯下身,捡起一枝,走下楼梯,插入床头的陶罐。床头已经飘满了羽毛,成为羽毛的湖。
我后来常常遥望八奶的楼顶。
我真正听到八奶的故事已是成年,村里的男人聊起女人对身边的我已经没有顾忌。最初听到他们聊到八奶是在地头的干沟,我和大人们在一起等待浇地,躺在沟里避风,麦子在地里伏动,小北风刮着路上的干柴。这一水叫封冻水,为了防止小麦被更冷的温度冻着,所以要在地里积攒墒气。我刚毕业回到村里,弄不懂麦田管理的道道,懵懂着防止小麦受冻还要浇那凉哗哗的水,小麦不是更要冻着吗?我看着满地的麦苗,对大人的话表示怀疑。一个技术员教育我,水是增加地暖的,小麦不但不会挨冻,麦根还会达到保护。我半信半疑,后来我拿了一本技术员的书看,才算信服了这个理由。等待浇地的时间是无聊的,要从地的一头往另一头浇,一块地里有好几家,后边的人要提前守在地里。我在地沟里听到他们聊到八奶,他们说起八奶的风流韵事,说到八奶寻找八爷,说到八奶的鸽子,八奶的鸽群。他们说到八奶的身体,八奶的奶子,说八奶经历过八个男人,我想这是他们凑数,为什么八奶恰恰会经历过八个男人,难道这也有一种巧合?他们说这八个男人都陪八奶出去寻过八爷,但八奶没有答应过任何男人,对每个陪他出去的男人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无法嫁给任何的男人。八奶对帮她的男人的回报,就是陪他睡上一觉,那一夜之后,彻底了断,谁也别再纠缠。后来的这么多年八奶不再出去寻找,但一天天都要爬上她的楼顶。
他们说到的男人我不感兴趣,况且八个男人中几乎一半不在老塘南街,另外四个才是我们老塘南街的男人。他们都太老了,我对不上号。我不关心八奶的风流韵事,我只关心八奶和她的鸽群。我听到八奶的故事时她已经60多岁,八奶被村里人称为疯婆子,她每天拄着拐杖出现在村口,出现在她家的地头,最后固定在她家的楼顶。八奶上楼的身影更加固定,也更加孤独。有一天,我看见八奶的手里握着一枝白花和一卷草纸,村里的又一个老头不在了,据说是八个人中的一个,她蹒跚地走过大街,朝着摆满花圈、响着唢呐的地方,走向一个人的灵堂,为一个老人燃上一卷纸钱。
我真正注意八奶的鸽群就是从这时开始。那些时光里,我在村子里有一种彷徨,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找不到方向,夜深的时候会在村子里游荡。我站在八奶的楼下,鸽子在夜色里咕咕地低叫,羽毛从风中飘下,落在我的胸前。一天傍晚,那是八奶固定站在楼顶的时辰,我在一棵椿树下看见一个老人,他满脸胡茬,头发花白,头枕在树杆上,目光
静静地朝着楼顶,我甚至听见他吧唧着嘴,在低低地诉说。我不敢更近地靠近他,怕惊动老人,我选择了一个既能看见八奶又能观察这个老人的地方。八奶的小楼墙体斑驳,土坯裸露,在裸露的土坯间隙住着很多的麻雀,和楼顶的鸽子遥相呼应。我听见了鸽子在楼顶的飞翔,八奶的白发在风中悠荡,大地和村庄的气息氤氲上升,围溢着小楼。我感到了岁月的流淌,黄昏越来越深,八奶的手边落满了鸽子。又一轮的守望和遥望即将谢幕,椿树边的老人艰难地站直了身子。

1998年10月《边疆文学》封面
又一个黄昏,我将他从树边扶起来。那个夜晚我走进了他的胡同。
老人叫张大化。
打开一个老人的话闸需要耐心。当我走进胡同里的小屋,我已经感受到老人的孤寂。我观察过他的胡同,一个小院,瓦房上长满了瓦松,瓦缝里挤出苔藓。我看见了他挂在墙头的板胡,后来我听过他几次弹奏,地方戏的曲调从老胡同里悠悠地溢出,拐过狭窄的胡同,在村庄的缝隙里流动,不能说拉得多好,但是一个老人的生活。那天晚上把张大化送进院子,我返身回到大街。我在一家小铺子里买了二斤猪头肉,一斤大肠,一份卤豆腐,在小卖部里掂了一瓶我们当地产的白酒。我恭敬地把酒放在他每天吃饭的小木头桌上,张大化捋捋胡子,瞪着我孝敬的酒菜,他找来了几个碗,将菜放进碗里,用来喝酒的两个小黑碗,有了一定的年代。他目光辣辣地看着我,像《射雕英雄传》里那个疯子,小子,你要陪我喝酒么?我犹豫了一下,端起了面前的一个黑碗,黑碗里映着一个乡下穷小子黧黑的脸颊,我说,听你老的。我第一次喝那么多白酒,每次朝两只小碗里倒过酒后,泛出的泡沫马上消融,白酒在黑碗里看不出具体的颜色,只看见粗瓷的碗底。我听见咕嘟咕嘟地喝酒声,他不说话也不问我。一瓶酒快见底时,我起身再去买酒,他拽住我,喷着酒气,说,小子,你要爷给你讲啥?我站起来才知道自己喝多了,头晕目眩,一瓶酒差不多和他平分了。我原来最多喝过二两白酒,可见不同的场合人的承受是不一样的。我晕晕乎乎重新坐下,头倚在身后一个破柜上。张大化还在顾自地喝,呱叽呱叽地吞咽着猪头肉和猪大肠,我说,张爷,我想听您说一说八奶,给我说说八奶吧……
我晕晕乎乎睡着了。我醒来时躺在一把老藤椅上,张大化坐在他的床边抽旱烟,那烟一窝一窝地在小屋里卷,绕着梁头,我以为我在雾里,我听见胡同里有风吹着树叶,远处的公鸡开始打鸣。
张大化说,给你说一说那匹马吧。他满脸的胡须在夜色里拌动,皱纹带动他脸上的肌肉。他说,那时候我是队里的饲养员,喂着队里的几十头牲口,夜里头和牲口朝一个地儿撒尿。那一年吧,我喂饱了牲口就想来楼下站一会儿,想看到八奶,你八奶这个骚货她很孤傲,对村里的男人其实待理不理,我们都叫她女魔头。有一天她终于找我,哈哈,这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像一个神仙,她看中了我喂的牲口。那时候牲口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也最自由,不像现在的车不加油就跑不动,牲口不那么娇嫩,路边的野草可以把它喂饱,沟里的水让它解渴,吃了草喝了水照样扬蹄子奔跑。你八奶看透了我手中的这点权力,她知道我在楼下看她,这个狡猾的女人利用我对她的爱慕,把我震住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她对我说,张大化,我要出去找我的男人,死要见尸,活要见人。其实,我知道她是去找你八爷的尸骨,只能这样了,早在打仗的时候就传来了你八爷被活埋的消息,活埋,你知道吗?你八爷到了部队,一天黑夜从部队里逃跑,可跑了半夜又跑回去了,跑到了原处,山路把他迷住了,部队里点人数发现少了你八爷,正在找他,他自投罗网,杀鸡给猴看,你八爷就被活埋了。这个消息是柳堡一个老乡带回来的,那个老乡多年前死去了。我对自己说不能软蛋,犯一次错搭了一条小命也要跟你八奶出去,毬,天天蹴在老塘南街也没意思,谁要咱管着几十头牲口。我就头一扬答应了。第二天凌晨我套上了队里的一匹枣红马,拉着你八奶出发,委托我哥替我喂几天牲口。
张大化掂起酒瓶喝掉了酒根,继续说,那一趟,我拉着这个女人跑了八天,哈哈,八天啊,小子。山里的路不好走,难走的路我下来牵着马的笼头,有些路是你八奶走过的,她来山里找过老八好几次,她只是不服还在找,山里头多见石头少见人,找一个人埋葬的地方哪有那么容易,战乱的时候有什么墓葬,早沤烂了。你八奶在山里打听,在山里喊着老八,老八,你倒是给我托梦,你好跟我回去。有一次我赶着马车,一群大鸟呼啦啦飞来,哎呀,那些野鸟把马惊着了,马在山路上奔跑,惊缰了。我和你八奶都吓坏了,怎么也收不住马缰,我想这下完了,能和这个女人死一块儿了,也算缘份。好在马终于收住了,马车撞在了一个石头上,拉不动了。马咴咴地叫,耸着耳朵,尾巴撅着,牙露出来。我对你八奶说,回吧,回去吧。你八奶说有一个方向还没去过,再去那个地方找找。我又收拾了马车,盘着山路去了山的又一边,谁知又遇见了一群山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那些鸟,那些鸟也是穷疯了,呼啦啦朝我们飞过来,叫得瘆人。马又惊了,又疯狂地跑,跑着跑着跑到了一个山崖边,和那边的山路横着一个山口,我大声喊叫,挤上眼,这一次真完了,要和老八都葬在山里了。你猜怎么着,马飞了起来,马的整个身体朝天上飞,它浑身的骨头咯咯吱吱地响,它带动着马车,我和你八奶紧紧抓住马车,拽住马的尾巴,马竟然飞过了山崖,哎呀,又一次有惊无险。你八奶真害怕了,回到家,我的被子早夹回了家里,饲养员干不成了。
张大化带我去了另一间小屋,院子的另一头养着一头黑驴。张大化说,这头驴我一直喂着,如果你八奶需要,我随时跟她出去。
三
我在一段时间里不断出现在那个胡同,每次去,都掂一瓶白酒和一斤猪头肉,一盘猪大肠。我曾经给他买过一次鸡腿,他啃得吃力,鸡肉不断塞进的牙缝,以后我就放弃了再给他买鸡腿,专买这种没有筋的猪头肉配酒。他吧唧吧唧吃得津津有味,喝完一碗白酒像喝完一碗粘稠的玉米粥,那一次我喝醉后他不再逼着我喝,叫我量力而行。张大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老人,他每次喝到半熏话闸子才会打开,才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有的人就是这样,打开他的嘴需要一个闸刀。张大化说,八个人,那是他们胡诌,实际上跟她出去过的不过三四个吧,我之前一个,我之后恐怕也就没有人了。八奶这个人,说起来也是个情种,对你八爷忠诚,你八爷走时不到30岁,几十年你八奶就这么熬着,熬成了一头白毛,让对她有心的人失望。张大化滋了一口酒,酒含在嘴里,咀嚼后才咽下。他好像触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又抬起小黑碗,你八奶这个人怎么说呢?让人失望,猜不透她的心思,几十年傻等,把自己几十年的好光景毁了。我之前的那个人是陪你八奶去塔岗车站,这老女人有一阵子天天跑到车站上等火车,坐在站台上,火车呼呼地从她的身边飞过,停下来的火车让她一次次绝望。那个人每天赶驴车去车站接她回来,一直到你八奶不再去坐站台。还有一个人,是陪她去的彰德,你八奶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她是你八爷一次从彰德把她带回来的;你八爷那时候跑火车、装车皮、押车皮,也捣腾点小生意,有一次在彰德的火车站,在铁路旁把你八奶带了回来,你八奶就成了咱老塘南街的人。你八奶去彰德站,那个人陪着你八奶,陪她坐在站台上,还不能坐那么近,隔十几米二十米的距离。张大化说,这两个男人现在都不在了……
那个女人呢?和八爷好过的那个女人?早不在了。张大化说。
四
当你真正走近八奶时,发现八奶真的漂亮,八十岁的人,风韵犹存。无情的岁月让她裹满了沧桑,许是几十年的孤独和遥望让她更有了这样的气韵。
我潜入了八奶的老屋。我是说我钻进了八奶的阁楼,对于这样的行动我谋划了很久,整个大半年我都在用一种心思,我每天都在寻找潜入八奶阁楼的机会,寻觅着潜入的方式。我像张大化一样在楼下找到了一个仰望的角度,我每天像一个看戏的人一样等待着主角的出场,我会看见一个老人从阁楼里拱出来,慢慢地出现在楼顶。我想说八奶的拐杖只是一种摆设,她上楼时从来不用拐杖,很简单地就打开了最上边的楼门,闭着眼就打开了一把老锁。在楼门打开的瞬间阳光迅速地钻进阁楼,灰尘和阳光混成一个整体像一个银色的滚球,阁楼在霎那间明亮,楼门的门搭还在当啷啷响动,一串门环悠远而且古老,像吊在楼顶的项链。八奶迅速地穿过楼上的尘埃,穿过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等待她的鸽群,咕咕地叫声淹没了她的脚踝,八奶像一个旗帜站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那里有一个人豁口,恰好卡住八奶的胸脯。她的手边落上了大约七八只白鸽,八奶朝远处望去,穿过街道,穿过街道上的树,看见了村西的老沧河,看见了石板的老桥,水从老桥下慢慢地流过,河还是老样子,很多的黄昏八奶从村里一步一步走到沧河桥,从桥东走到桥西。有时候她会沿着桥西的路再往前走,走到了双水村的村头,她失望地往回返,又是一个无望而归的日子。她高大的身影在夕阳的淡薄中渐渐缩小,她会在沧河桥等到天黑,在庄稼的影绰中返回小楼,然后她看见了插在床头的羽毛,那几只陶罐,又是一个日子的结束。后来她不再去沧河桥,每天固定地站在楼顶,站在能卡住她胸脯的豁口。她的目光在夕阳中从沧河桥,从满地庄稼,从庄稼间的道路上收回,看到的是越来越破旧的村庄。她想起她看到的那些男人,男人遥望的目光,男人在楼下疯狂的叫喊。她的头发愈加地白了,她偶然从水缸里看到过自己的样子,像《白毛女》里的白发女人。她看到过张大化,她在楼上骂过,这个傻瓜。
我越发地对小楼充满了向往,我想上到楼顶去看那些鸽子,我每天看到的只是鸽子遥远的身影,只是它们在天空飞,我想更亲近地看到鸽子,看到八奶的世界。我就是在这种欲望和强迫下开始寻找着走上楼顶的方式,我终于在一个夜晚钻进了八奶的阁楼,那个阁楼上的窗门,恰好容进了我瘦小的身子。我趁的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候八奶大概已经睡了,一个老人她不会睡得太晚。我撬开了阁楼的窗门,我侧着身朝里边钻,我不敢弄出响动,我像一只老鼠一样,吸着肚子,一点一点地挤着身子,我终于挤进了阁楼,可我还是在踩上楼板时发出了响动,虽然我脱掉了鞋,只穿了棉袜,可那种响动对我来说还是意外地惊心动魄,我在几分钟内惊魂未定,不敢再有任何的动静。我出着气,从小门射进来一缕夜色,秋天的凉气也从小门里钻进来。我缩着身子,想象着我怎样才能钻上楼顶,看见夜晚里栖息的鸽子,看到八奶每天占领的那个世界。楼顶就像八奶的一个高地,我常常想她就是一个将军。
我把窗门轻轻地合上,谢天谢地,这一次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动。我格外地小心翼翼,我在关上窗门时打开了带来的一只手电筒,为了防止碰掉,我在腰带上系了个绳子。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我惊呆了,我原来想象的阁楼上的空旷被一种景象击碎,我看到了一个世界,我在打开电筒的瞬间以为我误入了一个小树林,我的眼前影影绰绰,仿佛站着很多树或很多人。我又一次惊魂未定,我得喘口气,冷静一下,我在喘气冷静之后,这一次看清了,那是几十件衣裳,有冬天、有夏天的衣裳,它们挂在阁楼上几根悬挂的竹竿上。当我再细看时,看到的都是男人的衣裳,色彩大都是白色、蓝色和黑色,分别代表了一年中的几个季节。在我又近前看时,我在手电筒的光柱中看到了在靠近墙边的竹竿上搭着几十双粗布的袜子,甚至还有十几个吸旱烟用的荷包。我惊讶了,我就是竭尽想象也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衣裳,这种场景。无需多问,这是一个女人为男人始终准备的,可那个男人一直没有回来。
我忘记了要上楼的打算,我在衣裳间留恋。
我一件一件看着那些衣裳,甚至借助手电的微光看着那些细密的针脚。后来我发现了墙角的老柜,我在走近老柜时看见一把老锁,我好奇地想打开看看,我踌躇着该怎样打开柜锁,老柜里应该还有我想象不到的秘密,又是一个世界。几十套衣服在我的身前身后,我像钻在小树林里,或者进入了服装间,一个染屋,我对着老柜想我的心思,阁楼好静,楼上鸽子的叫声始终没有传来。就在这时,一件事情发生了,哗嗒,楼门开了,开门声很脆,猝不及防。我看见一只蜡烛,一只手举着,那只手上长满皱纹,同时有两只鸽子飞在她的两边,烛光颤动了几下,颤动后又迅速地亮起。
我看到了八奶。那一夜我是在八奶的老屋度过的,在我下楼时,我像一个引渡归来的犯人,内心充满了愧疚。我跪在八奶的面前,八奶不说话,蜡烛的光在夜色里闪动,八奶将蜡烛放在当门的方桌上,她坐在桌子的左边,两只鸽子站在几只陶罐的两旁。
八奶一直沉默着,这么多年八奶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既使走在村里也只是用拐棍发声,她去小卖部里买东西,也是用拐棍指一指,无声地付钱。可你们知道面对一个沉默的人,你多么煎熬。八奶让我站起来,她只是用拐棍指了指阁楼,拐棍拐回来,指了床头的陶罐、陶罐里苇樱一样的羽毛,她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日子,都是日子!
天亮了,我仓皇地逃出八奶的老屋。
五
八奶死了,她最后死在楼顶,一根拐杖通知了全村。
八奶在死前没有最后的预兆,她在最后一天还精神抖擞地攀到了楼顶。那是一个春天,太阳将村庄照耀得格外明亮,又一季的柳絮在村庄飞翔。八奶依然和她的鸽群守在一起,站在卡住她胸脯的那个豁口,只是她的眼有些吃力,看得不再那么遥远,眼前到处都是白色,白色的鸽子和白色的柳毛。下雪了吗?春天的一场大雪。她好像有一种预感,她最后对自己死亡的预告是从楼顶垂下了自己的拐杖,“嘭”地一声巨响,然后以遥望的姿式死在了楼顶。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她听到从楼下传来高喊她名字的声音,张大化接住了她的拐杖。
鸽群在楼上盘旋,疯狂地哀鸣。
她的儿子终于从远方回来,带来了他的儿女为八奶举行了葬礼。震撼老塘南街的是那一群鸽子——八奶的鸽群。哭声漫起的瞬间,一群鸽子凌空而下,整个棺柩前边一片雪白,雪团似的鸽子呼呼隆隆越旋越快,几十只鸽子朝八奶的灵柩上撞击,漆黑的棺柩染上白色的羽毛,棺柩顶上落满了死亡的鸽子。孝子们震惊了,抬棺手肩膀抖动,壮观的场面让他们想到两个字——陪葬!棺柩再次搁上了肩头,鸽子还在不断地飞翔,在灵柩前、灵柩上旋转,还不时有鸽子撞死在灵柩上,鸽子的羽毛飞扬了一路,鸽子的血滴在棺顶,和棺柩的黑漆融为一体。一路上都有鸽子的陪伴,直到动土前的仪式进行完毕,最后一路飞来的十几只鸽子抱团落入墓穴,撞棺而死,墓穴里像落进了一窝大雪。而在墓穴即将封顶之时,八奶孙子手中抱着的陶罐霍然碎裂,几千根羽毛旋空而起,一根根落入花圈的缝隙,竖在八奶的墓前。
这天夜里,张大化死在了八奶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