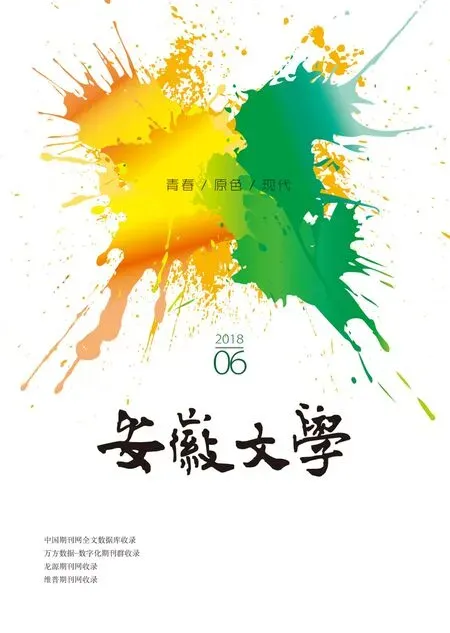女性自主性的建构
——论《屈身求爱》的女性主义维度
张文雯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1771年完稿、1773年首演的《屈身求爱》一直被传统剧评家视为风尚喜剧的典范。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借此剧,有力地反击了风靡18世纪英国剧坛的伤感之风,实践了他在《论剧院:笑戏剧和滥情剧之比较》中提倡的传统喜剧内核。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对“误解”、“欺骗”、“诙谐对话”等元素的多次应用,不仅制造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从而达到消解悲怆、抑制情感过分流露的目的,而且在无意中赋予了两位女性人物——凯特·郝嘉斯和康斯坦斯·奈维尔——极大的自主性。正如作品题目《屈身求爱》所示,在包办婚姻、女性失声的社会和文本背景下,郝嘉斯和奈维尔这两位乡村小姐巧用“欺骗”,策略性地曲身,最终征服了父权障碍,谋得了来之不易的个人幸福,获得了在婚姻上的自主性。这样“协商”过程契合了风尚喜剧推崇的理性精神,同时也彰显了女性对自主性的建构,从而赋予了观众和读者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屈身求爱》的契机。
一、女性主义话语下的自主性
如果把女性主义定义为女性对压迫的应对,如果女性抗争和解放意味着女性拥有按自身意愿生活的权力,那么自主性在女性主义视域中就处于无可撼动的核心地位。根据《自主性、压迫与性别》这一论著,女性自主性被定义为女性的自我决定能力,即真正地能够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外力操控、引导、扭曲。可以说,自主性这一概念为饱受男权支配之苦的女性呈现了解放自身欲望和确认自身权力的理想化状态。而在婚姻方面,女性自主性囊括了女性对自身婚姻的掌控能力,对婚姻伴侣的选择以及决定能力等。
然而,18世纪的英国女性与上述自主性的标准相去甚远。《屈身求爱》作为一部英国18世纪复辟时期的文学作品,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基于真实的艺术性还原,并将喜剧背景设置于此番社会图景之中。根据学者摩尔撰写的文章“十八世纪英国的爱情和婚姻”,当时,愈是富有的家庭,愈是社会上层的家庭,家长制的威力愈加显著,相应的,子女的择偶自主权就愈加受限。这是因为大部分贵族、富庶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婚姻是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或者阶级背景。孩子们常常在婴儿时就定了娃娃亲,在青少年阶段就结婚,对于另一半,他们所知甚少。在这样的包办婚姻中,女性相比于男性,受父母意志控制的状况更为严重,女性几乎被剥夺了所有话语权,最终新娘的点头同意仅仅是形式而已,所以“女儿除了依赖、服从着父母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屈身求爱》中的两位女性也面临着类似的境遇。凯特·郝嘉斯的婚姻命运掌握在“家长制的代言人”——父亲郝嘉斯先生和潜在的爱人马洛手中。在开场第一幕里,父亲郝嘉斯先生向女儿凯特·郝嘉斯宣布,他替女儿选为丈夫的那位年轻绅士马洛今天就要从伦敦来上门提亲,而凯特在此之前完全一无所知。换言之,凯特只需在这桩婚姻里扮演一名绝对“服从”与“听话”的角色。在第三幕里,领教了马洛的粗鲁无礼,郝先生怒气冲冲地改变了主意,直言这桩婚姻“将得不到我的同意”。若说父亲对自己判断力的自信和对女儿婚姻的定夺态度无疑为凯特套上了枷锁,而马洛脑中根深蒂固的“阶级——道德”双重标准更是雪上加霜。马洛在名媛闺秀前拘谨腼腆,在下层女性中却风趣滑舌,如此极端的反差在马洛与凯特的见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端庄典雅的郝嘉斯小姐,马洛就像朋友韩士廷所描述的那样,“口吃”,“浑身发抖”,“简直就像是想找个机会溜出外屋似的”,最终连正眼都没敢瞧过凯特,这也为凯特伪装成酒吧女侍与其再次相见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次,他的性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言辞上侃侃而谈,而且在行为上充满了风情的挑逗,数次企图抓住凯特的手,作势欲吻。根据马洛的自我辩白和自我剖析,他古怪的双面性格源于其在淑静的名门仕女面前缺乏必要的“自信”,而认为酒吧女侍“是归我们的玩乐的”。由此可见,马洛对于女性的定义仍旧落入传统男性对女性的“卡米拉”与“帕米拉”的极端叙述的框架之中。正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圣经——《阁楼上的疯女人》所写,女性形象程式化地分类,要不纯洁无瑕、高高在上、只可远观如“天使”,要不德行堕落、可任意亵玩如“怪物”,并无中间状态可言。对这位风流却可爱的情郎心生好感的凯特,若要赢得爱情,必须对马洛扭曲的女性观做出调整。
另一位女性角色奈维尔小姐的困境与凯特的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郝嘉斯太太觊觎奈维尔父亲留下的珠宝遗产,而根据当时继承法的规定,若郝嘉斯太太的儿子托尼在成年后不与他表姐奈维尔结婚,这笔财产就归属于奈维尔了。为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郝嘉斯太太千方百计地撮合自己的儿子和奈维尔成亲,而对两人的抗议,对奈维尔多次要回珠宝的请求,郝太太时而装聋作哑搪塞过去,时而假装珠宝被偷,花样百出。评论家布鲁克斯将郝太太精准地定位为“年老的父权制女性”:她内化了父权主义思想,将年轻女性视为婚姻交易的商品。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郝太太的贪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还是摆出一副为了奈维尔利益操心而后者不知好歹的痛心疾首的模样,这不仅制造了笑料,更体现了作为父权制的帮凶,女性更具伪装性和迷惑性,她压迫年轻女性重获应有财产的呼声,并试图操控她们接受附属品的屈从角色。奈维尔小姐为了能与心上人韩士廷先生终成眷属且能保住财产,她和郝太太之间的斗智斗勇不可避免。
二、建构自主性的方式——协商
压迫、禁锢和限制女性的社会环境也阻挡不了女性自主权的萌芽。《屈身求爱》情节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推动力来源于两位18世纪的英国中上层阶级小姐对于婚姻自主性的渴求。她们谋求自主性的策略——协商——也落入女性主义学家对于自主性的讨论话语中。纳拉扬就指出,女性通过与父权规范进行协商来达到自身目的,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真实的自主性。策略性的协商验证了女性自我反思、自我认可能力,体现了女性价值选择、寻求自我实现的能动性以及成本——收益的理性思考能力。在结构性的不正义绝对存在的情况下,协商作为个人应对方式,是女性能动性的重要体现。
女性犀利的目光瞄准了与 “温和派的父权者”之间的协商空间,并主动承担起“教育者”的角色。凯特与父亲的“讨价还价”在情节伊始就存在了。受城里时髦风气感染的凯特和思想保守的老古董郝先生达成了协定,凯特早上会见客人、探望亲友时按照自己的喜好穿着,而晚上必须换上主妇的衣着来讨父亲欢心。此后,在父亲不同意婚事时,凯特说服他再“进一步查明真相”。这两次成功的协商为凯特向父亲证明倾心者马洛的品德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为消解来自父亲的对她婚姻自主性的威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凯特与马洛的协商却没那么一帆风顺。凯特主动跨越了阶级界限,掩饰了自己作为贵族小姐的身份,假扮成一名下层阶级的酒吧女侍;之后,怕真实身份被马洛识破,凯特又伪装成“被指派来管钥匙并且尽力满足客人需求的穷亲戚”。她的“屈身”——放弃自己的阶级优势——是女性的让步与妥协,是为了换来能与男权者马洛进行正常沟通的机会。也正是在两人对话中,凯特展现出了值得马洛尊重的机灵与智慧,道德与品行。她挣脱马洛轻佻的攫手,严肃决绝马洛的吻,请他保持距离。面对马洛的道别,她大方而不卑微,直言“我不愿留您,也不能留您。……我们淡然相识,就淡然分手,”还发表了关于家世、教育、财富和爱情的见解。整个过程中,凯特扮演的是一个“女性教育者”的形象,她解放了自己的话语,把女性主义思想借助语言这个教育工具传播给被动承担起学生这一角色的男性,帮助男性学会如何尊重女性价值。“曲身”在此意义上,是一场指向征服的成功协商。
而与“年老的父权制女性”的协商时,女性不仅要借助智慧,更需发扬反叛精神。奈维尔小姐与郝嘉斯太太的博弈中也采取了协商策略。她在表面上有所放弃和牺牲,假装对郝太太唯命是从,假装无知到相信后者珠宝丢失的谎言,假装与托尼打情骂俏、处于热恋中,从而不仅让郝太太放下戒心,也掩饰了她暗中“征服”的小动作:与同样厌恶婚约的托尼结为盟友,与爱人韩士廷先生谋划私奔,在托尼和韩士廷的帮助下备好了离家的马车、重获了属于自己的财产。整个过程中,奈维尔展现了强烈的反叛精神,高度的理性与智慧,以及对婚姻自主的急切渴求。也正是这种精神,解释了为何即便在计划破产后,她仍敢于回到郝太太府上替自己求情,试图要回被剥夺的珠宝。她清醒得认知,在权力受限的父权社会中,协商是她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三、自主性的建构
这种策略性的协商的确推动了女性在与父权规范交易的某方面达成暂时性的动态平衡,以谋得对方的妥协以及女性自身相对的自主性。《屈身求爱》里两位女性人物通过与父权制协商,都摆脱了包办婚姻的约束,最终与心仪对象喜结连理。
凯特的“屈身”显然是成功的,她让父亲妥协,改造了马洛,这些都与她婚姻自主性息息相关。郝嘉斯先生从不赞同到最终支持两人的婚事,态度的转变源于凯特用协商来的时间竭力向父亲证明了马洛的品性。而马洛女性观的颠覆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客栈里的吧女有什么名誉我们都知道”,到“我真糊涂,全都看错了。把你的殷勤看成不知羞耻,把你的纯真当作有意勾引”,到“你我在出生、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上的悬殊,我们无法缔结名正言顺的关系。……我太在意舆论的压力和加氟的威势,以至于无法做主”,到最后一幕“教育和财富的悬殊、严父的震怒,以及同侪的蔑视,也逐渐失去分量。……我现在决定留下”。开头到结尾的巨大反差彰显的是马洛对男权主义思想的反叛。在女性教育者凯特的现身说法下,马洛终于明白了美德只是女性品性的表现,与她的阶级无关。这样“阶级——道德”女性观的转变,不仅是马洛对女性的再认识与再定义,也是对自身作为男性的再认识与再定义。他被凯特赋予了隐喻意义上的 “说话”能力,面对上流社会的女性时不再哑口无言。同时,他抛弃了对于财富和家长权威的屈从,勇敢地正视内心,追求爱情,最终转变成了值得凯特爱与尊重的男性。
奈维尔小姐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面对奈维尔小姐的坚定违抗,郝嘉斯太太不得不败阵下来。在最后一幕最后一场里,托尼做出了如下激动人心的宣言:“那我倒要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怎样头一遭使用自由的。(拉着奈维尔小姐之手)在场的诸位先生请作证,我,安东尼·兰普金,乡绅,拒绝你康斯坦斯·奈维尔成为我忠实合法的配偶。所以康斯坦斯·奈维尔可以嫁给她喜欢的对象,而托尼·兰普金又保有自由之身了。”这不仅仅是托尼个人的独立宣言,也是宣告了奈维尔小姐自由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她从此不再被包办婚姻禁锢,可以拥有应得的财产,自主地选择人生伴侣,去追求个人幸福生活。
四、结语
《屈身求爱》里的凯特·郝嘉斯和康斯坦斯·奈维尔是两个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角色。当个人幸福受父权压迫的威胁时,她们通过与父权规范进行策略性的协商,最终获得了婚姻自主。可见,在这场两性权力博弈中,女性的“屈身”通向了“征服”,彰显了女性建构自主性的能动力和反叛精神。在社会层面,作为风尚喜剧,《屈身求爱》反映了在18世纪包办婚姻、女性失声的背景下,英国女性要求在婚姻方面拥有发言权的呼声,达到了批判现实的目的。它与同时期的小说如《罗克珊娜》《帕米拉》共享了类似的主题,即对女性自我表达和自由意志的称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文学作品也播撒了女性主义的火种,撼动了家长制对女性婚姻的统治,冲破了剥夺女性声音的禁锢,为女性展示了获得婚姻自主的可能性。因此,在结构性的非正义绝对存在的情况下,它们为女性提供了不同的个人应对方式,为促进女性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为建构女性在婚姻方面的自主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1]Brooks,C.,Goldsmith′s Feminist Drama:She Stoops to Conquer,Silence and Language,Language&Literature,1992,28(1):38.
[2]Chrisman,J.,Autonomy,Oppression and Gen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Moore,W.,Love and Marriage in 18th-Century Britain,Historically Speaking,2009,10(3):8-10.
[4]Narayan U.,Minds of Their own:Choices,Autonomy,Cultural Pratices and Other Women,In L.Antony and C.Witt(Ed.),A Mind of One′s Own: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pp.418-432).Boulder,CO:Westview.
[5]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