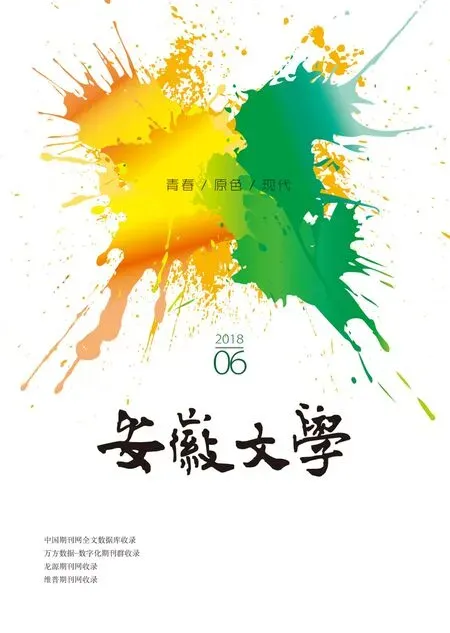再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陈 亚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诗经》自秦汉以来一直被尊奉为经典,但由于《诗经》诗歌的特殊本质,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文学性的一面。焦琳论《诗》充满了强烈的文学色彩,他认为:“诗之作也,本感于事而动于心,一时随口歌咏而出,采诗之人笔之于书,不过以文字记其所歌之语耳。”[1]6他的文学思想除了体现在注重咀嚼文本、把握人物情感和运用“以意逆志”及以诗解《诗》的方法上,还包括论诗歌的发生,论《诗》之艺术手法和《诗》论的审美批评化。
一、论诗歌的发生
“诗歌发生论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对诗歌发生目的之论述;对诗歌发生原因之研究;对诗歌发生过程之研究。”[2]278焦琳继承了《毛诗序》中关于“诗缘情”的思想,认为:“凡动物之出声者,皆以自达其心思也……人心之思,要妙宛折之无既,岂余物各有名称,于词能分断续之所得,之所得而穷其变乎。故曰:‘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足之舞蹈之’,蓋言诗之所由作,用以达人心难达之思云。”[1]1焦琳在前人基础上注重对诗人作诗的心理动因进行剖析,他坚持诗歌源于诗人内心喜怒哀乐情感的抒发,其情感的抒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心物感应。诗人将早以寓在心中的情感借助于所见之人或物表达出来。如《桃夭》篇“诗人见归女而作也,民被文王太姒之化,故其相好以德有如此者。”[1]3《3兔罝》篇“周之化行,圣人众多,诗人见兔罝之人,处微事而能久敬,赋其所事而美之也。”[1]559焦琳认为诗人感被文王教化,心中怀有对文王崇敬之情,看见美好的人与事,叹其受周之教化而成,见《桃夭》中女子出嫁,德礼相合,故感叹女子能宜其室家,发而作诗。遇野外打猎之人,见其英勇神武,赋诗而美之。诗人虽是对所见之人进行赞美,实质是抒发心中对文王、太姒的崇敬之情。诗歌的发生正是始于诗人内心寓于的情感与外在所见之物的互动。
(二)直接抒发情感,创作诗歌。焦琳认为诗歌发生的另一原因是诗人直接抒发内心的 “思”、“怨”、“哀”、“乐”等。如,《卷耳》篇:“言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1]26君子不在,妇人思念而赋此诗。又如《谷风》篇中,“士有别娶新婚,而弃逐其故妻者,故妻作此以怨之也。”[1]121妇人被弃,怨而作诗。又如《日月》篇“此诗为莊姜初见庄公,见其容止不类,而伤之也”[1]104莊姜所嫁之人面貌丑陋不堪,故忧伤而赋诗。如《汝墳》篇,“妇女喜其君子行役而归,而赋此诗。”[1]43女子见丈夫行役而归,喜极而泣,故作此诗等等。焦琳论诗歌的发生主要是对诗中人物的内心情感的剖析,体现了对诗歌“为情所造”之文学本质的把握。
二、《诗》论的审美批评
“在中国各体文学批评中,诗评最为早出,也最为发达,它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主脉。大量的诗评术语、概念或范畴则构成了这段主脉的主要内容。”[3]263古代《诗》评的术语主要有 “玩味”、“妙”、“意趣”、“气象”、“奇”等等,这些术语在文中多有朦胧之美,充满弹性,给人留下无限的意韵。焦琳解《诗》所运用的审美批评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味”评《诗》
《鱼丽》篇“蠲曰,盖愈咀嚼之,而意味愈无尽也,故下章又即其物以玩其情意云。”[1]586焦琳立足于文本,十分注重对诗文的把握,他常在书中教导读者“昔之人岂不能知,特以专心辩论《序》《传》,更无一心以细味诗文耳,此为解诗之大害耳。”[1]248注重对诗文的潜心玩索。在详味诗文的基础上,焦琳还常常以“直白无味”、“少味”、“寡味”等批评术语来批评旧说。如《雄鴙》篇“旧言迭往迭来,阴阳相配者,太卑下不足辩。“曷”字,本含盖无尽,与卒章用意呼吸相通,而说者以何日能来解之,不但率然少味,亦离宗已。”[1]117焦琳认为“曷”意味无尽,但旧解没有从整体上把握诗旨,理解诗情,以“何日能来”解之,使诗歌直白无味。
(二)以“气象”观《诗》
《沧浪诗话》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悲壮,曰凄婉。”[4]05一般把气象定义为作品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风貌,也就是作家主体精神和作品艺术生命的交融,是作家之“气”与作品之“象”的结合。焦琳把“气象”当作品评人物道德修养与精神风貌的常用词。如,《君子阳阳》篇“诗有自然之气象形容,亦作者之喜怒哀乐所发也,诵诗而未能观其气象形容,而诗人之志,仍不甚明,故著之以舞,以干戚羽旄,表其气象,以抑扬进退,为之形容,初本以喜怒哀乐之情态,发为气象形容也。”[1]227焦琳把作者之喜怒哀乐作为诗之气象的来源,他把握诗中人物情感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用气象品评。在《葛覃》篇品出后妃祥瑞凝重之貌;《卷耳》中品出诗中女子思念之貌;《汉广》中品出诗中女子端庄贤德之貌;《君子偕老》中品出诗中大夫舒俆安重之貌;《六月》篇品出吉甫老成持重之貌等。
(三)以“妙”品《诗》
“妙是指一切说不清楚的东西,一切从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好的但说不出好之所以然的东西都被冠之以妙。”[5]46“妙”在魏晋时期完成了由哲学范畴到美学范畴的转化。焦琳在解《诗》过程中常用“妙”来品评诗篇中的重要字词。如《四牡》中“載字妙,載则也,言驾马则驟,无一日驾而不骤也,是爱其勤,闵其劳,是所以知其急欲归养,”[1]536“载”即立刻之意,一个“载”字把诗篇中行役之人急欲归养父母之情刻画出来。诗歌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艺术形式,焦琳通过对每个字词的锤炼,点出《诗》中的字词之妙,使读者更能把握诗歌主旨。
(四)以“意趣”解《诗》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味’、‘韵’、‘境界’等范畴一起被人们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特征。‘意趣’是具有普遍概括性的‘趣’的审美形态之一。它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从宋代开始,‘意趣’作为对文学作品审美本质特征的概括,被运用于理论批评中。”[6]02焦琳把“意趣”看作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感受,常以“意趣”评诗。如,《大明》中:“旧解以文王之德言。夫文王之德明明,然贸贸然批评之,殊无意趣。”[1]968焦琳认为“明明”是指个人的言行举止均在众人的监督之下,举头三尺有神明,此解使诗旨更加充满张力。而旧解用其形容文王之德,直白阐释,缺少意趣。焦琳的《诗》论审美批评旨在让读者理解诗篇中句子、语气、情感、字词、主旨等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增强诗歌的美感,让诗篇的文字更有活力和韵味。
三、论《诗》之艺术手法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篇中蕴含了许多艺术手法,焦琳解《诗》则注重挖掘诗篇中的表现手法。《诗蠲》中分析了《诗》中之互文、想象、借景抒情、虚实结合、对面着笔、反衬等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焦琳的文学思想。
焦琳解《诗》揭示出的互文有两种形式:1.构成互文的词语含义不同,但两者相互补充,合而见义。如《山有扶苏》篇:“伪为谓之狡,伪为都,伪为充,皆为狂,互文也。”[1]227诗篇中“狡”、“狂”、“充”、“都”四字意思不同,但互相补充,以讽刺本无实德之人;2.构成互文的词意思相近,为避免重复而换作其他词替代。如《葛生》篇:“前两章,各上二句是互文,非葛不生于夜域,而蔹独无所蒙也。”[1]390“葛”与“蔹”形成互文,两者皆指荒野,为避免重复,下句换成“蔹”。焦琳在解《诗》过程中还常关注《诗》中借景抒情的表达手法。借景抒情是借助客观事物来抒发作者心中寓于的主观情感,使景与情相互交融,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增强诗歌感染力。如《草虫》:“草虫鸣,阜螽踙,非但触物惊愁,感时物之变,盖愁人眼中,遇悲凉景象,则伤其类已。遇欢娱景象,又恼其太不近人情,况草虫之鸣,阜螽躣而从之。又大有夫妇倡随情态,孤独无聊中闻见之,安得不聒耳刺目也,亦既见止,亦既觏止,复其词者,以见非此终不能解忧之意,非见字觏字意有异也。”[1]57思妇因丈夫不在身旁,心中思念,遇到悲景便觉更加凄苦。又闻草虫鸣叫,阜螽从之,大有夫唱妇随之态,于是更加痛苦,借景抒情。
对面着笔也称落笔对面,就是在表现怀远、思归等情感时,作者不直接抒发对对方的思念之情,而是从对方着笔。焦琳也善用此法来解《诗》,如《黄鸟》篇:“固是言心中汲汲欲归,愈是说此身急不得归,知此,然后知邦族父兄遥呼之切,如溺人望拯,相隔咫尺,而尚挽不着也。”[1]665焦琳写诗人到他乡,不得其所,于是思念家中亲人;但不是直接解说自己对亲人的怀念,而是从对面着笔说父兄思念自己。反衬是用反体衬托本体,通过对比更加鲜明地表现主题。反衬手法的运用也是焦琳解《诗》一种方式,如《杕杜》:“杕杜特生,似无依倚,而其叶萋萋,犹向荣而盛美,王事岂至今而犹未坚固也,王事一日不盬,则征夫一日不得归,使我心伤余悲,萧索低垂,曾杜不若也。”[1]578焦琳用杕杜与妻子作对比,以杕杜的茂盛来反衬妻子因等待久役不归的丈夫,相思成疾而枯萎萧索的样子,两者对比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思妇的痛苦之情。诗歌篇幅短小,字数有限,焦琳为了使读者能明白其丰富内涵,析《诗》时还多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增强诗歌的表现空间。如《汉广》篇:“再错薪是汉滨眼见之物,刈而秣马,虽非实事,乃直说实心愿为此。”[1]42焦琳把错薪解为江边实物,是实写。而刈之喂马,是虚写。是男子悦慕女子之情,看见身边的草,便欲割之给女子喂马以表达其对女子的爱慕之情,此诗虚实结合的手法突出表现了男子对女子的欣赏爱慕之情,给人无限的想象。
四、结语
传统认为,经学与文学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关系,实质上许多古代文人既是经学家又是文学家,他们常以文学的视角来阐释经典,又常以经学家的身份来从事文学创作。经学与文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者可以相互统一、相互转化。正如刘毓庆说:“《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它自身的素养,而‘经’则是历史赋予它的文化角色。作为‘诗’,它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它则肩负着传承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7]02焦琳是清末民初的一位经学家,在在坚持经学的立场下,多以文学视角分析《诗经》。他从诗歌发生论、情感论、审美批评和艺术手法等多方面展现《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文学内涵,文学思想洋溢其中,对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1]林庆彰.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诗蠲[M].台北:文听阁,2010.
[2]谭德兴.宋代诗经学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3]汪涌豪,骆玉明,主编.叶军,等,著.中国诗学第 4 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4]严羽撰.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冯晓林,著.论画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6]胡建次.中国古代文论“趣”范畴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2004(4).
[7]刘毓庆.从文学到经学序[J].名作欣赏,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