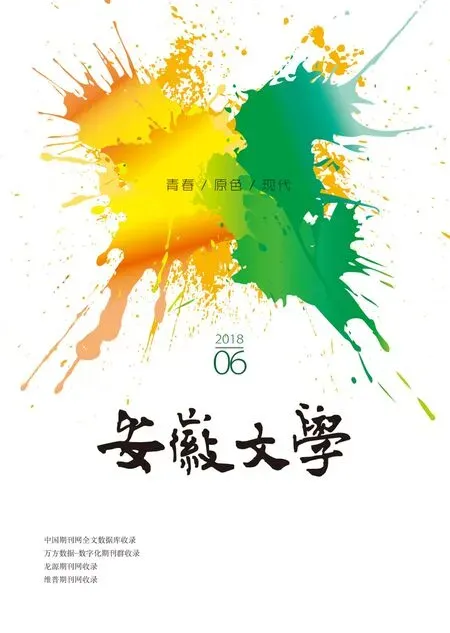论张镃的花卉词
宋亚凤
南京师范大学
张镃是南宋中期政坛和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因祖上遗荫,生活豪奢,构园林于南湖之滨。同时,他又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与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文人诗词唱和,交往甚密。其《玉照堂词》大量描写了牡丹会、登驾宵亭等风雅活动。因此,花卉成为张镃词的主要吟咏对象。况周颐云:“今读《南湖诗余》,泰半对花拊景之作。”[1]在《全宋词》所载的86首张镃词中,其专咏花卉之作达12首,而以花卉为抒情意象的词作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因此,研究张镃的花卉词对了解其词的总体风格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可窥见南宋花卉词的发展状况及审美范式。
一、张镃花卉词的思想内容
张镃乃贵胄之后,家资颇丰,在晚年被贬之前,一直过着富贵悠闲的生活。“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2]然而,张镃所追求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意图在自然美景之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他向往的是一种清雅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因此,花卉词成为其追求潇洒闲适生活的日常写照。这些词作内容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张镃的精神追求。
首先,张镃花卉词中最突出的部分便是十几首专咏花卉之作。此类词作蕴含了张镃丰富深切的情思。刘熙载云:“昔人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自有我在也。”这就道出了借咏物以咏怀的艺术真谛。张镃的专咏花卉之作,或以拟人手法描写所咏之花,将花与美人联系,寄寓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如其《菩萨蛮·鸳鸯梅》一词,紧扣“鸳鸯”二字大做文章,从鸳鸯到鸳鸯梅,表达对爱情的忠贞;或借花来抒写韶光易逝的伤感,如“免教春去,断肠空叹诗瘦”(《念奴娇·宜雨亭咏千叶海棠》)[3]。然而,就其此类专咏花卉之作来看,所表达的思想都是普泛化的,没有脱离晚唐五代以来传统的题材范围。就情感深度而言,此类词作更像是一个悠闲的富家公子消遣生活的随意之作,缺乏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他更像一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因而很难让人琢磨其词背后的意蕴。
除了上述的专咏花卉之作外,张镃的花卉词中还包括以花卉为观赏对象的词作。这类词在张镃词中内容更加丰富,题材范围也更加广泛,体现了他作为贵介公子的享乐意识和诗意的生活追求。例如,《昭君怨·园池夜泛》[3]描写与友人月夜乘舟赏荷、放歌吟诗的情景。荷花在宋代被视为“君子之花”,备“清”“贞”于一体,是独立人格的象征。因此,在这种文化认知下,张镃的“赏荷”之举于富贵之中透露出闲适淡然的心境。关于玉照堂的梅花,张镃《满江红》[3]云:“光摇动、一川银浪,九霄珂月”,此种景象,非普通人家可比,足见梅花之多,也可见张镃的享乐意识。梅花间的“诗仙”在醉归之时,看到“月过珠楼,参横蓬莱”,从而为这场欢愉盛宴抹上了朦胧缥渺的色彩,使繁华喧嚣归于清淡和虚无,加上“梅花”在宋代形成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使得这场纯粹的物质享受带上了更多的文化意蕴。
当然,这些花卉词同时也反映了张镃闲逸淡泊的心境。总体来看,张镃诸多花卉词中,以对梅花和荷花的吟咏次数最多。宋人喜爱梅花,已经成为共识。除此之外,荷花在宋代文人的笔下也频频出现,与梅花一起被视为“比德之花”、“君子之花”。可见,这些花卉已经成为张镃寄寓情感的重要寄托。[4]作为张俊之后,张镃对于保卫河山有自己的政治期待。然而,张镃生活的时期,宋金趋于一种稳定的对峙关系,国内朝政为权臣把握。士大夫在政治上难有作为,普遍选择了回避政治矛盾、冷淡功业建树,在享乐生活和自然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寄托。张镃便是在这种心态下,企图在日游湖山、持酒听歌、依红偎翠中逃避现实,求得心灵的安静。他在花卉词中频频表达这种意愿,如 “此身无系着,南北东西乐”(《菩萨蛮·遣兴》),“区区宦海浮沉,幸隐去、将酬素心”(《柳梢青·秋日感兴》)。可见,寄情山水,追求闲逸淡泊的心境,是张镃孜孜不倦的目标。
二、张镃花卉词的艺术特征
张镃是以咏物擅胜的能手,沈雄《古今词话》引周密的话评价张镃的咏物词“乃咏物之入神者”。而张镃的词推动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龙榆生在论及南宋咏物词时指出:“南宋词人,湖山燕衎;又往往有达官豪户,如范成大、张镃之流,资以声色之娱,务为文酒之会;于是以填词为点缀,而技术益精;其初不过文人阶级,聊以‘娱兴遣宾’;相习成风,促进咏物词之发展……张镃、姜夔出,咏物之作渐繁。”[5]无论是周密还是龙榆生,他们都认为张镃的词以“技”取胜,而此“技”的关键,便是“入神”。专咏花卉之词作为张镃咏物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佳作者都取得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而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与其运用的表现手法密不可分。
张镃的专咏花卉之作,最常见的表现手法是拟人与联想。张镃经常在上阕将花比作少女或美人,下阕则运用联想的手法由花及人,鲜少通篇拟人之作。这就使得花卉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即在追求“神”的同时,依然能够感觉到“形”的存在。如其《念奴娇·宜雨亭咏千叶海棠》[3]上阕描写海棠花的娇嫩慵懒之态:“紫腻红娇扶不起,好是未开时候,半怯春寒,半怯晴色,养得胭脂透。”“扶不起”三字生动描写出花娇而无力的情态,使人自然联想到“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贵妃形象。“半怯春寒,半便晴色,养得胭脂透”则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海棠花含苞待放的原因,突出海棠花的姿态和颜色,写出花的娇嫩和花色的匀净,使人印象深刻;下阕自然联想到昔日与情人携手赏花的情景,“一枝斜戴,娇艳波双秀”,既是写花,也是写人,花与人相映成趣。除此之外,其他咏花卉之作,如“依就花儿,深藏叶底,不教人折”(《玉团儿·香月堂古桂树十株著花,因赋》),“潇洒绿衣长,满身无限凉”(《菩萨蛮·芭蕉》)等都运用拟人手法写出花卉的不同情态,从而使得所咏花卉更具灵动之美。
除了专咏花卉的词作外,张镃词中以花卉为观赏对象的词,大都与词人的宴饮活动有关。在这些词作中,花卉只是作为整个环境的一部分出现的。尽管如此,此类词作中,花卉对于寄托词人的思想、反应词人的心境有独特的作用。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特点,在于词人在描写这类花卉时并非随手拈来,不加思考。相反,此类花卉的出现正是词人精心挑选的结果。与其他描写对象相比,鲜明的色彩是花卉的一大特点。这种色彩感是构成词的画面美的重要因素。在张镃的此类词作中,花卉色彩的运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巧妙配合是构成他花卉词特色的重要方式。其花卉词中的色彩,大致可分为同类色和对比色两种情况。同类色的运用往往使得画面和谐统一,如《菩萨蛮·遣兴》[3]写词人早晨读书完毕,准备卧床休息的场景,而“绕舍灿明霞,短长旌节花”句,写早晨柔和的金色阳光洒进屋里,照在旌节花上,使得淡黄色的旌节花愈加生动。在这种整体的淡黄色氛围中,再配以藤床的“青”色,使得整个画面既温暖又富有层次感,巧妙地配合了词人慵懒悠闲的生活情态。除了同类色调外,对比色的运用使画面更加富有层次感,起到了刺激读者视觉神经的观赏效果和情感体验。张镃笔下最常见的色彩搭配便是红与绿。如“红绿总吹香”(《昭君怨·游池》、“枝上凌霄红绕翠。飘下红英,翠影争摇曳”(《蝶恋花·挟翠桥》)、“红娇翠婉”(《鹊桥仙·采菱》)等。尽管红与绿是对比色调,但是由于花的红与叶的绿本属自然搭配,因此其组合显得浑然天成。无论是同类色彩还是对比色彩的运用,都起到了营造画面感、烘托气氛、唤起艺术想象的效果。
中国古典文学素有“香草美人”的传统。因此,以花卉为描写对象的花卉词,本身就带有词人的情感倾向。张镃词中频繁出现的梅花和荷花,正如前文所述,在宋代寓意“君子之花”,此类意象代表词人的人格操守,起到了为词人代言的作用。除此之外,张镃词中的菊花意象,也有类似的作用。提到菊花,不得不使人自然联想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菊之于陶渊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精神符号。张镃笔下的菊花意象,也具有相似的情感指向。如其《八声甘州·九月末南湖对菊》[6]写词人南湖赏菊的情景。在菊花的寒香中,词人自叹年华逝去,也有功业未就的无奈:“自叹平生豪纵,歌笑几千场。白发欺人早,多似清霜”,因此生发出愿与青灯黄卷相伴的感叹,抒发归隐的志向:“谁信心情都懒,但禅龛道室,黄卷僧床。把偎红调粉,抛掷向他方。□唤汝、东山归去,正灯明、松户竹篱旁。”值得注意的是,张镃的“归隐”,探寻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淡雅静谧,这种探索是建立在殷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与亲自躬耕的陶渊明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张镃笔下的桂花意象,常常与月亮结伴出现,如“香风浩荡吹蟾桂,影落澄波底”(《折丹桂·中秋南湖赏月》)、“初开数朵谁知得,却又是、金风漏泄。吹起清芬,露成香露,月成香月”(《玉团儿·香月堂古桂树十株著花,因赋》)。关于桂花与月亮的关系,人们常常能自然联想到吴刚伐桂的神话传说。因此,桂花的出现,多了一层文化意蕴和神秘色彩,使得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有了奇妙的结合。宋代士大夫一方面有兼济天下之志,另一方面又在宦海浮沉中企图寻求内心的安稳和平和,志行高洁始终是他们赞赏的人格典范。[6]因此,在张镃笔下,桂花意象不仅是营造氛围的植物,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词人的人格追求和写照。
总体而言,张镃词贯穿了其闲雅清丽的艺术追求。这种清雅词风,既是南宋以来社会政治局势推动的结果,也是词学发展之必然。南宋以来,词的风格趋于雅化,词坛上大兴“复雅”之风。张镃、姜夔、吴文英、张炎等都是词在雅化过程中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张镃写花卉,极少写牡丹、芍药等富贵之花,而是写梅花、荷花、芭蕉、桂花等,这些花卉都给人清新淡雅的印象,足见张镃嗜雅的情趣。另外,张镃虽出身豪门,他的词作中却鲜少看到错彩镂金的刻画,语言风格趋于清疏淡远,这都说明了张镃清雅的艺术追求。
三、张镃花卉词的意义
花卉词是张镃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所述,张镃的《玉照堂词》极少写实事,更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中的雅趣。同时,张镃是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的典型代表,其词作的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张镃的花卉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首先,张镃的花卉词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花卉词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宋词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体现了士大夫文人嗜尚清雅的精神追求。南宋时期苏杭一线经济繁荣、人气旺盛,私家园林极为盛行,这为登山游湖的雅趣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同时,偏安的政治态度以及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使得士大夫希冀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心灵的寄托,保持人格的操守,加上宋朝统治者的享乐之风,多方因素促成了宋代花卉词的繁荣。张镃词中大量的花卉描写,正是这种文化风尚的反映。其笔下的花卉,以对梅花、荷花、桂花的描写居多,而此种情况,正是宋代词人普遍的审美喜好。据黄杰的统计,《全宋词》《全宋词补辑》中专咏之花卉有54种,而梅花、荷花、桂花分列前三甲。同时,相较于牡丹、芍药等富贵之花,张镃尤爱梅花等小巧雅致的植物,且这些品种都较为常见,由此可见宋人整体的平民化审美趋向。钱穆在《中国传统文化之演进》中说:“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经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7]另外,张镃的花卉词在内容上多是一般的宴饮或赏玩之作,是达官显宦的日常生活,从而可见张镃花卉词的世俗化倾向,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化心态。
其次,研究张镃的花卉词,可以了解张镃的交游情况,同时也可窥见他与当时的文化名人诗词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比较。张镃身份特殊,他与“政界”的关系密切,与“军界”也有联系,尤与“文学界”的人物过往最为密切。[8]张镃与陆游是老友,与辛弃疾也有诗词唱和,此外与杨万里、姜夔等人交相往来,从其交往中不难想见张镃与众多文人间诗词的相互影响,同时也便于在相互比较中确定张镃词的风格。例如,张镃喜爱梅花,而与张镃同一时期的中兴名家如陆游、杨万里等都是擅长写梅花的高手,且各有特色。陆游在描写梅花时着重梅之“格”,侧重对梅花苦节意志的塑造。张镃的梅花,鲜少有这种精神品质。他的梅花词与杨万里笔下的梅花颇多相似之处。杨万里在描写梅花时多侧重观梅之“乐”、赏梅之“趣”。他以“活法”作为审美标准,注重具体切实的体验,捕捉梅花的各种风姿,展玩其意态情趣。他的这种赏梅的情趣,是士大夫物质无虞和精神优越流溢出的风雅气象,一种官僚地主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高雅情趣。这种生活体验,也是张镃的日常写照,二人有相通的生活旨趣。张镃写梅花也多侧重梅花的观赏价值,探寻的也是梅花的风姿和意趣。他推崇杨万里的“活法”说,并在诗词创作中有意效仿。然而,相较于杨万里自然活泼的描写,张镃笔下的梅花有“工丽”之美,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描写视角。相较于陆游、杨万里诸人多有逊色,更不要提之后被张炎称为“绝唱”的《暗香》《疏影》词了。因此,杨慎在《词品》中才会这样评价:“其佳处为‘光摇动、一川烟浪,九霄珂月’,又‘宿雨初干,舞梢烟瘦金丝袅。粉围香阵拥诗仙,战退春寒峭’皆咏梅之作。虽不惊人,而风味殊可喜。”
总之,张镃的花卉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镃的生活追求与精神意趣,其花卉描写的特点与其词学观念一脉相承。尽管张镃的词多有可取之处,然格局终究太过狭窄,因而在名家辈出的南宋中期词坛难有立足之地。这也正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价的:“镃词字句精整,而用笔流畅,在南宋词中,虽未臻博大,而工丽可称也。”
[1](清)况周颐撰.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俞香顺.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5.
[5]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于沙雯.论宋代中秋词中的嫦娥与桂花意象[J].名作欣赏,2012(5).
[7]黄杰.宋词与民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杨海明.张炎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