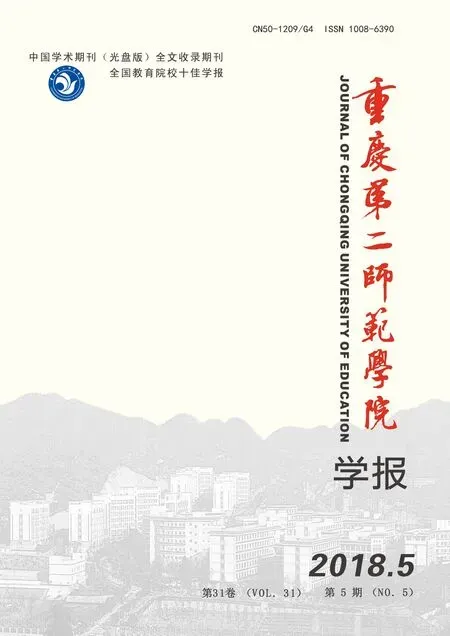论李贺诗歌的经典化历程
李刚刚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在诗歌发展史上,经典是对一个诗人及其作品价值的评价,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对经典的评判也是动态的。有些诗人诗作曾被认为是经典,后来却被推翻;有些诗人诗作不被当时所重,却被后世追认为经典;还有一些诗人诗作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其崇高地位,为历代诗论家和读者所推崇。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活跃着众多风格各异的诗人,不少诗人及其诗作成为后世尊崇的经典,李贺便是其中之一。李贺在大唐诗歌舞台上活跃了二十七年,留下诗歌作品二百三十三首,正是这些用其毕生心血浇灌的艺术之花,成就了李贺永恒的经典地位。李贺的经典化历程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对其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诗歌批评标准和审美价值取向,也可以觇知一个经典诗人的形成需要具备何种因素。
一、中晚唐:诗名鹊起
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一个悲剧诗人,二十七岁辞世,短暂的生命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大唐诗坛的夜空。与其他高寿诗人相比,李贺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经典诗人。元和时期,李贺就已名满京都,从此便开启了成为经典诗人的历程。经过中晚唐的沉淀,其经典诗人的地位就此确立。
李贺一出生似乎就注定要成为经典,据史书记载,李贺出身高贵,系唐宗室之后。《旧唐书·李贺传》谓其为“宗室郑王之后”[1]3772,《新唐书·李贺传》同样记载其“系出郑王后”[2]5787。此外,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称“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3]66,其为王孙身份,由此可得确证。李贺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但其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才名冠绝当世。李贺少年时代就名动京华,康骈在传奇小说《剧谈录》中记载:“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3]20李贺之名在唐人笔记小说中频频出现,其诗歌受韩愈援带而起的故事还见诸张固的《幽闲鼓吹》。另外,还有更传奇的记载:“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3]19这件事在唐代的文献资料中未有记载,最早见于宋人编写的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既然是小说,故事情节难免有虚构夸张之处,但《高轩过》出自李贺之手的事实不假。据朱自清先生考证,贺作《高轩过》诗时,不是七岁,而是在元和四年(809年),李贺二十岁时。虽然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这则材料足以证明,李贺的诗名在当时已经受到韩愈、皇甫湜等诗坛大佬的关注。元和五年(810年),“贺应河南府试,作十二月乐词,获隽。冬,举进士入京……或毁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韩愈为作《讳辩》,然贺卒不就试,归”[33]。李贺的才气为韩愈所赏识,鼓励他举进士。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贺的才能招致群小的忌妒,以避讳之由诋毁之。韩愈引经据典,作《讳辩》一文为其鸣不平。李贺作为诗坛新秀,在没有任何资历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文坛领袖韩愈的鼓励与支持,这对其经典诗人地位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和年间,韩孟诗派雄霸诗坛。韩愈主张诗歌要有所新变,他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主张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的审美风尚。李贺的诗歌创作主张恰好与韩愈、孟郊等人相契合。“殿前作赋声摩空 ,笔补造化天无功。”[3]154李贺主张诗歌创作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李贺诗歌凭借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等鲜明特点,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诚然,由于自身遭际所限,其诗歌视野不够宏阔,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但是,李贺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诗歌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美的风格特点,从而也为其经典诗人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李贺生前好友沈子明委托当时的京兆尹杜牧为其诗集作序。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中对他的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4]149杜牧连续用九个比喻句赞美李贺的诗歌,溢美之词虽稍显夸张,但也不可谓不精确。其论极为形象,极得要领。其中所云“态”“情”“和”“格”“勇”“古”“色”,指的是李贺诗歌不同题材的不同情调及其风格的多样化。而“怨恨悲愁”和“虚荒诞幻”则稍有不同:前者指思想感情,说他的思想感情像“荒国陊殿、梗莽邱陇”那样“怨恨悲秋”;后者指艺术构思,像“鲸呿鳌掷、牛鬼蛇神”那样“虚荒诞幻”。有了杜牧的盛赞,李贺的诗集在晚唐流传甚广。唐代诗人张碧说:“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5]1543唐代诗僧齐己《读李贺歌集》诗曰:“玄珠与虹玉,灿灿李贺抱。”[6]9585此外,晚唐人对李贺评价甚高,沈下贤在《序诗送李胶秀才》一文中云:“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7]8540诗僧齐己在其诗歌《还人卷》中云:“李白李贺遗机杼,散在人间不知处。”[6]9588在《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中又说:“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谁言后代无高手,夺得秦皇鞭鬼鞭。”[6]9593晚唐的戴叔伦还有专门诗作《冬日有怀李贺长吉》怀念李贺。不仅如此,晚唐时期诗坛已掀起学习李贺诗歌的热潮。《旧唐书·李贺传》记载:“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1]3772其好友沈下贤在《序诗送李胶秀才》中说:“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后学争踵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7]8540纵观文学史可知,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韦楚老等人的诗歌创作均受到李贺诗歌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从同时代及晚唐人对李贺的评价,李贺诗集在晚唐的流传情况,及其诗歌对晚唐诗坛的影响三方面可知,李贺经典诗人的地位在中晚唐已经确立。上帝给予李贺万人瞩目的经典诗人桂冠,但以此为筹码的却是其美好的嘉年华,何其哀哉!
二、 两宋:沉浮晦显
如果说李贺经典诗人地位的确立,得益于中晚唐诗人重主观、喜怪奇、尚艳情的美学趣味和诗歌理想的话,那么时过境迁,在两宋之际,其经典地位又将如何变化?
北宋时期,李贺名声有所下降。此时,对李贺诗歌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数。宋祁在《新唐书·李贺传》中对李贺诗歌进行了如下评价:“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2]5787显然,此论由杜牧之论而来,没有什么创新和灼见。同样,学习李贺的诗人也屈指可数,除了秦观《秋兴九首其四拟李贺》一首、张耒缅怀李贺的《岁暮福昌怀古四首其三李贺宅》一首外,还有就是梅尧臣在《答仲源太傅八日遣酒》中提及李贺:“李贺诸王孙,作诗字欲飞。闻多锦囊句,将报惭才微。”[8]636与此相反,李贺及其诗歌此时遭到更多的是批评与指责。首先指出李贺诗歌弊端的是宋初的孙光宪,他在《北梦琐言》中说:“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9]64从材料可知,孙光宪虽对李贺有批评之意,但他吞吐委婉,对唐人推举的经典诗人还存有敬畏之心。但到了南北宋之交的张戒,对李贺的批评则义正言辞,敬畏之心全无。他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10]94在此之前,杜牧在晚唐就已指出李贺诗歌“少理”的弊病,他在《李长吉诗歌序》中谓:“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3]12由此观之,孙光宪、张戒之说与杜牧之说遥相呼应。自从杜牧谓李贺诗歌少理及缺乏感怨刺怼,不足以激发人意,指出李贺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缺失后,又加之宋人发挥此说,李贺诗歌“少理”在北宋遂成定论。
李贺诗歌在“理”这一层面的缺失是其在北宋诗坛遭到冷遇的重要原因。与丰神情韵兼备的唐诗相比,宋诗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思理取胜。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1]173在宋人心目中,李贺诗歌不仅缺乏深刻的思想,而且缺乏他们念念不忘的思理、理致。但若仅因李贺诗歌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征与北宋文人的好尚相异,就置其在艺术表现上的险奇新创与冷艳瑰丽等可取之处于不顾,而对其大加指责,这难免有失公允。生命历程的短暂使得李贺缺乏老杜那样的人生经历与社会阅历,因此他写不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15]这样直抵人心的诗句。但是,李贺将自身具备的创造性思维、丰富的想象力、敏感的情感领悟等优势发挥到极致,重视内心世界的开掘与个体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的表现,为古典诗歌开辟出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北宋文人对李贺的批评正如手持放大镜观物,未免将个人的缺点过度放大,这种批评囿于时代所限,须由后人重新去审视和评判,还李贺一个客观、公道的定位。
与北宋文坛上的稍显寂寞相比,李贺在南宋觅到了大批知音。尤其是南宋中后期,李贺声望日隆,影响日深。南宋姚勉在其诗歌《赠行在李主人二子》中谓:“李家自古两诗仙 ,太白长吉相后先。”[12]239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18]1917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集》中评价:“乐府李贺最工,张籍、王建辈皆出其下。”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称:“李长吉、玉川子诗皆出于《离骚》。”[21]严羽在其诗学名著《沧浪诗话》中更是将李贺诗歌单列一体,称“长吉体”。用作诗作画的方式怀念李贺的也不乏其人。宋末元初的郝经用一首《长歌哀李长吉》怀念李贺,其中有“青衣小儿下玉京,满天星斗两手摘”[3]16。另外,还有为李贺作画的,如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徐俯的《李贺晚归图》、刘因的《李贺醉吟图》、陈师道的《题明发高轩过图》等。虽然这些画已经亡佚,但关于这些画的诗歌被保存了下来。由此可推知,李贺是当时画师们钟爱的题材。关于李贺的诗集,南宋刘辰翁和吴正子分别撰有《李长吉诗评》和《笺注李长吉歌诗》,这两部诗集对李贺诗歌在后世的流传有重大贡献。模仿李贺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刘克庄、谢翱、范成大、吕炎等都是模仿李贺诗歌的卓有成就者。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南宋诗人自觉抵制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有关,同时也说明南宋时期的审美风尚和诗学理想较之北宋已有所嬗变。
南宋中后期,时局的动荡使诗歌创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诗人渴望诗坛风气的新变。江西诗派末流主张的以议论、文字、才学为诗的创作主张流弊日显。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为代表的“中兴四大诗人”纷纷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自立门户,最终以全新的艺术风貌廓清了江西诗派的弊病残留。“四大家”作诗强调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描写,注重才情气质的自然流露,追求活泼自然的诗境。这样,富于奇气的鬼才李贺自然成为他们取法的对象。范成大是南宋较早自觉学习李贺的诗人,他有两首标明效李贺的作品,一首《夜宴曲》,另一首《神弦》。陆游在《赵秘阁文集序》中说:“魏陈思王,唐太白、长吉,则又以帝子及诸王孙,落笔妙古今,冠冕百世。”[13]杨万里十分推崇李贺诗歌,认为其“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3]35是惊人句。由于尤袤诗集遗失,故未能找到其关于李贺的评价。总之,由于上述几大诗人的推崇,李贺经典诗人的地位在南宋得以稳固。
李贺在南宋之所以得以显名,还要归功于南宋著名诗歌评论家严羽。严羽论诗主张“以盛唐为法”,对于中晚唐诗人则推崇不多。那么,李贺为何能够得到严羽垂青?这其实与严羽的诗学思想有关。严羽认为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其诗歌创作背离了唐诗传统。尤其在南宋中后期,江西诗派末流的流弊日益显现,针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1]173的诗歌主张,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篇中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11]129“别材”“别趣”说正是严羽论诗的核心主张,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穷理”之风针锋相对。李贺诗歌历来被视为“少理”,但此时却恰好与严羽的诗歌主张相契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32]这就揭示了李贺能得严羽青睐的原因。
李贺在两宋诗坛经历的由沉到浮的巨大变化与当时的诗学理想和批评标准密切相关。经过两宋之间的显晦变化,李贺诗歌的利弊得失已被世人所熟知。后人再评判李贺诗歌时,对其弊端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而更多关注其诗歌中的可取之处。
三、元明清:人诗并彰
元明清三朝,李贺本人及其诗歌都成为文人关注的对象。在元代文坛,李贺经典诗人的地位进一步彰显。明清两朝,李贺自身附带的悲剧性更多被文人所关注,这为李贺经典诗人地位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有元一代,叙事文学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即使在这样一个诗歌歉收(主要指诗歌质量欠佳)的时代,李贺经典诗人的地位反而愈加彰显。元人杨士宏积十年之功编纂唐代诗歌总集《唐音》,在卷七《唐诗正音》中称:“言诗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20]585在卷十一《唐诗遗响》中称:“李贺文体如崇严峭壁,万物崛起,人多效之。”[20]683在卷十二中又称:“李贺能探前事今古未曾经道者。”[20]683杨士宏对李贺推崇备至,由此可见一斑。至顺帝朝,诗坛掀起了一股学习李贺诗风的热潮,李贺诗歌风行一时。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说:“宋初诸子多祖乐天,元末诸人竞师长吉。”[1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人学习李贺的实况。此时,个性狂狷的诗人杨维桢横空出世,创作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向的奇特不凡。于是诗风以“冷艳瑰奇”著称的李贺自然为其所取资。李贺诗歌被杨维桢立为经典的创作范式,进一步指导其诗歌创作实践。这常常表现在对李贺诗歌的模仿和拟作上。如其《鸿门会》就是模拟李贺《公莫舞歌》的代表性作品。兹将二首诗对比如下:

——杨维桢《鸿门会》
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罂。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筝。横楣粗锦生红纬,日炙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宝玦光,项庄掉鞘栏前起。材官小尘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芒砀云端抱天回,咸阳王气清如水。铁枢铁楗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膑刳肠臣不论。[3]87
——李贺《公莫舞歌》
对比可知,杨维桢的《鸿门会》意象奇绝,气势雄放,较之贺诗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杨氏雄奇飞动,充满力度的风格特征与李贺一脉相承。除杨维桢外,模仿李贺者不乏其人,其中卓有成就者还有吾丘衍,他写的乐府诗仿效长吉体,诗的气韵堪与贺诗相媲美。总体而言,元人只是生硬地模仿李贺诗作,诗歌缺少鲜明的独创性。正如明代费经虞在《雅伦》中所说:“古人有翻案伐材,夺胎换骨之说,若宋人之生吞李义山,元人之活剥李贺。”[30]4780即使如此,李贺之名还是借杨维桢、吾丘衍等人之力而得以彰显。
明清之际,文人对李贺诗歌的评价虽有微词,但更多的是赞美之声。对李贺诗歌持有微词的有明代的李东阳,他在《怀麓堂诗话》中说:“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故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此外,清代的王弘撰承唐人之说,在《砥斋集·文论》篇中同样认为:“李贺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间。”[24]此二人评论一认为李贺诗歌用词过于雕琢,一认为李贺诗歌内容狭窄、诗境狭小。仔细分析可知,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不足以撼动李贺经典诗人的定位。
与其诗歌相比,李贺其人在明清之际反而得到文人的更多关注。在明清诗文中,李贺作为一个天才而失意早夭的形象反复出现。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感慨:“范摅子,七岁能诗,十岁卒;林杰,六岁能文,十七岁卒;李贺二十六;王勃二十九。”[30]3790瞿景淳在太学生顾君明的墓志铭中说:“且颜回之仁也而夭,李贺之才也而夭。”[25]明代康海在《对山集》中谓:“岂天亦无奈于数,而鬼神妬而夺之邪?抑如李贺,冀修文于天,天受而闭之邪?”[26]梅守箕在《梁生文草序》中说:“王子安、李贺辈,皆威颖天然,绮抅若素,而皆不永于年。”[27]田汝成在《田叔禾小集》中慨叹:“王勃李贺之悲,古今一揆矣。”[28]王恭在《白云樵唱集·挽镏牧》中咏叹:“凄凉贾生年少人,皆惜李贺才多世。”[29]同样是在借贾谊、李贺之悲来吊念镏牧。
清人步趋明人之后,在关注李贺诗歌的同时,同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李贺其人身上。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闻四弟编修骥元赴大恸率男朝礎设位北向祭之哭诗二首》之一中说:“好学颜回偏短命,呕诗李贺竟捐身。”[31]清代古文家吴敏树在《欧阳功甫遗集序》一文中说:“如唐之观李贺其人,非独当时为之嗟憾,而至于今读其书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23]清末王蕴章在《然脂余韵》中同样感慨:“才如李贺天还忌,哭比唐衢泪更多。”[17]
综上可知,李贺作为一个有才而早夭的悲剧诗人形象在明清时代已深入人心。那些失意早夭的天才,历来都能引起文人的同情与嗟叹,如汉之贾谊,魏之陈思,唐之王勃、李贺,宋之王令等,这些人才华卓著但大都抑郁不得志而早夭。明清之际,李贺的悲剧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才能和年寿的不成比例成为明清文人心中无法消解的块垒,每每让人心痛不已。李贺所遭遇的不幸与悲惨不仅没有影响他经典诗人的地位,反而对其经典化形成强大的助力,使之在诗歌艺术的殿堂里永垂不朽。
四、结语
李贺经典诗人地位的构建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它包括李贺诗歌的艺术价值、诗歌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变动、诗歌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几个方面。李贺诗歌在后世传播过程中经历一些显晦变化都是正常现象。历史经验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真正的“经典诗人”都要经历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所谓“诗人经典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地、接受各种力量考验地保值、增值或者贬值的动态过程。“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成尘。”[16]李贺这位天才诗人离开我们已经一千两百多年,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历史遗迹被漫长的岁月销蚀殆尽,而李贺苦心孤诣营造的诗歌艺术殿堂依然矗立于世间。笔者认为,今后不论学术如何发展,诗鬼李贺用自己一腔热血在诗歌史上浇灌的奇艳之花必定惊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