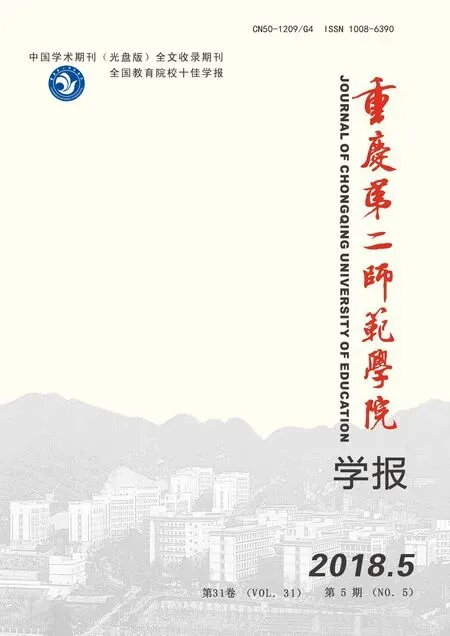《孔乙己》中的方言翻译规范化研究
张献丽
(安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1]100胡适对方言在文学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令人深思的见解:“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406
出于对作品受众的考虑,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语言一般采用标准语,然而方言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作者通常使用方言来塑造人物性格、雕刻人物形象,例如“多乎哉?不多也!”此语一出,孔乙己迂腐的知识分子形象就跃然纸上。也有作者通过使用方言来反映特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社会习俗。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时,译者都特别小心、严谨。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译者在翻译方言时选取的翻译策略、遵循的翻译规范及其内在的原因。
笔者通过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威廉·莱尔在翻译鲁迅经典小说《孔乙己》中的“方言土语”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尝试描述他们遵循的起始翻译规范,解释其翻译决策。
一、研究现状
(一)国外方言翻译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于19世纪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方言翻译,不过,对方言翻译的深入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Hatim和Mason[3]借用Halliday的语域理论,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探讨了方言的翻译;Nida[4]112从功能对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方言翻译,认为“如果一个文本是由非标准的方言所写成,译者面临的难题就是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对等语”;Newmark[5]提出了方言的功能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此后,对方言翻译的研究逐日升温,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方言翻译进行了探讨。笔者将西方学者最近20年的研究视角简略总结为以下三类。
第一,从语言学视角对方言翻译进行探讨。波兰学者Berezowski[6]是西方最早系统地研究方言翻译的学者。从语篇语言学的视角出发,Berezowski对文学方言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十种翻译策略。葡萄牙著名学者Pinto[7]认为方言翻译的语言媒介形式决定翻译的文体特点及其出现频率,并据此提出了语言变体翻译的策略模式。西班牙学者Sánchez[8]借助社会语言学的观点,阐述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境和语域理论与方言翻译的关系,认为方言翻译既是语言翻译又是文化翻译。
第二,从社会文化语境视角对方言翻译进行探讨。土耳其学者Erkazanci-Durmus[9]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意识形态对边缘语言翻译的社会制约作用。Berthele[10]认为,只有将译本放入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能对方言翻译的策略进行评估和选择。
第三,根据译文在目的语国家中的接受程度来探讨方言翻译策略。但是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如Leppihalme[11]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译文语言的标准化不会对译文的接受带来大的影响,而Herrera[12]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标准化语言会阻碍译本的接受度。
西方学者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在向更精细、更深化、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二)国内方言翻译研究综述
中国学者对方言翻译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至唐朝玄奘“五不翻”中的“此无故”原则,此后,虽也有学者论及方言翻译,但论述不够系统、深入。
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上1996—2016年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96—2016年间发表的方言翻译研究成果统计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方言翻译。对方言翻译的探讨在21世纪初进入一个小高潮,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韩子满[13-14]、黄忠廉[15]、汪宝荣[16-19]、桑仲刚[20]等。
韩子满[13-14]根据个案研究提出了两种方言翻译方法:如果原文本中方言的使用是为了体现人物的受教育程度或者社会地位,译者可以采用口语话的表达方式来翻译原文本中的方言;如果原文本中的方言只是反映地域差异,译者可以采用加注的方式,补充解释无法在目的语文本中再现的美学效果。黄忠廉[15]从理论高度总结了七种作用各异的方言翻译转换机制,在同一个文本中这七大机制可以单项运作,也可双项或者三项运作。汪宝荣[16-19]从社会学视域下探讨了方言翻译的规范问题,认为方言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规范,而译者遵循的翻译规范受制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作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桑仲刚[20]则从社会文化大语境出发,认为译者的方言翻译决策受到社会文化语境、译者语言习惯、源语文本功能等因素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方言翻译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翻译学角度出发对文学个案的批判——解释性研究。
二、方言翻译的规范化研究
描述翻译学派认为,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译者的翻译决策总会受到所处文化的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全忠实于原文或者与原文绝对对等的译文是不存在的。
(一)翻译规范理论
翻译规范理论由以色列学者Gideon Toury[21]29-56提出。他认为,翻译活动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译文是“目的语文化的产物”,受译文社会文化的规范制约。Toury指出,规范是“特定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如对错与否、适当与否)转化而成的、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行动指令”[21]56。Toury根据翻译的特殊性,提出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包括起始规范(initial norms)、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Toury认为,翻译时“译者或委身于原文的文本关系以及包含、表达在其中的规范,或倾向于使用目的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抑或其中某一部分的语言和文学规范”[21]54。如果译者选择前者,委身于原文的文本关系以及包含、表达在其中的规范,那么译文的充分性就高;如果译者倾向于后者,译文的可接受度就高。然而,这并不是说译文的充分性高,其接受性就一定会低。译文的接受性和充分性并非相互排斥的独立体,译文虽然可能会出现对原文某种程度上的偏离,但是上乘的译文应是接受性和充分性都很高的佳作。
(二)衡量译者方言翻译的规范化参数
汪宝荣[19]参照以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为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体,确立了可模糊量化的5个参数,其界定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了汪宝荣的可模糊量化参数对《孔乙己》中的方言翻译规范进行描述分析,并据此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原因。
(三)译者方言翻译的规范性
鲁迅的作品不仅思想深刻、见解透彻、富有内涵,而且语言幽默凝练且又不失锐利。王士菁[22]59对鲁迅作品的语言运用进行了概括,认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说来有三个来源:古代汉语、外来语和现代人口头上日常使用的活的语言。三者之中,后者又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口头上日常使用的活的语言就包括方言土语。鲁迅出生于绍兴,其作品必然带有成长环境的痕迹。因此,受其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小说中有些方言的使用是无意识的行为,比如对“伊”“茴香豆”“小栓的爹”“热蓬蓬冒烟”“乌篷船”等的使用。然而,为了凸显作品的主题、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创造独特的写作风格、再现地域文化,小说中很多方言的运用是鲁迅故意而为之的。

表1 可模糊量化的译文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参数
1.译者方言翻译的规范性分析
由于鲁迅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其小说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精彩、鲜活、形象、生动的地方话——绍兴方言,不仅为他的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和真实感。
例1盐煮笋
译文1:salted bamboo shoots[23]37
译文2:bamboo shoots[24]42
茴香豆
译文1:peas flavored with aniseed[23]37
译文2:fennel-flavored beans[24]42
“盐煮笋”和“茴香豆”对很多绍兴人来说是必备的下酒菜。“盐煮笋”是用盐水煮过的竹笋。此处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1对原文中该词的指称意义保留更充分,且无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非强制性偏离,所以译文的充分性很高,而且译文完全符合目的语的用语习惯和规范,接受性也很高。“茴香豆”以蚕豆为食材,加以茴香、桂皮等烹制而成。根据维基百科,“pea”主要指豌豆,而“bean”在12世纪之前主要指蚕豆或者其他豆科植物的种子,比“pea”要大,后来,“bean”被用来统称“豆”。所以,对于“茴香豆”,莱尔的译文2指称意义传递的充分性更高。
作家在进行小说创造时,为了凸显某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或者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会有意地使用时间方言和个人方言。
例2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译文1:He used so many archaisms in his spee-ch…[23]37
译文2:When he talked, he always larded whatever he had to say withlo,forsooth,verily,nay…[24]43
“之、乎、者、也”是古代汉语中起辅助作用的文言虚词,在现代白话文,尤其是口语中已基本不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词也会被用来讽刺某人说话喜欢咬文嚼字。孔乙己一贫如洗,潦倒不堪,但却自命不凡,时时端着读书人的架子,不屑与“短衣帮”为伍。时间方言在此的功能就是强调社会阶层的不同,体现人物的受教育程度或者社会地位。译文1用“archaisms”翻译“之乎者也”,传达了原语的指称意义,保留了原语的信息功能,但却没有传达出原文中的口语特征,人际意义传达失效。译文的可接受性较高但是充分性一般。译文2中莱尔使用古典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英语词汇“lo, forsooth, verily, nay”翻译“之乎者也”,并使用斜体对其进行强调,不仅实现了语义对等,也保留了原文中蕴含的交际价值,读者可以从中明显地感知孔乙己在语言使用上和酒馆里其他酒客的差异。由于担心读者对译者在此使用古英语翻译的意图不够了解,莱尔还增加了脚注,对此进行解释说明。相较而言,此处莱尔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都很高,在人际意义和概念意义的传递上要略胜于杨译。
例3“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译文1:“Taking books can’t be counted as stealing… taking books…for a scholar…can’t be counted as stealing.”[23]39
译文2:“The purloining of volumes, good sir, cannot be counted as theft. The purloining of volume is, after all, something that falls we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scholarly life. How can it be considered mere theft?”[24]44
“窃”和“偷”本是同义词,然而孔乙己却竭力争辩,认为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最多也只是“窃”。由此,孔乙己清高、迂腐的形象尽收读者眼底。杨宪益使用降格的方式,用无情感色彩的一般用词“take”淡化“偷”的意思,而莱尔则采用升格的方式,用更加正式的词汇“purloin”来翻译“窃”,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同,然而殊途同归、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复现孔乙己无力的强词夺理。因此,两个译文都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然而,虽然孔乙己是一个读书人,但是他穷困潦倒,又没有进学,“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所以他只能借助自己的衣着和言语表明自己与“短衣帮”身份不同,社会地位更高。笔者认为此处莱尔的升格处理方法更能传达出原文的交际意义,更有助于塑造孔乙己迂腐、可笑、可悲的读书人形象,译文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都很高。
2.译者方言翻译的规范性解释
通过对上述例子的分析,笔者认为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与莱尔的译文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上都处于中上水平,但相较而言,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方面都要略低于莱尔的译文。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译者的翻译诗学影响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杨宪益曾对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做出解释:“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25]84“总的原则,我认为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或减少。把‘一朵花’译成‘一朵玫瑰花’不对;把‘一朵红花’译成‘一朵花’也不合适。”[26]83-84而莱尔在“译序”[24]中说:“鲁迅是一位风格大师,我选择了努力在译文中表现鲁迅风格的某些方面。”与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相比,莱尔译文的最大特色就是努力再现鲁迅小说的独特风格,并增加了大量的脚注为读者提供历史及文化背景知识,既提高了译文的充分性,也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莱尔译文对鲁迅小说风格的再现是非常成功的,寇志明[27]对莱尔译文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评价鲁迅小说翻译的得失,不应以字面忠实为准绳,而应看译文是否再现了鲁迅辛辣、睿智的风格,对语境的匠心独运,以及作者塑造的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时至今日,还没有译者像莱尔一样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国内主流的翻译规范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决策。中国文化自清末就处于弱势地位,主流翻译规范强调重视翻译的充分性。因此,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必然受到当时中国国内主流翻译规范的制约,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不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作品在美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在美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因此莱尔注重译文的充分性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决策。杨宪益、戴乃迭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不明确、不具体。他们的目标读者可能是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甚至可能是非洲人或者亚洲人,可能是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知识的学者,也可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的人。唯一能确定的便是这些潜在读者能读懂英语。对目标读者的泛化定位使他们很难把握受众的审美期望和文学品位。因此,为了稳妥起见,杨宪益、戴乃迭便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莱尔的目标读者并“不是仅限于那些原本就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即使没有注释也能够阅读的读者”[24]xlii。莱尔的目标读者是广大普通的读者,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他就不仅需要考虑译文的充分性,也要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诠释翻译法便成了他翻译策略的首选。
第四,翻译赞助人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决策。杨宪益、戴乃迭供职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因此北京外文出版社便是他们翻译事业的赞助人,他们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赞助人的制约,自由创作的空间不大。而莱尔是学术型译者,他从事鲁迅作品翻译的驱动力是出自对鲁迅作品的喜爱,目的是把鲁迅的作品推广给更多的美国人阅读,译者主体性较强。因此,他的翻译手段灵活,采用夸张、阐释等多种手段尽量再现鲁迅幽默而犀利的文风。
三、结语
“方言土语”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传承者、直接表现者和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方言都能表现出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个性特点,都积淀了深厚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恰到好处的方言运用,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地域文化特性的凸显,对作家表达生活认识以及对作品语言的审美能起到很大作用。”[28]32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国经典作品中的方言时都非常谨慎。然而,仔细阅读不同版本的译作,读者会发现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
本文的研究表明,经过译者的翻译行为,同样的“方言土语”在译文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原因就在于不同译者遵循了不同的翻译规范,采用了相异的翻译策略,而这与译者的翻译诗学、所在社会的主流翻译规范、对目标语读者的定位以及翻译赞助人等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