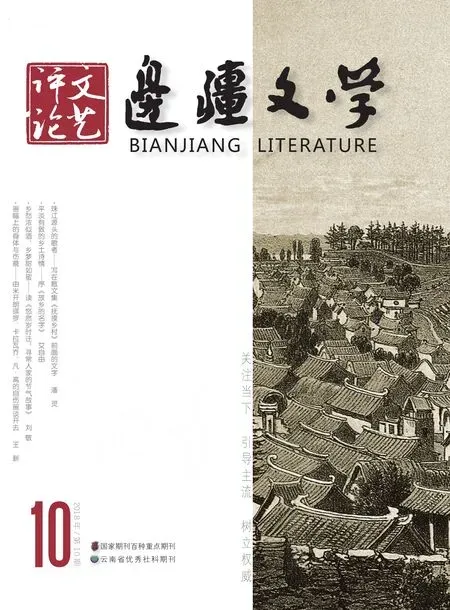吕翼长篇小说《寒门》的新乡土小说书写意义
朱海燕
迎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旭日阳光,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或者常被称作乌蒙山腹地的昭通,出现了一股文学创作的力量,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端,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盛,以致蔚为壮观。进入2000年以来,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更加凸显,尤其以长辈作家夏天敏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得2005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将昭通文学创作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一是凸显了昭通作家创作的实力,二是带动了外界对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的关注,三是带动了昭通文学整体创作的动力。时至今天,昭通文学创作一直在持续发展,一些中青年作家显示出了创作的强势劲头,吕翼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昭通作家,主要以中长篇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书写,已出版的小说集有《灵魂游荡的村庄》《割不断的枯藤》《别惊飞了鸟》,长篇小说有《土脉》《村庄的喊叫》《疼痛的龙头山》《寒门》等。吕翼对小说创作持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眼光时刻关注乡村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关注着底层民众生存的意义,探索着人性的复杂与闪光点。
吕翼现为云南省作协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签约作家,中国作协重点题材作品签约作家。他对于故土的关注,对于乡村叙事的执着,对于“三农”问题的深刻思考,使得其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2017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寒门》,书名虽然为《寒门》,乍一看上去,容易让人联想起近几年新闻报道之“寒门学子放弃高考无奈之举”,或者每逢高考之时,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讨论“高考真是寒门难出贵子?”“学历真的能改变寒门学子的命运吗?”“高考对寒门学子意味着什么?”等等。的确,吕翼长篇小说《寒门》确实是从敏感的高考制度入手,以一个中国西南偏远山区的村庄——碓房村作为乡村缩影,并以碓房村冯家、赵家、万家三家孩子在高考影响下各自不同的命运及发展为叙事重点,但是纵观全书,作家的创作主旨并不是借小说反思高考制度,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对高考制度的批判或者赞扬态度。作者是把高考这一敏感话题,这一自“文革”结束所恢复,影响众多社会阶层命运的人才选拔制度,切入到中国的乡土社会,以碓房村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把高考作为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以此展示了20世纪后20年到21世纪初十几年这个历史阶段,农民心态行为的变异以及思想观念的嬗变。没有史诗般的宏大视角,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没有风起云涌斗争发展,但《寒门》这部长篇小说在今天的新乡土小说书写中,却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寒门》这部27万字的长篇小说,打破长期大部分作家对新乡土小说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书写。而是在恢复高考40年的今天,把高考这一中国选拔人才的制度方式作为切入点,就像照相机的长焦距,深入到中国西南边区封闭的村庄,透过长焦距的镜头,看高考支配的村庄众生相。中国的乡土小说起源于20世纪初,鲁迅从文化视角对乡土中国封建性、人性、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和揭露;沈从文则从“真善美”方面展示着乡土中国的温情,反衬当时的战乱与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乡土小说,承担着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现代性的启蒙重任,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充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刷新着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度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现代化转型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把国人概念中的“乡村”挤进了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所以乡土小说创作面对的已经不是相对自足的“乡土经验”,那么表现在文本创作中,更多的却是“乡下人进城”“打工文学”“城市价值观对农村人的侵蚀”或者“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挤压”等等。抛却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新乡土作家的作品不论,但就昭通作家群中的作家也就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表现,比如夏天敏在《接吻长安街》中写道:“在长安街看着望不到头的车阵,看滚滚人流,你觉得自己就是一粒砂子,一粒随时可以被风吹走,吹走了不会起任何反响的砂子”;刘平勇中篇小说集《天堂邂逅》第一篇小说《天堂邂逅》写进城谋生的小摊贩张大鹏,杀死城管队长何胜利后畏罪自杀;《找啊找》中进城寻找丈夫的农村妇女赵岚失手杀了丈夫的情人梅子,身陷囹圄;《茶花的月亮》中清纯善良的茶花被城里的箫剑吸引后,春心荡漾,进城找箫剑无果后沦为失足女,最终遭凶杀身首分离等。在这些文学创作中,城乡差距的悬殊,农村人因为乡村匮乏的物质环境而到城市“讨生活”,城市是农村人幻想的“富裕天堂”,这种从乡到城的过渡中,乡不再是田园的乡,城也并不是理想实现的天堂,异化堕落、身体致疾、精神失落、心灵失去皈依,是大多数新乡土小说表现的对象。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以降中国文学最繁盛丰茂的叙事文学之一,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城市与乡村两大文化系统与人生样态相互碰撞的历史漩流中激荡流变,‘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是其基本内核。90年代以后,新乡土小说跨越40年代至8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重续此前城/乡二重奏的现代化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
的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在城与乡的叙事模式,及城市形象与乡村形象的塑造中,使得中国的乡土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迷状态中走了出来,丰富着中国的当代文学,并占据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模式化是特点也是禁锢,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新乡土小说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化书写方式,无疑是“问题小说”的一种变相呈现,本质上仍然持着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创作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文学作为社会发展的表征,向我们揭示社会转型期,乡村到城市,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带给我们的文本感受大多是乡村苦难,农民焦虑,被金钱异化,小农意识,价值观畸形……虽然大部分作家对农村、农民持着同情和悲悯的情怀,但不可否认,他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绝望,或者苦难无边的感性冲击,而很少理性的思索,思索现代化转型中乡土中国的出路问题。
昭通作为乌蒙山腹地的一块土地,一直属于中国欠发达的地区,拿当下的城市发展等级划分,就昭通作为市级单位,在国内也只属于五线城市行列,那么昭通市辖区的其他区域,城镇化进程也就相对比较缓慢。吕翼作为昭通的一个彝族作家,生于昭通农村,工作于昭通城,从来没有离开过昭通这块土地,所以其作品中“乡土”书写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是因为没有“离开”就没有“归来”,就没有对自己熟悉的这块乡土“间离”化审美,他看待自己生活的乡土,就像母亲看待怀中的孩子一样,具有天然的血脉情感。所以吕翼一直以一种博爱温和的情感书写着这块土地,没有强烈的批判与人性揭露,没有让笔下的村长有“衣不遮体”之感,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反映在其作品中,就表现为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土脉》讲述了彝族龙家三代人为核心的红泥村人的坎坷命运和对土地情感,作者蕴含在文本中的情感诉求像书名一样,具有深厚的“土地情结”;“杨树村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对乡风民俗,神秘传奇,性情人性等的书写,则重在展示乡村日常生活样态。
在《寒门》这部小说中,作者同样持着相同的乡土书写方式,所不同的是,《寒门》对于乡土的书写,介入视角比较开阔,与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当今教育改革的热点“高考制度”作为切入点,并以此来书写西南边区一个封闭的村庄“碓房村”的故事。因为介入视角开阔的原因,所以作者笔下的“碓房村”就具有了典型的特征,这个碓房村不仅是属于昭通的碓房村,也是属于中国的碓房村,它以农村出身的孩子求学为主线叙述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任何一个中国的乡村社会家庭都避免不了的,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之说,到后来的“知识改变命运”之说,通过制度性的选拔考试,是底层人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唯一途径。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它就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观念,尤其是前些年,拿“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让高考成为多少寒门学子心目中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高考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寒门学子,也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农村家庭,那么以此视角书写中国的乡土社会,既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注,又有对乡土社会时代变迁,所带来的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思考。高考是城的高考,也是乡的高考,在《寒门》中,虽然有冯婶带冯维聪到省城看精神病被医药骗子所忽悠,以及离家出走的冯天香到东南沿海都市打工从事不正经职业的书写,但那不是整部小说的重点,“城”在小说中不是“乡”裂变的导火索,也不是作为“他者”视角,构建乡土形象的参照物。
对应作者独特的叙事切入视角,小说采用的是完整的乡土经验叙事模式,把碓房村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叙述对象,重点以冯敬谷一家为叙事线索,兼及赵成贵、万礼智两家。冯敬谷家的三个孩子冯天香、冯维聪、冯天俊和冯春雨,赵家的赵得位与万家的万勇,六个孩子与高考紧密挂钩,从他们读小学到上大学到参加工作,这几个孩子的发展历程,是乡土中国一代农村娃成长的缩影;同时他们的父辈也是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望子成龙”的心态,还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儿读书”的决心,在这一点上,碓房村的父辈就是千千万万个农村的父母的真实写照。纵观小说构建的整体乡土面貌:贫穷的碓房村,苦苦挣扎的村民,以万家为权力代表的乡村势力对乡村政治伦理秩序的管控,生活重压下被高考逼疯的冯维聪,为获得高考奖反复高考的冯春雨,脑子灵活文学才华突出开广告公司挣钱的赵得位,还有为孩子付出所有一辈子心血、认定高考是唯一出路的冯敬谷、赵成贵以及万礼智等父辈农民,这样乡土的人与事,是当代中国农村最熟悉的场景。
但是作者笔下的碓房村又是个性的。从自然生态环境上讲“碓房村是茫茫无边的乌蒙山区里一个小小的村落,虽然隔酒州县城有五十多里,略显偏僻,周围是山,交通曲折,但怀抱着上千亩的良田沃土。那土层至少是上万年的堆积,黑得发亮,黑得发臭”;从农业生产状况上讲,“因为谷多,谷要脱壳,这里的石碓窝就多,几乎家家都有一个一抱大的碓窝。而生产队里,专门备下几大间房摆碓窝,数十个大碓窝,青石琢成,结实敦实,一字摆开,大半截塞在土里。”;从乡风民俗上讲,碓房村人对老人过世极其重视,“请道士先生,扎纸火,买烟酒鞭炮,办猪羊祭”,同时,信鬼弄神“赵婶是村里的巫师,常和神呀、鬼呀打交道……村里村外,好多人家关于求神打卦的事、生老病死的事、家里丢东西的事,一般都要问她”;从精神生活上讲,赵婶用巫术为冯维聪治病。碓房村还流行以一种说法,就是刚死去的人的脑髓可以治病,效果非常好,为此冯婶冲进刑场去收刚被行刑犯人的脑髓,这无疑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而坟地更有讲究,相信到了阴间的长者,会给后辈以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又实实在在的庇佑。如果长者的棺木埋在龙脉上,后辈就会通达顺畅,迟早是要出达官贵人。”为此冯敬谷、万礼智都请阴阳先生看过风水,在迁坟时候还闹过笑话。所以,碓房村是个性的中国西南偏远山区的碓房村,是封闭保守的碓房村,是物质匮乏,精神也略带愚昧的碓房村。
但是碓房村落后愚昧归落后愚昧,碓房村人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毅力,碓房村人贫穷,但穷得有骨气有正气。在冯天香出走后,冯家收到一大笔汇款,被外界猜测为来历不正经的钱,冯敬谷与冯婶为孩子的学费“跑了好些家,纸烟抽掉一包,好话说尽两筐,时间磨掉半夜,嘴上起了凉浆大泡,却一分钱也没有借到时”都没有动用那笔钱。冯婶到邮局去问,整不清汇款人是谁,退钱找不到退处,她还要弄清楚,如果钱是冯天香寄的,还要看钱的来路,如果是脏的就不用,如果有人寄错了还是要还的。冯天香换着地址与姓名寄给冯家很多钱,在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没动过那笔钱,家里的孩子也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刚正有骨气,上学及其需要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提出动用那笔钱,冯维聪看着父亲为借钱伤脑筋,觉得自己是累赘,服下农药想要了结生命;冯家受赵四之托,在自己养三个孩子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对赵四捡来的孩子冯春雨视如己出,把她培养成了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急剧地转型,经济领域的变革也冲击了人的价值观,人被物欲所奴役,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但在碓房村,作为偏僻乡村的农民,木讷老实,诚实守信,快被生活逼疯的时候,他们仍保持着铮铮铁骨,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没骨气。在碓房村,最高的精神追求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他们建孔庙,祭孔子,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碓房村有三件宝,前两件和土地有关,与肚皮有关:碓窝、稻谷,这不用多说。第三个宝,说的是村庄精神世界里的东西,读书人说的上层建筑——孔庙。”孔圣人生日那天,村里人隆重祭孔,曾经赵四在“破四旧”运动中,为了维护孔庙,为了保护孔圣人的泥像,被打残废,并导致了一生连家都没建立的悲剧,最后赵四死在了为修教室而倒塌的泥墙中。没赶上祭祀仪式,冯维聪虔诚地自雕孔圣人塑像,摆在堂屋正中,冯家孩子经常跪拜,就在冯天俊到城市漂泊之时,仍然怀揣孔圣人像,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虔诚,代表着碓房村人对知识的景仰与尊重。哪怕是冯天香在外靠出卖肉体挣钱之后,回到碓房村仍然想着重修孔庙,捐资助学。可以说,碓房村是偏僻落后的,但碓房村人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着中国大地的时候,当一切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当大众文化以感官享受建构着国人浅薄的审美观时,当娱乐精神至上的时候,碓房村,作为一个相对保守、乡土经验自足的村庄,由自己独特的精神信仰引领着,走向了新生活。在小说的结尾,碓房村得到了省教育厅的支持,教育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高考疯子”冯维聪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研究所的关注,碓房村也引来了外商,那是学有所成的冯春雨个人发展后对家乡的反哺。曾经执着于高考的碓房村的年轻人对学历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对知识依然尊重。碓房村人,迎着新生活的阳光,奔向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曾经有学者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特征这样判断“一是村庄社会多元化, 异质性增加;二是地方性共识锐减,村庄传统规范的力量渐弱;三是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丧失,更多的依赖村庄外部力量。”的确,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也使封闭的乡村社会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敞开,新的思想和思潮改变着农村人的观念,农村固有的社会秩序也在被瓦解着,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也与土地产生了疏离感。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除却国家政治层面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照,今天的农村,今天的农民,该何去何从,是迷茫,是守旧,是完全地失去自我,还是依靠自身固有的特质,改变不适宜的一些观念,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谋得自身的发展?无疑,《寒门》这部小说,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作为关注农村农民发展,并常写三农题材的作家吕翼,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乡土中国,用作品表达着自己的思考,他没有把新乡土小说的书写仅仅停留在“问题”的揭露上,而是针对中国的乡土现实,从内部审视中国农村发展的出路问题。
今天的农村,外部国家政策扶持是一方面,作为乡村自身,也应该审视自身,是否有像碓房村那样的文化积淀,是否有坚定的精神信仰,是否有恒定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定位。“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 , 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碓房村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就体现在它的精神心态文化层的稳定性上,碓房村人追求“寒门贵子”的理想,碓房村人对待知识像信奉宗教一样虔诚,碓房村人守信义,碓房村人贫穷但对金钱“取之有道”,碓房村人发家发达后不忘本……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比可贵的乡村品质,是它指领着碓房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观念,没有迷茫,没有堕落,价值观没有被现代化进程冲击得七零八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一个国家如此,那么于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如此,于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一个乡村发展更是如此,作家吕翼借《寒门》思考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此。
所以,纵观整部小说,虽然在情节构思与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冯天香为了减轻家里负担,离家出走,到东南沿海谋生路,这样一个农家姑娘,渴望上学,渴望知识,返回家乡后对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但是作家对其情节的设置就落入了俗套,冯天香在外谋生的手段好像与人物秉性出现了错位,当然也存着作家对现代都市异化人的想象。但这些并不影响《寒门》在当今文学语境中新乡土小说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肖文虎 国画 箐中柿子红
【注释】
[1] 程丽蓉.新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内涵[J].北方论丛,2010(4):3.
[2] 杨柳.刘小峰.乡村社会巨变与农村研究进路——以《乡土中国》与《新乡土中国》为范例的比较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9):155.
[3] 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J].天津社会科学,200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