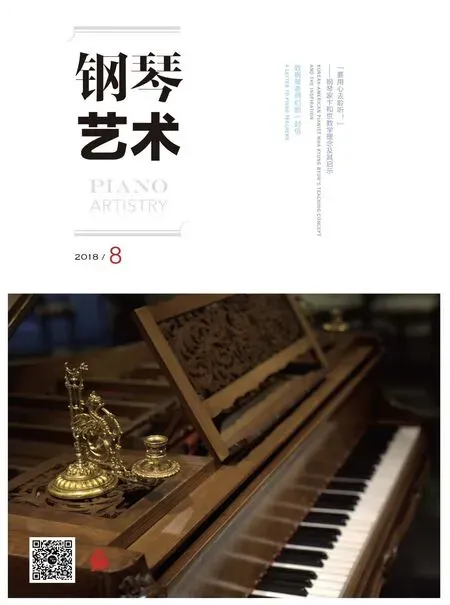“冷门曲目”的经验分享
文/ 杰米·尼古拉斯
编译/郭丽君

土生土长的加拿大钢琴家马克-安德烈·哈梅林(Marc-Andre Hamelin)的精湛技艺并不被大多数人瞩目,但他在探索自己未知的音乐曲目上却有着超乎常人和孜孜不倦的热情,这些都使得他在当今的钢琴领域有着不可小觑、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本文作者杰米·尼古拉斯(Jeremy Nicolas )与钢琴家着重探讨了大脑在面对音乐难题时是如何解决的这一重要问题,以及钢琴家自身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在我们开始之前你先听听这个。” 哈梅林翻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播放了由两把小号演奏的《胡梅尔小号协奏曲》(Hummel’s Trumpet Concerto)的最后一个乐章,其中一把小号的演奏高于原来协奏曲一个八度的主旋律线,而另一把小号则吹的是低一个八度的主旋律, 哈梅林为此笑得前仰后合,这种笑声确实非常具有感染力。“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吗?”由于晚上还要飞往都柏林,他玩笑道。
就在我们见面的头天晚上,他与利夫·奥韦·安兹涅斯(Leif Ove Andsnes)一起在威格莫音乐厅(Wigmore Hall)弹了一场双钢琴音乐会,曲目有莫扎特、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双钢琴协奏曲《春之祭》)的作品。他们两人仅仅在欧洲准备了几天(这些曲目已准备要录制专辑),并已经连续两晚在德国和荷兰演奏了这些曲目,且在这之后还要飞往伦敦。而且这次音乐会之前他们其实是非常缺乏睡眠的,幸亏演出当天下午打了一小会儿盹儿才刚好维持状态。“这些背后的奔波疲惫,听众是无从而知的,他们以为只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买了票来与音乐家分享音乐而已。”
我与哈梅林相识已25年了,他的演奏生涯已将近三十年,曾经录制过一些我的声乐作品(和他的前妻,女高音歌唱家Jody Applebaum)。我们每次碰面,都会热情地分享彼此的感想。这次在这样的场合下,他更想表达自己的一些音乐观点,并且说着就走到一架钢琴前。在这之前,我从没注意到他有这么一双轻巧灵活的手。他向我展示双手手掌的跨度,左手的降D—F—降A—降D—F;右手的降A—降D—F—降A—降D。“其实我的手很宽,但以前总被认为是手指较细。事实是我的手掌要比他们想象中更厚实,手指也更长。”说着,他弹起了贝多芬《“皇帝”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中的降E大调的一组三连音。“我发现弹奏降E音和降B音中间的还原G音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指法,按说这不应该啊……”哈梅林一边嘀咕一边在琴上比画着自己口中的音乐片段。
这次我们的见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讨论最近由亥伯龙(Hyperion,英国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发行他的梅特纳《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唱片的事情,由俄罗斯青年指挥家弗拉迪米尔·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和伦敦爱乐乐团(LPO)协奏。对于梅特纳的作品,他似乎总是饱含激情地去诠释(他录制的所有奏鸣曲作品在很多年里都保持在可作为主要参考标准的高水平上,为现在的“Dover版”再版树立了非常重要的水准标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吸引力让他对作曲家如此般地了解?“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诚心。就像拉赫玛尼诺夫,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去打动听众。我经常感觉到梅特纳好像是在讲述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他努力将听者的意识和感观一同拉进所描绘的世界当中。这个他营造的世界不太容易进入,但一旦被这种画面感所渗透或感染,他的这种力量就会牢牢将你吸引住。我是从他弹《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一段录音中感受到的。最初,我以为听众会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作品,但从最近一场演出中惊讶地发现听众很难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创作手法确实是错综复杂和不易懂的,因为梅特纳全部都是运用非常少量的主题和动机去发展变化出相应的音乐段落。几乎所有的连接句或发展手法都是与主题相关的。”哈梅林说道。
那么为什么哈梅林认为梅特纳的作品不是特别容易被理解呢?他说道:“听众们需要做一些功课才能懂,因为他的作品并不像拉赫玛尼诺夫的一样经常拿来和别的音乐比较,而且也很难去比较。就像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没有几个乐团能做到随时都能演奏,这对于一个交响乐团来说,基本表示乐团并不乐意去演奏梅特纳的作品。”
哈梅林认为,梅特纳应是众多著名作曲家中的其中一个,他只是没有被公平对待,略微受到大众的忽视。并且他应该在唱片界获得殊荣,正如阿尔坎(Alkan)、布佐尼(Busoni)、卡托瓦(Catoire)、杜卡斯(Decaux)、埃克哈特·克拉麦特(Eckhardt-Crammate)、菲尔德曼(Feldman)、戈多夫斯基(Godowsky)……弗雷德里克·谢夫斯基 (Frederic Rzewski)、索拉布吉(Sorabji)、 图依乐(Thuille)、沃尔普(Wolpe),等等,这些印刻在钢琴唱片上的名字。正是这种对音乐持续不断的探索,才使哈梅林赢得了他在音乐界的独特声誉,加之他惊人的聪慧才智、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和强大的技术能力,让那些同龄的佼佼者也羡慕不已。在音乐上,他的演奏几乎不动声色,即使在演奏最难攻克的作品也是如此,这一点非常令人惊讶(当然,会有一些观众认为这种演奏是“无聊”的,然而哈梅林得知后也只用自谦的话语予以回应)。
那什么是哈梅林的“小秘密”呢?他说:“我会在这一部分的谈话中花尽量多的时间,这是一个艺术家与听众之间的交流。但有几件事情我必须还是得拉回现实。首先,演奏中夸张的肢体动作是很好的个人特征,在音乐会中能够把某些片段很好的传达给台下的听众,也有记忆点。但这并非我本意。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还是要不断地重复。在舞台上,我不是在展示我自己,而是在传达音乐。我更喜欢向人们展示我的发展,或者寻找新的更有趣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你必须尽可能令人信服,而且必须尽可能克服各种障碍,如果你不想让音乐会变成一场‘奇观’的话。我更倾向认为人们来到音乐会‘听’要多于‘看’,当然这种想法可能太幼稚,观众也很想看到手部的动作和弹奏过程。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看法,以后也会为此不断去求证这个的观点。”
匈牙利钢琴家乔治·齐夫拉(George Cziffra)曾经说过,自己之所以能达到那样的演奏效果,是因为自己异常发达的生理和神经反应能力。我觉得这些因素也可能就是哈梅林拥有非凡演奏技能的缘由。“但其实并不是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哈梅林反驳道,“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和声、对位法等理论知识上善于分析,了解音乐的应用机制并且培养出一种能想象得更远的动态音乐思维。尤其是当你头脑中有各种不解时,或你不确定哪部分比较重要时,这种能力就会将这类问题解决。从作曲角度,你必须要了解音乐如何进行,特别是在攻克一些你从没有听过的音乐作品时。就比如莫什科夫斯基的那些美妙的作品,千万不能仅仅是觉得好听就不再认真分析。作曲是一门真正的技艺,必须去悉心钻研作曲家如何将这些音乐元素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对待塞缪尔·法因伯格那样复杂的作品一样,演奏之前的功课应当做足。所以,综合我之前提到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大量的技术练习之外,还要有非常敏锐灵活的音乐思维。”
在我们这次的会面之前,我专门上网查阅了一些有关他的信息,让我对哈梅林所掌握的曲目量和多样性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看到他2017年前四个月的演出曲目:第一首是拉威尔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此时哈梅林插话道:“信不信由你……”),紧接着第二天就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又道:“这首作品已经演奏了快三十年,所以没什么。”)成套的曲目有海顿第58首《C大调奏鸣曲》、法因伯格的两首简短的奏鸣曲、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几首幻想曲;舒曼、舒伯特《降B大调奏鸣曲》(D960);女钢琴家席曼诺夫斯卡(Maria Szymanowska)的夜曲,李斯特、普罗科菲耶夫、法因伯格的奏鸣曲和两首李亚普诺夫(Sergei Lyapunov)的《超技练习曲》。除此之外,还包括一首钢琴四重奏作品的首演、四次演奏梅特纳的作品,以及双钢琴作品,等等。这足以展现哈梅林庞大和多样的曲目存储量,不禁让人赞叹。
至少在我所遇到的钢琴家中,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对钢琴的文学知识了解得如此广博与细致。而这样的哈梅林确实是可被称之为典型,他对掌握音乐的狂热就像杂食性动物般没有什么禁忌。我问他,是否对有些音乐不太涉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曾录制过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的一些左手钢琴和交响乐作品,”哈梅林思考片刻后答道:“我很反感两首施特劳斯的作品,《家庭交响乐增补曲》(Op.73)和《雅典娜祭进行曲》(Op.74),这两首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一无是处,让我很厌烦。”
很多钢琴家可能在选择曲目时都是效仿别人,看别人弹什么就练什么,填鸭式的积攒自己的曲目储备,而且也不超过标准曲目。为何这些钢琴家们没有更多的好奇心呢?到底是为什么?不客气地说,为什么没有更多像哈梅林这样的钢琴家?“你的意思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像我一样傻么?”哈梅林一旁轻声笑道。他承认在自己的早年音乐生涯中没有利用好时间,1985年在卡内基音乐厅赢得“美国国际钢琴比赛”后就受到美国人的经纪与赞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一直弹我热爱的音乐,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指导,就这样一路走来。我曾经犯过的错误之多你难以想象。我的工作完全是随便选的,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也坚持了15年,这就是为什么说自己开始得太晚了”。
这几天他正在筹备的音乐会中还会包含一些比较“罕见”的曲目。他说:“有些曲目,必须得在年轻时候去涉猎,因为只有年轻人才会对奇妙而陌生的事物更加敏锐与好奇,更具吸引力,至少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当我看到一个陌生的乐谱,又没有音像资料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想听这个曲子’!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罗斯拉维茨(Nikolai Roslavets)的一首练习曲的乐谱时,一看到满眼散布着各种双升、双降记号,心里很是发怵。我不得不一个一个地转换过来,虽然花了很多工夫,但是我十分想让这三首练习曲被大众听到。因此,我也很荣幸地录制了这部作品的CD,能够最终促成这张专辑也归功于亥伯龙这样的高品质制作公司,当我一提出想录制这部作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我与他们也是初次合作,但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么晦涩陌生的曲目,也体现了他们的崇高信誉所在。”
哈梅林最后一个想要分享给我们的曲目是,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的《致巴尼塔·马库斯》(For Bunita Marcus),这首作品已经被录制过十几次了,给我非常大的听觉震撼。“这是一首连续72分钟的三重奏作品,乐曲开始处有一个ppp的力度标记,除去特别短的乐句,有大量的重复段落,踏板在全曲始终踩下。”专辑附带的小册子上如是写道。哈梅林也说,他第一次接触这首作品的时候就感受非同一般。“在我这么多年探索钢琴的各种领域难题以来,从没有类似的感受”。
哈梅林自己也作曲,逐渐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向传统的作曲方式靠拢,并且自己演奏这些作品,也取得了一些小有瞩目的成绩。他的《12首小调练习曲》在2010年由彼得斯出版社(Peters)出版发行。接下来问世的作品集是由他十几年来创作的一些小作品整合而成。有《小夜曲》、滑稽的利盖蒂风格的《小狗圆舞曲》,有令人咋舌的如李斯特《匈牙利第二狂想曲》的华彩片段,还有根据1945年的老电影《劳拉》(Laura)的主题曲改编的一首作品,还有一首肖邦/戈多夫斯基的改编练习曲,等等。不过他告诉我,目前他已经越来越少投入精力去创作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越来越侧重于社会性工作,如在圣地亚举办的“La Jolla音乐节”上为大提琴伴奏,为即将举办的“范·克莱本钢琴比赛”的钢琴独奏和钢琴五重奏创作曲目,他还会成为比赛的评委会成员。
“没有作曲家为你创作过作品吗?”“没有,说起来真是可悲,自我成名之后几乎每个和我打过交道的作曲家都表示没办法创作出对我来说有足够难度的乐曲,这一点让我很无奈。他们何尝知道,其实我非常喜欢像雅那切克的《荒草蔓延的小径》(On an Overgrown Path)那样简约却饱含情感世界的音乐小品,这才是我的最爱。”哈梅林回答道。
午餐之后,哈梅林向我透露了一些接下来的主要的独奏工作内容。2018年的夏季他要录制塞缪尔·法因伯格的12首奏鸣曲中的前6首,并且唱片将会在2019年出版问世。“这些作品不是钢琴家们热衷演奏的曲目,”哈梅林向我肯定道。“但他的作品中总有一条独立的声音线,不可被忽视。你们还有时间再听一下塞缪尔的《第一奏鸣曲》吗?”此时,我们的老板默认我们有,哈梅林便演奏了《第一首奏鸣曲》,一曲之后,意犹未尽。“你听说过莱库奥纳(Lecuona)的《埃斯库力亚尔》(Ante el Escorial)吗?”我问哈梅林,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不知道,但我们老板却不知从哪儿挖出一本乐谱(谱面看起来并不简单)。很快,哈梅林便用他敏捷的指尖和高超的视奏功力展现出这首作品的样貌。听罢,晃神间,觉得这首作品很适合作为音乐会结尾的安可曲……“马克,你是不是该出发了?”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