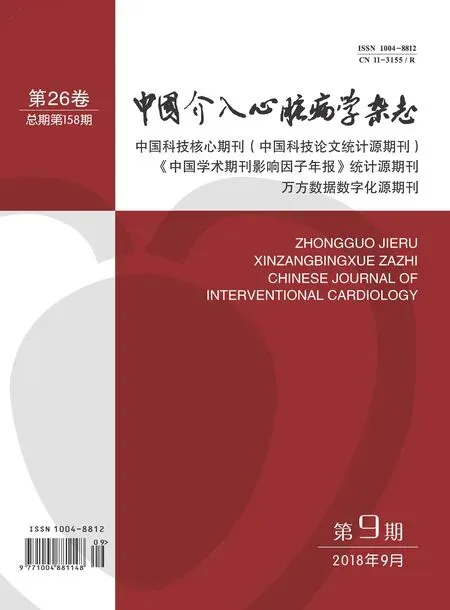利用瞬时无波形比值评估冠状动脉病变及指导血运重建的研究进展
高斯德 刘青波 陈晖
1 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概述
冠状动脉造影至今仍是评估冠状动脉解剖学狭窄程度的核心方法。对于临界病变,主观判断的造影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狭窄程度与心肌缺血的关系,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冠状动脉检查已从单纯的解剖学评价发展至如今的功能学评价,即利用血流或压力指标来综合判定狭窄病变能否继发引起下游供血范围内的心肌缺血[1]。1993年Pijls等[2]提出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verse,FFR),并定义为病变血管提供给心肌的最大血流量(Qs)与该血管完全正常时所提供的最大血流量(Qn)之比,其检测条件需满足低中心静脉压以及腺苷等血管扩张剂诱发的微循环最大充血。因心肌血流量与心外膜冠状动脉灌注压成正比,而与心肌内微循环阻力成反比,若忽略不计微循环最大充血时的阻力因素,则心肌血流量仅受灌注压影响,此时Qs与Qn之比可近似为冠状动脉狭窄远端压力(Pd)与主动脉压力(Pa)之比[3]。
有关FFR指导介入治疗的证据已十分充分[4-6],使其成为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的金标准,并受到国内外权威指南的一致推荐[7-8]。在我国,FFR的应用越来越多,已逐步成为识别临界或复杂病变、指导血运重建以及评估心血管预后的重要手段[9-10]。目前由FFR衍生的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方法不断涌现,大体可分为改良FFR或影像重建FFR[3]。前者旨在简化操作,包括静息压力指标如瞬时无波形比值(instantaneous wave-free ratio,iFR)和静息Pd/Pa以及用对比剂代替腺苷的FFR(cFFR);后者则需对常规造影或CT血管造影的影像序列进行三维重建,从而得出定量血流分数(QFR)以及无创的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 FFR(FFRCT)。
iFR自问世便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无需使用腺苷,iFR可允许操作者对狭窄病变进行更简便、更快速的功能学评估。近年来,针对iFR的研究相继展开,新证据的出现极大肯定了iFR的诊断价值及临床应用前景[11]。基于此,本文将简要回顾iFR的基本原理,并重点阐述iFR相比于FFR的诊断效能以及对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指导意义。
2 iFR的工作原理
Gould等[12]最早通过动物模型证实冠状动脉静息血流在管腔直径不断减少时仍能保持稳定,而最大充盈血流在狭窄至50%时便有明显下降。IDEAL研究[13]在人体中进一步证实冠状动脉跨狭窄压力阶差随病变加重而增加,充盈血流下降显著,但静息血流可凭借微循环阻力的代偿性减低而在较大范围内保持恒定,直至管腔近全阻塞。这为冠状动脉静息压力的测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2年ADVISE研究[14]通过心动周期波形幅度分析(WIA)首次证实iFR的存在。WIA能识别人体冠状动脉血流的6种波形,将压力与流速相比即为阻力指数,可用来评估心动周期中冠状动脉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与FFR不同,iFR无需应用腺苷使微循环达到最大充盈状态。研究者发现在舒张期的某一特定阶段(进入舒张期25%开始,至舒张期结束前5 ms停止),冠状动脉微循环波形处于短暂的静息状态,即瞬时无波形期(wave-free period,WFP)。此时的血流流速比整个心动周期的平均流速高出30%,冠状动脉内压力及血流随管腔狭窄呈共线性下降,微循环阻力最小且相对恒定,从而使心肌血流与灌注压成正比(图1)。类似于FFR的定义,认为在WFP期间跨狭窄处压力的下降程度反映了狭窄使心肌血流量减少的程度,由此可明确狭窄病变的生理学意义。
从本质上看,FFR必须用药物诱导微循环最大充血,其检测需要横跨数个心动周期,从而确保冠状动脉内压力相对稳定。iFR则极大简化了FFR的操作,其关键在于根据静息压力波形识别出特定的WFP期,此时的微循环阻力便相当于最大充血状态,由此测得的Pd与Pa之比即为iFR[14]。
3 iFR相比于FFR的诊断价值
近年来,多项iFR与FFR的比较研究确定了iFR诊断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准确率及应用价值。研究者先后对病变进行iFR及FFR检测,以此评估iFR与FFR的相关性,同时以FFR<0.8作为诊断的金标准,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得出曲线下面积、iFR最佳界值,以及此界值诊断病变功能学狭窄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其中,ADVISE研究[14]率先证实iFR与FFR高度相关且重复性良好,iFR为0.83时诊断效率最高,其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5%和91%,诊断准确率亦高达80%,且iFR基本不受心率、血压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影响。VERIFY研究[15]及VERIFY 2研究[16]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iFR的诊断准确率偏低,故不推荐用于临床决策。Johnson等[17]亦指出用iFR代替FFR存在偏倚。但后续进行的多中心、非随机、前瞻性由中心实验室独立分析的临床研究均证实iFR与FFR具有良好的相关性,iFR最佳界值波动于0.89~0.91,以此界值评估冠状动脉功能学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率均高于预期水平[18-27]。
为进一步提高iFR在灰区范围的诊断价值,Petraco等[26]于2013年提出iFR-FFR杂交技术(hybrid iFRFFR),即联合应用iFR及FFR评估病变,具体为:若iFR<0.86行介入治疗(阳性预测值为92%);若iFR>0.93延迟血运重建(阴性预测值为91%);若iFR在0.86~0.93的灰区范围,则病变的功能意义不甚明确,此时可再应用腺苷行FFR检测,并以FFR 0.8为切点决定是否行血运重建。这一策略可使57%患者避免使用腺苷,且与单用FFR的诊断一致性为95%。随后的ADVISE in-practice研究[18]、ADVISE Ⅱ研究[19]及 PALS 研究[27]亦证实,对于iFR在0.86~0.93的临界病变,联合应用iFR-FFR相比于单用FFR可大幅减少血管扩张剂的使用,同时可确保诊断的准确率高达94%~95%,极大地优化了诊断效能。
除了直接比较iFR与FFR,亦有研究分析了iFR及FFR与心肌缺血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充血狭窄阻力(HSR)为充血状态下跨狭窄的压力阶差与平均峰流速的比值。CLARIFY研究[28]证实iFR及FFR与HSR对冠状动脉狭窄严重度的诊断一致性相当,即便应用腺苷,也并未增加最大充盈下iFR与HSR的一致性。冠状动脉血流储备(CFR)反映了冠状动脉血流从静息增加至最大充血状态的能力。JUSTIFY-CFR研究[29]将CFR作为第三方评价指标,结果发现iFR与CFR的相关性及诊断一致性均显著高于FFR。在HSR基础上以心肌灌注显像(MPS)界定心肌缺血,结果显示iFR及FFR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心肌代谢显像(PET)被认为是心肌血流定量检测的金标准。新近研究证,实由PET得到的无创CFR与有创压力指标iFR及FFR高度相关,若以CFR<2定义心肌缺血,则iFR诊断心肌缺血的准确率与FFR 相似[31]。
综合来看,iFR作为冠状动脉静息压力的评估指标真实可靠,无论是功能性狭窄的诊断,抑或是心肌缺血的评估,iFR均表现出良好的诊断效能,有望成为FFR的无腺苷代替方法。

图1 ADVISE研究中对静息时冠状动脉血流参数的记录(A)以及对iFR的定义(B)。在瞬时无波形期(WFP)冠状动脉微循环阻力最小且相对恒定(A1),且冠状动脉压力与血流速度呈共线性下降(A2),此时冠状动脉狭窄远端压力(Pd)与主动脉压力(Pa)之比即为iFR(B);1 mmHg=0.133 kPa
4 iFR与静息Pd/Pa的相关性
由FFR衍生的冠状动脉静息压力指标除iFR外,还包括静息Pd/Pa。前者为特定WFP期的Pd/Pa,可由单次心动周期波形求出,取值范围较广(95%CI 0.39~1.00);而后者为整个心动周期的Pd/Pa,需连续分析数个波形,取值范围较窄(95%CI 0.59~1.00)[11]。冠状动脉在舒张期产生前向血流,若采用工程学中信号干扰比(SNR)的概念,则舒张期为信号而收缩期为干扰,由于iFR中舒张期的占比要远高于静息Pd/Pa,iFR的SNR值及检测性能亦随之优于静息Pd/Pa[32]。此外,iFR比静息Pd/Pa对压力导丝回撤的敏感性及稳定性更高[33]。目前,静息Pd/Pa尚无公认的诊断界值,亦缺乏指导血运重建的预后资料,致使其临床应用饱受争议。
尽管如此,仍有研究初步探索了静息Pd/Pa与iFR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RESOLVE研究[20]发现iFR与静息Pd/Pa高度相关,且两者与FFR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的一致性显著。最新发布的CONTRAST研究[34]同样肯定了iFR与静息Pd/Pa的相关性,若以iFR 0.89界定心肌缺血,则由ROC曲线求出的静息Pd/Pa最优切点为0.91,其诊断效能令人满意(敏感度91.4%、特异度94.4%、阳性预测值93.3%、阴性预测值92.7%、准确率93.0%)。Lee等[35]在论证iFR与静息Pd/Pa线性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两者的变化与PET测得的狭窄处静息或充血时阻力以及心肌最大血流量的改变密切相关,其中,iFR对解剖学及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更为敏感。此外,iFR与静息Pd/Pa均能反映延迟血运重建的患者在2年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风险(iFR: HR 0.596,95%CI 0.373~0.919,P=0.02;静息 Pd/Pa:HR 0.48,95%CI 0.25~0.923,P=0.027)。iFR 预 测MACE发生率的极差范围明显小于静息Pd/Pa[iFR(3.27 ±3.39)%,静息Pd/Pa(3.85 ± 4.00)%,P<0.001],提示iFR评估心血管预后的精准度更高,这可能与iFR较低的检测变异性相关。
5 iFR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的优势与不足
目前,iFR主要用于评价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功能学意义[36],亦适用于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NSTE-ACS)患者非罪犯血管临界病变的评估[24]。新近研究证实,iFR亦可用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急性期非梗死相关血管的功能学评价。Thim等[37]在对罪犯血管行直接干预后即刻检测非梗死相关血管的iFR,并于随后复测,结果显示iFR对病变前后的分类一致性为78%,而急性期iFR的阴性预测值为89%,这有助于判别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无需干预的非靶血管病变。WAVE研究[38]亦证实STEMI患者在急性期及随后的非急性期检测的非罪犯血管iFR的变化并不显著,且iFR在急性期相比于FFR对非罪犯血管病变的诊断效能良好(iFR界值0.89,敏感度95%,特异度90%,阳性预测值86%,阴性预测值97%,AUC 0.95)。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梗死相关血管的iFR检测存在较大变异,故不推荐使用iFR评价罪犯血管病变[36]。
除了单一病变,iFR仍具有评价冠状动脉串联病变及弥漫性病变的独特优势。Nijjer等[39-40]通过从最远端病变连续性回撤压力导丝而实时监测iFR的变化,并以此拟合生成iFR生理图,这有助于介入医师更有效地识别病变血管的位置、长度及功能意义,进而指导血运重建策略的选择。在串联病变的连续性压力曲线中,跨病变的iFR回升越大,则该病变对血流的影响越显著,建议优先处理。相比于孤立病变的陡峭压力阶差,弥漫性病变的iFR呈持续性及渐进性回升,此时不宜再行支架置入治疗。此外,研究者们设计了能够行虚拟PCI的计算机模拟系统,这一系统可有效预测病变血管在干预后的iFR值,iFR强度(即单位长度下iFR的改变)越大,则支架置入术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善越显著。不同PCI术式所对应的iFR强度亦不同。以此为参考,术者可在实际操作中更有针对性地对多支血管病变进行干预,从而保证在冠状动脉血流最大改善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支架的使用,由此实现最优化的PCI效益。
有关iFR在左主干病变以及分叉病变中的应用尚无相关证据,仍需积累经验。最新研究发现,iFR的诊断效能受冠状动脉病变位置的影响,与FFR相比,iFR评价左主干及前降支近端(LM/pLAD)病变的准确率(73.3%)远低于其他部位的病变(81.8%),原因可能为LM/pLAD所支配的心肌范围较大,致使iFR更易受心肌内微循环阻力的影响而产生测量偏倚[41]。此外,iFR无法用于微循环功能障碍、冠状动脉痉挛及易损斑块的评价[36]。
6 iFR指导的PCI策略对心血管预后的影响
临床结局一向是诊断性试验评价的硬指标。越有价值的检查,其对临床决策的帮助就越大,并对疾病的转归与预后有着深远影响。鉴于iFR在可操作性及诊断效能的双重优势,业界愈加关心iFR能否真正用于临床并指导血运重建。对此,2017年重磅发布的DEFINE-FLAIR研究[42]及iFR-SWEDEHEART研究[43]均证实iFR指导冠心病患者行PCI的心血管获益与FFR相当,就此奠定了iFR在评估冠状动脉临界病变及在指导PCI中的重要地位。两项研究均为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注册研究,分别纳入2492例及2037例患者,按1 : 1随机分为iFR或FFR指导的PCI组,使得两组受试者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表1),研究者以iFR 0.89或FFR 0.8作为单一界值决定血运重建的策略(iFR≤0.89或FFR≤0.8行PCI,iFR>0.89或FFR>0.8行延迟PCI),待评估的临界病变包括稳定性冠心病以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非罪犯血管,主要研究终点由随访1年内的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非计划血运重建组成。次要终点则为iFR与FFR的效价比,如操作时间及不良反应等。其中,iFR-SWEDEHEART研究证实iFR组患者主要研究终点(HR 1.12,95%CI 0.79~1.58,P=0.53)以及全因死亡(HR 1.25,95%CI 0.58~2.66,P=0.57)、非致死性心肌梗死(HR 1.29,95%CI 0.68~2.44,P=0.42)、非计划血运重建(HR 1.04,95%CI 0.69~1.57,P=0.84)等单项事件的发生风险与FFR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FR组患者的平均操作时间及不良反应则显著低于FFR组(P<0.001)。同期发布的DEFINE-FLAIR研究亦证实iFR与FFR指导的PCI治疗效果相当,两组患者发生主要终点事件的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 0.95,95%CI 0.68~1.33,P=0.78),且iFR组患者发生胸部不适的比率明显低于FFR组(P<0.00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项研究均采取了严格的随机对照设计,且样本量远高于既往FFR预后研究的总和(DEFER研究[4],91 例;FAME 研究[5],509 例;FAME 2 研究[6],447例),大幅增加了“iFR指导的PCI效果非劣于FFR”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及推广价值(表2)。在不考虑iFR灰区或iFR-FFR杂交技术的情况下,单以iFR 0.89作为病变是否干预的界值同样可行、有效。鉴于iFR检测能显著减少操作时间及腺苷的不良反应,且有减少支架置入数量的趋势,iFR有望被更多的介入医师采用,从而实现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的普及,并推动冠心病整体介入治疗水平的提高。

表1 iFR或FFR指导PCI预后研究纳入患者的临床资料

表2 iFR与FFR的比较分析
7 小结与展望
冠状动脉的介入治疗已迎来功能学评价及功能学血运重建的时代,借助FFR及其衍生技术,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病变(临界病变、多支病变、串联或弥漫性病变、左主干病变及分叉病变)更多的生理功能信息,以此来评估心肌缺血、指导血运重建,并最终期待能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心血管获益。iFR作为冠状动脉静息压力的评估指标,不仅能简化操作,更能有效评估狭窄病变的生理学意义并指导PCI。目前,iFR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指导意义、复杂病变的评估作用、以及在ACS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尚不十分明确,相信随着越来越多iFR研究的实施、发布,这些问题会愈加清晰,我们也期待iFR这项技术最终能从科研走向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