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一种必需品
橙红青
“如果知道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查理·芒格的这句话应该是在开玩笑,但人们却似乎当真了。世人普遍惧怕失败,千方百计避免失败,甚至试图绕开任何可能与失败有关的道路,更把不败当作至高成就,把求败当作强者发出的挑衅。
然而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努力避免失败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也许,失败并非难以摆脱的烦恼,某些失败甚至值得追求。也许,只有在一开始便将失败纳入目标,才有最后“独孤求败”的机会。也许,失败并非至暗之源,拒绝失败才是。
发现边界
人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极限所在?通过失败,而非成功。12秒01是一个人的百米极限,不是因为他能跑到12秒01,而是因为他每次冲击12秒均以失败告终。成功,意味着还没达到边界。
《超人总动员》《美食总动员》导演、皮克斯动画的布拉德·伯德曾回忆过他刚进迪士尼不久遇到的一件事。当时,老一辈动画大师接连退休,迪士尼打算让一位四十几岁的动画师接手工作室。一部新片的启动会上,这位动画师说:“我对我迄今做的很满意,让我来教你们怎么做。”这番话令他十分泄气。若干年后,成长起来的伯德面对自己手下的人如此说:“做些让你自己也感到害怕的事,那才是你的极限,你可能会失败,但那是每天呼唤你起床的东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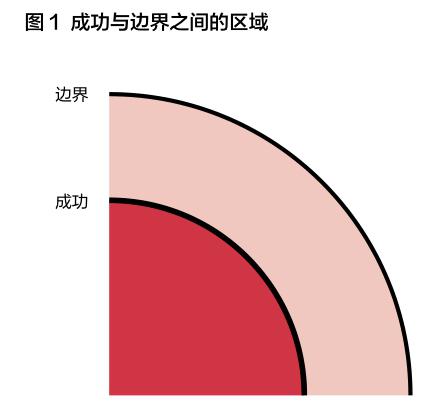
成功与边界之间的区域就是尚未开发的可能性。有些人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探索这片可能性区域(图1)。即便未必同意他们的观点,你也可以问一问自己看到那片空间的感觉,是向往还是恐惧。恐惧意味着当前所在就是你的边界,你将一遍又一遍地用成功来证明、巩固关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设定,但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不会行进到自己真正的边界。
很多企业的经理人在谈到自己的局限时就像在谈板球——一种没体验过也从沒明白过的东西。多么遗憾,他们画地为牢太久了,他们现下的行止范围比那牢又小了不少。他们脑中若有边界,也是自以为的边界。
除了放弃可能性,停留在现有边界也不意味着安全。守成之人倾向于以边际效率最大化为准则,不愿冒险进入低效率期(包括不停失败),如此就难以进入新的疆域。就像两块土地由一条浅溪分隔,不湿鞋是无法到另一块土地去的。等到原有疆域的边际效率也低到一定程度,常常已没有力气挪移,而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过往的成功——包括领域、原则、方法——往往会成为吸引所有资源和注意力的黑洞:一个巨大的沉没成本。
一家处在全面转型期的大型企业,如果每个新项目都是“成功”的,事情往往就要凉了。正如获得好评的演员会遇到压力,制片方、投资方、广告商会要求他们按以前的方式重复出演曾经“成功”过的角色类型,复制——这正是他们被找来的原因,而他们也确实没有把握新尝试是否会成功,此时的他们就会面临痛苦的选择。
在竞争环境里,长期不愿触及边界的最后结果,就是走投无路的死胡同。
感知疼痛
多次、多样的尝试均无胜绩,说明这里确是暂时的边界;一两次失败则提醒我们或许该换个方法(思路、地方、材料、对象……),你碰到的未必是真正的边界。此时的失败叫作“挫折”或许更合适,个人更建议把它们称为“反馈”,这是它们的真正意义所在。每一次行动,不论结果成功还是失败,都可视为一次试验。
多年前,一些美国学者试图解释为什么日本产品受到全球欢迎,为什么日本企业能拥有国际影响力。他们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被注意到的重要原因:日本有大量挑剔的消费者,如果一家公司能满足日本消费者,并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这家公司多半能应付世界上绝大多数消费者;日本有大量最新潮的消费者,能跟上他们,就能领先世界其他市场。这一规律继续扩展就是:在日本国内不算顶尖的企业,在海外也能获得成功,因为它们已被磨砺得足够优秀。
磨砺的基石就是一次次未能令消费者获得满足的“失败”。“好客户”包容我们的不足和疏失,让我们舒服地拿到订单、完成业绩;“坏客户”则令人产生挫败感,他们苛刻、挑剔、要求繁多,企业变着法儿去满足他们,最终也可能只是白忙活。然而,“坏客户”更像是授我以渔,“好客户”则只能给我一条鱼,或许还会让我麻醉和退化。与之类似的还有“好老板”与“坏老板”。
并不是你做得足够好就不会被挑战,而是没有那么多挑战,你不会做得足够好。这是很多人痛苦的领悟。没有对手,自己会变弱而不是变强,垄断巨头和它们的客户深知这一点。
把失败视作反馈,明天的你可能比今天的你更好,成功则没有这个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早失败越好。克尔凯郭尔说:“不冒险非常容易丧失即使在最危险的冒险中也很难丧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如果冒险出了错,生活会用它的惩罚来帮助我;如果完全不冒险,谁来帮助我呢?”
疼痛是有意义的,感觉不到疼痛的孩子识别不出危险,难免意外夭折。焦虑也是有意义的,它帮助人整合,促使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同样地,意料之外的失败更是提供了警报器的功能。沉溺在抗拒失败的情绪里或忽视、掩盖一次次试错,都是在错过检修的机会。
火尚小时,容易扑灭,但不易发现;火到大时,容易发现,但不易扑灭。每个王朝都知道这个道理,却宁愿假装太平盛世,直到无可挽回。
寻找“金蛋”
1637年前后,历史上最著名的“业余”数学家费马在一本古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数学猜想“费马大定理”:当整数n>2,关于x、y、z的方程xn+yn=zn没有正整数解。定理旁边还有一句话:“对这个命题,我有一个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没有人会想到,直到350多年后的1993年,这个猜想才被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证出,恐怕当初费马并没有真正找到答案。
很多人知道故事的头和尾,但不太关注中间,中间过程可以用20世纪上半叶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话来概括。当时有人劝他去证明那个猜想,他说他不会去“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虽然怀尔斯之前没人成功,但3个多世纪里证明费马大定理的努力正如不断下金蛋一般,吸引大量数学家,发展出了很多绝妙的数学理论和方法,甚至还产生了一些数学分支,可以说写出了一卷数学史。这些都远比费马大定理本身更加重要。证明者怀尔斯就曾说:“判断一个数学问题是不是好问题,就看它能否产生新的数学,而无关问题本身。”
相对目标而言,你的努力可能是失败的,但游戏里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藏有各种奖赏。
为此,面对失败,还需要有好奇心和嗅觉。“伟哥”最早的名字叫“西地那非”,是辉瑞制药的科学家们发明的心绞痛新药。首次临床试验时,这种新药(对心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疗效,可是参与试验的男性患者却大多拒绝退回剩余的药片,甚至还向医生索要更多药片。困惑之余,科学家们追寻这个新线索,最终发现了“西地那非”新的可能性:壮阳。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甚至能追溯到“杜康酿酒,其子酿醋”的传说。
把(相对目标而言的)失败的成果当作一粒种子,只要是新的,就去看看、想想这成果增加的可能性在哪里。
而找到“金蛋”的前提是对失败有足够的容忍。
一名篮球运动员的投籃命中率是35%,意味着20次出手会有13次失败。如果要求他不能失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停止投篮。成功或失败有随机因素,我们可以努力扩大成功概率,或增大每次成功的收益,但我们不能停止“投篮”。失败不是失误或过失,不是“不应该”的。失败的可能只是结果,不是行为。
正如优秀的企业会遇到效率魔咒:他们要求每件事都要做成,结果遏制了“投篮”行为,利润率稳步攀升,销售收入却停滞不前,乃至逐级下滑;规条越来越多,方法却越来越少;最终他们发现竞争者越来越少,并非自己一骑绝尘,而是走错了方向。
逃离子宫
《聪明的一休》有一集说,将军足利义满对珍馐美馔都提不起兴趣,怎么换菜换厨师都没用。一休和尚答应了求助,只提出一个要求:一天里,一休要将军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于是,一休带将军去做了一整天粗活。太阳落山,和尚们的粗茶淡饭将军吃得津津有味。缺乏调剂的所谓“理想生活”同样会令人难以忍受。
正如没有起伏的心电图昭示着死亡,失败除了现实功能,在心理上也是有意义的:没有痛苦,快乐会变得很轻;没有地狱,天堂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没有黑夜,白天很快会遭人厌弃。失败固然令人不快,但逃避失败的结果不是长久快乐,恐怕是失去感觉。
总的来说,对我们影响更大的,不是失败带来的痛苦,甚至不是对失败的恐惧,而是这种恐惧导致的回避。芒格大概也知道,希腊神话里,那些预知自己将如何死去的人们,最终死因往往肇始于他们为此采取的防卫措施。
恐惧是一种保护机制,一个通过限制行为来营造安全感的门卫,它站在你与充满可能性的开阔地之间。失败恐惧阻挡的东西如此重要,几乎要剥夺掉我们生之为人最为核心的一些价值。看起来,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保姆,实则被塞回了子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