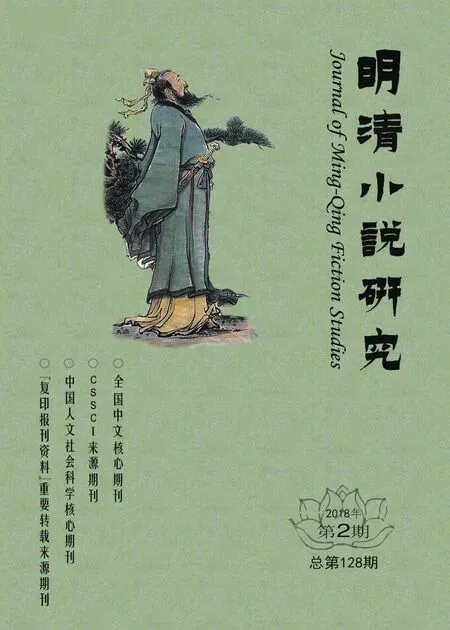大观园创作构思与曹雪芹的人生诉求∗
——兼谈红学理念的冲突及其研究格局走向
·赵建忠·
北京是曹雪芹结束“秦淮旧梦”——江南生活后的归宿,是“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不朽巨著《红楼梦》创作之地,随着“87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播30周年纪念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上演、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及讲习班的开课,使得近年持续的“红学热”达到了高潮。与上述高端文化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化部恭王府系列《红楼梦》讲座的举办,引发了网上几百万“红迷”们的现场关注。笔者参与了全部讲座六场中的两场,其中一场探考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另一场则通过大观园的创作构思探索曹雪芹的人生诉求,并关涉红学理念冲突以及与此相关的当代《红楼梦》研究格局走向问题。
一、大观园原型探考中涉及的红学理念冲突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将作者说成是曹雪芹独立完成尽管一直存在争议,但若说“没有大观园,就没有《红楼梦》”,恐怕不会有任何异议。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大观园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情形,《红楼梦》主体故事是在大观园内发生的,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后,诸钗风流云散,小说到此准备收束,围绕大观园的故事基本写的也差不多了。《红楼梦》本来就有个异名叫《大观琐记》,从这个书名看,顾名思义就是记载大观园里发生过的故事。伴随着《红楼梦》的传播影响,现在北京、上海、河北等地还有大观园实体建筑,足见其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地位。
大观园的研究历来是红学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叙事学中新兴的“庭院叙事”模式,又以新的学术话语将大观园的课题重新激活。所谓“庭院叙事”,属于一种空间叙事手法,曹雪芹的作品之前就有汤显祖在著名的《牡丹亭》传奇剧中对“庭院叙事”有过尝试,《红楼梦》出现之后,对这部作品的续仿更是层出不穷,像《镜花缘》《泣红亭》《海上尘天影》等等,它们的创作旨趣迥异,但其叙事模式确实是对《红楼梦》的因袭甚至某方面还有所拓展。作为“庭院叙事”的个案研究,如今关于大观园的专门论著越来越多,概括而言,研究取向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据《红楼梦》中薛宝钗那句诗“芳园筑向帝城西”去寻觅大观园的“原型”,另一种则认为大观园是曹雪芹心灵的艺术投影,根本不可能在人间找到其具体“遗址”,因此主张研究重点应该通过大观园的创作构思去进一步探索曹雪芹的人生诉求。
就前一种研究思路而言,探寻大观园遗址所在的“帝城”,主要有南京、西京、北京三说。“南京说”主张《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址是南京小仓山的随园。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乾隆时代的袁枚,他在《随园诗话》中明确说过“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袁枚及其《随园诗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名气都很大,“随园”也是南京和全国的名胜古迹,自然“大观园系随园故址”的说法也很有影响①,可是我们从《红楼梦》文本的内证可以看出这一说法的不合逻辑,如原著第五回写宝玉对警幻仙姑说“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说明此刻人在北方,如果宝玉本来就在南京,不应以这种口气表述。又如原著第三十三回写宝玉挨了父亲毒打,贾母很生气,对贾政说:“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说明此刻对话人的环境在南京之外。贾母如果本来就住在南京,怎么会说“回南京去”?显然不合逻辑。再从随园的传承源流考察,“随园”之名虽与接任曹家江宁织造职务、奉旨查封曹家的隋赫德相关,但是即使追溯到他之前,园主也姓吴,与曹家并无瓜葛,曹雪芹以此为蓝本去写《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直接依据不足,何况袁枚自己相关文字也描述过随园与大观园的地理环境无毫厘相似处。这里有必要指出:袁枚比曹雪芹出生早去世晚,又赶上了程伟元、高鹗百二十回印本的风行年代,却对声誉日隆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不置一辞,颇觉怪异!以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及与曹雪芹朋友圈的熟悉程度,本来最有条件澄清很多《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为后人留下宝贵文献,但遗憾的是,他不但没做到,反而还在很多方面给后来的研究者制造了不少混乱;至于“西京说”,其证据就更为薄弱。此说源自民国年间《新光杂志》刊出的一篇作者叫“圣美”的文章,认为《红楼梦》故事的背景在西安,即古称的“长安”或“西京”。论据是:《红楼梦》开篇甄士隐助贾雨村进京是“买舟西上”,书中刘姥姥曾对女婿说“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银子”,薛宝钗写的螃蟹诗,也有“长安涎口盼重阳”句,且八十回后写薛蟠打死人,所递呈文明说案犯“本籍南京,寄寓西京”。其实这些论据禁不住推敲,关于“长安”地名,甲戌本《石头记》“凡例”说的再明白不过:“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因此就不能仅从字面上呆解刘姥姥说的“长安”一词。而宝钗是作诗用典,“长安”不过是用作“京城”的代词,明朝人记北京的书,也题作《长安客游记》,可资佐证。所谓“买舟西上”,贾雨村从苏州出发,必须向西,经扬州、南京,才能北上进京。而写薛蟠打死人后所递呈文,系杂采八十回后情节立论,不足为据。比较而言,还是“北京说”比较靠谱些,其内证在《红楼梦》中也不胜枚举:如林黛玉从扬州坐船入京都,航程应该是南北直通的大运河,清代南方人进京,一般都是取这条水路而行。又如书中叙“宝玉坐车出西城门外,去天齐庙烧香还愿”。按“天齐庙”是东岳庙,即泰山之神,只有北京及华北地区的人才供奉,江南没有。再如《红楼梦》写“炕”的地方很多,北方苦寒,“炕”就成为明显特征。当然,即使确认“帝城”是北京,大观园“遗址”所在的“西”具体地理位置,也存在分歧。有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观园“遗址”在北京西郊圆明园,但书中写到元妃省亲系“戌正起身”“丑正三刻起驾回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从故宫走到西郊清华大学旁边的“圆明园”,需要多长时间?并且在这七个小时内元妃需要完成的仪式包括游幸、行礼、开宴、作诗、看戏、叙旧等,显然与《红楼梦》描写的实际情形相冲突,何况大观园基址并不大,只是因为布置穿插巧妙,显得丘壑很深罢了,而圆明园却很大。周汝昌先生出版的专著,详细论证了大观园“遗址”是北京北城偏西的恭王府②,他找到了一些《红楼梦》文本内证,如书中第五十七回,邢岫烟回答宝钗把棉衣当在哪里时说过是“鼓楼西大街”,这条大街,由鼓楼直奔西北,接近北京最西北处。又如第六十回,贾琏偷娶尤二姐,书中写到“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在护国寺街以北不远,确有花枝胡同。此外,周先生依据曹寅的几首《西城忆旧》词,认为所写内容很像恭王府一带情景,由此推断曹雪芹有可能将其作为大观园的蓝本。周先生还列了一些恭王府与《红楼梦》大观园关系的文献记载及口碑传闻:
《清稗类钞》:“京师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
《小说考证》:“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曰什刹海,前海垂杨夹道,错落有致,或曰是《石头记》之大观园。”
《旧都文物略》:“什刹海在地安门外,相传《红楼梦》大观园遗址在此。”
应该承认,恭王府中的环境特征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确有相似之处,首先,后花园“萃锦园”的名字就与“大观园”的命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大观园有两处制高点,一处是入门穿过迎面土山“翠嶂”后入眼的溪上桥亭,另一处是全园正中的大观楼;而恭王府后花园恰恰也有两处制高点,一处是假山高处的平台小筑,另一处是两翼斜坡引廊的正楼。尽管如此,笔者想在此强调:写景虽然可以有一个特定的蓝本,但周先生的论证,还是囿于“文史合一”的封闭思路,这在客观上也局限了包括恭王府与大观园关系这个课题在内的考证红学天地,何况《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与恭王府也有不相似处,比如大观园的“命脉”是贯穿全园的“沁芳溪”,而恭王府后花园的“元宝池”根本构不成主景,园中缺少溪流贯穿萦绕。既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明说大观园是“天上人间诸景备”,那么“大观”这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不可能拘泥于一个恭王府,《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应该是融合“苑囿”与“庭院”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
与此相反的后一种研究思路,就是认为在人间去寻觅大观园的“遗址”是徒劳的,用香港红学家宋淇的话讲,大观园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③。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又将大观园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提出曹雪芹书中所描述的大观园是“乌托邦的世界”或“理想世界”,而大观园以外是现实世界。他还特别强调“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④。余英时的观点,引发了红学界的争鸣,周汝昌先生从《红楼梦》文本出发⑤,首先确定大观园的地理坐标。根据原著第一回交待的石头下凡历世的去处“(僧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以及下文明言的“花柳繁华地(脂批:伏大观园)”,可见石头是从所在地大荒山“下凡”即向往“现实世界”,怎么会从“理想世界”又去“理想世界”?这存在一个论证逻辑问题。可见大观园应该是红尘人世,并非什么“理想”世界。
周汝昌、余英时这两位红学大家的争鸣焦点,表面看是《红楼梦》内的大观园究竟是“理想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的分歧,而深层的实质问题却涉及到大观园之外的两种红学理念的激烈冲突。在余英时看来:《红楼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一种史学研究,红学家所作的是史学家性质的工作,研究重点在《红楼梦》的写实性内容还原方面,在“自传说”的影响下,这种还原工作进一步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向了曹雪芹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而周汝昌则认为:余英时不过是借提出大观园的所谓“理想世界”去批评曹学及考证派,认为那些都要不得,到了“眼前无路”的地步了,要急于去建立新“典范”。
余英时作为美籍华裔学者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他与长期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周汝昌学术背景差异很大。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那场交锋,不应拘泥于所谓“理想”和“现实”的成分究竟在大观园中占多少比例,事实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余英时夸大了大观园中的虚构亦即“理想”成分,而周汝昌由于无法完全摆脱“自传说”的影响,又无视这种“理想”成分的存在,两者各有偏颇,都属于对《红楼梦》文本的“过度诠释”,就红学研究理念而言,考证派的曹学与批评派的文本阐释同样不可偏废,正如红学前辈徐恭时先生形象比喻的,“考芹探红,是大鹏的左右翼,缺一,不能高飞入云霄。鸟身,就是芹红的溶合”⑥。
二、大观园的创作构思与曹雪芹的人生诉求
那么,曹雪芹究竟是如何构思、创作大观园的?或者说,他通过这种构思,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关怀和人生诉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索的形而上哲学命题。我们不能单纯把《红楼梦》视为文献考证的“学问对象”,还应作为生命感悟的“审美对象”。任何企图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截然分开对它们作孤立的了解,都无法把握到《红楼梦》内在结构的完整性。
从《红楼梦》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为我们具体描述过至少三个世界:一、大荒山青埂峰;二、太虚幻境;三、贾府和大观园。这三个世界有着密切联系。贾宝玉来自大荒山青埂峰,又游历过太虚幻境,但常态生活是在贾府和大观园里,而更多的活动空间还是大观园。因此研究大观园的创作构思,对把握《红楼梦》艺术结构的精神内涵极其重要。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构思,自《红楼梦》流传后就有不少探索者。清新睿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成》有首七律,颇得芹书意旨神髓,原诗如下: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
痴情尽处灰同化,幻境传来石也愁。
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
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此诗前四句,可谓《红楼梦》开卷标题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详细恰切注脚。后四句表达了对曹雪芹价值关怀、人生诉求的深切感悟,尾联“红颜黄土”“麦饭啼鹃”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红楼女儿命运的写照,而“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两句,概括了大观园“花落水流红”的葬花场景,可与原著第二十八回文字对看:
……(宝玉听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⑦
这段描写实际是中国文人伤时情怀的体现。难怪贾宝玉常有青春期的烦恼,时刻“无故寻愁觅恨”,他拒绝成长,幻想留住岁月,诗意栖居。推己及人,一见“绿树成荫子满枝”,便推想邢岫烟的出嫁以至红颜枯槁,因而无限伤感。这就是痴情,非一般常言所能表达,亦非常人所能感悟。林黛玉又何尝不是如此?通过她“葬花”的行为艺术表述,可以看出大观园少女们面对“出嫁”和“死亡”的生存焦虑,最美的花也是最脆弱的,中国的社会环境还没有空间容纳林黛玉这稀有的、美好的生命景观。“葬花”预示了她的“香消玉殒”和“爱情夭折”。至于“葬花辞”中出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夸张句子,也许一般人颇难理解,尽管她寄人篱下,但我们看不出她受到过什么虐待,所以很多读者认为她是无病呻吟。其实林黛玉的愁,是骨子里的幽怨,相比之下,薛宝钗就没有深刻的忧伤和刻骨铭心的缠绵,因为她能适应社会规范。林黛玉的苦闷根本不是什么物质匮乏,而是渴求精神上的知音。《红楼梦》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名伤感,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跌宕曲折的情节,如新历史主义认为的“碎片再现”而非“宏大叙事”,但这些地方恰恰体现出曹雪芹的人生诉求。
鲁迅说过:“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⑧这话非常深刻,在《红楼梦》之前,即使是最优秀的经典如《史记》等,也难摆脱“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似乎男人创造历史,女人污染历史。古代小说中的《金瓶梅》《水浒》《三国演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大都不具正面意义,《红楼梦》第一次为女性塑造了正面的群像⑨。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曾指出:“《红楼梦》为我们树立了文学的坐标,这部伟大小说对中国的全部文化进行了过滤。”⑩这话概括的很到位。文学史上汗牛充栋的一般性作品姑且不论,《红楼梦》对传统经典作品过滤吸纳后的再创造,值得深入探讨,曹雪芹实际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建构。就先秦文学最优秀的作品而论,说曹雪芹“师楚”固然不错,《红楼梦》确实拥有《天问》的想象力,但他同时又突破了屈原对大自然的追问,而提升到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生命叩问,突破了“香草美人”的士大夫情结局限,而把《芙蓉女儿诔》献给了底层丫鬟晴雯;说曹雪芹没有摆脱《庄子》的虚无思想也不必讳言,但《红楼梦》又说“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说明他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并未幻灭,同时在言情中又具有禅宗的深度,认为人人具有佛性,都有正邪两赋的一面;说《红楼梦》“假语村言”堪比“高文典册”的《史记》,评价也不算低,但曹雪芹能以一座贾府去囊括百千世家,《红楼梦》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具有陶渊明幻想的“桃花源”理想境界,也有一定道理,但“桃花源”是“有父子无君臣”,虽无政治秩序,却仍保持其伦理秩序,而大观园的秩序则是以“情”为主;说《红楼梦》是部诗画小说并且继承了唐诗宋词的意境也不错,但曹雪芹是“羹调未羡青莲宠”“苑招难忘立本羞”,从不与权贵有染,更不会去写“悲士不遇赋”;说《红楼梦》深情呼唤着王实甫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更没问题,曹雪芹本来就让主人公共读“西厢”还郑重把书名写进题目,但《西厢记》中张生仍热衷科举,崔莺莺的思想境界与林黛玉也有天壤之别,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文化含量和灵魂含量的爱情;至于说同时期先后的那些最有名的明清小说,与《红楼梦》比较方知高下:《三国演义》作为形象的历史教科书确能给人“以史为镜”的教益,但仍局限于“明君贤相”模式作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而《红楼梦》完全解构了圣人话语权,小说满纸是人的宣言,彻底打破中国传统的功业思想,将之视为生命之轻而另有自己的定位;《水浒传》虽将眼光下移到市民,然“造反有理”的宣传暴力倾向至今也还有负面影响,《水浒传》的局限还在于武松那种变态英雄对潘金莲的快意恩仇,居然赢得了那么多的“看客”,作者根本不屑于去追究造成这一女性悲剧的深层原因,而《红楼梦》却为同样“淫丧”的秦可卿举行了隆重的丧礼;《金瓶梅》在描写市井社会方面比从前的古代小说更胜一筹,对《红楼梦》的创作构思也有很大影响,但性多情少,尤其是因果报应模式,缺乏曹雪芹那种深层的哲学思考。《红楼梦》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结局,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大团圆”俗套而令人耳目一新。《红楼梦》的悲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且这种悲剧并不全是恶人造成,好人也可以制造悲剧,构成共同犯罪,是病态的“集体无意识”使然,这种悲剧才算真正的“悲剧中的悲剧”,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的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互相“吃人”。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价值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曹雪芹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对人生深刻思考后才大彻大悟。《红楼梦》的深度在于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名利迷关,时时提醒人们做精神的守望者,呼唤生命所本有、应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而生活于当下社会的人们,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原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反认他乡是故乡”,《红楼梦》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回答了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年的曹雪芹,会否期盼后人由书中字字句句读懂他对这人世的诉求?
三、当代《红楼梦》研究的多元格局及走向
大观园的创作构思体现出了曹雪芹的人生诉求,正因为《红楼梦》是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才超出了一般的作品而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罕至的高境界。如前所述,周汝昌、余英时关于大观园究竟是“理想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的交锋,涉及到大观园外的两种红学理念冲突。在这场红学理念的冲突中,两位红学大家通过辩难,各有所赢,各自在一个方向上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又形成互补,共同丰富发展了红学世界⑪。
当今的红学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多元世界。总括而言,《红楼梦》研究已经形成了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三足鼎立格局。毋庸讳言,当代红学界发生的有影响学术论争基本属于文献研究方面,如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之争、曹雪芹祖籍之争、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真伪之争、通州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红楼梦》版本的“程先脂后”之争等。这些论争的产生,是由于“文革”结束后人们厌倦了政治转而将精力投注于纯学术方面。不可否认,各种论争都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然而,这些论争存在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再以当下文献研究中最受瞩目的根据脂砚斋批语探求《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探佚派及后四十回的辩护派为例,前者想弄清八十回后的曹雪芹文字原貌,势必会采取力求恢复情节片段甚至一字一考的研究方式;而后者要维护后四十回的文字,就设法去证明那些文字也是曹雪芹原有的,两个学术派别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研究方法上却是殊途同归,都受到传统干嘉学派理论的影响,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认为只要把文字还原为最初古义,经典的涵义便自然呈现,尽管语言的厘清有助于理解思想,但却不能代替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带着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脂砚斋提示的后半部线索,或者真的还原出了八十回全部情节,也不一定就能碰触到《红楼梦》涉及的精神境界,不能指望文献研究所承担的任务超过它的功能极限,心灵感悟的文学毕竟不同于具有科学性质的文献。
当“文化”已成为人文学科“新”大陆的时候,各学科都在“文化”这块无边的处女地上跑马占地,《红楼梦》研究也不例外,由于红学这门学科本身呈现出的边界性⑫,它向文学以外的其它领域延伸,近年来又出现《红楼梦》研究中的“文化热”,如《红楼梦》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等……好比须弥芥子中看到了大千世界,这种研究虽也能开阔读者视野,增加人们对博大精深《红楼梦》的认知,但有的这方面红学著述却游离于《红楼梦》本体而泛谈文化,从而取消了红学的独立性。这种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借助名著效应,是对其它任何名著也可以套用的研究模式,这样就势必将名著消融于无所不包最终又一无所包的“泛文化”之中。《红楼梦》既有中华大文化的宏观叙事,又有具体文化景观的微观细刻,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均有相对合理性,但尊重红学的这些“微观”研究,不代表因此就可以将《红楼梦》肢解。《红楼梦》作为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不该简单进行“碎片化”阅读。《红楼梦》也绝不是“知识摆摊”,而是一个“活的”大整体,是中华文化的活生生的传播感染的伟大表现与载体。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关照,从而在与世界对话中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哲学思辨精神。
避免《红楼梦》文化研究中的“碎片化”阅读和文献研究中支离破碎、无关宏旨的一字一考,正是呼唤红学的“大气象格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大陆的演成主潮,主体价值学阐释成为文本批评新理论为不少红学研究者采用。应该承认,新范式让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意义自不可估量。要求对作品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这种由外向内的诠释维度的转换,正是对传统红学范式偏向的反拨,但如果夸大认为是红学的全部,那就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特别是新范式不惜割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只剩下“作品”一项,显出“见木不见林”的形而上学。倘若我们把《红楼梦》这部作品放置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去进行宏观考察,追溯作品之所以在此时出现的根由,岂不是分析得更圆满、得体、到位?作为具有兼容性、开放性和边界性的红学,各种红学范式应该互相阐发和解释。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是任何一种研究范式能笼罩住的,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应该看到,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内线”与“外线”的樊篱,实现《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应该是红学转型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代《红楼梦》研究多元格局整合后的走向。
注释:
① 对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记载颇有质疑者,如乾隆时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曾指出袁枚“善于欺人,愚未深信”,袁枚后人翻刻《随园诗话》特将大观园系随园的话删去,并特声明“吾祖谰言”。
② 周汝昌《恭王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宋淇《红楼梦识要》,中国书店出版2000年版,第15页。
④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⑤ 周汝昌《红楼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
⑥ 徐恭时《〈红楼梦补〉作者归锄子寻名》,《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期。
⑦ 引《红楼梦》原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⑨ 吕启祥《〈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期。
⑩ 刘再复《红楼梦悟》,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页。
⑪ 张惠《中美红学的交锋与双赢:周汝昌与余英时对当今红学研究格局之贡献》,《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5期。
⑫ 参见陈维昭《论红学的边界性》,《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