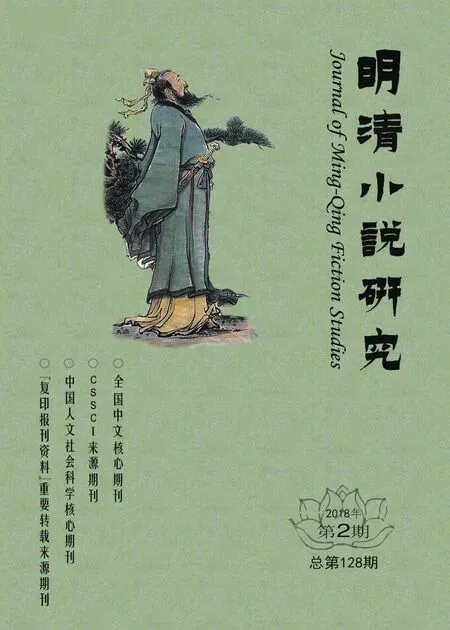序跋与《聊斋志异》的传播∗
·刘彦彦 李 楚·
经典在形成过程中,文本原生层固然非常重要,而次生层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样不能忽视①。次生层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经典传播过程中的序跋。序跋作者往往是作品最早的读者,他们对于作品的评论起着桥梁与“导游”的作用。读者在开始阅读之前,时常会受到序跋的影响,对作品产生阅读期待,序跋中蕴含的文学理论观点也起着提升读者理解水平的作用。《聊斋志异》写于康熙年间,虽然文采动人、曲折可感,但是它并不是一出现即受到大众关注和欢迎,而是缓慢地为读者所接受从而实现自身的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序跋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手抄本时期的序跋:以淄川朋友圈为核心的传播
蒲松龄在家乡淄川(今山东淄博)并非籍籍无名,他虽然屡试不第,但是天性慧颖,长于诗文乃至俗曲;年少时他就与同邑名士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与他交往甚密的高珩、唐梦赉也都是当地名士。因此他创作《聊斋志异》的时候,不仅为同邑文人圈所周知,而且手稿“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矣”②,由于文人之间相互辗转借抄,使得《聊斋志异》在乡间逐渐具有一定的名气。
高珩与蒲松龄诗书往来颇为频繁,关系也最为亲密,他的序和蒲松龄的《自志》同时附于八卷本的手稿之上。高珩在序中夸赞《聊斋》为奇文,不能当作一般的“怪力乱神”之作看待,用圣人之言为志怪小说开解,认为《聊斋》所记虽然是圣人所不语,却“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③。高序之后,又有唐梦赉于康熙壬戌年(1682)为《聊斋》作序,唐梦赉和高珩都是《聊斋》最早的读者。二人序文之意大致相似:一是申明鬼怪不怪,是世人孤陋寡闻方才以此为异,批评那些人“以目所见者为有,所不见者为无”,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以至于“见橐驼谓马肿背”;二是称赞《聊斋》文章通达,以为其能够“破小儒拘墟之见”,又能“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④。两人的序都表达出《聊斋》具有精深微妙的意旨,而且强调“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一贯之”⑤,言下之意,能够读懂《聊斋》的人必须是鸿儒硕学。这便为《聊斋》在精英文化圈中的传播制造了正面的舆论氛围。
当时在政坛和文坛皆为显赫的大学问家、尚书王士禛阅读手稿本后,对《聊斋》极为喜爱和欣赏。王士禛是《聊斋》评点第一人,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前后和康熙四十年(1701)两次为蒲松龄作评,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载“《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禛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⑥。王士禛对蒲松龄的欣赏可见一斑。可是当蒲松龄将《聊斋》抄本寄给王士禛,并附信《与王司寇阮亭先生》委婉地表示了希望王士禛能为自己传扬文字,即为《聊斋》作序的请求时,王士禛却回信婉拒了蒲松龄之请。
王士禛拒绝为《聊斋》作序,一方面因为小说稗史毕竟是被当作消闲、补阙的“小道”,历来为上层文人所不屑,另一方面当时屡兴文字狱,官方对坊肆小说创作的审查尤其谨慎和严苛。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颁布谕令:“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而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俚,渎乱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蛊心焉,败俗伤风所系非细,应即通行严禁等谕九卿议奏。通行直省各官,现在严查禁止。”⑦谕令中尤其提出臣下必须实力奉行,可见康熙非常重视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尽管王士禛很欣赏蒲松龄的文才奇笔,但是毕竟官高权显,自然不会轻易应允为这样一部书写鬼狐妖魅、荒诞诡幻的小说写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当时的传播范围主要还是在社会中下层。
王士禛的弟子名士朱缃也是《聊斋》的早期读者之一,他所作《聊斋文集题辞》表现出了对蒲松龄的推重,题辞中称赞蒲松龄之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以大奇;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岚耸翠,非复人间有”⑧。朱缃比蒲松龄小二十岁,但他与蒲松龄是忘年之交,情谊非同寻常,蒲氏生前,朱缃就曾借《聊斋》手稿进行抄录,但是后来被人借走传看而失落所在。之后,其子殿春亭主人又通过蒲松龄另外一位友人张元(曾为蒲松龄做墓表)之子张作哲从蒲家借出原稿“累累巨册”,于是花钱雇人,于1732年结成殿春亭抄本。该抄本现已遗失,目前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铸雪斋抄本就是根据殿春亭抄本转抄,基本保留了手稿本的原貌。
“铸雪斋”是历城张希杰书斋之名,铸雪斋本是目前能见到的《聊斋》最早抄本,抄本卷首有序三篇,分别是“康熙己未春日谷旦,紫霞道人高珩题”“康熙壬戍中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题”“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题”,后者即蒲松龄自序。卷末附三篇跋,分别是“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后二日,殿春堂主人志”“雍正癸卯秋七月,南村题跋”“乾隆辛未秋九月中浣,练塘老渔识跋”,练塘老渔即铸雪斋抄本的编者张希杰。由此可见,从手稿到铸雪斋手抄本近半个世纪以来,《聊斋志异》尽管在文人中有一定影响,但是抄录毕竟工程浩大,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转借出去有可能会散佚,这些都成了影响传播的主要因素,因此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淄川地区的亲朋好友之间,他们既是传播者同时也是接受者。
从他们的序跋内容来分析,当时的传播效果应该是褒贬不一的,甚至包括蒲松龄的朋友对作品内容也略有微词。张笃庆就曾在《寄留仙、希梅诸同人》一诗中劝他:“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切莫竞谈空”⑨。在蒲氏死后,张笃庆在《岁暮怀人诗》中还责备他“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⑩;另一位好友宝应知县孙蕙亦曾写信劝诫:“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谬否?”⑪而上层文人对《聊斋志异》的诟病就更严苛了,《阅微草堂笔记》后附“纪汝佶六则”中纪昀写长子的不幸人生:“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⑫纪昀将长子之死归结于为《聊斋》所惑,又把《聊斋》与“公安竟陵两派”相提并论,其中隐藏着“歪门邪道”的批评。这虽然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但也可以窥见上层文人对于《聊斋》的态度。
之所以对《聊斋》语涉花妖狐媚、鬼灵精怪訾诟,主要因为,儒家向来认为“怪力乱神”为不正之事,于教化无益,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解释:“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易语人也。”这种观念作为主流文化思想一直被官方作为褒贬文学作品的标准。由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摒绝神怪荒诞之说,故而在《聊斋》传播最初,高珩、唐梦赉等人作序都将重点放在诠释这部志怪小说的意旨上,强调小说合乎大道,不悖于圣人之旨。高珩曰:“欲读天下之奇书,须明天下之大道。”唐梦赉曰:“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⑬这对人们接受这部奇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刻印本时期的序跋:大规模传播阶段
《聊斋》手抄本传播过程中,既收获了赞赏之词,也不免因为题材的“边缘性”而为人所诟病。即使是在张元为蒲松龄所做的墓表之中,也含蓄地指出《聊斋》“事涉荒幻”⑭,恐非大雅之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聊斋》在中下层文人间的影响很大。据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记述刻印《聊斋志异》之始末,提及多位士人手录收藏《聊斋》手抄本,包括塾师周季和、沂州知府郑荔芗,以及吴颖思等。赵起杲通过勘校各手抄本,判定郑荔芗所藏乃原稿,于是与诸位文士一同斟酌考订,可惜剞劂之工未竟赵起杲奄然而逝。最终在其弟赵皋亭与杭州知名藏书家鲍廷博的主持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印出版。青柯亭本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刻本,它是其后的刻本、评本、注本等版本的祖本。根据孙济奎的说法:“其《聊斋志异》一书,自莱阳赵荷村太守刻于睦州官舍,书乃盛行。著者评者,相继而起。盖是书之脍炙人口久矣。”⑮刻印本的问世打破了手抄本的局限,不仅扩大了发行量,而且统一了版本。赵起杲作为一地官长,身份特殊,之所以出面印行,一方面说明这部小说的手抄本在民间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俨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口碑和认同。正如赵起杲在《例言》中所赞许的:“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谬于作者,是所望于知人论世之君子。”⑯将《聊斋志异》与庄子、列子、司马迁、班固之文,甚至《春秋》相提并论,这样高度的评价不仅使《聊斋》的创作主旨更加贴近儒家文论思想的标准,以便获得上层文化圈的认可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当时的文人圈也是有共识和被认同的。此外,为了更加顺畅地令上层主流社会接受《聊斋》,赵起杲对当初王士禛婉拒作序一事,也做了新的阐释,他称蒲松龄成书之后请王士禛斧正,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而蒲松龄坚拒。鲍廷博在《聊斋志异题辞》中也附和赵起杲之说,有“莫惊纸价无端贵,曾费渔洋十万钱”之语。赵、鲍之说不仅增加了《聊斋》一书的传奇性,而且也为《聊斋》能进入缙绅视野抬高了身价。
赵起杲于睦州为官时,名士余集假馆于郡斋,赵起杲就提出了请余集审定《聊斋》并为其作序的邀约。余集在阅读之后,欣然答应,以为此书虽然多涉诡荒忽不经之事,但若以志怪小说观之则完全有悖于作者本意,乃“井蠡之见”。他以三闾大夫屈原和佛家释氏为例指出蒲松龄是以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泄愤懑抒愁思,寓有深心微旨。并且也深有体悟地指出蒲松龄“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余集的观点与赵起杲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无疑跟铸雪斋手抄本卷末所附南村跋“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奇哉”相呼应,南村曾经预言“后有读者,苟具心眼,当与予同慨矣”⑰,果然,无论是对社会现实还是自身遭际有所愤懑不平的文人都能从这部寄托之作中产生共鸣,这样的序跋增强了受众的阅读期待,对那些现实人生不如意的文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由于手抄本的《聊斋志异》已经在文人圈中具有了一定的名气,一些有能力的文人为了公诸同好纷纷产生付梓刊刻的念头。几乎在青柯亭本刊刻的同时,山东长山县县丞王金范也在手抄点窜。翌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刻成,仅比杭州刻本迟五个月。当时他并不知道杭州已经有青柯亭本刻印,两个刻本所依据的手抄本也并非同一个本子,根据王金范在自序中所言,乾隆二十六年(1761)“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⑱。据袁世硕先生考证,王约轩即蒲松龄家乡淄川的县丞,曾氏则是为蒲松龄写墓表的张元的弟子曾尚增⑲,由于王金范所依的曾尚增家藏抄本传抄讹误甚且凌乱无序,王氏仅凭一人之力,将卷帙浩繁的抄本删繁就简刊刻了摘抄本。从王金范所作序看来,王金范就节选刊刻《聊斋》一事,花了近六年的时间,“手抄而点窜之”用力甚勤。他在序言中表达出对这部搜奇立异的小说喜爱的主要原因在于“天下固有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则不妨与圣贤中庸之道并行而不悖”。在他看来天下之事无论有无,重在其理,而《聊斋志异》“凡其所言孝弟廉节,达天知命,与夫鬼怪神仙,因果报应之说,无不可以警醒顽愚,针砭贤智,即所谓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者”,言下之意,具有劝世社会功效的小说当然不应该视为无稽荒诞之言。显然王金范对这部小说的价值认同更在于其书“警醒顽愚,针砭贤智”。正因为王金范视这部小说为寓托“圣贤切近之理”的“觉世之言”,因此他别出心裁地将《聊斋志异》部分内容按照儒家思想中孝、悌、智、贞、义等伦理准则分类编排,旨在阐明这部言狐妖鬼魅之作实乃为圣贤名教之旨。显然这种卫道士的解读并不受欢迎,有迎合道学家阅读期待之嫌,而令慧业文人所不屑,俞樾就曾评说此刻本“至所分门类,则无甚深意,殊觉无谓”⑳。而且王氏“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将后世称道的《促织》《梦狼》《席方平》《考弊司》《林四娘》《花和尚》等优秀作品都删除未录,这就使原著中讥讽滥官酷吏贪利虐政的主题大打折扣,甚至还冒作《淄川吏》篇添入选本,大大损伤了原书面貌。尽管如此,但是根据袁世硕先生考证,乾隆五十年(1785)有重刻本,据日本藤田祐贤、八木章好合编《聊斋研究文献要览》,光绪年间还有王毓英之重刻本,题《聊斋志异新本》,且王金范的这个版本前后刊印过三次,故此至少说明王金范序言所阐明的《聊斋志异》醒世之寓引起一些格调不高的官僚的兴趣,但是恣意删改的硬伤最终令这个刻本声销迹灭。
青柯亭刻本风行天下,集结了高珩、唐梦赉的序,蒲松龄的自志、蒲立德识语,以及余集和赵起杲的序,这无疑对小说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时之间模仿之作勃然而兴,仅乾隆年间的仿作就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管世灏的《影谈》、冯起凤的《昔柳摭谈》,这批小说完全受《聊斋志异》的影响“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也有不刻意模仿却显受其影响之作如袁枚《子不语》,还有专意与之相抗衡之作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这些作品都以构建怪异之事为能事,蕴涵劝善惩恶的意旨,尽管有些作品有试图突破和超越的倾向,但仍不能摆脱《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
三、注评本时期的序跋:《聊斋》文本的再诠释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青柯亭本后,《聊斋》被多次翻印,随后为了辅助人们的阅读、理解又推出了多种注评本。通过对序跋的分析,可以看到注评本出现是随着《聊斋志异》广泛传播,为了满足文化程度较高的受众阅读精细化、学术化的需求。总的来看,道光年间以注评本为主。
随着《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这部奇书几乎家喻户晓:“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册。”㉑在这种情况下“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聊斋志异》笔意高古,诸多文士指出“书中之典故文法,犹未能以尽识”㉒,“《聊斋》善于用典,真如盐著水中也。读其四六,可以见无一字无来历”;“《聊斋》胎息《史》《汉》,浸淫晋魏六朝,下及唐宋,无不薰其香而摘其艳。其运笔可谓古峭矣,序事可谓简洁矣,铸语可谓典赡矣”㉓。清代干嘉学派以考据为主的学术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阅读思维,因此对这部知名作品的考据注释也在逐渐酝酿中,直到道光五年出现了第一本注释本,即观左堂刻吕湛恩注释。吕注重考证章句典据,于其所征引,搜摭无间,如书中人物的简历、词条的旨意和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这对文人阅读大有裨益。
但是为《聊斋志异》作注释非满腹经纶者所难成也,正如舒其锳《注聊斋志异跋》所言“非读破万卷书亦不能注《聊斋》也”㉔。第一位为《聊斋志异》作注的吕湛恩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他曾受知于山东学政、大学问家阮元(芸苔),成为诸生(秀才),怀抱利器但屡入科场而不第,因此作注的初衷与蒲氏写《聊斋志异》动机相合,俱有舒抑郁之情的因素。吕湛恩注释本刊行之后,果然再次掀起士林争购的热潮,据孙锡嘏跋可知,吕注本梓行后独行于世,“迄今光绪改元,予在曲阜,见有将吕注刊于全部各篇之后者,上又载江南何地山音释训诂,亦有便初学。予喜而购之,携至家,考其典故,而尤致以论其文法也”。《聊斋志异》注释本的受众倾向于重典故和作文纪事之法等考据学的文士儒硕,而这部充满学术含量的注本受到士林的欢迎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继吕注本之后第二个注释本是道光十九年(1839)南陵何彤文刻何垠注释的本子。从何垠自序和何彤文序可知,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有吕湛恩注释本,何垠在自序中称:“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何彤文也在序中道:“且近之读《聊斋》者,无非囫囵吞枣,涉猎数遍,以资谈柄,其于章法、句法、字法,规模何代之文,出于何书,见于何典,则茫夫未之知也,即读焉如未读也,有执以相问难者,十不得其一二焉,良以读书未破万卷,故无从索解人耳。”㉕说明这时由于南北交通阻隔,传播速度缓慢等原因,吕湛恩注释本还未传至南方,故南方文士的阅读需求引起了刻书儒商的关注。何垠跟吕湛恩一样是博学多识之士,其注释本“某字句见何经、见何史、见何子、见何诗文集,必溯其源而求其实,绝无恍惚依稀附会牵诬之弊”,令读者涣然冰释。虽然何彤文在序中对何垠注本赞不绝口,但是由于吕注比何注更详细,因而何注本翻刻不多,流通也不太广。
道光年间,除了注释本之外,还陆续梓行刊刻有《聊斋志异》评本。实际上第一个对《聊斋》进行评点的就是王渔洋(王士禛),之后相继有人进行评点,据盛伟《清代诸家批点〈聊斋志异〉述评》统计,前后共有十六人之多,但是保存下来并受到关注的仅有四家,这主要缘于光绪十七年合阳喻焜刻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将王士禛、何守奇、冯镇峦、但明伦四家评语集于一书,此刊本不仅对读者理解小说具有非常大的帮助,“仁见仁,智见智,随其识趣,笔力所至,引而伸之,应不乏奇观层出,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在慧业文人,锦绣才子,固乐为领异标新于无穷已”㉖,更便于人们对他们四位评点的对比,曾有人对比评论:“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㉗据喻焜序中称:“但氏新评出,披隙导窍,当头棒喝,读者无不俯首皈依,几于家有其书矣。”㉘由此可见,但氏所评为注评本之翘楚。
但氏在序中自称“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㉙。但明伦认为《聊斋志异》承袭了古文传统,因此从文章学的角度评论《聊斋志异》的文法,而且常常有颇具理论色彩的归纳,诸如评点《王桂庵》时提到的“蓄字诀”以及在评《葛巾》时提到的“转字诀”,都是但明伦受古文章法的启发来探索小说情节设计的变化多变,不仅对总结小说行文的叙述技巧和艺术规律功不可没,而且对后世小说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明伦的评骘不仅揭橥了《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而且认为《聊斋志异》花妖狐媚“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对小说思想意义也有更深入的挖掘和升华,正如但氏在序中所云“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但氏的评点在当时代表着《聊斋志异》评点的顶峰,不啻为踵事增华,锦上添花。
这些知名的文士热衷于对《聊斋志异》评点,除了文本自身的魅力之外,也旁证了当时《聊斋志异》在士林的影响力。《聊斋志异》传播至此俨然已经口碑载道,在长期历史沉淀的过程中,对文本的诠释和评点实际上也是被赋予更大的艺术张力,更丰富的艺术蕴涵的过程。《聊斋志异》的价值通过名士们的挖掘,已经不再只是普通的小说,而是“用为研文之助”的教科书,因此尽管受其影响很多人仿效其作,但是“效颦者纷如牛毛,真不自分量矣。无聊斋本领,而但说鬼说狐,侈陈怪异,笔墨既无可观,命意不解所谓”㉚。显然《聊斋志异》已成为公认的难以超越的高峰,在当时文人心中奠定了经典地位。
至光绪年间,《聊斋志异》绘图本广泛刊出,无疑满足了老百姓以及学童的阅读需求,而有的绘图本专门聘请名手绘图并附图咏,装帧成精美的珍品,已然已经超越了传播的诉求,旨在为了满足高品位审美情趣的文化精英游目骋怀便于收藏的冀愿。
四、《聊斋志异》序跋对受众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序跋分析,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聊斋志异》各个时期的传播情况。尤其至光绪末年,《聊斋志异》已经“传遍宇内。吾国十龄以上稍识字童子,无不知者”㉛。由此可见《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受众范围很广,上至缙绅名士,下至童叟百姓,可谓家喻户晓,这样的传播效果跟序跋的作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序跋主要是给文士们引为资鉴,因此对于文士来说影响也更大些。
首先是对那些为博功名久困名场的读书人具有激励的作用。蒲松龄的遭际与大部分寒儒一样,他们博才多识但却穷愁潦倒,发愤著书以抒不平之气几乎是中国文人宣泄不满的主要途径。通过序跋,可以看到大多数序跋的作者都有着跟蒲松龄相似的命运,如蔡培序中称,吕湛恩“盖吕子之才识,不让于柳泉,而其功名之困顿,亦与柳泉等,士君子穷而在下,怀抱利器能不得展,往往托于文章,以自舒其抑郁无聊之气,则吕子之成是书,吾知其性情所寄,欲与柳泉为徒,岂沾沾于鬼狐仙怪云尔哉”㉜。再如何彤文作序称,何垠“吾家地山老人幼而好学,老而不倦。其于经史子集既能强记,多求解说,乃以通才而不达于命”。喻焜在序中称冯镇峦“先生一官沈黎,寒毡终老……惟是书脍炙人口”。正所谓知音识曲,相似的命运使这些文士更能够感悟《聊斋志异》蕴含的遥深寄托,从而产生惺惺相惜之感。这对于身处名场之困的文士来说不啻为一种人生的鼓励,正如孙锡嘏在《读聊斋志异后跋》中所言:
是则《志异》一书,由其困于场屋而作,人皆为先生惜,吾独为先生幸。盖其困也,正天所以练其气者,其材乃使成为扶持世道之文,以传于万世。设其博一第,作一官,食禄天家,为国效力,方且溷迹簿书,以钱谷刑名为急务,即建功立业,亦或有赫赫之名,又何暇著为异书,以警世而励俗哉?㉝
确实如此,序跋的作者们在表达对蒲松龄的同情与敬佩之外,对《聊斋志异》创作动力的评述无疑对受众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对《聊斋志异》作文纪事之法的挈领提纲起着指导阅读和醍醐灌顶的作用。《聊斋》序跋的内容最开始致力于为志怪正名、突出其中教化功能,之后逐渐转移到欣赏其幽奇笔墨、发掘其中审美价值,迨注评本蜂起时,《聊斋》的读者们已然将它奉为文章经典,以解读史传、诸子散文的态度来解读它。随着时代的推移,接受者们已经逐渐能够欣赏《聊斋》中悖离世事人情的精怪妖魅,《聊斋》已经很少再因其特殊的题材为人所诟病,但是对于《聊斋》有益世道人心的宣扬,却是从头至尾从来不曾断过。但明伦在《聊斋志异序》中称其“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孙锡嘏《读聊斋志异后跋》也以为“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瘅恶,期有功于名教而正”,其观点与唐梦赉、高珩序无疑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后来序跋中所言以看经文法看《聊斋》的观点,则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读者的接受。刘瀛珍在《聊斋志异序》中直言:“将欲区文章之善否,不必以理法绳也,但取而读之:读未终篇,以厌其词之长,必弗善矣;读既终篇,犹嫌其词之短,必甚善矣;至于全卷读竟,心怅然如有失,深恨作书者之不再作,刻书者之不再刻,则善之善者也。”㉞这段话无疑制造了吊人胃口的悬念,增强了读者的吸引力。
注评本的序跋作者纷纷阐说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夸赞《聊斋》文章之美,如何彤文在序中慨叹:
其志异也,大而雷龙湖海,细而虫鸟花卉,无不镜其原而点缀之,曲绘之。且言狐鬼,言仙佛,言贪淫,言盗邪,言豪侠节烈,重见叠出,愈出愈奇。……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
再如孙锡嘏在《读聊斋志异后跋》中更加形象的评述:
其文法有一线穿成者,有两峰对立者,有如长江大河突起波澜者,有如悬崖峭壁屡现怪异者,有先立总案后用分疏者,有提名在前再用详叙者,有追叙前事者,有埋伏下文后乃点明照应者,有实写正面屈出不穷者……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亦是一再申明:“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尤其是后期注评本序跋,更是提纲挈领谈到《聊斋》的“作文之法”,虽然由于篇幅所限,序跋作者无法很具体地述说《聊斋》中的运笔之法,但是对于阅读序跋的人来说,无疑具有醍醐灌顶阅读指导的影响作用。如谢鸿申在《答周同甫书》中有“《聊斋》笔力雄厚,气息深醇,非浸淫《汉书》者不能道只字”㉟,《与惺斋书》中又称“《聊斋》气息深醇,妙在无笔不转,尤妙在伏笔草蛇灰线,无迹可寻”㊱,与但明伦序、孙锡嘏跋言异而意同。因此舒其锳在《注聊斋志异跋》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然则注《聊斋》者可谓《聊斋》之功臣,而序注《聊斋》者实亦注《聊斋》者之知己矣。注之难,序之正,不易。注者序者或许余为能读《聊斋志异》者。”此言深中肯綮。
另外,《聊斋志异》的序跋对廓清异议和促进仿作的创作热潮具有深远的影响。《聊斋志异》虽然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但是纪昀所编的《四库说部》并未将其收入,尽管纪昀不得不承认《聊斋志异》乃“才子之笔”,但他用传统的眼光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传奇式的志怪,有违传统的著述文体观念“非著书者之笔”。在纪昀的影响之下,当时有些人也持相同观点,如邱炜萲在《菽园赘谈》中称:“谈狐说鬼者,自以纪昀《阅微草堂五种》为第一,蒲松龄《聊斋志异》次之。……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馀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挈长而较短也。”㊲乃至于到民国时期,仍有人对《聊斋》有所指摘和鄙薄,而所针对的无非就是说鬼谈狐涉及迷信。
针对类似拘迂的批评,序跋的作者们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辩驳,余集曾慨叹这部托志幽遐之作“然则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㊳,舒琪锳在《注聊斋志异跋》中直言:“《聊斋志异》大半假狐鬼以讽喻世俗。嬉笑怒骂,尽成文章,读之可发人深醒。”冯镇峦则更为深刻的阐明:“予谓泥其事则魔,领其气则壮。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此变化气质、淘成心术第一书也。”㊴这段议论辨明了蒲松龄“有意作文,非徒纪事”的卓识独见。不仅如此,冯氏还直言不讳地驳斥“袁简斋议其繁衍,纪晓岚称之为才子之笔,而非著述之体,皆言也”,将袁枚、纪昀批驳蒲氏之言论斥为吹捧、虚伪之言,更是不遗余力的通过对《聊斋志异》悉心评点增强其说服力。
正因为序跋对《聊斋志异》的文学表现有所提摄,那些对《聊斋志异》文章之法的归纳和总结在读者的潜意识中往往起了提示和引导的作用,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序跋的指导,自然产生较为一致的审美体会和感受,“多有崇拜其笔墨之佳者,甚且欲学之以为作文纪事之法”㊵,诉诸笔端就是《聊斋》的仿作。如《萤窗异草序》中言明其书大旨“酷慕聊斋”㊶,解鉴的《益智录》杜乔羽作序称:“近今则蒲留仙《聊斋志异》,怡心悦目,殆移我情,不厌百回读也。其叙事委曲详尽而不嫌琐屑,其选词典赡风华而不病文胜,其用笔轻倩波俏而不失纤巧。其奇想天开,凭空结撰,陆离光怪,出人意表,而不得谓事所必无,以乌有子虚目之。向以为绝调独弹,殆寡和矣”㊷。从其钦慕的口吻中便能想见该作的仿效程度。《柳崖外编序》更是称赞其文“无愧《聊斋》再世”㊸,还声称作者即是蒲松龄的转世。尽管《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多,但是大多数的模仿之作画肉难画骨,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而后之效仿此者,若《谐铎》,若《秋坪新语》,若《夜谈随录》,若《子不语》,各有取义,而品斯下矣”。《聊斋志异》创造了文言志怪小说的高峰,堪称绝世之作。
综上所述,在《聊斋志异》经典化的过程中,序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出手眼,别具会心”,就是说不仅需要作序跋者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广博的见识,更要别有匠心及慧心,既能玄感作者之志又能扩充延宕作者之意,令受众真正能够获得开卷有益的欣喜和启发。自古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生前穷愁落寞无力梓行,身后不仅有诸多知音君子将其作付之梨枣公诸同好,更援笔成章,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遂流布于世成不朽之名,此诚可谓蒲氏不幸中之大幸。
注释:
① 詹福瑞认为:“一般认为,经典就是文本本身,但是从阅读与接收角度来看,经典应该是包括经典文本及其诠释文本的整体。就此而言,经典可分为原生层和次生层,次生层包括整理与注释文本、评点与批评文本。”参见詹福瑞《试论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
② ⑯ ⑰ ㉑ ㉖ ㉗ ㉘ ㉙ ㉚ ㉞ ㊴ 张 友 鹤 辑 校 《聊 斋 志 异 会 校 会 注 会 评 本 》,中 华 书 局1962年版,第32、27、31、24、20、15、20、19、12、22、9页。
③ ④ ⑤ ⑬ ㉓ ㉔ ㉕ ㉜ ㊳ ㊶ ㊸ 丁 锡 根 《中 国 历 代 小 说 序 跋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1996年版,第135、138、136、138、142、144、143、153、139、169、175页。
⑥ 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7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258,影印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⑭㉛[清]蒲松龄《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1814、738页。
⑨ 邹宗良《蒲松龄年谱汇考》(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中文系,2015年,第21页。
⑩ 马瑞芳《一生遭尽揶揄笑,撰定奇书万古传—〈聊斋志异〉创作过程探源》,《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⑪ 欧阳健《〈聊斋志异〉序跋涉及的小说理论》,《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Z1期。
⑫[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3页。
⑮⑱㉒ ㉝㉟㊱㊲㊵ 朱 一 玄《〈聊 斋 志 异 〉资 料 汇 编 》,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2012 年版,第294、316、495、496、499、500、510、507页。
⑲⑳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413、424页。
㊷[清]解鉴《益智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