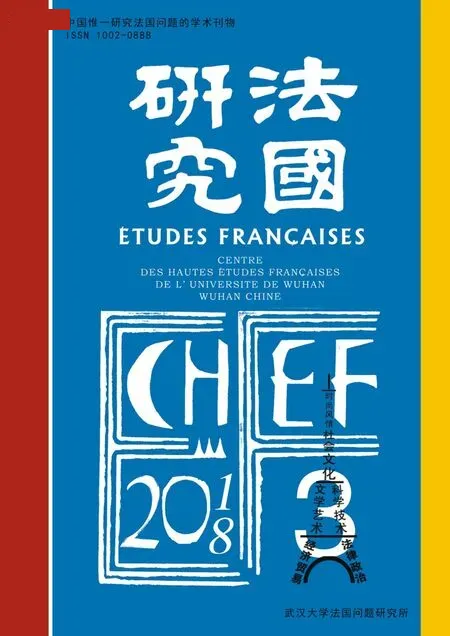墨洛温先祖与墨洛温王族的崛起
刘虹男
就西欧中世纪前期的众多蛮族王族来说,墨洛温家族(la famille mérovingienne)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支。不过,与墨洛温诸王清晰的“征服史”相比,其先祖们的历史则存在诸多悬疑,这也成为早期法兰克史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难题之一。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史料匮乏:早期法兰克人很少留下落笔于纸的文字史料,导致某些问题或某位墨洛温先祖仅有少量史料可供考究,且常常带有传说性质,结果便出现单文孤证、神话色彩浓厚、可信度不高之类的问题。正因如此,有关墨洛温先祖的诸多问题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那么,现存叙述性史料中提供的墨洛温先祖谱系是否具有共通之处?它们给出的墨洛温先祖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否完全可信?这些墨洛温先祖对墨洛温家族的崛起做出了哪些贡献?墨洛温家族的崛起又能反映出何种文化特性?对于上述问题,西方史学界已有较多关注,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并未进行充分的考证与分析。①19世纪末期,随着《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中有关墨洛温王朝的拉丁语文献相继面世,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到墨洛温先祖谱系的问题。一些学者在有关墨洛温王朝的主要叙述性史料《法兰克人史》、《弗莱德加编年史》和《法兰克人史纪事》中发现,它们给出的先祖谱系不尽相同,这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百余年来的争论。1893年,比利时历史学家戈德弗鲁瓦·库尔特(Godefroid Kurth)在其著作《墨洛温王朝诗歌史》(Histoire poétique des Mérovingiens)中利用一些相关的辅助文献,对早期法兰克人的多位首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与考证,为之后早期法兰克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墨洛温先祖之间的亲属关系问题上,库尔特并未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此外,他并没有充分分析墨洛温先祖与墨洛温家族崛起之间的关系。Kurth, Godefroid. Histoire poétique des Mérovingiens.Bruxelles: Société belge de librairie, 1893, pp.133-208。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学者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墨洛温先祖史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第一,墨洛温先祖史事。Wood, Ian.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New York: Longman, 1994, pp. 36-38; James, Edward. The Franks.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1, pp. 51-58, 后文凡出自詹姆斯《法兰克人》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Chevallier, Béatrice. Clovis un roi européen. Paris: Brepols, 1996, pp. 24-30。事实上,虽说诸多著作都提到了墨洛温先祖的史事,但是,它们并未对墨洛温先祖的谱系进行详细的论证与分析。第二,墨洛维身世之谜。Wood, Ian. “Deconstructing the Merovingian Famil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exts, Resources and Artifacts. Ed. Richard Corradini, et al. Leiden: Brill, 2003, pp. 149-153。至于我国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较为稀少。②国内涉及墨洛温先祖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两篇。其一,李隆国在《〈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祖》一文中,对“格雷戈里命题”与“弗莱德加”给出的墨洛温先公先王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新的政治形势下,“弗莱德加”一方面通过增加故事,构建谱系为墨洛温王室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一代不如一代的传说故事,对后来诸王的统治无能表示了不满。李隆国:《〈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祖》,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83-92页。其二,陈文海在《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一文中,以多部原始史料为论证依托,从社会文化和史书编纂意图角度考察法兰克民族的起源问题,认为“特洛伊族源说”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以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出现于法兰克国家,既是法兰克社会、文化、宗教及族群走向综合与融通的一种反映,也是进一步推动法兰克社会聚合、增强法兰克集体意识的一种途径。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 10期,93-102页。不过,上述学术成果并未对墨洛温先祖谱系存在的争论、墨洛温先祖与墨洛温家族崛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的阐述与分析。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克洛维建国之前的墨洛温先祖,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早期法兰克政治史的发展脉络。
一、王族源流:法兰克史料中的墨洛温先祖谱系
一个家族的成功通常与其先祖的励精图治密不可分。然而,就口头传承而言,墨洛温先祖似乎已经无从寻觅,因此后人只能从文献资料当中去搜寻他们的蛛丝马迹。从存留下来的早期文本来看,最早明确记述墨洛温先祖的著作是 6世纪末成书的《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在该书第 2卷第 9章中,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38-594年)对法兰克人早期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与考证,但是,对于墨洛温先祖的具体谱系,他在表述上则显得颇为严谨,并且留有可供探究之处。7世纪中期成书的多卷本史书《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que de Frédégaire)不仅先后两次对法兰克族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而且在以《法兰克人史》为底本的第3卷中,对模糊不清的墨洛温先祖谱系进行了扩展,梳理出一幅较为明确的墨洛温先祖图谱。8世纪初期,佚名作者的《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则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先祖谱系。此外,还有几份墨洛温国王的谱系名单流传至今。因此,在对上述史料进行重新梳理与比较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墨洛温先祖的谱系脉络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相互矛盾之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以下文献资料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法兰克人史》中的先祖谱系。如前所述,关于墨洛温王族的先祖谱系,现存最早的文本当属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该书成书于公元6世纪末,共10卷,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公元594年。纵观全书,读者不难发现,除去宣扬天主教正统信仰的说教以外,法兰克人政治格局的变迁一直是格雷戈里叙史的主线。①关于《法兰克人史》的叙史主线问题,参见陈文海,《墨洛温王朝的“国土瓜分”问题——〈法兰克人史〉政治取向释读》,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118-120页。作为这一变迁的领导者,墨洛温先祖自然成为格雷戈里笔下早期法兰克人史事中的主角。他在引用编年史学家苏尔皮西乌斯·亚历山大(Sulpicius Alexander)的历史著作时提到,苏皮尔西乌斯在其著作中没有指出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国王,而是说他们在格诺鲍德(Genobaud)、马尔科梅(Marcomer)、松诺(Sunno)几位公爵的率领下,闯入日耳曼。②[法兰克]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4页。后文凡出自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此外,他还在《执政官录》(les Tables Consulaires)里找到了里歇梅尔(Richemer)之子提乌德梅尔(Theudemer)曾是法兰克国王的证据。(格雷戈里:69)不过,对于墨洛温先祖的详细谱系,格雷戈里显然保持着较为严谨的态度,对此问题的记述也更加谨慎。他在书中记述道:“按照传说,以才干卓异和门庭高贵而超越流俗的克洛吉奥(Clodio)做过法兰克人的国王,他住在图林根人所居地带的迪斯帕古姆(Dispargum)。”(格雷戈里:69)对于克洛吉奥的后代,他也只是表示:“有些人认为墨洛维(Merovech)——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父亲——属于他的家族。”(格雷戈里:70)
可见,根据《法兰克人史》第2卷中的相关记载,墨洛温先祖谱系可归结为里歇梅尔——提乌德梅尔——克洛吉奥——墨洛维——希尔德里克。然而,就格雷戈里在上述史料中的用词来看,除墨洛维与希尔德里克的父子关系较为明确之外,这一谱系中的其他亲属关系显然不够明确。在《法兰克人史》中,提乌德梅尔与克洛吉奥之间的关系、克洛吉奥与墨洛维之间的关系或是没有提及,或是传说,或是道听途说,并无其他史料可考。
其二,《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的先祖谱系。就墨洛温先祖的记载而言,图尔主教格雷戈里词严义密,在没有充足史料依据时,从不妄加揣测。然而,在墨洛温先祖史事的记述上,“弗莱德加”则不仅显得“胸有成竹”,而且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先祖谱系,即:提乌德梅尔生克洛吉奥,克洛吉奥生墨洛维,墨洛维生希尔德里克,希尔德里克生克洛维。①Frédégaire. 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II. MGH SRM II. Ed. Bruno Krusch.Hannover, 1888, pp.93-98。事实上,“弗莱德加”是近代西方学者为了指代《弗莱德加编年史》这套史书的作者所设定的名字,至于这套包含 6部编年史的著作,其作者的数量以及身份至今尚无定论。②学术界目前的主要观点有三种,即,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一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历史学家斐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马塞尔·博多(Marcel Baudot)和莱昂·勒维兰(Léon Levillain),丹麦历史学家阿尔瓦·埃里克森(Alvar Erikson)以及耶鲁大学教授沃尔特·高法特(Walter Goffart)。二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尔曼(Siegmund Hellmann)和华莱士-哈德里尔(J. M. Wallace-Hadrill)。关于他的二元论可参阅 Wallace-Hadrill, J. M., trans. and ed.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60, ix-lxvii。三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什(Bruno Krusch),参阅 Krush, Bruno. “Die Chronicae des sogenannten Fredegar.” Neues Archiv VII(1882), pp. 249-345;关于这些观点的详细阐述与分析,参见[法兰克]弗莱德加,《弗莱德加编年史》(第4卷及续编),陈文海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62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套史书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期,其6部编年史经后世史家整合为4卷本,其中,有关墨洛温先祖谱系的记述出现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当中。③Frédégaire. 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II. MGH SRM II. Ed. Bruno Krusch.Hannover, 1888, pp. 93-95。
从总体布局上讲,尽管该卷的底本为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但在墨洛温先祖谱系问题上,“弗莱德加”不仅“确认”了《法兰克人史》中记载的传说,而且,在原有墨洛温先祖史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扩展与补充。在“弗莱德加”的笔下,克洛吉奥成为了上接特洛伊王公贵胄下起墨洛温家族其他先祖的关键性人物。根据“弗莱德加”的记述,一方面,克洛吉奥的父亲提乌德梅尔(Theudemarem)属于普里阿摩斯(Priamum)、弗里加斯(Frigam)和法兰吉奥(Francionem)那一世系,且与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Aeneas)以及征服者亚历山大(Alexander)有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克洛吉奥的儿子叫墨洛维,正是依据这个名字,法兰克诸王后来被称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

表1 法兰克核心文献中的墨洛温先祖谱系① 上述三部史料中体现出来的先祖谱系如表 1所示。“?”代表不清楚两个先祖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先祖。无“?”之处,默认两个国王为父子关系。
其三,《法兰克人史纪》中的先祖谱系。公元8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境内出现了一部记述法兰克人历史变迁的“通史性著作”,即《法兰克人史纪事》。该著作共有53章,就本文内容而言,最具价值的当属作者在1-9章中给出的相对明确的墨洛温先祖谱系,即,法拉蒙(Faramundus)——克洛吉奥——墨洛维——希尔德里克——克洛维。②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MGH SRM II. Ed. Bruno Krusch. Hannover, 1888, pp. 241-251.只是在克洛吉奥与墨洛维之间的亲属关系上,这位匿 名作者并未严格地照搬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说法,认 为墨洛维确是出自克洛吉奥的家族。此外,作者还在王 位更替的过程中补充了不少链接性的政治事件,使得 早期法兰克人的政治更迭一气呵成、栩栩如生。然而, 对这位并不精通古代历史的匿名作者来讲,他很难以 真正的荷马式的真实性记述墨洛温先祖的历史,因此, 可以说,该著作虽具“荷马史诗”之型,却无“荷马史 诗”之魂。
其四,现存的墨洛温国王谱系手稿。第 一份手稿 A是德国历史学家贝尔茨(Georg Heinrich Pertz)于 19世纪前期在圣加仑(Saint Gallen)图书馆中 发现的,该手稿可能抄写于公元 9世纪的巴伐利亚 (Bavaria)。如图所示①手稿A来源: St. Gallen, Stiftsbibliothek, Cod. Sang. 732, p. 155。这张手稿可在下面的网址中获得:http://www.e-codices.unifr.ch/fr/csg/0732/155/0/Sequence-654。,手稿A中有关墨洛温先祖谱系的内容如下:

墨洛温国王谱系手稿A
“法兰克王国(谱系)。法兰克王国第一位国王是克洛吉奥。克洛吉奥生克洛多鲍德。克洛多鲍德生墨洛维。墨洛维生希尔德布里克。希尔德布里克生戈尼奥多。戈尼奥多生希尔德里克。希尔德里克生克洛维。”②该手稿中的拉丁原文如下:De regum Francorum. Primus rex Francorum. Chloio. Chloio genuit Glodobode. Ghlodobedus genuit Mereueo. Mereueus genuit Hilbricco. Hildebricus genuit Genniodo. Genniodus genuit Hilderico. Childericus genuit Chlodoueo. Chlodoueus genuit Theoderico, Chlomiro, Hildeberto, Hlodario.Chlodharius genuit Chariberto, Ghundrammo, Chilberico, Sigiberto. Sigebertus genuit Hildeberto. Hildebertus genuit Theodoberto & Theoderico. & ante Hilbericus genuit Hlodhario. Hlodharius genuit Dagabertum。
可见,在这份手稿中,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为克洛吉奥,但在克洛吉奥与墨洛维之间出现了一位名叫克洛多鲍德(Ghlodobedus)③按照字母音译,“Ghlodobedus”应译为戈洛多贝德,但是,考虑到中世纪时期拉丁文手写体的变化和抄写人的书写习惯,此处的“Ghlodobedus”应该与后文的“Chlodebaudus”为同一个人。因此,为了保持同一个人的译名相同,此处将“Ghlodobedus”译为克洛多鲍德。的国王,即,克洛吉奥之子,墨洛维之父。此外,在墨洛维与希尔德里克之间,还出现了另外两位国王,一位是墨洛维的儿子希尔德布里克(Hildebricus),另外一位是墨洛维的孙子、希尔德里克的生父戈尼奥多(Genniodus)。
第二份手稿B有两个版本,按照比利时历史学家库尔特的说法,第一版本B1和第二版本B2都抄写于公元10世纪,其中有关墨洛温先祖谱系的内容基本一致,即“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国王是法拉蒙;法拉蒙生克勒诺(Chlenus)和克洛吉奥;克洛吉奥生克洛多鲍德(Chlodebaudus);克洛多巴德生希尔德里克;希尔德里克生克洛维和克洛德玛尔(Chlodmarum)。”④手稿 B1 可参见 Généalogie B1, Paris, BnF, lat. 9654, fol. 121r: Primus rex Francorum Faramundus dictus est Faramundus genuit Cleno & Cludiono. Chludius genuit Chlodebaudo. Chlodebaudus genuit Chloderico.Chlodericus genuit Childeuio & Hlodmaro;手稿 B2 可参见 Généalogie B2, Paris, BnF, lat. 4628A, fol. 5v: Primus rex Francorum Faramundus dictus est Faramundus genuit Chlenum et Chlodionem. Chlodius genuit Chlodebaudum. Chlodebaudus genuit Chlodericum. Chlodericus genuit Chlodoueum et Chlodmarum。
概略而言,从以上有关墨洛温先祖的史料中,可以读出以下几点核心要素:第一,上述所有史料中都提到克洛吉奥是墨洛温家族的先祖。第二,克洛吉奥与墨洛维之间的亲属关系存在一定差异。格雷戈里认为墨洛维可能是克洛吉奥的亲属;“弗莱德加”认定克洛吉奥为墨洛维的父亲;《法兰克人史纪事》的作者则认定墨洛维出身于克洛吉奥的家族,但并未交代两者的具体亲属关系;手稿A认为克洛吉奥是墨洛维的祖父;手稿B的两个版本中则根本没有出现墨洛维的名字。第三,关于克洛多鲍德的记载存在差异。手稿A中出现的国王克洛多鲍德只出现在了手稿B的两个版本之中。前者认为他是克洛吉奥的儿子、墨洛维的父亲;后者虽认为他是克洛吉奥的儿子,但他并不是墨洛维的父亲,而是希尔德里克的父亲。不过,被手稿A纳入墨洛温先祖谱系的希尔德布里克和戈尼奥多两人,既没有出现在B手稿的两个版本中,也不曾出现在任何一份目前已发现的叙述性史料之中。第四,墨洛维与希尔德里克之间的关系并非“无懈可击”。从上述三部史料的字里行间来看,他们都很确定墨洛维就是希尔德里克的亲生父亲。正因如此,史学界通常认为墨洛维是希尔德里克的父亲。不过,就目前存留的墨洛温国王谱系的手稿来看,这种说法尚有待商榷。因为在手稿A和手稿B的两个版本中,没有一份手稿指明墨洛维是希尔德里克的父亲。尽管学者们目前无法证明这两份手稿的可信度,但也没有人能够拿出充足的证据否定它。
综上所述,除了上述三部史料给出的墨洛温先祖谱系以外,尚有多份墨洛温国王谱系的手稿流传至今。在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可以看出,这些谱系当中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相互矛盾之处,因此,墨洛温先祖谱系远非“弗莱德加”给出的那么清晰。甚至可以说,墨洛维是否真的存在于世间,也是一个令人疑惑不解的谜团。即便墨洛维真的存在,他与希尔德里克之间的父子关系也不能确定。不过,无论这些史料中给出的墨洛温先祖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世间,也无论他们之间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他们都为后世墨洛温家族的崛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王族崛起:从克洛吉奥到希尔德里克
虽然说克洛维继位之前曾有多位墨洛温先祖统治过滨海法兰克人,但诸如法拉蒙、克洛多鲍德等先祖的史事似乎已经难以寻觅。不过,就现有史料来看,自5世纪40年代至克洛维继位的这 40余年中,有三位先祖对墨洛温家族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克洛吉奥和希尔德里克这两位先祖都同罗马当局建立了一种较为牢固的同盟关系,从而加速了墨洛温王族崛起的步伐,而这一步伐与后世王族成员“西出图尔奈(Tournai),开创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墨洛维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则为后世墨洛温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墨洛温家族血统神圣性。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克洛吉奥与早期墨洛温王族领地合法化。根据《法兰克人史》的记载,身出名门的法兰克国王克洛吉奥以迪斯帕古姆为根据地,①关于迪斯帕古姆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大体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迪斯帕古姆位于莱茵河以东的图林根地区,主要依据是《法兰克人史纪》中的相关记述,参见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MGH SRM II. Ed. Bruno Krusch. Hannover, 1888, p.27。第二种观点认为迪斯帕古姆的位置无法确定。1893年,库尔特在其著作《墨洛温王朝诗歌史》中认为迪斯帕古姆的位置难以确定,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之地,参见 Kurth, Godefroid. Histoire poétique des Mérovingiens. Bruxelles: Société belge de librairie, p. 118;1896年他又在《建国者克洛维》(Clovis, le fondateur)一书中强调迪斯帕古姆只存在于墨洛温时代的诗歌之中,参见 Kurth, Godefroid. Clovis, le fondateur. Paris: Tallandier, 1896, p. 150;法国历史学家德穆若(Émilienne Demougeot)在其著作《欧洲的形成与蛮族入侵:从戴克里先登基到蛮族占领西罗马帝国》(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à l'occupation germanique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中指出迪斯帕古姆可能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边界上,参见 Demougeot,Émilienne. La formation de l'Europe et les invasions barbares: De l'avènement de Dioclétien à l'occupation germanique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 Vol. 2.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79, p. 489;波尔多诺弗(Georges Bordonove)也在其著作《克洛维与墨洛维王朝》(Clovis et les Mérovingiens)中写道:“克洛吉奥居住的迪斯帕古姆是一个无法被确定的地区。”Bordonove, Georges. Clovis et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Pygmalion, 1988,p. 35。第三种观点认为迪斯帕古姆位于今比利时的杜伊斯堡(Duisburg)地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皮埃尔·里什(Pierre Rhiché)和帕特里克·贝恩( Patrick Périn),他们在《法兰克人字典-墨洛温时代》(Dictionnaire des Francs - Les temps Mérovingiens)一书中极为肯定的认为迪斯帕古姆位于今比利时境内的杜伊斯堡,参见 Riché, Pierre, et Patrick Périn, Dictionnaire des Francs - Les temps Mérovingiens.Paris: Bartillat, p. 103。借助“蛮族迁徙”“帝国危机”等有利时机,同其他蛮族一样,开始在帝国境内谋求新的领地。①从5世纪开始,诸多蛮族再次向高卢地区进行大规模迁徙或入侵,其中包括后来在高卢建立政权西哥特人(Visigoths)、勃艮第人(Burgudians)等日耳曼蛮族,还包括匈国王阿提拉率领的匈人(Huns)。公元432-435年间,克洛吉奥率军侵入防守兵力薄弱的比利时第二行省,②关于克洛吉奥出兵比利时第二行省的时间,参见 Rouche, Michel. Clovis. Paris: Fayard, 1996, p.108;Rhiché, Pierre, et Patrick Périn, Dictionnaire des Francs - L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Bartillat, p.103。攻占康布雷(Cambrai)等地,并一度将领土向西南扩展至索姆河(la Somme)③索姆河位于法国北部地区,该河从皮卡第地区(la région Picardie)流入英吉利海峡的索姆湾,途经法国埃纳省(le département de l’Aisne)和索姆省(la département de la Somme)。流域。(格雷戈里:70)克洛吉奥的这次军事行动得到了罗马元老贵族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ine Apollinaire,生卒年约430-486)诗歌作品的印证。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拉丁语名字为:Caius Sollius Apollinaris Sidonius),公元430年出生在里昂的罗马元老世家,公元486年在克莱蒙(Clémont)去世,是罗马帝国晚期与中世纪早期著名的主教、政治家与作家。他的作品集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前夕与早期中世纪西欧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关于这位罗马显贵的生平与著作简介,参见Baret, M. Eugène. Œuvres de Sidoine Apollinaire Texte latin. Paris: Ernest Thorin, 1878, pp. 1-171。他在458年致马约里安(Majorianus,457-461年在位)的赞美诗中写道:马约里安在防御图尔(Tours)时,并没有和埃提乌斯(Aetius)在一起。此时,法兰克人在克洛吉奥的率领下侵入阿尔图瓦(Artois)⑤阿尔图瓦,位于法国北部,旧制度时期(Ancien Régime),该地原为法兰西王国的一个行省,现属法国加莱海峡省(Pas-de-Calais)的一部分。原野。马约里安与埃提乌斯迅速合兵一处,他们在一条河流附近的山丘上发现了正在高声庆祝一场蛮族婚礼的法兰克人。马约里安当机立断,向法兰克人发动突然袭击,后者惊慌失措,四处逃窜。①Baret, M. Eugène. Œuvres de Sidoine Apollinaire Texte latin. Paris: Ernest Thorin, 1878, p. 524。不过,当时罗马当局的实际控制者埃提乌斯并没有能力一举歼灭克洛吉奥统帅的滨海法兰克人,限于帝国军力,这位老谋深算的罗马元帅不得不用其惯用的外交手段与克洛吉奥签订了一纸盟约(Fœdus)②当罗马帝国皇帝无法压制日耳曼人时,便与他们签订被称作Fœdus的盟约,将他们视为同盟者,安置在帝国境内,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法律、习俗和首领。但是,这些同盟者需要为帝国提供军事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 Aldebert, Jacques, et al. ed. Histoire de l’Europe. Paris: Hachette, 1994, p. 93, 亦可参见该书的中文版:[法]J. 阿尔德伯特,[英]德尼兹·加尔亚等著《欧洲史》,蔡鸿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91 页。关于这份盟约的签订,参见 Rhiché, Pierre, et Patrick Périn, Dictionnaire des Francs - L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Bartillat, p.103。,令后者不仅成为了帝国的“同盟者”,而且获准“合法”占领图尔奈、阿拉斯(Arras)③阿拉斯位于法国北部,是现在法国加莱海峡省(Pas-de-Calais)的市镇。和康布雷等地。
埃提乌斯与克洛吉奥订立的盟约看似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实质上则是后者的胜利。这纸盟约不仅让他“合法”占据了曾经到手的土地及财富,而且还巩固了他身为法兰克首领的统治地位,因为绝大部分法兰克战士的“忠心”是用“赏赐”换来的,“贫穷”的首领很难得到战士们的青睐。此外,罗马“同盟者”的身份让克洛吉奥与罗马当局建立起军事互助关系,这也成为后世墨洛温家族率军参与罗马政府在高卢腹地的军事行动的有力契机。
第二,希尔德里克一世与墨洛温家族染指高卢腹地。自阿尔图瓦原野一役后,以墨洛温家族为核心的滨海法兰克人与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他们不仅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比利时第二行省,而且时常参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行动。451年,他们就曾与罗马勋贵埃提乌斯联合抗击匈人④按照《法兰克人史》的说法,沙隆战役中加入埃提乌斯一方的主要蛮族军队有两支:一支是西哥特人,他们的首领是在此战役中战死的提奥多里克一世(Theodoric I,418-451年在位);另外一支是法兰克人,其当时的首领身份不明。关于沙隆战役中的法兰克首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当时法兰克人的首领是墨洛维。此外,由于对学术界尚未确定中世纪早期出现在西欧的Huns是否与我国秦汉时期盘踞在北方草原的匈奴人有联系,因此,笔记将此处的Huns翻译成匈人。关于匈人起源的争议,参见[拜占庭]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VI-XII页。,并最终在沙隆战役中打败了可怕的“匈族大帝”阿提拉(Attila,434-453年在位)。(格雷戈里:61)对于罗马当局来讲,同墨洛温家族的合作并未使深陷危机的罗马高卢重获生机。但是,对于墨洛温家族来说,同罗马统治者的合作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约公元457年,希尔德里克继承滨海法兰克首领之位。起初,他并不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他曾因侮辱族人的女儿一度被罢黜王位,后在其忠诚的仆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东山再起。(格雷戈里:73-74)也许正是因为这段颇不平凡的经历,让希尔德里克幡然醒悟,从贪杯好色的庸主蜕变为精明能干的明君。他先是在公元463年借助哥特人入侵卢瓦尔河北岸之机,以罗马“同盟者”身份率军进入高卢腹地,与埃及迪乌斯(Aegidius)统领的罗马军队一起打退了西哥特人的这次进攻。埃及迪乌斯死后,这位干练的滨海法兰克国王与保罗伯爵合作,再次击败西哥特人。随后,他挥军西进,在保罗伯爵被杀之后,成功占领了昂热城(Angers)。此后,希尔德里克又与奥多亚克(Odovacer,476-493年在位)一起征服了曾经侵略过意大利一部分土地的阿勒曼尼人(Alamanni)。(格雷戈里:78)值得注意的是,据《圣格诺韦法传记》(La vie de sainte Geneviève)的记述,从465年开始,希尔德里克的军队似乎围困巴黎长达10年之久。①Pierre, R. P., trans. La vie de sainte Geneviève: écrite en latin dix-huit ans après sa mort. Paris: Perisse frères, 1859, p. 25。在此过程中,他不仅获得了比利时第二行省军事长官的职位,而且很有可能获得了来自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支持。②关于东罗马帝国对希尔德里克的支持,参见Wood, Ian.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New York: Longman, 1994, p. 40。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希尔德里克国王率领的滨海法兰克人已经越过了高卢北部的索姆河流域,开始向高卢腹地进军。在高卢西部,他攻占了昂热城,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卢瓦尔河下游的北岸地区;在高卢中北部,他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至巴黎周边地区;在高卢西南部,他的影响力已直抵阿尔卑斯山北麓地区。因此,正如爱德华·詹姆斯所说:“无论处于何种情况,我们都应该断定,在公元5世纪60-70年代,希尔德里克和他领导的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James:70)
第三,克洛维与墨洛温王族血统神圣性。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刚刚迈入“文明世界”的蛮族首领来讲,一种不可压制的直觉告诉他们,以武力为源泉的统治权力,绝不可能亘古长存。因此,他们急需借助某种方式来证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可以看出,刚刚建立政权不久的滨海法兰克首领已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具有足够统治权威的身份,即,被“神”赋予神秘力量的人。就现有史料来看,第一位被赋予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滨海法兰克人首领正是身世不明的墨洛维。
对于墨洛维的身世,格雷戈里似乎有所隐瞒,他仅表示有些人认为墨洛温出自克洛吉奥的家族。此处,格雷戈里用了“有些人认为”这一字眼,可见,在格雷戈里所处的时代,有关墨洛维的身世问题,至少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但格雷戈里对此守口如瓶。不过,在“弗莱德加”笔下,墨洛维的“诞生传奇”终究浮出水面,即墨洛维是克洛吉奥之妻所生,但其父却有可能是一头“牛头海怪”(Quinotaur)。③关于墨洛维的身世传奇,参见 Frédégaire. 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II.MGH SRM II. Ed. Bruno Krusch. Hannover, 1888, p. 95。比利时史学家库尔特(Godefriod Kurth)认为这个充满异教色彩的传说应该出现在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某个时间。格雷戈里之所以没有提及“另一些人”的说法,并不是因为他不清楚,而是因为这些人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弗莱德加”给出的充满异教色彩的神话故事。因此,作为天主教正统信仰的信奉者和正统天主教会的主教,格雷戈里当然不愿意相信这类异教神话故事,更不愿意将墨洛温家族的权力源泉与上帝以外的神明联系在一起。
然而,就该段故事而言,其最大的争论并不在于它出现的时间段,而是在于它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此举是为了神化墨洛温王族。他们认为“弗莱德加”添加这个神秘故事的目的在于说明墨洛温国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强调墨洛温国王统治权力的合法性。①关于这一观点,参见 Le Jan, Régine. “La sacralité de la royauté mérovingienne.” Annales. 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 6 (2003), pp. 1217-1241; Heuclin, Jean.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Ellipses, 2014, pp. 83-84;Demouy, Patrick. Le Sacre du Roi. Strasbourg: La Nuée Bleue, 2016, pp. 12-13。另一派则认为此举是为了贬低墨洛温国王。该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伊安·伍德。他在《解构墨洛温家族》(Deconstructing the Merovingian family)一文中明确指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三卷给出的这个故事存在诸多疑点,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神化墨洛温王族,而是为了嘲讽墨洛温王权的衰落,支持丕平家族的政变。不过,只要对早期法兰克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的写作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以伊安·伍德为代表的“贬低墨洛温王权说”的观点并不成立。
首先,“贬低墨洛温王权说”与“弗莱德加”构建的“特洛伊起源说”相互矛盾。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 3卷的相关描述中可以看出,“弗莱德加”不失时机地将墨洛温国王与“特洛伊起源说”联系在一起,即,在经历公爵统治之后,法兰克人还是从特洛伊世袭中推举出他们的新国王。“虽然这一王朝名曰‘墨洛温’,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万世一统、绵延不绝的‘特洛伊世系’。”②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97页。可见,“弗莱德加”在书中意在表明墨洛温家族世出名门,又怎会借墨洛维的身世来贬低自己赞许的家族?
其次,早期法兰克人有偶像崇拜的宗教仪式。在法兰克人皈依正统基督教之前,“这一族人似乎一向崇拜偶像,对真正的上帝毫无所知。他们把树林、河水、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自然要素都当做偶像,甘心奉若神明,加以崇拜,并且向他们供奉牺牲”(格雷戈里:70)。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早期的蛮族首领来讲,他们经常将自己或自己的家族与本族群崇拜的神明联系在一起,希望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巩固其自身或其家族在整个族群当中的领导地位。③伦巴德人将其族群名称的来源与奥丁神(Odin或Godan)联系在了一起。故事中讲道:当时汪达尔人要求伦巴德人的祖先交税,伦巴德人祖先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在日出时面朝东方,成为了第一个被奥丁神看到的人,奥丁神不仅赐予了他们langobardi的名字,而且还为他们带来了胜利。关于这一故事,详见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trans. William Dudley Foulk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P,1974, pp. 16-17。由此看来,上述故事的作用显而易见。墨洛维身世传说中出现的“牛头海怪”很有可能是早期法兰克人崇拜的神明之一。④这一推论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明。在希尔德里克一世的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牛面马具”。关于这件考古物品,参见 Kazanski, Michel, and Patrick Périn. “Le mobilier funéraire de la tombe de Childéric I;état de la question et perspectives.” Revue archéologique de Picardie N. 3-4 (1998), p. 17。通过这一超自然现象,墨洛维便与神明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达到了神化墨洛温家族的目的,有利于巩固墨洛温家族在法兰克人当中的领导地位。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血肉之躯,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影像,墨洛维对墨洛温王族的贡献都是不可替代的。克洛吉奥去世以后,其后继者极有可能借助墨洛维的身世传说,将自己与本民族崇拜的“海牛”联系在一起,把这一“神奇”的力量纳入王族政治架构中,证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弗莱德加”之所以收录墨洛温身世传说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贬低墨洛温王权,而是为了说明墨洛温王族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综上所述,公元5世纪中叶后,以墨洛温家族为核心的滨海法兰克人的活动范围不再只局限于地处高卢东北部的比利时第二行省,他们在希尔德里克的领导下,逐步向高卢腹地渗透。更为重要的是,墨洛维的身世传说把墨洛温家族同法兰克原始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权力披上了“合法”外衣。正因如此,可以说,克洛维一统高卢的壮举并不是万丈高楼平地而起,而是在站在历代墨洛温先祖的肩膀上向高卢宣布“墨洛温时代”的降临。
三、文化统合:墨洛温王族政治构架的初成
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初,无论是在罗马帝国西部还是罗马帝国东部,统治者们想要在整个帝国建立普遍权力的梦想愈加难以实现。帝国西部的衰落和日耳曼蛮族的大规模入侵浪潮使西欧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崛起的墨洛温政权积极地参与到西欧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他们长期唯帝国马首是瞻,最后将它彻底摧毁,但又仰慕其昔日璀璨的政治文明,这些举动加速了法兰克世界和罗马世界之间缓慢的相互渗透进程,这一进程也给西欧大陆带来了崭新的“法兰克传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的势力也完成了质的飞跃。君士坦丁(Constantinus,306-337年在位)时期的教会政策显然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此后,基督教不仅拥有了良好的传教环境,而且能够参与到罗马帝国的政治运转当中,并逐步成为帝国自治城市的主宰。
帝国覆灭之后,基督教会成为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它巧妙地运用自身的智识成功地“征服”了以墨洛温王族为统治核心的法兰克人,成为了法兰克世界与罗马世界之间的媒介。正统天主教的主教们在耐心引导墨洛温王国逐步踏入“文明王国”领域的同时,也在其政治构架当中注入了基督教元素。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有多种异质文化元素共存在于高卢社会政治舞台之上,但墨洛温先祖以及后世的开国之君克洛维都以恰当的方式逐步将上述三种异质文化元素统合在王族政治构架之中,为刚刚在高卢立足的墨洛温王国提供了长期统治该地区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其一,法兰克政治元素与罗马政治元素的统合。在西欧地区,法兰克政治文化与罗马政治文化都是在自身的地域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公元3世纪之前,两者之间可能并没有过多接触。就目前史料来看,尽管公元2世纪60年代的罗马军歌中出现了庆祝斩杀数千法兰克人的歌词,但直到公元289年,“法兰克人”这个名词才第一次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之中。(James:35)此后,有关罗马人战胜法兰克人的记载逐渐增多。例如: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an)在287年打败了法兰克“海盗”;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293-306年在位)将战败的法兰克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特里尔(Trier)等地,令他们承担军事义务。(James:38-39)可见,公元3世纪末到公元4世纪前期,罗马当局与法兰克人的关系比较紧张,两者之间冲突不断。不过,自 4世纪前期以后,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很多法兰克人加入到罗马军团当中与罗马军队共同作战,其中有不少人擢升至罗马高级官员,有的人甚至获得了执政官的头衔。(James:43,45)可见,在军事协助的基础上,一方面,罗马上层认同法兰人与自己同居高位;另一方面,法兰克人对罗马政治文化的认同度已逐渐加深。
及至公元5世纪中期,以墨洛温王族为统治核心的滨海法兰克人已经成为罗马当局主要依仗的日耳曼“蛮族”之一。他们时常以“同盟者”的身份派出军队协助罗马军团对抗其他蛮族。正因如此,罗马当局任命滨海法兰克首领为比利时第二行省总督,希望后者继续对它惟命是从。希尔德里克墓室中的文物足以说明墨洛温王族政治架构中的这一政治文化统合现象。1653年5月27号,考古学家们在图尔奈附近的斯海尔德河北岸发现了一座墨洛温时代的墓地。①关于法兰克首领希尔德里克一世墓地的状况,参见 Effros, Bonnie. Merovingian Mortuary Archa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lifornia: California UP, 2003, pp. 120-121。不幸的是,该墓地出土的文物在1831年11月5日或6日晚上被盗。偷窃者将很多珍贵的文物扔进了塞纳河中,因此,存留至今的文物已经屈指可数。尽管雅克·希弗莱(Jacques Chifflet)记录了当时出土文物,但这份文物名单名并不全面。关于希弗莱的著作,参见Chifflet, Jean-Jacques. Anastasis Childerici I, Francorum regis,sive Thesaurus sepulchralis Tornaci Nerviorum effossus et commentario illustratus. Antverpiæ: Ex Officina Plantiniana Balthasaris Moreti, 1655。在发掘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枚刻有CHILDERICI REGIS字样的指环印章,并以此认定这个墓地的主人正是希尔德里克国王。从这个指环印章上可以看出,希尔德里克不仅留有史料中记载的象征墨洛温王室成员的“长发”,手持法兰克长矛,而且还身着罗马将军战袍,而这一战袍很可能就是在他墓室中找到的象征罗马军事长官身份的紫色披风。(James:61-62)
克洛维上台以后,联合自己的亲属拉格纳卡尔(Ragnachar)消灭了西阿格里乌斯(Syagrius)统领的罗马残余势力,占领了苏瓦松及其周边地区,结束了滨海法兰克人与西罗马残余势力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格雷戈里:84-8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西阿格里乌斯统领的罗马残余势力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在政治或军事上满足滨海法兰克人的利益。对于一向本着典型实用主义的克洛维来讲,铲除西阿格里乌斯势力并不能说明法兰克元素与罗马元素已经到了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地步,反而从侧面反映出克洛维对罗马政治文明的迫切需求。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强大,引起东罗马皇帝的注意,以谋求在高卢罗马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抢占优势地位。他的这一愿望很快变为现实。
508年,克洛维在取得对哥特人的胜利之后,接到了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的敕书,受任执政官的职务,获得奥古斯都①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常被用来指代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屋大维,后来“奥古斯都”常用作罗马皇帝的头衔。寿纪瑜和戚国淦两位先生认为这个称号只有后来的法兰克国王采用,克洛维此时似乎不曾用过,这个称号也不大可能由皇帝赐赠。的称号,享誉整个高卢。(格雷戈里:101-102)此后,克洛维接连铲除了西吉贝尔特父子、卡拉里克、拉格纳卡尔以及威胁他统治的近支亲属,他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法兰克族群传统的多王统治形式,成为整个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国王。(格雷戈里:102-106)此时,对于法兰克人来讲,克洛维是他们高举在盾牌之上的合法国王,他们期待从他那里获得丰厚的赏赐;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讲,克洛维是阿纳斯塔西乌斯皇帝钦点的高官,它希望克洛维能够和其先祖一样,继续以罗马官员的身份与其保持联盟关系;对于罗马高卢人来讲,克洛维是身穿紫袍、头戴王冠的“执政官”,他们期待他们高呼的“奥古斯都”能给高卢带来新的生机。可见,墨洛温先祖以及开国之君克洛维利用法兰克国王与罗马高级官员的双重身份,很好地将罗马政治元素与法兰克政治元素统合在了一起,为后世墨洛温王族政治架构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法兰克政治元素与基督教政治元素的统合。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一神教,与早期法兰克人的偶像崇拜之间发生矛盾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教义和宗教观念上的互不相容,更是因为当时依靠罗马当局保护的正统基督教会带有某些现实性的痕迹。它不清楚被其视为“异教徒”(païen)的滨海法兰克人是否会像罗马帝国那样与其分享统治人民的权力。事实上,在西部帝国彻底崩溃之前,只有基督教会在精神上是坚强而富有生气的,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展现其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罗马城市当中,正是基督教会以其组织机构、市政官员有力地抵抗了帝国城市的崩溃。因此,已成为罗马城市实际掌控者的基督教会,并不希望失去自身在世俗政治当中的统治权力。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在写给克洛维的信中已经向日益强大的克洛维表露了基督教会的力量与愿望。
“……您应该倾听你的教士们,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在一起对您有好处,您的行省能够更好地得到维持。哺育民众,扶持被压迫者,照顾寡妇,抚养孤儿。如果能学习如何让所有人对您既爱且敬,会更好一些。司法公正出自您的嘴,不要觊觎穷人和外地人,以免你更加指望得到礼物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你的法庭应该欢迎所有人,以免有人悲伤而去。……如果想高贵地治理、裁决。那就与年轻人戏耍,与老年人交流。”②该部分内容的法文版可参见 Demouy, Patrick. Notre-Dame de Reims Sanctuaire de la royauté sacrée.Paris: CNRS, 2008, p. 104; 该内容的中文翻译详见李隆国:《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译释》,载《北大史学》2013年00期,255页。
从这份信件的部分内容中亦不难看出,在罗马社会政治文化中形成的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政治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它不仅能够以其政治才能为克洛维领导的滨海法兰克人全面打开罗马政治文明的大门,而且希望在此过程中继续保有自身在世俗世界中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尽管基督教元素与法兰克元素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甚至是敌对之处,但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撑的基督教会,只能暂时“抛去”与法兰克人之间的文化隔阂,以期寻求法兰克人保护。
对于在高卢立足未稳的墨洛温国王来讲,基督教会的态度显然为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融入高卢社会的机会。496年,在博学圣洁的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的支持下,克洛维率领约三千战士承认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受了洗礼,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国王。(格雷戈里:91)尽管克洛维的改宗行动并非出自对基督的信仰,但此举以恰当的方式将两种异质元素中的“神权政治理论”统合在了一起。对于依旧信仰异教的法兰克人来说,克洛维是一位拥有神秘力量的墨洛维的后代;对于寻求庇护的基督教会来讲,克洛维就是他们心目中“新的君士坦丁”;对于信仰正统基督教的高卢民众而言,克洛维则成为了上帝选派的新的牧羊人。
可以说,身为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基督教会与墨洛温王国在权力来源上的“合作”仅仅是三种文化元素统合的开始,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统合将继续深化,它们各自拥有的“王权政治理论”或“王权政治仪式”将成为未来墨洛温政治架构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对于中世纪早期的墨洛温王朝来说,它并不是罗马政治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西欧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兼具多元文化元素的新文明。
——读托马斯·克洛《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