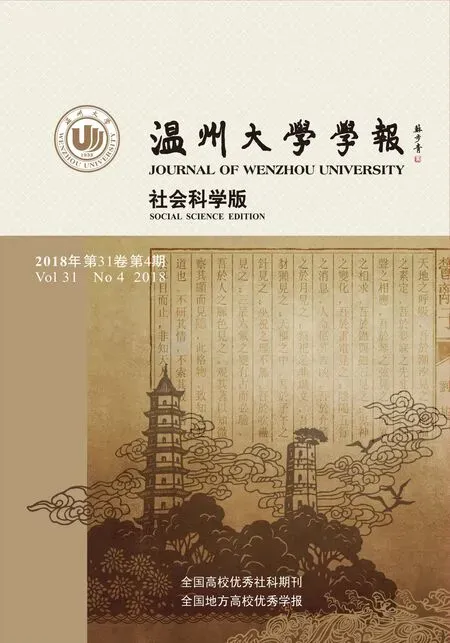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沿革初考
林清凉,陈 越
(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1121)
据《元史》中的有关记载,“余杭南山大普宁寺”曾是元代浙江地位显赫、规模庞大、影响极广的一座佛教寺院,也堪称当时非常活跃的汉传佛教活动中心。元代中期,南山大普宁寺及其附属寺院的僧众一度达到五千人,追随的信徒(时称“道民”)更是多达十万之众,其迅速膨胀的组织规模与影响力,使得当时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有所忌惮。不过从佛教史角度而言,普宁寺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在藏经刊刻。著名的元代私刻大藏经《普宁藏》(全称《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其刊刻工作就是由普宁寺主持开展的①有关《普宁藏》刊刻的组织工作,参见: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30-338。。
然而,由于普宁寺所属的宗派——白云宗,除了在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得到官方的短暂扶持之外,总体上未能获得中国历代佛教正统力量的认可,因此,历代史籍与佛教文献对普宁寺(以及以该寺为中心的白云宗)均语焉不详,以致对普宁寺这一曾经的佛教重镇,其兴废流变的具体过程与真实样貌一直存疑。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关于普宁寺的记载便鲜有内容上的更新,甚至“销声匿迹”,这一点颇为令人费解。本文拟结合前人相关研究,通过对包括正史、方志、佛教史籍、文人笔记等在内的各类文献的考证,将有关普宁寺的材料加以钩沉连缀,从而把普宁寺的历史沿革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由于这项工作在此之前尚无人尝试过,笔者所做的初步努力必有诸多未成熟之处,还俟方家不吝指正。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混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杭州市余杭区范围内,历史上被称作“普宁寺”的著名佛寺有两处:一处位于今余杭区仁和镇普宁村(古时属仁和县),由吴越国王钱元瓘创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3年),在《嘉靖仁和县志》中曾记为“普宁院”;另一处位于今余杭区瓶窑镇南山村(古时属余杭县),北宋末年由白云宗祖师孔清觉创建,此即元代的“余杭南山大普宁寺”。本文所要讨论的显然是后者。
一、普宁寺的兴衰与地方史志中“普宁寺”踪迹辨析
(一)普宁寺的渊源
关于元代“余杭南山大普宁寺”的前身,学界的意见,一般均认可是宋代僧人、白云宗开创者孔清觉的归葬之所。但对其具体的演变情况,长期以来却各执一词。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普宁寺初名“白云塔院”,后改“传灯”,再改“普安”,后于淳熙七年(1180年)改额为“普宁寺”。著名佛学家吕澂在《元刻普宁寺版藏经》一文中即主张“普宁寺的前身普安寺,原为白云宗创立者北宋清觉逝世后所建白云塔院的遗址”[1]。由朱金坤总主编的《运河梵隐》一书也认为:“南宋绍兴年间,白云塔院改称为传灯院。淳熙七年改称为普宁寺。”[2]
另一种说法则完全不提白云塔院,只认为普宁寺初名“传灯院”,后改为“普安院”,且最终变为“普宁寺”。持这一说法的人数最多。如《蒙元版刻综录》就采用“初名传灯院,淳熙七年改今名”[3]一说。
还有一种说法则白云塔院、传灯院二者均不提,直接认为普宁寺前身即为“普安院”。闫孟祥《宋代佛教史》一书就有“……建白云塔,筑普安院(即后之大普宁寺)”[4]340的说法。而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一文则更直接地认为“存放其舍利之塔曰白云,院曰普安,后其弟子改曰普宁”[5]。可见上述作者仅将白云塔视作一座灵骨塔,而非寺院,因此并不认可“白云塔院”的说法。
以上诸说中,普宁寺前身为“普安院”的说法应该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而“白云塔院”一说则较为可疑,因为无论是杭州或余杭的历代地方史志还是宋元以来的佛教史籍,均未见有关“白云塔院”的直接记载。我们知道,普宁寺在宋元时期是浙西一大教派——白云宗的主要寺院,其在创立之初即与白云宗创始者孔清觉密切相关。元代僧人觉岸撰写的编年体佛教史《释氏稽古略》中有“白云庵”一条,较详细记述了孔清觉如何创立白云宗以及其弟子建立该寺院的过程①参见:大正藏:第49册[M].886。:
白云庵,杭州灵隐寺方丈后山之庵也……有比丘曰清觉,自号本然……以寺后白云山庵居觉,玄化开阐,乃自立宗,以所居庵名为号,曰“白云宗”。移居余杭龙门山,庵曰福地,为龙神说三皈五戒;至是崇宁三年,至钱塘六和塔开化寺后紫云庵居.道俗请就正济寺讲《华严经》……至期乃化去,世寿七十九岁,僧腊五十二夏。弟子慧能禀遗训,奉灵骨舍利,归葬杭州余杭之南山,当宣和五年之二月也。塔曰“白云”,院曰“普安”,后弟子改曰“普宁”……
这几乎是现今可见到的对普宁寺源流进行追溯的最早记载,可以印证普宁寺是由普安院演变而来这一判断。其中文末有“塔曰白云,院曰普安,后弟子改曰普宁”,实际上已经指明了最初“白云”只是塔名,“普安”才是院名。由于孔清觉的弟子慧能于宣和五年(1123年)建此“白云塔”本是为了供奉孔清觉的灵骨舍利,而这时的“普安院”应是为了方便弟子瞻仰兼平时修行方便而设的居所(不同于后来的绍兴二十七年也即 1157年曾一度将整个宗教活动场所称作“普安院”),因此后世所称“白云塔院”可能只是对以白云塔为中心、包括白云塔和普安院在内的宗教活动场所的笼统称呼,而不是这一处所的正式称谓。
同时,我们再参考地方史志资料中有关普宁寺渊源的最早记载,也即明《成化杭州府志》中关于“南山普宁禅寺”的一段文字①参见:《成化杭州府志》:卷五十三:“南山普宁寺”条。:
南山普宁禅寺: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以居,绍兴间改庵为院,曰“传灯”,又改“普安”,淳熙七年改今额,元至正末毁,皇朝洪武三年重建,今为丛林。
此后历代方志包括《万历杭州府志》《万历余杭县志》《康熙杭州府志》《康熙余杭县志》《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杭州府志》《嘉庆余杭县志》乃至《民国杭州府志》中关于普宁寺演变的记录,差不多均与《成化杭州府志》中的这段文字大致相同。如《万历余杭县志》记为:“普安院②《万历余杭县志》分别记有“普安院”、“普宁禅寺”,但对二者历史及地理位置的描述均高度一致,应可判断为同一寺院。其中“普安院”条单列而未与“普宁禅寺”条合并,或因沿用旧志而误记。——笔者注: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通教大师创,改庵为院,一曰传灯。”《康熙杭州府志》则记为③参见:《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五:“南山普宁禅寺”条。:
南山普宁禅寺: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通教大师建,淳熙七年改今额,元末毁,明重建。归并者慧照塔院、定一院、松隐庵。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普宁寺的所在地,最早应该是孔清觉(白云通教大师)在世时于此“创庵以居”,至于这个庵的名字则不详,后来又于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改庵为院,院名先后有“传灯院”“普安院”等叫法,到了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最后改名为普宁寺。如果再结合《咸淳临安志》的记载:“普安院: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常熟乡,绍兴二十七年建请今额”④参见:《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三:“普安寺”条。,那么定名为“普安院”的时间应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此后尽管在淳熙七年(1180年)又改名为普宁寺,但至少一直到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还沿用过(也有可能是再度恢复过)“普安院”这一旧称。
值得注意的还有宋僧志磬撰写于宝祐六年(1258年)到咸淳五年(1269年)之间的重要佛教史著《佛祖统纪》,该书第 48卷载有白云宗请赐额一事:“嘉泰二年,余杭南山白云庵道民沈智元乞赐敕额。”[6]按理来说,沈智元“乞赐敕额”的嘉泰二年(1202年),距“改庵为院”的绍兴年间已经过去了至少约半个世纪,距改院为寺的淳熙七年(1180年)也已经有22年,为何还是用了“余杭南山白云庵”的称呼呢?这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寺院的正式命名与传统习惯称谓之间的纠结,即如今日杭州的“灵隐寺”与“云林禅寺”,以及“径山寺”与“万寿禅寺”之间的关系一般,正式的命名与改名,并不一定就能够完全终结人们原来对寺院的传统习惯称呼。而这正好反过来提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历代方志中所说的“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以居”的那个“庵”(同时也是历代方志所言“改庵为院”之“庵”)当初的名称,很可能就是“余杭南山白云庵”。这一点,从宋末元初普宁寺住持道安为孔清觉《白云和尚初学记》所作注中也可找到明确佐证[7]:
师初诞日有白云满室,因以白云自称,兹庵之名默与心契,从而居焉,由是白云之名,流芳益著,且白为众色之本,洁净无瑕之谓;云者,应用而来,来无所从,用谢而去,去无所至,而能含润法雨,益济万物,重重无尽,有云像焉……上清下觉,记主尊讳也,字本然,号白云,姓孔氏,即至圣文宣王五十二世孙也。
这段话很详细地讲述了孔清觉与“白云”二字极为深厚的因缘。首先因为有出生时“白云满室”的传奇故事,孔清觉才以“白云”自称;其次,“白为众色之本,洁净无瑕之谓”、“云者,应用而来,来无所从,用谢而去,去无所至,而能含润法雨,益济万物,重重无尽,有云像焉”,这就使得“白云”有着清晰的“表法”意味;再次,当时他之所以随顺因缘一度居于灵隐寺后山的“白云山庵”,也正是因为“兹庵之名默与心契,从而居焉”。这一系列情况表明,“白云”二字对于孔清觉而言,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宗教意象。这应该是这一宗派之所以被称作“白云宗”的根本原因(而非觉岸在《释氏稽古略》中所称只是“以所居庵名为号,曰‘白云宗’”),也是供奉孔清觉灵骨舍利的塔被其弟子命名为“白云塔”的原因。同样,孔清觉在余杭南山“创庵以居”之处,在经历了“改庵为院”、改院为寺的漫长历程后仍被当时的天台宗僧人志磬呼为“白云庵”,这似乎间接地表明当初孔清觉在南山所创庵的本名可能也正是“白云”二字。可惜目前仍缺乏充分的史料,难以对此加以确证。
(二)元代普宁寺的兴盛与衰亡
普宁寺真正的壮大发展,始于宋末元初。孔清觉创立的白云宗,在宋代虽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总体而言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白云宗不仅不被当时主流佛教界所接纳,而且也受到朝廷的多次严厉打压。信奉佛教同时对汉传佛教各宗又不持先入之见的蒙古人对南宋的军事征服,为白云宗境遇的改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此外,据有的学者考证,“西夏灭亡后,大量的僧侣从贺兰山南下杭州,加入了白云宗”[8],而在元代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西夏人的加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白云宗地位的提升。鉴于普宁寺在元代差不多一直是白云宗的管理中心和重要活动中心,在白云宗发展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中枢地位,我们梳理元代白云宗的历史,大体上也就同时再现了普宁寺在这一时期的兴败史。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6年),曾为西夏皇族宗亲的普宁寺住持道安(慧照大师)北上大都觐见忽必烈,希望朝廷准许普宁寺刊行大藏经。道安的建议得到了同样作为西夏遗民的佛教界权贵杨琏真迦等人的赞同,并最终获得忽必烈的恩准。白云宗也由此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从地下走向公开。获准刊行大藏经这一标志性事件,使得白云宗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而普宁寺成为大藏经的刊刻所在地,盛极一时。我们仅从《普宁藏》中的大藏经板记便可以看出当时刊雕经藏时的繁华景象:会同大普宁寺以外的其他众多寺院,邀请了诸多其他寺院的高僧大德,一起前来对经藏进行刊刻校对[9]330。除邀约各寺各方高僧共事外,当时为刊刻《普宁藏》还动用工匠数百,化缘僧侣涉及周边数个府县,其工程之浩大可见一斑。这套藏经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①《普宁藏》中最早题记记于至元十五年,故目前多认为《普宁藏》刊雕于至元十五年。详见:何梅,魏文星:元代普宁藏雕印考[J].佛学研究,1999:210-218。,刻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历时14年基本完成,以后又陆续刻印,直至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年),南山普宁寺总计刊印经文约1 532部5 996卷②关于《普宁藏》所收经卷数目,学界有多种说法,详见: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具体可参见该书第八章第一节。。其雕板为普宁寺住持道安及其继任者如一、如贤、如隐等发起募缘,以思溪、福州二藏校勘而成。《普宁藏》的刊刻,不仅有“庵院僧人、优婆塞”等大量“施力施财之士”的参与,还直接获得了西夏裔藏传佛教高僧胆巴国师和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的支持,二者分别以“功德主”和“都功德主”的身份具名,这实际上意味着《普宁藏》虽是私刻,但却得到了元朝官方的强有力扶持。元代雕印的大藏经存世甚少,惟《普宁藏》较为齐全,因此“元藏”几乎就是《普宁藏》的代称。后世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从距离浙西较远的山西、山东、陕西等地均出土了元刻本《普宁藏》,而清人毕沅所编《山左金石志》中收录的“灵岩寺广公提点寿碑”亦记载了位于山东济南地区、自唐代以后就曾位列“海内四大名刹”的灵岩寺,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专门派普觉禅师(广公)“领本寺数人,前往杭州南山普宁寺印经一大藏,渡江而北龛于灵岩”①参见: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清嘉庆刻本,第511页。,[10]511。我们据此可以大略推知普宁寺雕刻大藏经一事在当时所产生的“声名远播”的巨大影响力。除了编刻《普宁藏》,白云宗还参与了刊印西夏文《河西藏》、补刻南宋《碛砂藏》等事务,可谓功不可没[9]316-354。
道安觐见忽必烈以后,在余杭南山大普宁寺设立了掌管白云宗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白云宗僧录司(由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管辖),道安成为第一任僧录②此后白云宗僧录司的僧录一职,一般由普宁寺住持兼任,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主要有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普宁寺也由此得以迅速扩张,直至元代中前期,余杭南山大普宁寺已经拥有40座下院(即附属寺院),分别是孝慈院、广济院、资福院、雨化庵、真觉院、宝明院、普度院、致庆院、广远院、竹隐院、净福庵、常定院、积庆院、真庆院、真武庵、葛山院、妙德院、妙严院、妙圆院、十地院、普明院、庆福院、崇庆院、颐浩院、华严院、圆通院、志远院、嗣光院、庆寿院、普照院、崇福院、政山院、慈济院、政福院、福胜院、平湖院、普集院、万寿院、崇兴院、福地院等[9]331-332,散布在杭嘉湖一带。南山普宁寺成为白云宗的中心,其盛况一度如日中天。
白云宗势力的膨胀与扩张,直接招致了元政府的一系列打压。《元史》中有不少元中期以后政府对白云宗实施的限制性措施的记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中书左丞尚文“又奏斥罢南方白云宗,与民均事赋役”[10]2661,即要求白云宗道民与普通百姓一样向朝廷缴纳赋税,随后朝廷下令“罢江南白云宗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10]307,也即撤销其行政管理机构(摄所),取消其所拥有土地的免税特权。大德十年(1306年),又“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令输租”[10]316。不过此时的整顿多限于经济层面,对其社会声望和发展势头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并未撼动其合法地位,因此普宁寺的生存根基仍然稳固。
元武宗统治时期(1308–1311年),白云宗的地位有所上升。至大元年(1308年),“复立白云宗摄所,秩从一品,设官三员”[10]336。不仅恢复了大德年间被撤销的白云宗摄所,而且给予一品官阶,地位极高。只是第二年(l309年),又“罢杭州白云宗摄所,立湖广头陀禅录司”[10]346,刚复立才一年的白云宗摄所再度被裁撤。
元仁宗在位时期(l31l–1320年),朝廷对白云宗间施恩威,白云宗的发展也因此经历了几番起落。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白云宗以沈明仁为首,已形成一个近于“附佛外道”的世俗地主集团。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有御史台臣上奏:“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10]365当年四月,朝廷宣布“罢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头陀、白云宗诸司”[10]367。不过,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授白云宗主沈明仁荣禄大夫、司空”[10]386,其官阶为从一品,使白云宗领袖沈明仁的政治地位得以迅速恢复,在随后的延佑三年(1316年),竟“剃度游民四千八百余人”[11]。此外,还有“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诱愚俗十万人”[12]等说法。因此就在延祐三年,元仁宗命宣政院院使般剌脱因来到杭州整顿江南佛教,取消了白云宗都僧录司,命所集之僧归所籍之寺,所聚之民归所籍之州县。根据《元史》《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延祐六年(1319年),沈明仁终以“强夺民田”“诳诱愚俗”“私赂近侍”“妄受名爵”等罪入狱。次年(1320年)元英宗继位后,沈明仁以“不法”罪名被处死。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更是下令把白云宗田产全部籍没。时人对此事曾有记述:“湖州豪僧沈宗摄承杨总统之遗风,设教诱众,自称白云宗……及沈败,粮籍皆没入宫,后拨入寿安山寺,官复为经理。”[13]可见,由于土地、寺产被剥夺,白云宗的寺院经济遭到严重打压,尽管有些措施可能囿于某些实际情况而未能严格实行,但普宁寺随之走向没落已属必然。此后,白云宗在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3年)又略有恢复,并索还了部分原被官府籍没的田产,但总的来说大势已去。
从史料来看,白云宗主沈明仁应是白云宗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值得留意的是,得到朝廷认可并担任白云宗领袖的沈明仁,并非南山大普宁寺的住持,而是当时“湖州路归安县大慈隐寺”的住持,这可能表明,最迟在元仁宗时期,普宁寺在白云宗的核心地位已有所削弱。不过,从普宁寺比丘崇恩、普宁寺住持明实分别于延祐四年(1317年)、泰定元年(1324年)为“补刻入藏”的《景德传灯录》所作的题记来看,不论是沈明仁担任白云宗领袖期间,还是沈明仁被处死、白云宗受到严厉打压期间,《普宁藏》的续刻工作都仍然是在普宁寺进行;元宁宗元统三年(1335年),奉朝廷的命令,普宁寺还将《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续刊入藏,时“佛智妙应广福大师”、“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住持”明瑞还专门为此撰写了题记[9]325-326。这些事件说明,在白云宗由盛转衰之际,普宁寺仍然是白云宗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到了元末,饱经风雨而一蹶不振的普宁寺最终毁于战火。明代学者徐一燮《重刊中峰和尚广录序》一文曾记:“……镂版于杭之南山大普宁寺,未及广布而数遭小劫,板与寺俱毁。”[14]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对民间宗教秘密结社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以“禁淫祠”之名取缔各种宗教异端(“中书省臣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①参见:(明)雷礼:《皇明大政记》:卷二,明代万历刻本,第66页。),白云宗被列为“左道”,终于走向消亡。曾长期作为白云宗祖庭的普宁寺,也随着白云宗的被禁而无能复兴。
(三)明清时期普宁寺的重建、改宗、兼并、重修及“销声匿迹”
根据《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②参见:(明)刘惟谦:《大明律》:卷十二:《礼律二》,日本景明洪武刊本,第39页。因此,有明一代所有秘密教门,如白云宗、罗教、弘阳教、闻香教、黄天教等,皆在被禁之列,白云宗至此已基本停止了活动。根据《成化杭州府志》的记载,毁于战火的普宁寺,“洪武三年重建,今为丛林”,也就是说,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为跟白云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丛林”(对禅宗寺院的通称)。从地方史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洪武三年有大量被毁的寺院重建,普宁禅寺只是其中的一座。需要注意的是寺院名称的改变,从原来的“南山大普宁寺”自明代起变成了“南山普宁禅寺”。我们知道,孔清觉创立的白云宗被认为是华严宗的一支(尽管其所著《证宗论》已对传统华严宗有所背离),其基本教义是排斥和贬低禅宗的[4]341,而明、清方志中对普宁寺的称呼改为“普宁禅寺”,恰是洪武年间重建的普宁寺已改宗禅宗的一个重要证明。
《成化杭州府志》对“南山普宁禅寺”的记载,表明洪武年间重建的普宁寺,至少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仍然存在。明后期万历年间的《武林梵志》,对普宁寺亦有如是记述①参见:(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页。:
南山普宁禅寺:在县东北三十里常熟乡,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以居,隆兴间②此处原文有误,应为“绍兴间”。——笔者注改庵为院,曰传灯,又改普安,淳熙七年改今额,元至正末毁,洪武三年重建,归并与此,曰慧照塔院(在县东北三十里),曰定一院(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曰松隐庵(在县北七十五里)。
其中提到的“归并与此,曰慧照塔院,曰定一院,曰松隐庵”(《康熙杭州府志》则作“归并者慧照塔院、定一院、松隐庵”),表明还有三个寺院被普宁禅寺兼并。综观整个明清时期,这几乎是普宁寺在明初重建、改宗以来仅有的一次明显涉及扩大寺院规模的文字记录。《万历杭州府志》《万历余杭县志》所述更为简略,不过对其沿革的描述与《成化杭州府志》及前述《武林梵志》大体一样。但此后的方志,包括《康熙杭州府志》《康熙余杭县志》《乾隆杭州府志》,尽管仍会提及“南山普宁禅寺”,但内容却都完全照搬万历旧志所记,不复更新其中的内容。一直到了嘉庆年间所修的《余杭县志》,才再次出现一次“重修”的记录③参见:《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五:“寺观一”。:
南山普宁禅寺:在常熟乡瓶窑镇西,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以居,绍兴间改庵为院,曰传灯,又改普安,淳熙七年改今额,元末毁,明洪武三年重建,国朝嘉庆十年重修。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之间,仅从史料来看,普宁寺的发展历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不仅在方志中没有更新,在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发现有“余杭南山普宁禅寺”的记录。而且,自嘉庆十年重修之后,普宁寺在各类文献史料中再次“消失”,尽管修成并铅印于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杭州府志》仍照搬了《嘉庆余杭县志》中所记的“南山普宁禅寺”全部内容,但修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的《杭县志稿》却未见收录,我们可据此估计,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普宁寺可能已不复存在。
二、“南山寺”与南山普宁寺关系考辨
查考清代《康熙余杭县志》,其中有“南山寺”条,记为“在瓶窑镇西”④参见:《康熙余杭县志》:卷三,第39页。,不仅寺名为“南山”,而且在地理方位上与普宁寺完全相同。但是,《康熙余杭县志》在“南山寺”之外,还另外专门记述了“南山普宁禅寺”。也就是说,至少在康熙年间,方志的编撰者是把南山寺与南山普宁寺作为两座不同的寺庙来看待的。那么,南山寺与普宁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一)“南山寺”即是南山普宁寺
其实,早在明代文人田艺蘅的《游径山记》一文中,就已经提到了“南山寺”,其中甚至还有对该寺地理位置的简略描述⑤参见:(明)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八:“乙卯稿文”,明嘉靖刻本,第80页。:
丙午新霁,泛舟过小青坂,泊亭桥,游南山寺。寺在螺峰之北,由山趾折而东南观石佛,岩壁镌石佛像者二十有四,傍有石佛庵。南山僧鉴公邀酌,晚归已月印澄溪,舟影与山光荡漾,空明中矣……
戊申霁,买舟东归,过瓶窑镇……尽管全文主要讲述的是田艺蘅游径山的情况,但这段文字说的却是游径山途中,顺道游览瓶窑南山寺的有关情形及其在南山的交游纪实。就地理位置而言,文中有“买舟东归,过瓶窑镇”一语,而南山正是在瓶窑镇的西侧,位置上完全符合。其中还涉及“螺峰”“澄溪”两处地名,“澄溪”应为现在的苕溪。据明代郑麟《冷溪晚钓》一诗:“薄暮疏林挂日低,持竿闲坐傍澄溪。遥山螺髻云霞丽,隔岸人家烟火齐。攒食虾鱼影自乱,忘机鸥鹭伴堪携。扁舟罢钓归来晚,一曲沧浪浦水西。”①转引自:汪宏儿.南湖史话[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2。因宋时《咸淳临安志》“苕溪”条即谓:“又舆地志云,自县之西名冷溪,盖取清冷之意”②参见:《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山川:十五:“苕溪”条。,郑诗中的“冷溪”显然即是苕溪,其诗所述则为诗人在苕溪旁钓鱼的情形。如此,则诗中首句“持竿闲坐傍澄溪”中的“澄溪”,自然也就是苕溪了。田艺蘅所述“澄溪”,据此也应是苕溪。
此外,《游径山记》一文所描述的“(南山)寺在螺峰之北”,其中“螺峰”则应为现在的南山。瓶窑当地居民近年在南山北面挖地建房时,曾出土大量寺院遗物,据信很可能便是南山寺的遗存[15];而游记中所说的“由山趾折而东南观石佛”,更是在方位上与现存的南山造像完全一致,南山造像大致面南,但是的确偏向于东方,与其所述的“东南”符合;另,田艺蘅的游记中称东南侧有“石佛庵”,应为紧傍着南山寺的一个规模较小的寺院,考察现在的瓶窑南山摩崖三龛造像,其造像特征与南山造像主体迥然不同,有明显的明代风格,则应为此“石佛庵”另凿的造像;再者,文中又有“千仞石佛岩”的形容描述,意为佛像雕凿在石壁之上,瓶窑南山经过宋代采石之后,后来的摩崖造像的确雕凿于采石后留下的笔直崖壁上,这点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而且,从石佛的数量上来看,田艺蘅记为“二十有四”,据有关实地考察访谈记录,原来大约有30龛左右,20世纪后期被损毁了一半,至今比较完整的造像仍存13龛[16],因此佛像留存的数量也与田艺蘅的记录大体吻合。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相信《游径山记》中提到的石佛造像就是现在的瓶窑南山摩崖石刻,而这座“南山寺”所在的“螺峰”,则是普宁寺所在的南山。
实际上,田艺蘅不止一次提到“南山寺”,如他的《游南山寺鉴上人指十韵索诗》,文字中可见其与南山寺僧人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可能是由于受到其父田汝成的影响,田艺蘅的记述具有很强的“实录”特征,如《径山游记》中的有关文字,便是田艺蘅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十四日造访南山寺的日记[17],可靠性十分强。不仅如此,田艺蘅的好友蒋灼也在诗里提到“南山寺”,他在《闻田子艺御倭寇于瓶窑往访南山寺》诗中写道:“溪上悠悠鼓角鸣,知君已守此乡营。雨深客路曾分袂,夜静辕门独请缨。访旧偶从萧寺集,移尊还对竹堂清。相看况有参军在,好让穰苴奕世名。”③转引自:郑发楚,仲向平.西溪名人[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66。其中的“田子艺”即田艺蘅。根据诗题中的“往访南山寺”以及诗句“访旧偶从萧寺集”,我们可推断蒋、田二人曾在南山寺会面。
这表明,《康熙余杭县志》中所记的“南山寺”,不仅早在明代就已存在,而且其位置也正是在普宁寺所在的瓶窑南山,这跟作为白云宗普宁寺遗存的瓶窑南山造像在地理位置上恰好重叠。而在《嘉庆余杭县志》的“田艺蘅别墅”条中,记有田艺蘅别墅的地址,为“在寡山之东”①参见:《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七:“古迹”。。寡山在瓶窑东南侧,距瓶窑镇不过数里,可见田艺蘅实际上就住在附近,而蒋灼也居住在余杭方山,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情况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更何况田艺蘅当年组织义民抗击倭寇时就曾驻扎南山。从情理上说,田艺蘅对南山普宁寺的存在不可能毫不知情。
综上所述,田艺蘅数次造访南山,均只提“南山寺”,而对久负盛名、成化年间即“立为丛林”的南山普宁寺,他们竟只字未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连旁边毫无名气的小庙“石佛庵”都有幸被捎带提及),与此同时,田艺蘅所描述的“南山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造像景观特征上均与普宁寺的情况高度吻合,那么,我们能够对此作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南山寺”,实际上就是南山普宁寺。倘若如此,《康熙余杭县志》中把南山寺和普宁寺分而记之,可能就像《万历余杭县志》中错把普安院和普宁寺分开独立记述一样,同属误记。
(二)“南山寺”应为明清时期对普宁寺的民间俗称
在清代晚期绘制的余杭苕溪地图中,也标有“南山寺”。地图名为《杭属苕溪险塘图》,绘制于1885年,图中十分清楚地注明了“南山”以及“南山寺”,并在南山寺位置旁记有以下文字:“山腰多石壁,刊有石佛,岁久如新,不知始自何时,惜□□未志。”[18]此句所记即是现今仍可见到的瓶窑南山摩崖造像。从图上可以隐约看到,“南山寺”坐落在南山的北侧,与前文提到的田艺蘅的记述完全相同。
该地图上方题有一则《杭属苕溪险塘图说》,其中说道[19]:
……水入内河,不特钱、余两邑受累无穷,而仁和、德清亦波及之。嘉、湖形势最低,俨成泽国矣。仆平日未谙水利,虽得父老传言,茫无头绪。壬午中夏,险塘大溃。钱邑尊赵,会商于善堂,大绅集款修筑。蒙遣执鞭历游数十里,遍访二三年,始得粗知大略,爰将耳目所克及者,集绘成图,以供同心共览。
苕溪小隐、布帆无恙子谨绘,并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得知绘制者自称“苕溪小隐、布帆无恙子”,而绘制缘由是“险塘大溃”。很明显,此地图是民间自发绘制的。那么,就像前文曾经提到过的余杭“万寿禅寺”因地处径山而通常被称人们作“径山寺”一样,“南山寺”是否就是“南山普宁禅寺”的民间称谓呢?因为普宁禅寺就建在南山上,而且历来就是南山上规模较大的代表性寺院。我们无论是从明代文人田艺蘅的记述中,还是从清代后期的地图记录中,都可以推断出“南山寺”应该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跟倚傍一侧的“石佛庵”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凡是前往南山实地考察过的人都知道,南山规模很小,乃至于在历代的山川记载中都没有把这样的小山记录在内②历代《余杭县志》与《杭州府志》的山川章中都未收录“南山”。,所以不可能有像“南山寺”和“普宁禅寺”这样的两座大寺同时存在。所谓“南山寺”与“普宁禅寺”,二者只能是同寺而异名。如此,则《康熙余杭县志》中将“南山普宁禅寺”与“南山寺”分开记述的做法,实为误记。这也正好可以用来解释《康熙余杭县志》中“南山寺”条的一些疑点:一般方志记载某个寺院,总要叙述一下其历史渊源,且在记录寺院方位时也通常以县治所在地作为坐标的原点,如记为“县东北三十里”等,而《康熙余杭县志》记录的“南山寺”只有“瓶窑镇西”四字,既显得过于简略,也违背了通常以县治来确立方位坐标的惯例,令人不禁怀疑记述者是否只是从当地民众的口中听说瓶窑镇西侧有个“南山寺”而已。除《康熙余杭县志》外,其他相关方志均未收录“南山寺”条,这应该是后来的编撰者在修《乾隆杭州府志》《嘉庆余杭县志》时发现了这一错误,故没有在“南山普宁禅寺”之外另对“南山寺”作单独收录。
(三)清代后期“南山寺”的衰败
在明代中后期,被称作“南山寺”的南山普宁禅寺应该发展较为顺利,还不时有田艺蘅这样的文人去喝茶谈诗,可见其寺僧也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从清代开始,随着瓶窑地区其他寺院如真寂寺的兴起,南山寺已逐渐走下坡路。到了清代末年,随着一波又一波毁佛运动的发生,南山寺也迅速衰败。但作为一个寺院,南山寺在清末仍然存在。
民国时期曾任教于华北弘道院的翁楚望先生在其《任芝卿与衢州教案》一文中,记录了发生在南山寺与清末著名牧师任芝卿之间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对清末南山寺的没落有部分述及[20]:
又如余杭瓶窑南山寺因和地方人士发生产业纠纷,引起争执,该寺住持来杭求见任芝卿支持,愿意入教还俗,任以将该寺全部房屋田地山林等悉数捐助为条件,同意所请,给以名片一张报县息案,借此又吞没了大量产业。
文中提到的任芝卿(1870–1929年)系江苏人,为内地最早的本土传教士之一。他主要在杭州地区传教,大约于1903–1915年间势力达到顶峰①1903年“衢州教案”一事平息后,任芝卿地位上升。详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103。。上面这段文字,直接指出当时的南山寺住持为了获得任芝卿的支持,“愿意入教还俗”,也就是说,通过该住持还俗并加入基督教,同时将寺院房产地产捐出,从而借任芝卿之力,平息了原来南山寺与地方人士之间的产业纠纷。这种通过承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可谓极不寻常,究其原因,应与清末佛教风雨飘摇的社会处境相关。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凡太平军途经的寺院即遭受重大打击,“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②转引自:夏维中.南京通史清代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443。,又对庵观寺庙的田产进行了剥夺[21],而杭州正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此后,一些本已衰弱不堪的佛教寺院,在戊戌变法之后兴起的“庙产兴学”运动中又一次遭遇灭顶之灾。前面这段文字所提到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段文字尽管没有记载南山寺住持与任芝卿之间谈话的具体时间,但结合这一时代背景可以大致推知。南山寺住持与地方人士发生的“产业纠纷”,应为寺庙田产房屋的纠纷。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地寺院与地方人士的此类纠纷,多起源于1898年清政府在康有为、张之洞的建议下发起的“庙产兴学”运动。所谓“庙产兴学”,是指用寺院财产兴办新式学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说:“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22]此项提议在实施之初便受到了各地乡绅的积极拥护,不难看出庙产兴学一事实质上也关系着当地政府之利益,故强占强夺事件层出不穷。尽管 1905年因浙江杭州有 30余座寺院自愿寄名于日本东本愿寺下以寻求保护,从而引起清政府的不安,随后发布了一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借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的规定③转引自:杨健: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58。,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1906年侵占寺产的情况有所好转之外,总体来说这一规定的效果并不显著,剥夺寺产事件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反而加剧。这一状况直至 1912年起才开始有所缓解,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废止僧官制度,成立佛教总会,且发出公告明令禁止侵占寺产事件,至1914年全国寺产方渐趋稳定[23]。根据以上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任芝卿的个人情况可以推知,南山寺住持与任芝卿打交道的时间,应为1898年到1914年之间,同时,南山寺的房产、田产也是在这时全部捐出。这应该是南山寺(也即普宁禅寺)历史上所遭遇的最后一劫。因此,编撰于民国时期的《杭县志稿》未再收录有关“南山寺”或是“南山普宁禅寺”的内容,可见该寺在民国年间没有得到恢复或重建。
三、小 结
普宁寺所在的余杭南山(即现在的瓶窑南山),至今还留存有佛像、菩萨像以及真武大帝像等十余龛摩崖造像,这些造像体型巨大,线条遒劲,在造像内容构成上有着较为明显的白云宗信仰特征,且其中的两处元代题记均刻于普宁寺在南山居主导地位期间,因此研究界一般认为该造像群实际上就是元代余杭南山大普宁寺的造像遗存。该造像群被命名为“瓶窑南山摩崖石刻”,于1997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面考察南山普宁寺的历史脉络,不仅对我们认识宋元时期白云宗的起源与流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探究“瓶窑南山摩崖石刻”的宗教史、艺术史、文化史价值,也无疑是必需的。
根据前面的详细考论,笔者认为,余杭南山普宁寺的历史沿革大致如下(见图1):其前身最初为孔清觉创建于余杭南山的一座小庵,名称可能是“白云庵”;孔清觉去世后,这里成为他的归葬之所,在原庵址上建有白云塔和普安院;绍兴年间,此庵开始改称“传灯院”,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又改名为“普安院”;至淳熙七年(1180年)改额为普宁寺;元代,普宁寺随着白云宗的发展而进入鼎盛期,不仅成功刊刻了《普宁藏》,而且一度成为白云宗的管理中心,但在元中后期开始衰落,至元末被战火所毁;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为“南山普宁禅寺”,此时应该已经与白云宗无关,而一变为禅宗寺院;明中期有慧照塔院、定一院与松隐院合并于南山普宁禅寺,该寺规模再次扩大;明中后期,普宁禅寺尽管正式名称未变,但在民间已逐渐被称作“南山寺”,该名称在清代亦被沿用;清嘉庆十年(1805年),普宁禅寺得到重修;清代后期,普宁禅寺渐趋衰败,大约于20世纪初僧散寺亡。

图1 余杭南山普宁寺沿革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