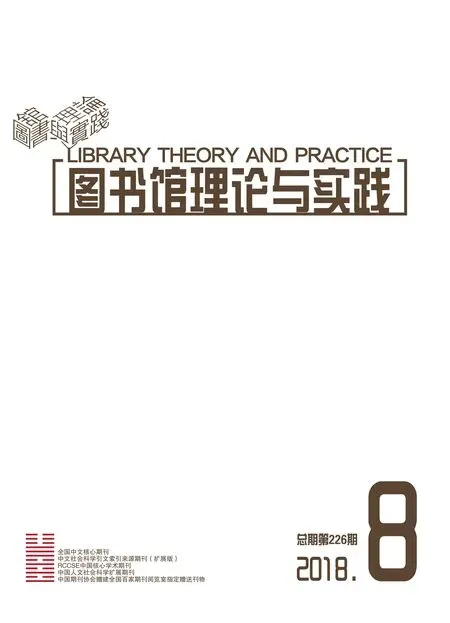《苍颉篇》之流传与“苍颉、仓颉”孰是考
孙新梅
(河南省图书馆)
1 “苍颉”之成书与流传考
《苍颉篇》,秦李斯所作。此书何以“苍颉”为名?古代字书大多以起首二字名篇,今存之《急就篇》,首句为“急就奇觚与众异”[1]可证。经书之名篇,亦常用篇首之字,《诗·关雎》 《论语·学而》皆是其例。王国维以为,“《苍颉篇》首句当云‘苍颉作书’”,[2]1972至1974年发现的居延新简载“苍颉作书,以教后嗣”[3](此简编号为EPT50.1A)二句,既证王氏之说,亦证古代字书命名之特点。
《苍颉篇》,《汉志》录之。班固《汉志·六艺略·小学类》小序言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4]1721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言仿此。则《苍颉》《爰历》《博学》三篇皆是在周代童蒙字书《史籀篇》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算是《史籀篇》的选编、修订本,用秦篆书写,秦篆即小篆。秦统一六国后需要对文字进行规范,是编纂这三篇字书的主要原因。后世所言之“苍颉篇”,一般非单指“李苍”,而是此三篇的合称。到了今天,为了与汉代学者改编、增补的“苍颉篇”进行区分,也将李斯等人的三篇称为“秦三苍”。秦代国祚仅14年,“秦三苍”的推广情况与正字作用到底如何,难得其详。《苍颉篇》的广泛流传当在汉代,汉代在将它作为童蒙字书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编、增补和注释。班固《汉志》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按:西汉平帝年号)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按: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按:正确识读)者,张敝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4]1721
据班固所言,汉初闾里书师(按:后世之私塾先生)将“秦三苍”合为一篇,仍名《苍颉篇》。此合编本打乱秦本次序、篇章,定60字为一章,凡55章。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一枚三棱觚(按:觚,古人用以书写或记事的木简。此觚编号为9.1),其上抄写有《苍颉篇》第五章,每面20字,三面恰60字。正合《汉志》所言书师合编本各章字数。《苍颉篇》在汉初合编之后,不断有新的增补本、选编本、续编本出现。如,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的《急就篇》、成帝时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以及班固的《训纂篇》续本等。然而流传至今的惟有史游的《急就篇》了。
《凡将篇》算是《苍颉篇》的增补本,收字或不与《苍颉篇》重复;《急就篇》《元尚篇》,主要是选择《苍颉篇》中的正字(按:字形符合标准的字)重新编排而成,算是《苍颉篇》的选编本。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急就》《元尚》,字皆在《苍颉》三千三百之中,《凡将》则颇有增多《苍颉》者”。[5]扬雄《训纂篇》是汇编西汉元始间有用之存字,以续《苍颉篇》,并且将《苍颉篇》中重复之字改为新字。闾里书师合编本原作55章(3,300字),《训纂篇》作为续编,凡34章(2,040字。按:扬书是否每章60字,并无文献记载。前人如王国维、姚明辉、张舜徽者多以书师本每章60字,而认为顺续之诸本皆每章60字,姑暂从之。以下班固续本、贾鲂续本、贾鲂合编本字数之计算,皆仿此)。扬书34章与其修订之书师55章本合编行世,总89章。而后班固续扬雄《训纂篇》,又增13章(780字)。
东汉和帝时,贾鲂又扩充班固续本13章为34章,名《滂熹篇》。唐人张怀瓘《书断》卷下“能品”云:“贾鲂又撰异字,取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之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是《训纂篇》末尾二字作“滂熹”也。《书断》卷上“隶书”云:“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苍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所谓《三苍》也。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6]可以看出,贾鲂不惟扩充班固续本,更为合编之事。贾鲂之后再无增补“苍颉”者。是“三苍”之名,当自贾鲂而始也。此“三苍”总123章(7,380字),《隋志》以三卷著录,并云郭璞注。今人为与“秦三苍”区别,亦呼之为“汉三苍”,也有“五苍”的叫法,合李斯《苍颉》、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扬雄《训纂》、贾鲂《滂熹》五书言之。
虽说“三苍”至于贾鲂为备,但此123章本恐怕已非童蒙所习之书,此本字数达到7,380字,断不能作为蒙学读物。因此怀疑扬雄之89章(5,340字)本,已经失去了识字功用,而被作为字典一类的工具书来使用。在西汉元帝时史游之《急就篇》出现后,童蒙所习者乃是史书;到了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行世之后,童蒙所诵更是周书。[7]
为便观览,将秦汉“苍颉”之演变过程,推动其演变之责任者、责任方式,各书之章数、字数列于下表 (见表 1)。[8]

表1 秦汉“苍颉”演变过程
2 “苍颉”之注本考
“苍颉”不惟原文本在流传,由汉至晋还出现了六个注本。《汉志》中著录《苍颉传》一篇,不题撰人名氏,谢启昆《小学考》以为扬雄所作,张舜徽非之,张说甚是,此注当本之闾里书师本。《汉志》于扬雄《训纂篇》外另记扬雄《苍颉训纂》,是前者乃扬雄所续之89章本,而后者为扬雄自注之89章本。《汉志》还著录杜林《苍颉训纂》《苍颉故》各一篇。关于杜林《苍颉训纂》,王先谦认为“此盖于扬雄所作外,别有增益,故各自为书”。[9]窃以为王先谦于此未得《汉志》体例,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汉志》小学类共著录12种书,其中扬雄、杜林各有2种,故云“凡小学十家”。[4]1720《汉志》所录之后4种,皆当训释“苍颉”之书,即《苍颉传》、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杜林《苍颉故》,有意者可覆按。是班固认为此4书之地位未可与前8种诸如《苍颉》《凡将》等原文之书等量齐观,即后4种注释本之地位低于前8种原文本之地位,班书体例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这里还有个疑问,杜林的注本为什么会有两种?笔者认为,其《训纂》或训《苍颉》之秦篆本,其《故》或诂《苍颉》之汉隶本也,此则正应《小序》所言“杜林为作《训》《故》”[4]1721者也。《隋志》 云:“梁有 《苍颉》 二篇,后汉司空杜林注,亡”,[10]942两《唐志》复以《苍颉训诂》二卷著录,是杜林注本流传甚久。阮《录》云二篇,两《唐志》云二卷者,恰与《汉志》所云《训纂》《故》各一篇暗合。据王国维《重辑苍颉篇·叙录》,杜林所注当汉初闾里书师合编之55章本,最初的合编本自然秦篆所书,汉隶盛行之后自有隶变之本,是秦篆本、汉隶本在杜林之时皆存。综上所述,汉代人不仅增补、修订了《苍颉篇》,还为《苍颉篇》作注,使其逐渐成为一部形义兼具的训诂书籍。
此外,“三苍”尚有三国魏张揖注本,《旧唐志》以《三苍训诂》二卷著录,《新唐志》以为三卷,当据二卷本所析。晋郭璞亦有注本,《隋志》以三卷录之,两《唐志》仍之。据王国维说,张、郭所注为扬雄89章本。然而笔者的认识与王国维有所不同,如以“三苍”之名始于贾鲂为断,张揖、郭璞所注当为贾鲂合编之123章本,且《隋志》明云“《三苍》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 《滂熹篇》,故曰‘三苍’”[10]942者也。自郭璞以后,再未见注释“苍颉”者。列“苍颉”注本于下表(见表2)。

表2 “苍颉”注本
3 “苍颉”之亡佚考
关于“苍颉”之亡佚情况,王国维认为:“《训纂》先亡,至隋而《苍颉故》亦亡,张、郭之书,至唐末而亦亡”。[11]笔者与王国维的看法有所不同。杜林之注,《隋志》确云梁有而今亡,而两《唐志》复以二卷著录,盖宋初尚存。《隋志》失载或云亡之书,而《唐志》复载者不惟此一种,至于张揖、郭璞注本,两《唐志》皆录之,亦宋初尚存。王国维言“苍颉”之亡佚仅此短短22言,是其并未致力于“苍颉何时亡佚”之研究。今人主王氏此“隋唐”说者,藉静安先生名重耳,为佐证王说,发挥诸多臆断之辞。关于“苍颉”的亡佚,孙星衍认为:“杜林《故》亡于隋,《仓颉》《三仓》及《故》亡于宋”。[12]孙氏所云,甚是模糊,首先其上句“杜林《故》亡于隋”的说法非是,详上;而下句复言“《故》亡于宋”,此《故》又应何书所言耶?关于“苍颉”之亡佚,试陈管见。
窃以为李斯《苍颉篇》7章之单行本,在汉初书师合编本出现后,即开始慢慢散亡。至于班固之时,或已未见单行本,《汉志》将《爰历》《博学》置于《苍颉》之下皆不独为一条,即此之故。想来总“三苍”为童蒙字书,非独“李苍”为童蒙字书,童蒙学习时自然以使用“三苍”为便,故弃之“李苍”,情理之中。是故,书师合编之“三苍”盛行之后,“李苍”单行本则渐渐散亡。
书师“三苍”单行本之慢慢散亡,当在东汉杜林注本盛行之后,此前已述杜林注本据书师“三苍”。兼之书师“三苍”与《训纂》《滂熹》合编之后,更是加剧了单行本散亡的速度,最迟至于唐代,书师“三苍”单行本散亡殆尽。
扬雄《训纂篇》89章单行本,最迟至于唐代散亡殆尽,《隋志》不录是其证。贾鲂“三苍”123章单行本,最迟至于唐代散亡殆尽,《隋志》不录是其证。
另,司马相如《凡将篇》、李长《元尚篇》之亡佚,亦当在唐代之前,《隋志》不录是其证。至于杜林、张揖、郭璞三家注本,前已述,皆亡于宋。
概言之,“李苍”7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西汉时候;书师“三苍”55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扬雄89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贾鲂“三苍”123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杜、张、郭三家4种注本,皆亡于宋。为何强调各书“单行本之不存”,是各书单行本虽散亡,而赖合编本或注本以传。如,“李苍”在书师“三苍”中,书师“三苍”在杜林注本中;扬雄本在贾鲂“三苍”中,贾鲂“三苍”在张揖、郭璞二注中。实者,言“李苍”、书师“三苍”、扬雄本、贾鲂“三苍”皆亡于宋亦无不妥。
4 “苍颉、仓颉”孰是考
“苍颉”,亦有写作“仓颉”者。许慎《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段玉裁注:“‘仓’,或作‘苍’。按《广韵》云:‘仓,姓,仓颉之后。’则作‘苍’非也”。[13]并举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晋卫恒《四体书势》所引为证。殊不知晋时书证依然太晚,何况《广韵》更是宋时书耶,段说非是,以下详述。清人任兆麟补正任大椿所辑《苍颉篇》篇首题名下高承勲按:“‘苍’字从《汉志》。孙星衍本作‘仓’,非”。[14]是高承勲以“苍颉”为正。高氏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仅以《汉志》为据,不能服人。若欲发难高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言班固《汉书》中亦有“仓颉”的用法,则高氏的论证方法则不攻自破。今人鲜有讨论“苍颉、仓颉”孰是者,惟孙淑霞《汉简〈苍颉篇〉辑校》第一章第二节《汉简〈苍颉篇〉的篇名》稍有提及,言:“苍颉,又作仓颉。苍、仓,没有统一的用字”。[15]这是一种无奈之下强为调和的做法,言之无物,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一书之名应该是惟一的,既然流行两种写法,必有一种是三人成虎之误说。如今可通过调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征引“苍颉、仓颉”的情况,来判断二者到底孰是孰非,以及非者出现的时间。
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调查,可以得到确切的结论,“苍颉”为正,“仓颉”为非。西汉以前包括西汉在内的文献中,皆书作“苍颉”。如,《鹖冠子》凡4引,《近迭》“苍颉作法,书从甲子,成史李官,苍颉不道,然非苍颉,文墨不起”,《王鈇》“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16]《吕氏春秋》凡1引,《君守》“奚仲作车,苍颉作书”。[17]《韩非子》凡2引,《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18]以上三者皆先秦之书。再如,《淮南子》凡3引,《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务训》“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泰族训》“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19]《法言》凡1引,《吾子》“或欲学《苍颉》《史篇》”。[20]以上二者皆西汉之书。截至西汉,并无“仓颉”的写法,追本溯源,则“苍颉”为正。
那么“仓颉”的写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笔者认为,或肇自东汉王充《论衡》与班固《汉书》。《论衡·别通》“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感虚》“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言其应仓颉作书,虚也。……图书文章,与仓颉所作字画何以异?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或时仓颉适作书,天适雨粟,鬼偶夜哭”;《骨相》“苍颉四目,为黄帝史”,《奇怪》“苍颉作书,与事相连”。[21]此王充《论衡》并引“苍颉、仓颉”,王书引“苍颉”5次,引“仓颉”15次,此不一一表出。《汉书》引“仓颉”两次,《扬雄传赞》“史篇莫善于《仓颉》,作 《训纂》”,[4]3583《武五子传赞》“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4]2771引“苍颉”12次,皆在《艺文志》,前《流传考》《注本考》述之甚详,此不赘述。是班固《汉书》亦并引“苍颉、仓颉”,由此可以看出,“仓颉”的写法始于东汉,王充、班固二人或即误写之始作俑者。
至于许慎之时,《说文解字》亦将二者并用。《许慎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斯作《仓颉篇》。……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卷八下“秃”字“王育说‘苍颉出见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卷九上“厶”字“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22]许慎《说文解字》作为流传至今的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果说王、班二氏或误写之始作俑者,那么许慎就是这个错误的推而广者。自东汉以后“苍颉、仓颉”更是混用、滥用了。
虽说如此,东汉以后就没有人对“仓颉”产生过怀疑吗?没有人认为当作“苍颉”,或“苍颉”为是的可能性更大吗?通过调查发现,不仅有人而且是有一批人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审慎的做法。从班固说起,他虽然在整部《汉书》中并用二者,然而其《艺文志》部分皆用“苍颉”,后世之《隋志》、两《唐志》亦皆题“苍颉”。
另外,作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十三经,其注、疏在引用“苍颉”时也是非常慎重的。如,《尚书》《毛诗》之孔颖达正义,《周礼》之郑玄注、贾公彦疏,《春秋左氏传》之孔颖达正义,《春秋公羊传》之徐彦疏,《孝经》之邢昺疏,《尔雅》之郭璞注、邢昺疏,皆引作“苍颉”。对于注、疏所引“苍颉”的次数,总40次。如,《左传·庄十八年》孔疏“《苍颉篇》‘’作‘珏’”,《宣十五年》孔疏“许慎《说文序》云‘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谓之文’”,[23]实际上《说文序》此处本作“仓颉”,恐怕是孔颖达认为“仓颉”有问题,而改作了“苍颉”。再如,《尔雅·释亲》郭注“《苍颉篇》曰‘考妣延年’”等。[24]毋庸讳言,十三经注、疏中也有引作“仓颉”者,然而仅有2次,《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引《仓颉篇》1次,《论语序》邢昺疏引“仓颉”1次。也就是说注、疏所引“苍颉、仓颉”的比例为四十比二,所以注者与疏者对于二者何者为是的认识,虽非毫无瑕疵,但还是有着一定判断的。
随着朝代的更迭,由于众口一词,积非成是的缘故,到了清代,即令高明如段玉裁者,也未能批沙沥金、究其本源,反倒以误为正,以“仓颉”为是,致使清代成为“苍颉、仓颉”滥用的重灾区。何者?清代考据、辑佚之学发达,多有从事“苍颉”之辑佚者,然而误题书名者不在少数。如,任大椿辑王念孙校之《仓颉篇》二卷、附《仓颉训诂》《仓颉解诂》;《三仓》二卷、附《三仓训诂》《三仓解诂》,孙星衍所辑《仓颉篇》三卷,黄奭所辑《仓颉篇》一卷、郭璞《仓颉解诂》一卷、郭璞《三仓解诂》一卷,皆误写书名之例。并不惟此四人误写,下文《“苍颉”之后人辑本考》于清人辑本广有搜罗,谨供覆按,此不一一。任大椿、孙星衍等人都是清代考据学、辑佚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的一流学者,他们也没有搞清“苍颉、仓颉”谁对谁错,这是我们迫不及待对于这个问题理而董之的原因之一。
5 “苍颉”之后人辑本考
关于《苍颉篇》一书的重要性,历来学者素有认知。清代以降,广有从事《苍颉》《三苍》及其注本之辑佚者。诸家竞相搜佚,试图得到一个完备的本子,以窥其原貌。然而《苍颉篇》屡经增改,各书征引或出李斯原本,或出增改之本,或出扬、杜、张、郭各家注本,来源甚杂。据笔者统计,前此从事“苍颉”之辑佚者共有21人,“苍颉”“三苍”并注本之辑本,达30余种。
任大椿辑王念孙校《仓颉篇》二卷(附《仓颉训诂》《仓颉解诂》)、《三仓》二卷(附《三仓训诂》《三仓解诂》),收入《小学钩沉》。任大椿考逸、任兆麟补正《苍颉篇》二卷、《三苍》二卷,此本参考了任大椿辑本,故题任大椿考逸,然多有新辑与补正,可视为一新辑本,收入《有竹居集》。顾震福辑《仓颉篇》《仓颉解诂》《三仓》以及郭璞《三仓解诂》,此本在任大椿辑本基础上复广事搜辑,收入《小学钩沉续编》。以上属于任大椿辑本系统。
孙星衍辑《仓颉篇》三卷,收入《岱南阁丛书》。孙星衍辑、梁章钜校证并补遗《仓颉篇校证》三卷、《补遗》一卷,有清光绪五年(1879)梁恭辰刻本。陈其荣增订孙星衍辑本《仓颉篇》三卷,收入《观自得斋丛书》。孙星衍辑诸可宝续陶方琦补《仓颉篇》三卷、《续本》一卷、《补本》二卷,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江苏书局刻本(按: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收陶方奇辑、姚振宗编录之《仓颉篇续辑》)。曹元忠续陶方琦补本《仓颉篇补本续》一卷,收入《南菁札记》。叶大庄《仓颉篇义证》三卷、《校义》二卷、《笺释》一卷,有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以上属于孙星衍辑本系统。
其余尚有王绍兰辑《杜林训诂逸文》一卷,有《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书七种》本。马国翰辑《苍颉篇(张揖训诂、郭璞解诂)》一卷、扬雄《训纂篇》一卷、杜林《苍颉训诂》一卷、《三苍(张揖训诂、郭璞解诂)》一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黄奭辑《仓颉篇》一卷、扬雄《苍颉训纂》一卷、郭璞《仓颉解诂》一卷、郭璞《三仓解诂》一卷,有《黄氏逸书考》本。龙璋辑《仓颉篇》二卷、《三仓》一卷,有《小学蒐逸》本。郑文焯《扬雄训纂篇考》一卷,有《大鹤山房全书》本。王仁俊辑《仓颉篇》三卷,《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目录》题“别行”,王氏辑本或未行世。王国维《重辑苍颉篇》二卷,有《王国维全集》本。姬觉弥《重辑苍颉篇》二卷,有民国九年广仓学宭排印本,原书所题责任者为姬觉弥,实则即王国维辑本。别有臧礼堂《增订苍颉篇》三卷、程廷献《苍颉篇辑本》、龚道耕《苍颉篇补本续》一卷、陈荛春辑《苍颉篇逸文》者,以上四种辑本,据1987年6月 《汉学研究 (第5卷第1期)》中,林素清《〈苍颉篇〉研究》一文所录,未详所据。臧本与龚本当亦属孙星衍辑本系统。
笔者广泛调查“苍颉”辑本的原因,一百年来,大家沉醉于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对近在眼前的传世文献则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大道甚夷而民好径”[25]的表现。出土文献乃吉光片羽,自然弥足珍贵,但绝不应该忽视诸多“苍颉”辑本的研究。出土文献中,北大简本《苍颉篇》字数最多,1,300余字,而王国维辑本倍之有余,着实不敢偏废。希望通过本次对于“苍颉”辑本的梳理,推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苍颉篇》研究的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