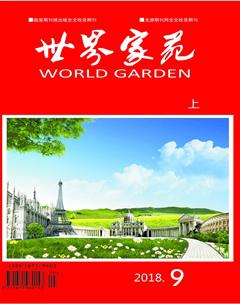论《推拿》对底层社会尊严的关注
郭有志
新世纪文学一般都具有一种个人化的写作立场,而在“进入到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共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描写一种残疾人根本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在共名状态下,根本不能“名正言顺”的存在。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商品化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导致“无名状态”的出现,因为在当今时代,即多元化社会,一种简单或者说单一的价值观根本不能笼罩全社会,所以个人立场的写作蓬勃发展起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朱文的《食指》和《尖锐之秋》等等作品都展现出了个人化的写作力场。在时代的影响下,《推拿》这种作品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同样获奖的还有莫言的《蛙》和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优秀作品。这次评奖与前七次评奖的机制完全不同,评委来自于各类职业,评委群体相对前几届来说层次安排更加合理。从以上三部获奖作品看来,“本次茅盾文学奖并不把‘宏大和‘史诗性作为评判的唯一尺度,他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多元化寫作,既强调获奖作品的精神内涵,也强调作品的文学品质。”《推拿》是一部以描写沙宗琪推拿中心的盲人推拿师为主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有王大夫、小孔、沙复明、张宗琪、都红、徐泰来、金嫣等人物。在这篇小说的描写中,不仅有对盲人的心理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而且“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形、事业追求、生理欲望以及真挚的情感、纯洁的友谊、坚贞的爱情等都有细致的描绘。”
何谓尊严,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与定义。毕飞宇曾经说过:“尊严感不是某一个人的特异功能,它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如何面对“尊严”,呈现“尊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之一。”
作者毕飞宇作为一名“后先锋”作家,具有很强的观察力,他观察到了底层社会的尊严问题。进入新世纪,““面对现实”仍是判断文学价值的首要标准。”毕飞宇的一直延续着现实主义的传统,一部作品如果完全脱离现实,那么其价值也微乎其微,艺术一定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毕飞宇的“现实主义”落脚在对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关注上。”在《推拿》中更注重的是对底层社会尊严的书写。《推拿》中,作者成功的刻画了一个盲人推拿师都红,都红作为一个音乐天才,能很简单的唱准音高和音程,自从弹了一段巴赫之后,主持人的话让她厌恶了音乐。“可怜的都红”是为了“报答全社会——每一个爷爷奶奶、每一个叔叔阿姨、每一个哥哥姐姐、每一个弟弟妹妹——对她的关爱”!主持人的话让都红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是报答?报答谁呢?她欠谁了?她什么时候亏欠的?还是“全社会”。”这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盲人,甚至是残疾人群体,都已经被社会打造成了一种“弱势群体”。盲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情爱,有欲望。他们也是一群正常的人。《推拿》中的这种隐喻在笔者看来,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平等和对人性意识的呼唤,表现出作者拒绝差异化,拒绝尊严的压迫。
盲人在马路上行走需要有盲道的帮助才能更加顺畅,盲人回家需要健全人引领才能准确返航,盲人的床位需要固定在墙上才能安全……诸如此类,都证明了盲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看似正常的人就没有局限吗?不。科学研究证明,人的眼睛之所以等看见东西,光的反射与折射帮助很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就是一个几乎没有光的世界,一个看似健全的人也就等于一个盲人,没有光的辅助,眼球就失去了作用。这就证明了,人都有局限性。而盲人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他们成为“异类”的依据,而只能看做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在某些程度上,“正常人”比盲人更有局限性,小马作为一名后盲者,才能对让时间做到如影随形。而社会与个人往往强加给盲人一些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怜悯,甚至是压迫,对盲人,甚至很多残疾人一种心灵上的压力与压迫。作者之所以刻画都红这个形象,其实也是为了说明一些东西。盲人也有尊严,但是盲人的尊严感往往比平常人要强很多,这种近乎自卫般的尊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种不安全感和不平等感而造成的。小说中很多描写都体现出了一种写作立场,即“人类的写作立场”,即将人类平等化,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并不是一种写作技巧的渲染。作者还列举了一些反面人物来表现一些没有尊严的人。例如王大夫的弟弟和弟媳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凡此种种描写,都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力和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盲人尊严的关注。
在报纸,杂志上,很少能见到关于盲人的报道,而盲人群体也经常被人们所忽略。不得不承认,盲人生活在底层社会。而对底层社会的描写无非就是为底层人民博得社会同情。但《推拿》不同于其他作品,这部作品是对盲人的“日常化”书写。在底层题材的书写过程中,如何尊重真实生活,应该是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毕飞宇就是底层社会书写的集大成者。“《推拿》叙述的是盲人的生存境遇,但是其话语压抑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确是普遍性的,小说的价值和内涵因此获得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描写底层社会的作品当中,很多普通人的写作动机甚至作家的写作动机无外乎两个字“怜悯”。虽然怜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美德,它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情感,但是不要把怜悯当做恩赐,要处理好怜悯的表现手法。《推拿》里面描写的小孔手的变形,和沙复明拖垮的身体,都是展现出作者“怜悯”的一面。但是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度,即“他对“怜悯”保持着一种十分警惕的态度。”这种度的把握体现了作者强大的人文精神。
对盲人,往往人们会强加一种弱者形象,做什么事都是要报答社会,报答每个人。而很少有人关注盲人真正的生活与内心,盲人有其生活的规律与方式,盲人有其自己的尊严与底线,都红因为一次演出主持人的“表现”从此对音乐失去兴趣,感到恶心;而王大夫还想花自己的钱为其弟还债,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对人性本身的漠视,也就是普世价值的缺失。《推拿》完全的展示出了一种对普世价值的关注,对人性的真实描写与思考。而这种普世价值对于底层社会的意义更巨大。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36.
2.说法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36.
3.张莉.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史意义[J].文学与文化,2011(04):15.
4.李斌.荡气回肠的人格尊严——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论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60.
5.张莉 毕飞宇.理解力比想象力更重要——对话《推拿》[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29.
6.说法参见孟繁华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11.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4.
8.张莉.论毕飞宇兼及一种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实践意义[J].文艺争鸣,2008(12):45.
9.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4.
10.同9
11.俞佩淋.探寻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读毕飞宇的《推拿》兼谈底层文学创作[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37.
12同11.39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