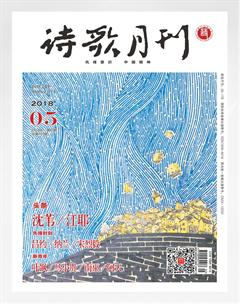约翰·海恩斯诗选
[美国]约翰·海恩斯著 史春波译

预言
一种孤独而浩大的力量
在黄昏时分割大地。
九年来我一直在观看
从内部的一道门:
像一幅混沌图景,
似人的形体在逼近,遮住
他们的脸,不停走着,
铁和距离使他们沉重。
没有声音,除了风
横吹路面,用白垩般细微的尘土
填充车辙。
仿佛内部的门在关闭,
一天迎来它黑暗的
旅程,身后的九座桥
——摧折。
夜间动物的声响
看不见的翅膀扫过
头顶的叶簇;霜
在兽蹄下碎裂,河水流动着
汇入郊狠的孤鸣。
创门踩着月光行走,
我们借着跳跃的营火
来去,身体里的鬼
怀揣巨大、受伤的心。
诗
那即将袭来的
严冬的巨大悲伤
悬挂在空气里
这阴沉的九月。
今天一条泥泞的路
粘满落叶,明日
冻硬的土地
和一只足印
將发出冰的釉光。
透过来的太阳
依旧暖和,而路
陷在影子里;
你的手在我的手中发冷。
我们的桨果已摘下,
蘑菇也采好,
我们各自在心里
藏起一小块
夏天,
就像老鼠把根茎
储存在
唯有它们知道的地方。
我们相信还未降临的生命,
当一棵光秃的树
默默站立在
变黑的树叶上;
但此时在那条路的转弯处
停下脚步聆听:
一只南飞的鸟
它奇异的歌声
涨满
静寂的黄昏
正从那棵树梢
流淌。
写在陶渊明之后
这绝非第一次
我在荒野中独眠。
高草怀着沉沉的草籽
把影子投上石碑,
风将盘问白杨
然后留下我独行。
九月在即,催种子
入土地——路过的小鸟
搅动落叶瑟瑟。
那些带我到这里的
必将消散,回归各自的屋宇,
各自的生计。
独自在沙子的黑暗中
我将躺卧千年,
千年没有温暖
没有触摸,千年
不语。
暮色中的李煜
香气自玫瑰飘落。
冰雨,
东风撒播
一千颗种子……
一切事物之光,
你凋零。
洒掉的牛奶
每当我看见牛奶洒在桌上,
又一只玻璃杯打翻,
我会想起那些徒劳的奶牛。
多少吨草料被用尽,
多少奶牛的乳房被注满再挤空,
森林一片接一片
砍光了制成纸箱,
成千上万支蜡烛在消融……
一大张洒满牛奶的桌布
铺在全世界的餐桌上,
有个孩子站着
手中拿一块浸透的海绵,
说他不是故意的。
你肩上的太阳
我们挨着在草丛里躺下,
睡一会然后醒来,
仰面看三叶草
和箭一样的叶片,
看树叶和云朵
黯淡、毛茸茸的腹面。
成为一粒种子真神奇,
面对整个生命的成长,
就像童年时
一切事物都很近
又很远,
一只徐徐爬行的昆虫
一堂无声的课。
可能不会再有
明澈如水的眼神,
你肩上的太阳,
当我们站起身来
抖落满身的草,
高高的在这初放的绿色清晨。
宇宙尘,一首小诗
从垂死的星体的残骸
这场粒子雨下下来
用光明浇灌空虚……
原子的海浪急着回家,
巨星崩塌,
不安定的客人无力久留……
太阳的心脏变红,膨胀,
他强大的气息在延续,
而他物质的外壳
终有一日将蒙上白霜。
在猎户座光热的领域
群星在聚合,
正如我们每天夜里所见,
炽烈,至死不渝。
从冰冷的逃逸的尘埃
那未在和永在,
静寂与空虚将到来……
这臂膊,这手,
我的声音,你的脸,这爱。
梦游者
那曾分配给埃及的时间
叫作睡梦,
而行走在那里的人
叫梦游者。
大步穿过滚烫的尘雾
在泛着蓝色釉光的夏天,
穿过守时的洪水,
穿过沙暴和热病。
存在,睡觉,苏醒……
那是一只昆虫的天赋。
带着闪光的鹰眼
和朱鹭的喙;
带着粗砺的狗的舌头;
然而比它们全都强大
漂流与寂静的法则
透过芦苇的私语
和不歇止的犬吠
传入耳中。
黄昏,一个王朝在归返,
比黎明更广阔,
在没有屋顶的神庙,书吏
和猴子祭司整理了鸟
的肠子;顺着一根烟柱
陶土的灵魂攀爬,
从光与莲花中诞生。
然后,在石头的
绿色心脏,终于入眠。
跻身不安的,被太阳驱逐的中间,
成为那个治愈的、久驻的
男人:守灵人的王。
夜是一条眼镜蛇,盘成
一个永恒的双结;
在睡眠中保持对称,
浸满毒液,等待着
最先醒来的法老。
原注:这首诗是对一些埃及神话和宗教现象的糅合,也是对奥
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重要小说《梦游者》的间接引用。
命运女神
阿特罗波斯或命运女神
——戈雅
北即是东,南即是西
开始是底下,上面
是结束——符咒撒光了
我们失去了魔力。
我们是你眼中所见的燕子
有被裁过的舌头,
被修剪过的翅膀,
挨挤着栖在电线上。
我們是天使中的老处女
被上帝驱逐:
我们保全了我们的剪刀
携带了我们的针——
四个老妇人在纺织
纺织着风,
然后随一阵狂怒的咕哝
把线从云彩中抽去。
我们不再于门廊上
静坐,也不再与
树和枝桠打交道。
日光对我们有害,
夜晚则更加美好:
星辰纷纷坠落,
狮子与天蝎西沉……
想想你的房间吧
还有你的家具,
叠好你的床
揣起你的钥匙:
你们当中有影子的
将继续与之为伴,你们
没影子的即将死去:
这块玻璃,我们透过它
来观看,这些孔洞
全由我们制造。
再看我们盘绕、扭织的
丝线,我们啐出的
词语,我们掷出的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