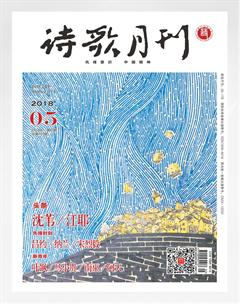沈苇访谈: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
沈苇 张杰
问:西域与江南,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的张力,在您的生命里,恰恰是滋养了你的文学写作。您认可吗?您可以具体展开谈一下您的感受。
答:我离开浙江到新疆已30个年头了。大学四年主要写小说,进疆后才开始写诗,所以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诗歌浪潮没有参与。30年中我写了1500多首诗,有一半是新疆题材,还有一半难于归类。如果30年前不到新疆,我同样会写诗,但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写法、现在这个沈苇。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如你说的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张力,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我是差异性的受益者,也是分裂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域分裂症”患者,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中间有鸿沟,有裂痕。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变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我的“地域分裂症”。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我在1990年代提出“综合抒情”“混血写作”,针对当时的抒情与叙事之争、学院与民间之争,更主要是直指并弥合自己的“地域分裂症”。
问:您一般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写出一首诗。比如先有一个感觉,写出几行字,然后再修改?还是要考虑成熟再下笔?
答:一首诗的诞生有其复杂性,也有一些基本规律,但可以谈论,你说到的情况都存在。我可以试着这么回答:一首诗的诞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得益于持久的期待,长期的沉思和观察,是耐心的產物;一首诗可能诞生于一次旅途、一次阅读,当我们凝视风景时也被风景凝视和庇护,当我们读到一本好书时,往往会被一个句子、一个词点亮;一首诗也会诞生于一次生活的变迁和变故,一次情感的波澜,一次书房里的枯坐……总而言之,一首诗诞生于虚无,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
问:您曾经说,在去楼兰之前,写了不少关于楼兰的诗,但终于去了之后,发现写不出诗,只能写写游记散文了。您怎么看待诗的神秘性?
答: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力的势力范围,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不必夸大诗的神秘性,我也不太赞同诗的可计划性,但“工作”一词还是蛮喜欢的,创造性劳动就是工作吧?诗歌容易被“灵感说”“迷狂说”误导,自然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神秘化了。爱伦·坡是“灵感说”和“迷狂说”的率先反对者,他说,大多数诗人喜欢让读者相信“他们是在一种美妙的癫狂状态下创作他们的作品的,他们的创作受到了一种自我沉迷的灵感的激发……”,今天仍有一些诗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喜欢在写作和生活上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做一位诗人,首先要做到不装神弄鬼,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两百年前爱伦·坡的观点对现当代诗人影响很大。罗丹曾说“永远工作”,茨维达耶娃把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手艺》,把诗歌创作比作手艺活,“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我是手艺人——我精通手艺。”(《尘世的特征》)。我倾向于认为,诗歌是“工作”也是“手艺”。
问:您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到鲁迅文学奖。但我看到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沈苇作为一个优秀诗人,一直没受到足够的关注度。对诗歌与名气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答:我觉得自己的关注度还不错嘛,出过七八部诗集,得过国内几个重要文学奖项,几位我尊敬的诗评家撰写过非常好的评论。我不知道“关注度”是指发表数量、媒体曝光率、公众前的露面机会,还是因为我远居新疆、孤悬塞外容易被人遗忘?远离中心有远离中心的好处,沉下心来,旁观潮流,看风云变幻。诗歌无需讨好大众,却需要寻找自己的“精选读者”,面对“广大的少数人”。我有我的“精选读者”、我的“知音”,他们常常给我极大的写作动力和勇气。从性格上讲,我总是不愿过多谈论自己,遇事愿意为别人着想。一个男人过了50岁,老是我啊我啊的,是很让人讨厌的。事实上,认识一位诗人,读他的诗已足够了。说到名气、荣誉什么的,我认为是围绕一个人的种种假象的总合。
问:就您对文坛当下小说、诗歌等观察,什么样的小说、诗歌,是令人欣喜的,哪些则是较为平庸的?或者说,一个初写作者,最容易犯的写作毛病有哪些,特别明显的误区是什么?
答:因为工作原因,各种门类的作品都要读,老实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没有大问题,最让人犯愁的是小说,经常为找到一篇好小说煞费苦心,好多小说在我眼里连语言、结构等基本关都没有过。我是写诗的,作为主编,对小说语言自然多了些敏感和挑剔。当一本文学刊物把自己的门槛和品质抬高的时候,自然会看到更多的平庸之作。我喜欢质朴而有锐气的作品,希望青年写作者多一些实验和探索精神,持续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让我们看到他的朝气、潜力和可能性,这才是关键。初习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感伤主义、情感泛滥、形容词癖好等。我经常对年轻朋友讲,不要闷头写,要多读书,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参照系,这比闷头写作更重要。而且要多读死人的书、少读活人的书,因为死人的书是经过时间检阅和淘洗留下来的经典,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
问:当下,诗歌这种文体,在社会上处于回暖态势。您曾经说,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是尊重诗,差劲的小说家往往远离诗甚至低毁诗。您如何看待这种小说、诗歌等文体的差别?
答:我认为能真正代表一个时代文学原创力和最高水准的是长篇小说和诗。长篇小说有体积、有容量,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而在诗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时代最内在、最本真的声音。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是惊人的,1980年代每年大概八九百部,进人新世纪,每年已接近3000部,但几十年过后,我们能记住、得以留存下来的长篇有几部?布罗茨基说得好,“作为最高语言形式的诗歌,必然是我们人类学,其实是遗传学的目标”。我也相信,一个读诗的人比一个不读诗的人更难被打败。我认识好多小说家,他们的文学起步是诗,梦想做一个诗人,后来转向小说,这是一种个人选择,无可非议。一流小说家读诗、尊重诗,是因为他们深知小说同样是语言艺术,他们以诗的严苛来要求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小说家是十分了不起的。
问: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很多人都对新诗发展有自己的想法,您有怎样的思考?
答:尽管有人指责诗坛存在这样那样的“乱象”,尽管这是一个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期,尽管新诗的传播和影响还不能与唐诗宋词等古典名篇相提并论,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表面现象。新诗百年之际,已进人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优秀作品与优秀诗人的大量涌现,其内在活力呈喷涌勃发之势。时间会甄别杰出与平庸。
问:您拒绝“西部诗人”“西部诗歌”这种大概念,认为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生活在西部的诗人。做出这种判断,应该是出于您对诗的个体性的充分认识。您认为,用笼统的大概念去套一个一个人,有哪些坏处?
答:评论家为了谈论的方便,喜欢用大概念去套一個具体的作家、诗人,这样一来,这位作家、诗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简化了,他只能归类于“西部文学”“西部作家”了,仿佛已是中国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学、中国作家之外的另一种作家了。但是,在我老家浙江,我从来没听到存在“东部文学”“西部文学”的说法。用地域来划分文学,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不是评论家的偷懒行为,就是“西部作家”的自我矮化,有时我还怀疑是一种历史、现实和惯性造成的“文学阴谋”。试想一下“西部人民”这个概念,在沪沽湖打鱼的一位摩梭人和在新疆草原放羊的一位哈萨克人,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性、思维方式等,存在多大的差异啊。同在“西部作家”之列,每个人写作的志趣与追求大不相同,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超过东西部作家的区别。所以,当有人称我是“西部诗人”时,我会告诉他:我不是“西部诗人”,而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这种表述,丝毫不影响我对西部的热爱。
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踏上西去的旅途,聆听丝路的历史回响。对于这股浪潮,您有怎样的观察和观点,以及年轻人从历史地理中汲取更多营养,有怎样的建议。
答:“旅游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说得有意思。相对于“旅游”一词,我更喜欢“旅行”“远足”“漫游”“漂泊”等词汇。在当前的全民“旅游热”中,我们尤其要警惕那种对“远方”和“偏僻”的消费心理,那种居高临下的猎奇行为。消费主义已经把我们的旅游业毒害了。旅行需要平等与尊重,再偏远的地方、再偏远的人民,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唯一性。来的都是客,当你深知自己是一位过客时,就会学得谦卑与尊重。内地人去西部、去新疆、去西藏看看,可以领略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开阔自己的眼界,说不定还能认识到自己的“偏僻”。阅读是一种“室内旅行”,旅行则是一种“户外阅读”,天地人生都是一本大书。张杰,女,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80后,来自中原,求学华东。毕业奔赴巴蜀。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