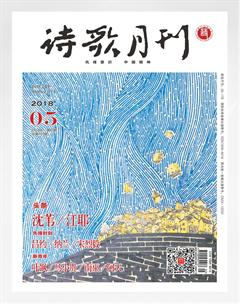诗,从来就不是远方(创作谈)
江耶
淮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一直都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内心里。淮河是我写作的母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淮河,写淮河的水,写淮河两岸的作物,写淮河上空的气候,写淮河下的煤矿,写淮河流域的风土人情,写淮河滋养草木的独特意味。
诗从来就不是远方,淮河对于我,是与生俱来的,与我的诗、我的所有文字异形同体。我相信一位大师说过的话,要刻画一个艺术形象,必须久久地凝望它。从记事开始,淮河的水就在我的眼前,有时是养育,有时是灾难。淮河,不仅仅是我睁开眼就能看到,支起耳朵就能听到;它还存在于我的生命里,对我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在起着决定作用。写淮河,不仅是我的选择,更是我的命运。诗意就是如此,在事物的深处,幽微地阐述着事物的本质,给人以痛,给人以美。淮河也是这样。
淮河对我的滋养源远流长。我的家乡在江淮分水岭的北边,雨水落下,就顺着地势向北汇集,不管多么盲目,最后它们都会抵达淮河。老家村子门前就有一条小河,长年不息地流淌着,有时缓缓的,仿佛河水已经静止;有时激流汹涌,仿佛要把一切都冲垮、带走。大多的时候,河水不慌不忙的,与农民走路的样子一致,在季节里有条不紊。没有谁太在意什么,农民们背着农谚,看着天气,算着农时,准确地播种、收割。多少年之后,我仍然能背诵那时的谚语,对什么节气播种、什么时候收割都清清楚楚的,仿佛某一株作物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这是写作之后的重要母题,我仿佛已深陷在农业生产中无法自拔。长时期以来,我一直自称为农民,哪怕天天待在灰暗的城市,在我的身体里,庄稼却始终争分夺秒地生长,并支撑着我面向阳光,不断地得到光、得到温暖。淮河的气息是我诗歌最初的养分,深厚地滋养着我不停的寫下去。
仿佛命中注定,从学校大门出来,竟然神奇地被分配到淮南煤矿上班,从此与淮河生息与共。很多年过去,我还时常能想起,第一次走上淮南这片土地,是在一场洪水退去之后。放眼看去,满眼都是淤泥浸淫的土地,黄色的泥浆铺天盖地的,是壮美,更是悲壮。偶有作物,也都是耷拉着脑袋,没有一点精神。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暗示,那时候我也不善于表达,只是心绪久久难以平静。但我没有在这种情绪中沉陷过久,很快地,我喜欢上了淮南这个地方,喜欢上了淮河岸边的一草一木。比如,二十四节气,我觉得每个节气都是诗情画意的,它们在天意授予之下,按部就班地呈现出秩序之美。“平原阔,一条地理分界线/在这里变得宽厚,平原上的男人/不是分,也不是界,不急不慢的日子里/吸纳了南方、北方的所有优点/他在心里界线分明,一亩三分地上/看云识天气,看天播种收割/他吃着淮河水,用着淮河水/也像淮河一样本分、朴素地守着/足以养家糊口的小小收成/流水一样,平凡而自足的时光/使这个中间地带,最像中国”(《他就是这条地理分界线》)。这里仿佛是世外桃源,人们热爱自然,也以自然的形式存在。他们不求名利,怡然自得,直接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首诗。
诗在我们内心,是我们自己。写诗也好,写散文、小说也好,我首先是要写淮河,从淮河汲取丰富营养。几十年来,生活在淮河流域,淮河的中间、中原、中庸的基因进人了我每一个细胞,它们是我的方式,形成了我温和的诗意。这里的民风、民谣、民歌都是诗,有花鼓灯、拉魂腔、大鼓书等,里面的句子大多是诗;很多农民的一句话往往也是诗。我们始终生活在诗意之中。什么是诗?我认为,诗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美好。人是从大自然中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人类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一株草,每一棵树,都有诗性的光芒。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一句诗,一首歌。每次回到家乡,每次在风景中观赏,那些不知名的花草,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虫子、飞鸟,它们不问前生、后世,自在地活着,俯首听命于眼前的一切。它们给了我启示,也给了我清澈的激情,我在细微的辨认中,得到了诗的途径,并且越来越走向深入。时间是无限的,地域是辽阔的,而人总是在局限之中。这是必然,在时间里面,也在空间之中,我们一直在路上。生命不止,生生不息,就得一直走下去。当诗歌来临,诗歌在安慰,我在记录,力求用自己的看见和感悟传达诗歌。这仍然是我们自身,我们自己在情境之中:“树叶完全凋落,麦子还没有伸出头来/田地里空空荡荡的/大地不再羞涩/开阔、苍凉、孤寂、无助/起起伏伏都呈现了出来/最隐秘的心思也完全敞开/仅仅十个月吧,时间就无情地/掏空了一切。那些旺盛的季节、稠密的果实/吸食了地里多少养分/天从来没有如此地靠近/一声鸟鸣,孤单地走得更远/地上的事物再一次坚定了信仰/用本来的姿态依偎着/大地,在这个时候/更像一个母亲”(《初冬的田野》)。这是典型的淮河边上的冬天,它的孤寂、苍凉、时空感,让我读到了诗的味道,诗的深意。
淮河不是表面,淮河同样在深入。淮南、淮北是中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下井采煤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淮河两岸长大的农民或者“矿二代”,他们身上有淮河的秉性。二十一世纪初,我由煤矿的机关调到井下岗位,一个专门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设施的单位。到了井下之后,突然从以前的忙碌中抽身出来,走在黑洞洞的巷道里,看看左右都是上亿年的岩层和煤,想象着那些漫长的时间,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种空洞之中,我感到茫然而惶恐。更多的独自行走中,看到小跑着走路的矿工,看到他们满脸乌黑、偶尔露出洁白牙齿的单一形象,令我的思绪万千。诗句随时而来,我在下井时用的安全记录卡片上记下一句两句,我在值班床头上贴画中写上突然想起来的词语,茫茫无际的空洞就这样生出了无限可能。诗来得突然而简单。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好,每天都能写出一点什么。在地下一千米深处,我深入思考后得出,诗根本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它的每个词、每一句、每个意象,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它们与我息息相关,朝夕相伴。
淮河也比任何地方更适合成为一个诗人的家乡。“烟波江上使人愁”,诗歌带领着我,在混沌的境界中,强调自我,再迷失自我,发起一个一个的追问。在某个深夜,我在淮河北边的一座煤矿井下,在一个狭窄、局促的巷道里。这个巷道在两条更大的巷道之间。两条大的巷道,一条是矿井的进风系统,新鲜的风流,从中央广场的井口下来,一路流动到这里,还带着地面的气息,冰冷、干燥,丝丝腥味;另一条是矿井的回风系统,新鲜的风流经过了正在采掘的地方,带上那里的东西,岩石的硬,煤粉的油腻,大地深处的火热。两股气流之间有巨大的压差,它们相互吸引,更相互冲突,被两道将近半尺厚的木门阻挡着,仍然在用力冲撞,形成了强大的声响。彼时的我却仍然觉得此时此刻有着无比的安静。我停下脚步,我蹲下来,慢慢地坐在了钢轨上,金属的凉迅速地袭击了我。
走千走万,走不过淮河两岸。我的诗只能在淮河上漂流,在淮河水中浸润。淮河的两边埋藏了大量的煤炭,而煤炭来源于亿万年的树木。可以想象,淮河一带,原本就是树木葱郁,童话一般的世界。我想象,我深入,我发现,我吟唱,“一千米/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仍然十分浅薄/对于生活在大地表层的人/深入到地下一千米/已经是无比的深奥/煤矿里的这些人/打了井,打通了巷道/揭开岩石,直到煤层/把煤一点一点地掏出来/让它们走到地面,阳光地里/多么深刻的事件啊/深陷时间的迷局瞬间通畅/我们听到了远古时代的呼吸,以及/压抑在深处的声音”(《深刻》)。大河在我的头顶流淌,我感受到,诗就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诗就是我们的内心,再远的路只在我们内心行进;诗和路途,就是我们自己。
2018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