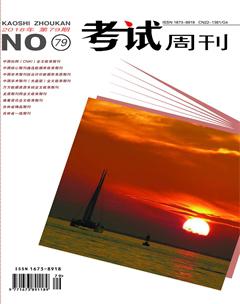古代册封体制下的儒家礼乐思想研究
摘 要:古代东亚格局当中,中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进的科学技术、繁盛的文化交流,使得东亚各国纷纷向中国学习,并在此期间形成了长达千年的册封体制,在这种伴随着朝贡行为的册封体制下的儒家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相继传播开来。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乐对当时各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辐射作用,直至今日,在东亚国家的学术界仍影响深远。
关键词:儒家礼乐思想;册封体制;仁和理念;文化交流
一、 文化互通的土壤——古代“册封”体制
古代东亚世界格局中,东亚诸国向中国朝贡,以各种形式与中国相联结,逐步形成所谓的“册封体制”。公元3世纪,魏王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其中的“册封”一词,足以显示出当时中国在东亚的重要地位。册封,即交换国书,天子赐予国王金印玉玺,同时伴随着“朝贡”行为,即两国间赠送和回赠礼物的一种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有人可能看到“册封”,就会认为中国自诩为大国,周边国家都是小国的具有等级尊卑的观念,其实不然。缘何东亚数个国家,唯有中国能够册封他国,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中国,指的是占据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政权,统治这个政权的民族不仅仅有汉族,还有其他各少数民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天子之国,但是最终国家都走向了衰亡。这里提到的天子之国,也必须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大陆政权才有权力册封他国,而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此外,册封体制,是为东亚各国所公认的,只有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从中汲取要素,才能发展本民族文化,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而只有囊括在册封体制内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明,东亚才会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册封朝贡体制,能够在多重方式上巩固文明圈的同质性。
中国人亦称华夏人,华夏民族从古至今都包含着一种文化观念,即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在《孟子·滕文公上》当中便能体现这种论断:“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听说中原有改变蛮夷的,未曾听过蛮夷改变中原的。孟子的这一论断恰恰也证明了其真理性的一面,辽金元等各少数民族都曾试图在中原建立自己的文化,取而代之中原文化,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民族几近灭亡。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经久不衰,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是否强大。中国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完善,推陈出新,如果说中国丝毫没有借鉴别国文化,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即便是儒家思想,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杂糅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千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古代的中国则以册封国姿态与周边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更能看出以儒学为主要价值观长期在东亚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了东亚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二、 儒家礼乐思想的解读
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区别之一,它具有等级性,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点。其等级性贯穿于礼乐规范之中,礼器则象征着权势和地位,而所有与礼乐相关的思想形态则被历代君主运用到治国理政当中。周朝建立宗法等级制度,目的在于通过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都结合在一起的血缘网络之中,上一等级和下一等级之间以血缘关系和道德来加以强化,以此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制定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王位世袭制下的封建王朝,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不同,且不提各诸侯争夺王位之事,随着历史发展,每更新换代,其血缘关系必定会淡薄一层,上下等级之间终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单单依靠血缘关系来维持政治,是苍白无力的,只会使诸侯对王室的离心力愈加强烈,最终导致宗法等级制崩溃,随之礼崩乐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朝的礼乐文化就是一种失败的制度,相反,礼乐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更广泛的推崇,可以说孔孟荀子三大家皆反思并继承了周礼,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删,孔子的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人”形成了以“仁”“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为政以德”,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倡民为国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进步的一种政治观念,大大深化了孔子的“修己”“安人”学说。此外,孟子注重德行的培养,主张统治者应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即“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世人多晓孔孟二圣为儒学先师,其实,先秦时期还有一位对儒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他就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强调礼乐思想在政治王道当中的合理运用。他主张统治者要实行“王道”,对内要“平政爱民”,对外要“以德兼人”(《荀子·议兵》),但是他的道德规范与孟子不同,他主张以礼约束人的行为,且夹杂着法的成分,故他常常礼法连用,或是礼法不分,根据罪行的轻重來判断刑罚。“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荀子的礼法结合治国观念,究其原因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必须适当地使用刑罚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孔,孟,荀子三人的思想特征来看,恰恰印证了儒家“和而不同”的特殊理念。
儒家思想充满了现实的、政治的、伦理的色彩,这已是学界通识。并且,“乐与政通”是儒家音乐思想的绝对律令,但是声音之道为何却与政治相干?“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音乐在于和同,礼仪在于区别,因为和同,故能使人亲近,因为别异,故能使人互相尊敬。然而过分强调“乐”,则易使人流湎其中,过度强调“礼”,则易使人产生隔阂而疏远彼此。所以儒家的“乐”思想与“礼”思想一脉相承,不可分离。西汉董仲舒将儒学提升到了统治者的层面,以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由此可见儒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罗艺峰认为:古代社会建元定朔,敬授民时的天文是政治,与此有关的音律法度与天文历法发生了数算上的深度关系,因而音乐与政治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伦理观念的传统是政治,与此有关的音乐制度文化、音乐行为文化与这个传统有牵涉,因而与政治有必然联系。由此得知,音乐不可简单理解为礼乐思想当中的等级观念以及维护封建统治,反而其中体现的“理性”特质,成为其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观念。所谓理性,总是与尺度、比例、原则、规律、关系等有关,这是中外皆然的思想事实。基于这种理性,儒家通过教育行为传播音乐,譬如元代余载的《韶舞九成乐补》,明代朱载堉的《灵星小舞谱》,其功能和目的,无非是通过教育过程,把历史和神话内化成儒家的文化精神,甚至内化为儒教中国的心灵世界。如此具备人文主义的儒家文明,那么礼乐合同,共治天下的统治方式自然成为中国古代历代君王所推崇的一种治政原则了。
三、 结语
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前两代礼乐加以损益,孔孟荀三大家的儒家思想对其文进行一种系统地总结。由于周朝奉行宗法封建等级制度,此制度是一种既能“分”又能“群”的制度,而制礼作乐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巩固社会秩序,加强统治者对国家机构的管理能力,更是提升国民综合素质的一种柔软方式。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只有“礼”或只有“乐”,过度的礼仪会拉大人们之间的距离,彼此间容易生分,但过度的乐则又会导致国家沉浸堕落,不思进取,上下异心。历代君主通过儒家礼乐结合的思想,治国理政,达到治理国家和修身安民的政治目的。因此,只有通过礼乐中和,才会使人们“分”而不离心离德,“群”而不流于尊卑不分,从而达到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的政治目标。即便在汉唐以至于明清时期,儒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以仁和礼乐为主流的观念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道德规范方面发挥着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1]周东平.律令格式与律令制度、律令国家——十世纪中日学者唐代法制史总体研究一瞥[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2]马振铎等.儒家文明[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3]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0年.
[4]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M].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
[5]赵东一著,李丽秋译.东亚文明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6]罗艺峰.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
[7]杨华.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N].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姚惠鑫,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神木大剧院